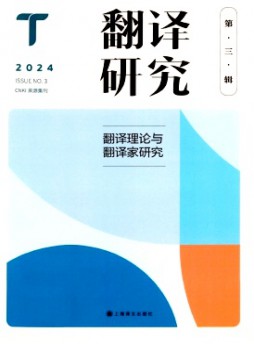翻譯題材選擇分歧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翻譯題材選擇分歧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922年,創(chuàng)造社與文學(xué)研究會(huì)就如何翻譯介紹外國文學(xué)問題,引起了一場(chǎng)爭論。以茅盾為首的文學(xué)研究會(huì)認(rèn)為,文學(xué)翻譯的目的是為了針砭時(shí)弊、拯救靈魂,所以應(yīng)該審度事勢(shì),要有輕重和先后之分。而以郭沫若為首的創(chuàng)造社則認(rèn)為,文學(xué)研究或文學(xué)翻譯都屬于研究者或翻譯者的個(gè)人自由,文學(xué)介紹者對(duì)文學(xué)作品有選擇的權(quán)力,只要被譯的文學(xué)作品能涌起創(chuàng)作的精神,能使讀者有所觀感,這樣的介紹就有必要。這次論戰(zhàn),表面上看來是一次簡單的文學(xué)翻譯討論,其實(shí)爭論的背后隱含著的是文學(xué)翻譯文本如何選擇的問題。
一、重政治功能與重藝術(shù)功能的爭論
德國功能翻譯理論認(rèn)為,“任何行為都有一定的目的行動(dòng)者參照實(shí)際環(huán)境選擇一種他認(rèn)為最適合的方式以求達(dá)到預(yù)期目標(biāo)”[1]。譯者就是在翻譯目的的指引下,選擇最適合的行動(dòng)方式,以達(dá)到預(yù)期目標(biāo)。“翻譯的過程就是一個(gè)選擇的過程,可以這樣說,從材料的選取到詞匯的運(yùn)用,翻譯行為的每一個(gè)階段無不涉及對(duì)多種選擇的確定”[2]。首先譯者在獲取源語材料時(shí)不是盲目的,他要考慮選自的國別、原作者等,這個(gè)選擇是由翻譯行為的發(fā)起者按照既定的目的和預(yù)期的目標(biāo)有計(jì)劃地進(jìn)行的。完成了翻譯過程中選材這個(gè)首要環(huán)節(jié)后,譯者才可以對(duì)翻譯實(shí)踐環(huán)節(jié)的其它方面做出抉擇,比如翻譯策略、體制和翻譯方法等的選擇。
梁啟超在《變法通義》中談到翻譯時(shí)曾明確指出:“故今日而言譯書,當(dāng)首立三義:一曰,擇當(dāng)譯之本;二曰,定共譯之例;三曰,善能譯之才。”[3]梁啟超所談?wù)摰牡谝稽c(diǎn)“擇當(dāng)譯之本”,說的就是譯者的選材問題。選擇什么樣的作品加以介紹和翻譯是翻譯過程中首要的問題。在歷史大變革時(shí)期,較之“怎么譯”,“譯什么”更成為譯事的頭等要義。如何“擇當(dāng)譯這本”,取決于翻譯的目的和動(dòng)機(jī)。著名的翻譯家嚴(yán)復(fù)選擇翻譯了英國亞當(dāng)·斯密的《原富》、赫胥黎《天演論》等社會(huì)學(xué)名著,以達(dá)到革新國人思想、建立新體制、富國強(qiáng)兵的目的。魯迅在談到翻譯俄國作家愛羅先珂和日本作家江口渙的作品時(shí)說:“其實(shí),我當(dāng)時(shí)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fā)國人對(duì)于強(qiáng)權(quán)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并不是從什么‘藝術(shù)之宮’里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5]
茅盾認(rèn)為文學(xué)作品除了能給人愉悅外,至少還須含有永久的人性和對(duì)于理想世界的憧憬。由此而知,文學(xué)研究會(huì)成員選擇翻譯材料時(shí),他們的目的和動(dòng)機(jī)是用翻譯文學(xué)去糾正時(shí)代的缺陷,拯救墮落的人性。[6]
而以郭沫若為首的創(chuàng)造社則認(rèn)為,文學(xué)的好壞,不能說它古不古,只能說它醇不醇,只能說它真不真,不能說19世紀(jì)以后的文學(xué)全是好文學(xué),都有介紹的價(jià)值。[6]
很明顯,創(chuàng)造社從對(duì)文學(xué)材料的愛好出發(fā),選擇能夠真正打動(dòng)和陶冶譯者和讀者的文學(xué)杰作來翻譯。創(chuàng)造社成員比較關(guān)心文學(xué)的藝術(shù)價(jià)值,而文學(xué)研究會(huì)則更多地關(guān)注文學(xué)的社會(huì)價(jià)值。
二、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與個(gè)人意識(shí)形態(tài)的分歧
翻譯不僅僅是符號(hào)之間的轉(zhuǎn)換,它承擔(dān)著一種重要的社會(huì)功能,翻譯的主體不是獨(dú)立于社會(huì)之外的存在。AndreLefevere認(rèn)為,包括翻譯在內(nèi)的一切改寫都受到意識(shí)形態(tài)的操縱,其中影響翻譯活動(dòng)的主要有三個(gè)因素:贊助人、意識(shí)形態(tài)和詩學(xué)。[7]
20年代創(chuàng)造社和文學(xué)研究會(huì)面臨的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概括為:一是以文學(xué)作為反帝反封建工具,二是通過文學(xué)宣揚(yáng)民主科學(xué)的思想。在這種背景下,兩大主要文學(xué)組織創(chuàng)造社和文學(xué)研究會(huì)大量譯介了為無產(chǎn)階級(jí)文藝革命運(yùn)動(dòng)和反帝反封建服務(wù)的文藝?yán)碚摵臀膶W(xué),為中國革命斗爭和人性解放做出了重大貢獻(xiàn)。
意識(shí)形態(tài)涉及的范圍很廣,它可以大到代表某一特定的重要社會(huì)團(tuán)體的觀念和信仰,也可以小到某個(gè)個(gè)人的思想意識(shí)。“不同的譯者由于個(gè)人閱歷、學(xué)歷、修養(yǎng)等方面的不同,會(huì)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識(shí)形態(tài),人的意識(shí)形態(tài)使其成為主體的同時(shí)形成了自己的區(qū)別于社會(huì)上其他人的意識(shí)形態(tài)”。[8]
這里的各自不同的意識(shí)形態(tài)就是個(gè)人意識(shí)形態(tài)。按照這樣的推理,就可以理解創(chuàng)造社和文學(xué)研究會(huì)之間的論爭了,論爭起因于個(gè)人意識(shí)形態(tài)與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偏差,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設(shè)法干擾,而個(gè)人意識(shí)形態(tài)卻堅(jiān)持不放棄,爭議因此產(chǎn)生。
我們可以從文學(xué)翻譯實(shí)踐窺見一斑,很多翻譯家在適應(yīng)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前提下,堅(jiān)守個(gè)人意識(shí)形態(tài)的陣地,比如,翻譯家穆旦在上世紀(jì)50年代到60年代在翻譯中有意識(shí)地堅(jiān)持個(gè)體的意識(shí)形態(tài)和詩學(xué)觀,他頑強(qiáng)地按照個(gè)體的意識(shí)形態(tài)和詩學(xué)觀來進(jìn)行翻譯。穆旦“沒有選擇更加符合政治氛圍的拜倫的《該隱》,而是選擇他的抒情詩《唐磺》,沒有選擇雪萊的政治抒情詩《伊斯蘭的起義》、《解放的普羅密修斯》,而是選擇了《云雀》等抒情詩”。[9]
創(chuàng)造社受到當(dāng)時(shí)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支配,但它們并非被動(dòng)地成為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操控對(duì)象,它們?cè)诓粩嗟囟窢幰员磉_(dá)自己的話語。郭沫若選擇翻譯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和席勒的《華倫斯坦》等,更多地吻合他自己內(nèi)心世界的一種不平衡,不滿足。他說:“特別是那一部開首浮士德咒罵學(xué)問的那一段獨(dú)白,就好像自己的心境。”[10]
三、邊緣與中心的斗爭
法國后結(jié)構(gòu)主義哲學(xué)家米歇爾·福柯認(rèn)為,整個(gè)社會(huì)就是一個(gè)權(quán)力機(jī)構(gòu),眾多的人文學(xué)科從根本上就有一種對(duì)“權(quán)力的屈服”。[11]
其實(shí)從歷史每一階段翻譯文本的選擇,都可以看出權(quán)力話語的競(jìng)爭和斗爭行為。20世紀(jì)初,文學(xué)研究會(huì)的作家在翻譯選材方面就大力提倡譯介現(xiàn)實(shí)主義尤其是俄羅斯文學(xué)以及被壓迫民族文學(xué),他們代表的是主流思潮,主流的詩學(xué),一開始,就處于中心位置,牢固掌握話語權(quán)力。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描述說,“創(chuàng)造社是貴天才的,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與同時(shí)上海的文學(xué)研究會(huì)相對(duì)立。那出馬的第一個(gè)廣告上,說有人‘壟斷’著文壇,就是指著文學(xué)研究會(huì)”。[12]
盡管“壟斷文壇”(郁達(dá)夫言)聽起來有點(diǎn)過激,但也充分說明了文學(xué)研究會(huì)處于絕對(duì)的中心地位。創(chuàng)造社成員被排除在主流之外,他們?yōu)榱藸幦≡捳Z權(quán)力,從邊緣走向中心,而開始與文學(xué)研究會(huì)就翻譯選材問題進(jìn)行辯論。
翻譯外國文學(xué)要講究經(jīng)濟(jì)意識(shí),要有系統(tǒng)性,這構(gòu)成文學(xué)研究會(huì)成員的共識(shí)。他們?cè)谝?guī)定當(dāng)時(shí)的文學(xué)應(yīng)該是什么樣,文學(xué)人應(yīng)該怎么去做,漸漸地“建構(gòu)起來的新文學(xué)話語,對(duì)新文學(xué)陣營內(nèi)部其他不同的聲音構(gòu)成了壓抑或遮蔽”。[13]
文學(xué)研究會(huì)的話語權(quán)力的后盾實(shí)際上是與商務(wù)印書館的結(jié)合,這樣一來他們的贊助人就是他們自己,他們從不擔(dān)心翻譯書籍的出版問題,可以規(guī)定各種標(biāo)準(zhǔn)供文壇作家執(zhí)行,在文壇上惟我是從,就我獨(dú)尊,所以處于話語霸權(quán)地位。與茅盾、鄭振鐸等文學(xué)研究會(huì)成員隨己所愿的選擇相比,創(chuàng)造社成員如果想另辟蹊徑,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權(quán)力的壓抑,為壓抑和爭奪話語權(quán)的反操控行為勢(shì)必就產(chǎn)生這場(chǎng)文壇激烈的論爭。
四、個(gè)體風(fēng)格的差異
翻譯文本的選擇除了受到翻譯主體的動(dòng)機(jī)和個(gè)人意識(shí)形態(tài)等影響外,還受到譯者的寫作風(fēng)格或文筆的影響,不同翻譯家有不同的個(gè)體化傾向,他們選擇與自己寫作風(fēng)格或者文筆相近的作家的作品來翻譯。
風(fēng)格是某位作家作品中重復(fù)出現(xiàn)的個(gè)性與創(chuàng)作技巧的總和,是作品主觀思想和他生活時(shí)代的產(chǎn)物。選擇文本從某種角度看就是挑選性情相同的作家,風(fēng)格一致的作品。傅雷關(guān)于選擇翻譯文本的比喻恰如其分,他說:“選擇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終與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強(qiáng);有的人與我一見如故,甚至相見恨晚。”[14]626
再比如,郭沫若翻譯了眾多德國文學(xué)作品,但最受自我和他人推崇的譯作卻是他翻譯的英國詩人雪萊的《雪萊詩選》。主要是因?yàn)楣舻墓P法浪漫奔放、自然飄逸,在很多方面與雪萊的文筆相似。郭沫若曾這樣描述他的翻譯體會(huì),“我愛雪萊,我能感聽到他的心聲,我能和他共鳴他的詩便如像自己的詩。我譯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在創(chuàng)作一樣”[15]。傅雷認(rèn)為:“從文學(xué)類別來說,譯書要認(rèn)清自己的所短所長,不善于說理的人不必勉強(qiáng)譯理論書,不會(huì)做詩的人千萬不要譯。”[14]80創(chuàng)造社成員本身都是“為藝術(shù)”而創(chuàng)作的浪漫主義作家,不難理解他們力求介紹西方浪漫主義文學(xué)以及西方象征派、未來派、表現(xiàn)主義等作家的作品。蕭乾說得好,“縱使狄更斯的作品那么缺乏譯本,一個(gè)不能掌握他那種悱惻和幽默文筆的人也是翻譯不好的”[16]。他選擇翻譯了諷刺幽默作品《好兵帥克》、《里柯克幽默小品選》、《培爾·金特》等,那是因?yàn)樗救司褪侵S刺幽默文學(xué)寫作的高手。
20年代創(chuàng)造社與文學(xué)研究會(huì)之間發(fā)起的那場(chǎng)論爭,就是翻譯的選材是否以經(jīng)濟(jì)性和系統(tǒng)性為主,還是以藝術(shù)性和審美觀為主,孰對(duì)孰錯(cuò),很難決斷,本文并非要給出爭論的是與非,只是想通過爭論來分析其隱含的原因,意在得出對(duì)翻譯理論研究有參考價(jià)值的論題。必須承認(rèn)譯者對(duì)翻譯文本的選擇有其客觀性和主觀性,譯者所處的時(shí)代背景、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環(huán)境、翻譯動(dòng)機(jī)和目的、個(gè)人的道德觀、文學(xué)觀、翻譯觀等諸多客觀和主觀等因素對(duì)文本選擇都產(chǎn)生影響。當(dāng)我們強(qiáng)調(diào)其客觀性時(shí),不要忘記譯者的主體性;反之,談?wù)撟g者的主觀能動(dòng)性時(shí),也不能忽略文本選擇受客觀因素的制約。有時(shí)外部的意識(shí)形態(tài)或話語權(quán)力占主導(dǎo)地位,有時(shí)內(nèi)部的文學(xué)觀、價(jià)值觀和審美意識(shí)成為決定性因素,矛盾和斗爭是難免的。然而,不管是互動(dòng)的還是斗爭的關(guān)系,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jìn)了文學(xué)翻譯事業(yè)的發(fā)展和繁榮,20年代的這場(chǎng)論爭就大大地開拓了人們的視野,提高了人們思考翻譯問題的層次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