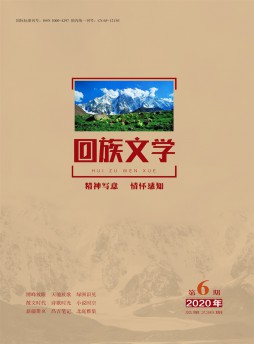文學翻譯文化不同處理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翻譯文化不同處理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文化研究是當前學術界的一大特點。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對文化的共同定義是:“文化是人類群體或社會所共有的產品,包括價值觀、語言、知識和物質對象等。文化中無形的這一部分-信仰系統、互動模式、政治程序等-構成了非物質文化。文化中的物質部分-機器、工具、書籍及其他-構成了物質文化。”(戴維•波普諾:89)可見,文化包含的范圍非常廣。東西方不同的歷史、地理和生存模式等,造就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又造成了人們語言、知識、信仰、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的不同,也造成了對相同事物或概念的不同理解。翻譯是運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思想內容準確而完整地表達出來的語言活動,是跨文化交際的重要手段。翻譯的目的在于促進不同文化間人民的溝通與交流。由于文學樣式的多樣性,文學翻譯中存在的文化差異也更為多樣和復雜。而如何處理和解決這些文化差異便成了文學翻譯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本文意在通過分析和對比《老殘游記》第二回《明湖居聽書》的兩個英譯本-分別由HaroldShadick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翻譯(以下簡稱Harold譯和楊譯)-來討論文學翻譯中文化差異的處理。
1數字的處理
就中西方數字而言,英語中的數字往往是實數,這與他們邏輯分析型的思維模式有關,而漢語中數字的虛實則要根據上下文來判斷。這跟漢英語的構成方式有關。“西方語言是形合的語言,而漢語是意合的語言。”(徐行言:158)而且,從語法上講,英語的詞語有人稱、數、格、時態的區別和變化,而漢語則很少。比如“我”,漢語就說“我”,而英語相應的則有I,me,myself。因此也就造就了漢語的模糊性,相比之下,英語的精準度要高一些。漢語的數字往往虛實兩用,因此具有比較英語多的修辭和文化含義。在翻譯的過程中,尤其是文學翻譯的過程中,對數字的處理一定要根據不同的語境和意義,采取不同的解決方法。《明湖居聽書》中采用了大量的數詞,Harold和楊做了不同的翻譯。原文第二段在談到觀眾對王小玉唱曲的反應中有這么一句話:“五臟六腑里,象熨斗熨過,無一處不服帖;三萬六千個毛孔,象吃了人參果,無一個毛孔不暢快。”這句話是運用通感的修辭手法,把本來訴諸于聽覺的王小玉的唱曲聲用膚覺、味覺、意覺等貫穿起來,來表現王小玉曲聲的優美。這里的五,六和三萬六千都不是實數,而是指全身上下的每一個部分,每一個器官。Harold將其分別譯為“thestomachandbowels”和“thethirty-sixthousandporesoftheskin”,而楊則將其譯為“alltheorgansofthebody”和“thewholebody”。可見,楊是在理解了意思以后進行的意譯,而Harold則是直譯。類似的例子在文章中出現的還有很多。例如:三四疊,Harold譯為“threeorfourhighestflourishes”,楊譯為“thehighestpitch”;千回百折,Harold譯為“withathou-sandtwistsandturns”,楊譯為“windingskillfullywithallitsart”;削壁千仞的“千仞”,Harold譯為“thethousand-fathomcleftwall”,楊譯為“theprecipice”;三十六峰,Harold譯為“thirty-sixpeaks”,而楊沒有譯。由此可見,在翻譯的時候,Harold往往將其直譯,而楊時在理解源語意思后進行的意譯。這也反映了中西方思維模式的不同,即:西方注重邏輯分析,而中國講究整體意義。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中西方學者在翻譯上的差別恰恰體現了他們在文化上的差異。正如上個世紀前半期,美國著名語言學家,人類學家薩丕爾•沃爾夫師徒共創了“薩丕爾-沃爾夫假說”,他們認為:“語言不同的人們應該具有相應的不同的思維模式,語言決定了人們的思維,思維不能脫離語言而存在。”(徐行言:147)可見中西方不同的思維模式是與各自的語言分不開的。由于數字廣泛地應用于成語、俗語、諺語和文學作品中,作為夸張或者比喻的修辭手段,所以在文學翻譯中經常出現。李白的《望廬山瀑布》在中國是一首幾乎家喻戶曉的詩: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之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這里的“三千”不是個實數,而是描寫瀑布奔流而下的壯觀。“九天”也不等于英語的ninedays,而是一個富含中國文化內涵的詞。古代傳說天有九重,九重天為最高一層。(顧正陽:165)對于“九天”,許淵沖的譯法是“azuresky”,王守仁和美國詩人約翰•諾弗爾將其譯為“theheavens”,而文殊的譯法則是“theninthheightofHeaven”。(顧正陽:165)筆者認為這里文殊的譯法比較好,因為他在翻譯的過程中保留了“九天”一詞的中國文化內涵。在中國經典小說《紅樓夢》中有很多后來廣為流傳的俗語,例如:古話說的好:“一龍生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是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其相對應的譯文是Asproverbsoaptlysays,“Adragonbegetsnineoffspring,eachonedifferent.”Andin-evitablyamongsomanyboystherewerelowtypestoo,snakesmixedupwithdrag-ons.(包惠南:199)這里的九當然也不是實數,而是形容賈府的人多。但在翻譯的時候,采取這種直譯的方法,中外讀者都能理解,同時也能了解中國的俗語和傳統中國文化。還有一句“女大十八變”,譯文是“Agirlchangeseighteentimesbeforereachingwomanhood.”(金惠康:95)他采用的是以源語文化為認同的直譯,較好的保持了源語的特色,但筆者認為這容易讓西方讀者產生困惑或者錯誤的理解,因為他們往往把漢語中的虛數等同于英語中的實數。那么,原本的十八變就成變了十八次,意義完全不同了。在我們耳熟能詳的成語、諺語、歇后語里,也經常包含著數字,而這時候對數字的翻譯就應該做到通俗易懂,不見得要與本來的數字對等。如“接二連三”,中西方都能認可和接受的譯法是oneafteranother;亂七八糟:atsixesandsevens;九死一生:anarrowescapefromdeath;五光十色:multi-colored;顛三倒四:incoherent;萬無一失:noriskatall;三思而后行:Lookbeforeyouleap;吃一塹長一智:Afallintothepit,againinyourwit;七上八下:inaturmoil;不管三七二十一:regardlessoftheconse-quences;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Twoheadsarebetterthanone;人無百日好,花無百日紅:Mancannotbealwaysfortunatejustasflowersdonotlastforever;此地無銀三百兩:Aguiltypersongiveshimselfawaybyconspicuouslyprotestinghisinno-cence;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Oncebit-ten,twiceshy;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Thegiftitselfmaybeaslightasafea-ture,butsentfromafar,itconveysdeepfeelings;半斤八兩:sixofoneandhalfadozenoftheother,等等。可見,在包含數字的習語、成語、短語等的翻譯中,并不是一是一,二是二,而是以習慣為準則,將他們譯成了中西方讀者都可以接受的形式,這其中對數字式有取有舍的。
2中國文化特有事物的翻譯
《明湖居聽書》第一段在王小玉出場時,提到她“把梨花筒丁當了幾聲”。這里的梨花筒在英語中沒有對等的詞,所以只能根據意義來翻譯,因為它是中國特有的事物。根據中國曙光教育網的介紹,“梨花大鼓起源于山東農村,也稱山東大鼓,因其早期用梨鏵片為伴奏樂器,又有梨鏵大鼓之名。梨花大鼓最早在農村流行,清劉鶚《老殘游記》里說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筒,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些前人故事。”可見這里的梨花筒類似于唱板,所以Harold和楊都將其譯為castanets。五臟六腑也是中國特有的成語。Harold將其譯為thestomachandbowels,很顯然他的翻譯是異化過度,因為這里的肝和腑是代指全身,而不是他理解的肝和腑。這里楊譯的比較好,他將其譯為alltheorgansofthebody。人參果,Harold將其譯為ambrosia,這個譯法西方讀者比較容易接受,因為ambrosia的意思就是仙果,神的食物,但因為它出自希臘語,所以容易讓西方讀者產生誤解,認為西方文化涵蓋了中國文化。楊將其譯為nectar,是根據意思進行的意譯,因為nectar來源于希臘神話,意思是眾神飲得酒。可見,在沒有對等詞的情況下,應該根據意義再結合源語的民族特色和語言風格進行翻譯。而人參,作為中國特有的事物,應該音譯為Ginseng。在中西方文化中,有些動物代表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翻譯的時候要特別注意。比如“龍”,我們中國人經常說自己是“龍的傳人”,父母都“望子成龍”,可見在中國文化里弄是威嚴榮耀的象征。但在西方文化里,弄卻是一頭怪獸,而且中西方文化中龍的形象也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里對應中國的“龍”的是“虎”。以前我們說的“亞洲四小龍”,翻譯成英文就是fourAsiantigers,而不是fourAsiandragons。狗仔西方國家是人們的朋友,是忠實的象征,因為關于狗的一般都是褒義,比如Youarealuckydog(.你真是個幸運兒)Everydoghasitsday.(人人皆有得意日)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于狗,往往取其兇狠殘暴的一面,和狗有關的詞語一般都是貶義,比如“狗仗人勢”,“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血噴頭”等等。現在,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一些中國特有的事物越來越多的被世界各地的人們了解和接受,而這些詞也就被直接音譯。比如“饅頭”,以前被譯為steamedbread。其實這個譯法倒是容易讓西方讀者產生誤解:烤好的面包為什么還要蒸呢?現在將其直接音譯為mantou。還有豆腐,以前譯為beancurd,現在譯為tofu;餃子,以前譯為dumplings,現在譯為jiaozi;旗袍,以前譯為mandaringown或者cheongsam,現在譯為qipao。近年來,隨著中國影視作品在國際上影響力的增強,中國功夫也被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所接受和喜歡,而功夫也就被音譯為kungfu,但為了便于外國人理解,需要加上注釋,“aChinesemartialartbasedontheuseoffluidmovementsofthearmsandlegs”。(馮慶華:423)這樣既保持了功夫的中國特色,又讓外國讀者有了明確的了解。還有象“氣功”,qigong,asystemofdeepbreathingexercises;磕頭,kowtow,totouchtheforeheadtothegroundwhilekneeling,asactofworship,respect,etc.esp.informerChinesecustom等等。這些詞在西方文化中都不能找到對等詞,但因為是中國文化特有的,所以在翻譯的時候就采用了音譯加注的方式。
可見,由于翻譯是跨文化交際的橋梁和紐帶,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語言表達習慣,因此我們在具體的翻譯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源語和目標與的文化差異,盡可能地道忠實的反應源語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內涵,同時也要注意考慮目標語國家讀者的文化背景。正如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奈達提出的讓西方翻譯界奉為現代翻譯理論代表的“動態對等”即“功能對等”理論:“接受者和譯本信息之間的關系,應該與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間的關系基本上相同。”(馮慶華:422)文學包括各式各樣的題材,因此文學翻譯中存在的文化差異更是復雜。所以,在處理文學翻譯的過程中,譯者應該在理解源語意義的基礎上進行準確地道的翻譯,保持源語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內涵,同時也要深入了解目標語及其文化,只有這樣才能將文化信息準確的傳遞過去,從而讓兩種語言的文化交流順利的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