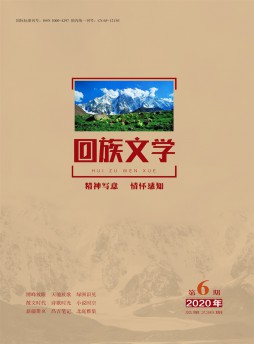周政保文學(xué)現(xiàn)實主義評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周政保文學(xué)現(xiàn)實主義評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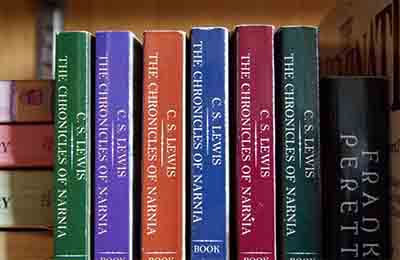
周政保大致成名于中國當(dāng)代第四代評論家與第五代評論家交接之時。如果說第四代評論家在新時期初激濁揚清,破舊立新,重塑和找回失落已久的現(xiàn)實精神,為新時期作家作品及思潮發(fā)風(fēng)氣之先,行鼓吁之力;第五代批評家大多以懷疑和否定為性格,以探索和追問為方向,以多元和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基石,以自由和自主的批評個性為信條,那么,周政保身上無疑兼具這雙重優(yōu)勢。這也成就了他一步步扎實地挺進(jìn)中國一流文學(xué)評論刊物,成為新疆新時期至今唯一一位獲得全國聲譽和廣泛推崇的批評家。周政保雖有過人的才情和驚人的韌性,但成就其成功的首先是他“是一個善于安排自己人生道路的人。”[1]。1965年17歲的周政保從家鄉(xiāng)常熟支邊到偏遠(yuǎn)的新疆和田,經(jīng)歷過長期底層生活的礪煉和考驗,從農(nóng)工到記者、編輯、機關(guān)干部、軍人一級一級的奮斗和起起落落的曲折———1975年周政保從新疆大學(xué)中文系畢業(yè)后又回到和田,直到1979年考入新疆大學(xué)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方向攻讀碩士,畢業(yè)后進(jìn)入部隊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現(xiàn)為八一電影制片廠副師級研究員。
一、以生活經(jīng)驗為批評基石
在批評個性的諸種構(gòu)成因素(如觀念個性、方法個性、思維個性、美感個性和文體個性等)中,占主導(dǎo)地位的是批評家所獨見的文學(xué)批評觀(即觀念個性)。周政保不僅將文學(xué)評論作為生存手段更是作為存在方式,他借文學(xué)之力把握生活思考社會,又以對社會人生的洞悉與理解更近地體察文學(xué)。因為,“我的小說評論也是一種‘自我表現(xiàn)’。這就是我的理論批評的伎倆”。[2](p287)周政保文學(xué)批評的基點始終是立足于民族———人民,因為“懂得了生活,懂得了命運,也真正明白了‘底層勞動者’這個詞組所包含的意義”,但“真正要理解我們的民族與人民,卻必須要付出終生的代價。”[3](P280)相比較于書齋式與學(xué)院式批評家精巧的閣樓建制,周政保毫不諱言“我的思維世界里總是挾帶塔里木的沙味與土氣,也免不了那種昆侖山與天山之間所固有的粗俗與偏執(zhí)。”[4](P281)但在主張“批評即選擇”和“深刻的片面”的新時期,在各種理論方法走馬燈式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80年代,在文學(xué)批評很大程度上成為人文社會學(xué)科之間跨學(xué)科互滲的富于示范意義的實驗場的90年代,周政保始終固守著民族———人民———生活———現(xiàn)實的批評基石和前提,這使“他的文章或許不那么新穎、尖銳,但往往是正確的,時隔數(shù)年不會變質(zhì)變味。這說明他是有眼光的,這眼光里含著更多的社會因素、歷史因素和政治因素,而不僅是文學(xué)的技巧。這就使得他的批評比較穩(wěn)練,比較大氣,他的有些文章隔幾年再讀反而顯得越好。他的文章文學(xué)上的超前性不那么明顯,在這方面他不如有一些批評家;但他有一種社會經(jīng)驗上的超前性,在這方面,那些足不出京都的、從未在實際生活中摔打過的先生們是望塵莫及的。”[5]可以說,生活理解和生活經(jīng)驗是周政保豐厚學(xué)術(shù)理性的基礎(chǔ),這決定了他始終以現(xiàn)實主義批評作為自己的美學(xué)原則和價值標(biāo)尺,表面看這是他的狹隘和固執(zhí),本質(zhì)上確是證明了他做人與做文內(nèi)在相通的機理,證明了其文學(xué)評論與人生經(jīng)驗的血肉聯(lián)系。
二、對現(xiàn)實主義的開放理解
在周政保的評論中,梳理和確定最多和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命題有:現(xiàn)實主義(精神),思情寓意、生存景況(人類前途和人類命運)等。在其充滿活力的現(xiàn)實主義批評范式、方法和話語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即是他對現(xiàn)實主義的開放理解。在80、90年代之交的系列文章中,他首先對長期在教條主義、公式主義及形形色色的極左思潮影響下,嚴(yán)重被戲弄或誤解的現(xiàn)實主義在新時期被排斥和冷落的命運發(fā)出慨嘆:“這是一種‘怪圈’,即由于倡導(dǎo)目的扭曲或非文學(xué)化,欲得‘現(xiàn)實主義’而終于不得‘現(xiàn)實主義’。”[6]又對“尋根”文學(xué)和“新寫實小說”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做出準(zhǔn)確定位,并得出80年代的現(xiàn)實主義的發(fā)展線索就是“從創(chuàng)作方法到審美精神的潛移”的卓然見解,并強調(diào)現(xiàn)實主義精神:“是一種永遠(yuǎn)來源于生存現(xiàn)實的、因而永遠(yuǎn)充滿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shù)精神,或者是一種因了人類生存景況的探索而始終不懈地關(guān)注周圍生活狀態(tài)的審美氣度。”“這種‘精神’并不像‘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那樣要求小說的描寫必須接近生活的原生面貌:它不排斥‘重現(xiàn)’或‘再現(xiàn)’,但也不以此為唯一的傳達(dá)方式。它可以充滿假定性,可以變形,可以象征,可以寓言,也可以‘詩化’或‘散文化’,等等。”[7]對于中國80年代的現(xiàn)代派小說,學(xué)界是有著廣泛爭議的,周政保以敏銳強烈的藝術(shù)直覺力與系統(tǒng)清晰的思辨性理論性品格,沒有單純地從中西語境的比較入手,而是直接切入薩特等西方現(xiàn)代主義大家仍強調(diào)現(xiàn)實關(guān)注品格的基本思路,在不同文章中反復(fù)引述了諾貝爾文學(xué)獎獲得者、著名現(xiàn)代派小說家索爾貝類在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受獎演說》中的警言:“我不知道今天誰會對藝術(shù)提出這樣的要求,要它使靈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現(xiàn)實。”所以即使到了90年代末,他的《泥濘的坦途》的副題仍是:“現(xiàn)實主義與中國當(dāng)代小說”。“我承認(rèn),我是肯定現(xiàn)實主義的,因為我實在找不到可以否定它的理由。”
三、建構(gòu)批評理論的自覺嘗試
周政保顯然有一套爛熟于心的自省方法,他的研究思維富有邏輯性,有內(nèi)心恒定的批評體系和審美理想。他對世界和文學(xué)的看法是明晰和概念化的,這也是其內(nèi)心思維格局外化的產(chǎn)物。在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學(xué)者中,有如此定力和整體性的人并不多。或許周政保的這些觀點在很多人看來過于保守,但在其中確實顯示出一位具有自主的原創(chuàng)意識、恢宏的批評視野、堅定的學(xué)術(shù)個性和深遠(yuǎn)的歷史眼光的一流文學(xué)研究學(xué)者最重要的能力:能對具體個別的作家作品以及單獨的文學(xué)現(xiàn)象進(jìn)行綜合、概括、總結(jié),發(fā)掘其中具有整體和發(fā)展眼光的文學(xué)發(fā)展規(guī)律和趨向,建構(gòu)新的文學(xué)理論形態(tài)———批評理論(critical-theory),從而在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起到宏觀引導(dǎo)和提醒之效的同時,補充、豐富和發(fā)展文藝?yán)碚摻ㄔO(shè)。可以說,周政保在評論中始終都著意于打通文學(xué)評論與文學(xué)理論的壁壘。在其第一本專著《聞捷的詩歌藝術(shù)》中,他通過對敘事詩如何成功關(guān)鍵問題的思考,從如何調(diào)和敘事與抒情的矛盾出發(fā),發(fā)現(xiàn)了詩的敘事成功的兩條藝術(shù)措施,一是以情節(jié)的單純化達(dá)到敘事的簡潔化;二是把所要敘述的故事情節(jié)浸泡在情感的抒寫中進(jìn)行。由此,他對《復(fù)仇的火焰》的結(jié)構(gòu)方式做出精準(zhǔn)概括:“‘叛亂與反叛亂’作為敘事詩整體的情節(jié)主線,‘覺醒與反覺醒’作為‘象外之意’的思想激情———思想主線”,并得出“作為一部長篇敘事詩的抒寫目標(biāo),情節(jié)主線是戰(zhàn)術(shù)性的,而思想主線是戰(zhàn)略性的”[9]的“形象化”的理論結(jié)晶,這顯然已上升到理論品格了。有時,他也會直言不諱地向“經(jīng)典”理論挑戰(zhàn):“‘形散神亦散’或‘神散形不散’同樣可以成為出色的散文。關(guān)鍵并不在于‘散’或‘不散’,而是在于‘散’或‘不散’的敘述形態(tài)之中所隱含的思情的質(zhì)地及精神發(fā)現(xiàn)的深刻性———這就是所謂的神。”[10]“形散神不散”作為“常識化”的散文理論的內(nèi)在匱乏與矛盾昭然若揭。
四、關(guān)注西部文學(xué)的發(fā)展動態(tài)
尤其是對西部文學(xué),周政保也在長期深思熟慮和大量文本閱讀后,提出了很多可以為當(dāng)時的創(chuàng)作做警鐘、為后來的創(chuàng)作所證實的真知灼見。如他認(rèn)為“文化視角所實現(xiàn)的文化剖析與文化闡釋,也是社會分析與社會判斷的一種,只不過是洞察角度或感受側(cè)面的不同罷了。”[11]并且反對那種“盲目地大胃口地企圖把握‘中國西部文化’的整體格局及理論建構(gòu)”的虛妄,認(rèn)為作家只可能描寫或表現(xiàn)“某一個‘文化圈’的歷史與現(xiàn)實。”[12]他還在很多文章中堅決“認(rèn)為不通曉民族語言的作家,很難創(chuàng)造卓越的描寫與表現(xiàn)民族生活的作品。”(他同時不斷肯定熟練掌握雙語的作家王蒙與張承志的創(chuàng)作),對新疆漢族作家,他充滿憂慮的指出:“新疆小說創(chuàng)作的平庸是思考的平庸所釀造的———它不是醇酒,不是碩果,而是缺乏內(nèi)在力量所患的‘貧血癥’。這種小說思情寓意的‘貧血癥’,并不是靠技巧、靠寫法的更新所能掩蓋的。”[13]因為他們“對于生活在新疆這塊土地上的漢族人(同樣作為社會的人的一部分)缺乏一種歷史的文化心理或心態(tài)的領(lǐng)略與感悟,一種因其他民族的歷史文化的沖擊與融合所產(chǎn)生的過去或現(xiàn)在的思情形態(tài)與心緒方式的理解及認(rèn)識。”[14]他對新疆中青年小說作者的批評振人發(fā)聵,但在今天看仍然切入肯綮。但對優(yōu)秀的少數(shù)民族作家,他也不遺余力的予以肯定,如他對艾克拜爾•米吉提的小說風(fēng)格的詩意描寫:“冷靜而不平庸,委婉而不柔媚,細(xì)致而不瑣碎,悠長而不拖沓,表面看來從容不迫、不動聲色,但其中卻蘊含著令人回味的韻律。這有點象作者筆下的草原,雖然云淡風(fēng)輕或細(xì)雨迷蒙,但在那里卻發(fā)生著種種充滿了時代氣息的深刻變化,流淌著一條莊嚴(yán)肅穆的情感的河流,而且在這條河流之上,又籠罩著對于哈薩克民族生活的深深的思考。”[15]并以民族學(xué)、文化學(xué)的視角,發(fā)現(xiàn)其小說“與他的哈薩克人的草原生活、以及某些沉積在血液里的古老記憶的影子具備著千絲萬縷的神秘聯(lián)系。”[16]五、真誠尖銳的作家作品論雖然周政保評論的最大長處和特點體現(xiàn)在將個人化理解與歷史化眼光成功對接的宏觀批評理論的建構(gòu)上,但其評論中最具生命力和活力、也最能體現(xiàn)其才情的卻是其融入了生命感受、閃耀著思想鋒芒、溢揚著沛然文采的作家作品論。它們厚重不失靈動,大氣不失細(xì)膩,將其識見與才氣發(fā)揮到幾乎淋漓盡致。如他最早發(fā)現(xiàn)了《雜色》在王蒙“在伊犁”系列和反映“右派”知識分子心路歷程作品中獨一無二的價值:“《雜色》的這種局部描寫與整體旨意的巧妙組合及富有強大思想容量的升騰,在中國小說界是出類拔萃的。”[17](P210)這一“深深地打上了維吾爾文化或新疆文化的烙印”的“那種可悲的自我平衡方式,那種可慨可嘆的人生達(dá)觀形態(tài),那種自我詰難、自我挖苦與自我嘲弄”的生存方式[18](P218),以及作品奇詭復(fù)雜的敘事藝術(shù),也在時下“重返80年代”的當(dāng)代文學(xué)經(jīng)典打撈中再次浮出水面,由此也驗證了周政保眼光的犀利和超前。
周政保最令人欽佩的還是他作為評論家不趨時、不唯上、不流俗、不唯名的學(xué)術(shù)品格,相比于某些只是寄生或應(yīng)聲的“影子”批評家,他以勇氣、坦率與真誠在文壇混亂又充滿泡沫的今天,忠實履行了批評家的職責(zé):做作家的良師益(諍)友,洞悉作品的得與失,成為為其導(dǎo)航的一盞塔燈。對20世紀(jì)80年代正在成長中的青年作家,他既充滿期待又不忘恪守其職,如他認(rèn)為趙光鳴“倘若能在情調(diào)、蘊藉、含蓄性、寓意性、以及作者主體介入之后的赤裸裸評價的節(jié)制等方面,再作一些適當(dāng)?shù)淖聊ヅc調(diào)整,那才可能造就一種真正具有獨特品格的小說敘述語言。”[19](P218)發(fā)現(xiàn)80年代前期,董立勃小說“對墾荒生活、對墾荒者生命現(xiàn)象的感知和洞見,還只能說是處于一種被動描寫,因而還談不上主動表現(xiàn)的狀態(tài)之中。不言而喻,其中的原因是極為復(fù)雜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僅僅屬于作家的小說觀念所致,而且也屬于作者的生活觀念所致。”[20]坦言“文樂然的中篇小說《荒漠與人》是一部光澤與斑點都十分引人矚目的作品。”[21]甚至是在為自己的戰(zhàn)友和好朋友做的書序中,他不為親者諱,一反寫序的慣例和潛規(guī)則,直言“作者的散文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并指出其散文隨意中的力度不足、語言表達(dá)的欠精到、議論的浮于表面,全文言辭懇切、肝膽相照,無一句溢美夸飾之言。其實今天轟轟烈烈的文壇塵囂落盡時,“顆粒無收者大約是絕大多數(shù)”[22],周政保完全不必如此苛刻,但從這樣真性情的文字中,我們不難窺見論者的真誠和作者的勇敢。從90年代中期開始,周政保似乎意識到可能會走向模式化和定勢化的理論框架的潛在危機,轉(zhuǎn)向既重視整體文學(xué)環(huán)境又注重細(xì)致文本分析的雙效之路,他將先前的理論品格和追求內(nèi)化為內(nèi)心一種強大的力量和源泉,在更廣闊的視野中以更豐富的參照系,將文學(xué)批評的思維引向更多元更開放的空間,注重對文學(xué)作品和文學(xué)現(xiàn)象作多維多向多角度的認(rèn)識和考察,并在其中豐富和完善著自我的理論結(jié)構(gòu)。其文學(xué)批評的視野也由西部面向全國,之后十余年來銳氣不減,韌性依舊,更有大量為批評界所推崇的評論面世。
周政保是一位閱讀視野恢宏的評論家,他廣泛涉獵報告文學(xué)、散文、軍事文學(xué)、電影文學(xué)等不同文體,關(guān)注風(fēng)格迥異的不同作家(如他曾分析過非常個人化和私語化的女作家斯妤)。在批評方法上,他最重視的是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因為“就一個具體的西方漢學(xué)家而言,他可以不信仰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文學(xué)理論,或可以認(rèn)為文學(xué)發(fā)展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毫無因果關(guān)系;但一旦當(dāng)他涉足中國當(dāng)代小說世界的時候,那他必定會意識到回避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文學(xué)觀念,將是一種絕不可能的思想行為。”[23]同時,他更是以兼容并蓄的胸懷吸納著一切能內(nèi)化為生命一部分的理論方法。酣暢淋漓的文字、源源不斷的思想、堅如磐石的信念使他的文章顯出一種博大,一種超脫,一種飛動之勢。其結(jié)構(gòu)文氣貫注,渾灝流轉(zhuǎn),其文句議論風(fēng)發(fā),神采飛揚,只有一個思想澄明、情感純摯、見識高卓的人,才能寫出這樣一瀉千里、熠熠生輝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