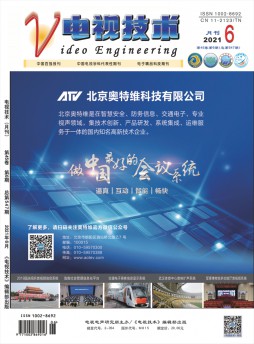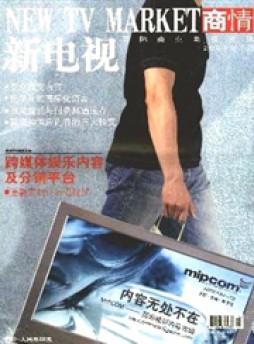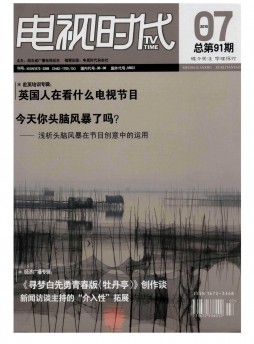電視紀錄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電視紀錄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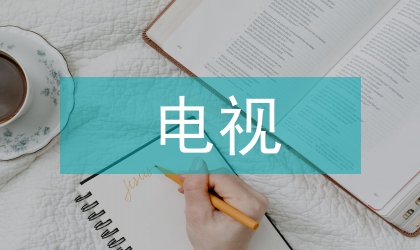
當人們談論紀實時,總愿意把它與真實聯系在一起,似乎紀實就是真實。
紀實是真實嗎?
真實是電視紀錄片的本質屬性,它要求把現實生活的存在方式和本質意義通過創作者的創作活動體現到作品中。在以非虛構的方式來對待現實生活的創作中,創作者的體現方式則是多種多樣的。
紀實,首先是一種美學風格,是一種與真實的關系。
風格,是對現實生活進行藝術觀照的方式,是藝術形式的組織類型。它帶給人們的不是現實本身的信息,而是藝術對現實的折射程度和性質的信息。面對同樣的現實,不同創作者會用不同的折射方式。
伊文思曾在1987年論述過:“對于紀錄片的看法和要求,各個國家都不相同。例如在法國,并不那么嚴格地要求它的基礎必須是真實的,只要和故事片不同,就可以稱為紀錄片。”○1事實如此,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把紀錄片的范圍放得很寬,為了敘述某一件事的過程,可以用演員來扮演,可以虛構故事情節。在《萬里長城》中,我們看到了日本漂流民的身影,在《金字塔》里又出現了古埃及大臣和王子的摸樣;我們甚至在中國的紀錄片家族中也尋找到了扮演的角色,《南京血證》里再現當年巧藏珍貴影集的過程;《故宮》一片,編導則向觀眾展示了清王朝皇室活動及日常起居,并輔以大量虛擬動畫場景;《大國崛起》里這種手法的普及應用更是俯仰皆是。可以說,在當今的電視紀錄片大潮中,扮演、虛構情節等“務虛”的創作手法已漸為圈內人士所關注,并引起諸多的爭論。其實,這個話題隨著紀錄片的產生發展就一直伴其左右,只是近幾年來,紀實之風尤盛,當看慣搶拍,偷拍,跟拍的節目又忽地一下子冒出許多擺拍來,難怪一些人士接受不了。
電視,這個現代電子媒介,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發展,它的觸角遍及千家萬戶,它的影響力、權威性也與日俱增。傳播學上講究雙向交流,講究受眾論,效果論,總之是十分注重傳播方式和結果,尤其是后者。那么,對于紀錄片的編導者來說,無論前期怎樣殫思竭慮觀眾是不得而知也不感興趣,觀眾只看到最終的節目成品,并由此產生聯想,啟發或受到某種感觸。于是,這就需要編導們要把節目做的好看、耐看,尤其是如今電視劇一統天下,文藝娛樂節目五花八門,紀錄片若要爭得一分天下,必須在信息量、知識性、趣味性、及畫面造型上下功夫。這就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必要的虛構與恰當的扮演。”
藝術真實,指藝術作品通過藝術形象反映社會生活時所達到的正確性。藝術真實一方面要求藝術作品中細節的真實,同時更要求達到本質的真實。藝術是社會生活經過藝術家改造、加工的產物。藝術虛構的特點決定了藝術的真實不同于生活的真實。生活的真實是一種客觀存在,藝術的真實則是往往是可能存在的真實。它既受客觀真實的檢驗,同時也要受人們主觀認可的真實標準的檢驗。從另一個意義上,也可以稱藝術真實是藝術作品與客觀生活、與觀眾的主觀認可中建立起來的一種真實的對應關系。
藝術的真實一方面是可能的真實,另一方面也是可信的真實。在不同類型的藝術作品中,人們對它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在新聞性紀錄片中,人們更多的要求它與客觀社會的直接的對應,要求它細節到過程、從事件到人物都逼真于實際生活。紀錄真實環境真實時間里發生的真人真事。對于新聞紀錄片“四真”原則,匈牙利電影美學家貝拉*巴拉茲說:“在紀錄片里,‘藝術’不在于虛構,而在于發現,藝術家必須在經驗世界的廣闊天地中發掘出最有特征意義的、最有趣的、最可塑造的和最有表現力的東西。”○2伊文思不止一次說:“紀錄片把現在的事紀錄下來,就成為將來的歷史。”○3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揭示了紀錄片的真實性和文獻性的直接關系。
在藝術性紀錄片中,人們則會更多的從主觀感情與可能性上來要求它的真實程度,而不會在外在形態和細節等方面去要求它逼真于客觀生活。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是因為人們在長期的創作,欣賞中,已根據不同的方法,風格,通過無數次的反復,建立起來的一種對于藝術真實的默契關系。其中情感的真實與邏輯的真實是極其重要的。在明顯的虛構段落中,情感的真實是獲得觀眾認同的最重要的保證,邏輯的真實主要是指人物的心理行為軌跡上的可信性。藝術不排除偶然,虛構和獨特的想象,但它總是以可理解為基礎的。《故宮》一片中有許多模擬表演及動畫再現當年皇室祭祀、迎娶、登基活動的場面,稍有常識的觀眾一定不會認為這是歷史實景,雖然都是在同一地點同一環境中。記得美國的埃里克*巴爾諾在《世界紀錄電影》中曾指出:“真實感和權威性是紀錄片的命運所系,無論動機如何,對于利用它的人來說,這兩點是引誘力,也是對事實進行啟發或者欺騙的力量源泉。”○4
在紀錄風格的紀錄片中出現扮演,應該說是對于紀錄片創作時空的一大突破。因為,紀實不是目的,紀實是為了最終產生感染觀眾的藝術效果。在以往的創作中,對于歷史時空的展現多采用歷史圖片、舊影像資料、當事人或見證人言語回憶等手法。然而,電視這一大眾媒介的最大特點就在于表現活動具像,我們應努力發揮自己的特長,盡可能給觀眾提供一種認識世界,觀照自我的可能和舞臺。前蘇聯的勒瓦爾拉莫夫等人也主張可以允許用故事片扮演的手法來拍紀錄片:“在個別情況下使用演員可能不至于破壞嚴肅的真實性”,“至于按照事件或事實的真實情況,邀請當時事件的參加者在真正是當時的環境和順序下把它們再現出來,這都是另一回事。”○5
當然,我們并無意倡導在紀錄片中大量運用這種“務虛”的方式,但適當地、恰如其分地整理和構成事實、追求真實,應當無可厚非。問題的關鍵在于觀眾對扮演的允許度上。日本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在日本國內挑選了120人進行隨機問卷調查。對于扮演的允許度的調查結果顯示:“紀錄片是依據事實獲得了主題后的一種創作品。其中既有演出也有再現,它們是以逼近本質的程度的多少為大前提而存在的。作為傳播的內容,欲對其進行證實時,直接利用的材料必須是事實,因此,如果扮演僅僅是為了促進理解的話是可以存在的,這對觀眾來說也是必要的。”○6
藝術的創作手法是多種多樣,而觀眾也需要風格各異的節目滿足不同層次的需求,對于創作者來講,處理好扮演的分寸及真實與虛構的銜接,筆者認為是極其關鍵的。
扮演、模擬再現與真實紀錄是紀錄片創作中虛與實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即便是在真實紀錄的過程中,即展現生活現實原生態的過程中,也要講究虛與實。
虛實論是中國古典美學的重要理論,認為天地萬物以及一切藝術和審美活動都是虛實的統一。從我國的審美傳統看,藝術創作中強調要使“實”的描寫能夠引導人產生某種想象,從而構成一個“虛”的境界。
意境,是中國古典美學中具有民族特色的范疇之一,“指的是詩、畫、戲曲以及園林等門類藝術中借匠心獨運的藝術手法熔鑄所成情景交融,虛實統
一、能深刻表現宇宙生機或人生真諦,從而使審美主體之身心超越感性具體,物我貫通,當下進入無比廣闊空間的那種藝術化環境。”○7這里重點是強調虛的作用。老莊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笪重光的“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鏡”,劉禹錫的“境生于象外”都是講要通過具體的藝術描寫引發人的聯想,在象外構成一個虛的境界。《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意思是說,道既具有“無”(虛)的屬性,又具有“有”(實)的屬性。
從藝術和現實的角度來講,藝術創作就是借助可視形象解釋歷史,闡明抉擇,寄托自己的情感。現實生活是一切藝術的源泉,這個意義上說,藝術都是寫“實”的,那么中國美學家何以提出化實為虛的問題呢,這是因為藝術并非機械地復制生活,它有賴于創作主體和欣賞主體各種心理因素的積極介入。清方土庶在《天慵庵隨筆》中說:“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實境也;畫家因心境造境,明乎道心,此虛鏡也,故以實帶虛,以虛明實。”○8
從觀眾的角度講,人們的接受欲望,并不是僅僅要看到一些生活表象,而更多的是要求從一部作品中感受和發現某種能引起共鳴的東西。那么通過生活表象去接觸及觀眾的內心,通過自然環境去營造心理環境,就成為藝術表現的重要任務。克拉考爾認為,“現實生活的存在是一種含義模糊的存在,在影片中也應具有一些含義模糊的鏡頭,以便去觸發各種不同的心情,轉而表現某些物象,使它們處于一種暗示性的模糊狀態。”○9這種暗示與觸發是為了給觀眾提供體驗的可能性,這種體驗又可以去引發想象,可以以本能的認同去引發心理的認同。但《望長城》恰恰在這一點上留下了諸多的遺憾,從拍攝方法和敘事方式講,它的確精到地體現了紀實的本性,可以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電視紀錄片中的佼佼者。但作為藝術創作,則顯得功力欠缺。許多段落,除人物活動的自然真實促進了觀眾的本能認同外,很少能從整體上觸發觀眾的想象,誘發觀眾的心理活動認同,有些段落為了紀實冗長拖沓,甚至缺少必要的鋪墊和交代。任何事物都不應走極端,否則,“紀實”就有可能成為“隨意”和“淺薄“的代名詞。
紀錄片來源于生活,但以為紀錄片就完全等同于生活肯定是不科學的。伊文思打過這樣一個地方,他說:“實際上這也就跟石料對于一個建筑家和雕塑家一樣,石料本身并沒有藝術價值,經過建筑家和雕塑家的加工,才成為藝術品。同樣生活也只是素材,而不是藝術品本身,藝術開始于素材的選擇。現實生活需要經過選擇、剪接,才能形成一部具有藝術價值的影片。”○10
首先可以“化實為虛”。通過對表現對象形聲結構及運動形態的描述,借助隱含于物象之中的隱喻、類比、暗示等藝術表現因素,去引導人們產生一種必然的心理聯想從而使實在之物傳達出一種虛的境界,使實的內容與虛的意境成為渾然一體的完整的藝術形象。比如《沙與海》中打沙棗的長鏡頭,正是這種象征對生命的愛惜與渴望,由實境而聯想產生的虛境,才構成了完整的藝術形象,對觀眾才具有長久的吸引力和震撼力。在當下的創作中,出現了一股“跟拍跟拍再跟拍”的“自然主義”潮流。一個長鏡頭拍下來,記錄了無任何新意、巧意、視覺沖擊力、心理感召力的“生活原始狀態”,什么搬東西、洗衣服、尋找某人等等這些內容的確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把它編排在節目中就必須賦予這些活動以新的、獨特的內涵,讓觀眾感覺到正是這些生活的方方面面才形成主人公的個性化語言、行為,是表現人物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才行。否則,一味的“紀實”,只給觀眾看到“類語言”、“類行為”這些人們早已司空見慣的東西,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紀錄片本質屬性的一種歪曲、誤導。
其次,可以“以實出虛”,通過有形的現實對象引出創作者虛化了的情況,這種虛鏡是實鏡的延續,也是實境情緒化了的意義的顯現。《沙與海》里在牧民的大女兒關于婚姻問題的沉默之后,作者巧妙地編入了小女兒在沙丘玩耍行走滑下的鏡頭,這個被電視界稱為經典鏡頭的畫面的確是帶給我們太多的思考和啟示,無論是片子內容本身,還是創作手法都留給大家極其深刻的印象。《故宮》一片,這樣的手法就更為常見。空蕩的龍椅、斑駁的老樹、變幻的光影、震顫的水波,一切都敘述著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故事。
虛以實而具體,實以虛而豐富。隨著人們思想觀念的不斷革新,紀錄片的創作方法也將呈現多樣化的局面。記錄生活,展示人生,尊重每一位生命是紀錄片永恒的主題;豐富節目內容,擴展創作思路,拍攝出好看耐看的高品位的作品則是每一位創作者責無旁貸的任務。就拿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一句名言作為本文的結尾吧,任何事物,我們在那里面看見依照我們的理解應當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東西凡是顯示出生活或使我們想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