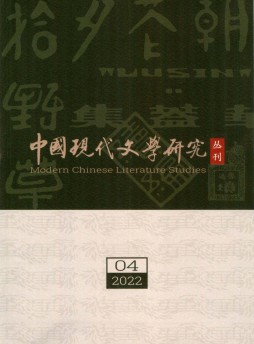現代文學的半殖民性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現代文學的半殖民性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與文化矛盾心理
中西“會通”問題依然在延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也面臨新的學術轉型。恰當而有效地認識、理解與闡釋“半殖民性”命題,不僅需要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實際狀態與情形進行再考察、再理解,還需要看研究主體應具備怎樣的胸襟、氣度與立場。中國現代文學誕生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壓抑、恐慌境遇中,是在被迫與無奈中學習、模仿西方文學。西方強勢文明憑借武力的“大棒”和文化的“胡蘿卜”,不但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擴張,而且在宗教、語言、倫理、文學、藝術等各層面進行文化價值的推廣與普及,用政治話語來表述,就是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和平演變”。華勒斯坦認為:“普遍主義是作為強者給弱者的一份禮物而貢獻于世的。我懼怕帶禮物的希臘人!(TimeoDanaosetdonaferentes!)這個禮物本身隱含著種族主義,因為它給了接受者兩個選擇:接受禮物,從而承認他們在已達到的智慧等級中地位低下;拒絕接受,從而使自己得不到可能扭轉實際權力不平等局面的武器。”③這種等級秩序和權力不平等,是后發的現代民族國家在文明的碰撞與交融中所遭遇的一個基本歷史事實。這一歷史遭遇,往往給弱勢民族國家帶來頗難堪的精神后果,即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和文化矛盾心理。如果說隨著弱勢民族國家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崛起,作為民族創傷和文化創傷的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能在較短時段內得到較大程度修復;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克服,則因為文化變遷的相對緩慢而需要更為漫長的時光。如果說民族自卑感和歷史悲情敘事,能為后發的現代民族國家帶來集體激勵效應,使之知恥而后勇,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為其帶來的實際效應,則相對復雜和隱蔽。在文明的碰撞與交融中,文化矛盾心理及其反饋的文化兩難選擇,是一種普遍現象。正如華勒斯坦所說:“這種矛盾心理反映在許多文化‘復興’運動中。在世界許多區域廣泛使用的復興一詞,就體現出矛盾心理。在談論新生時,人們肯定了一個先前文煌的時代,但同時也承認了那時文化的等而下之。”①從某種意義上看,如果說民族自卑感和歷史悲情敘事,關乎后發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自我認同,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調適與化解,則更關乎這些國家的自我選擇。這是理解和闡釋“半殖民性”所指涉的普遍主義和地方主義、現代性和民族性等元素在近現代中國呈現犬牙交錯狀態和復雜情形的一個研究前提。
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等命題,是一種既對立又統一的邏輯分類和難以截然分離的認知模式。這一命題的兩端,既相生相克又相輔相成。我們從現象中提取普遍主義、現代性等概念,并不意味著存在一種“純凈”的普遍主義和現代性標尺。普遍主義和現代性的形成與發展,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和區域現象。普遍主義不是生而就有,而是從地方主義擴張而來;現代性也不是勻質的和固態的,而是雜質的和流動的。英、美、法、德等現代民族國家所呈現的普遍主義與現代性,均有重要差異,只是我們很少有興趣辨別而已。從更長遠時段看,這種普遍主義和現代性,只是人類文明的盛衰在特定歷史時空的一種具體展現。被迫、后發的現代民族國家如果抵制、拒絕這份“禮物”,其地方主義和民族性究竟能否存在,在全球一體化時代都是一個嚴峻考驗;如果加以充分吸收與借鑒,其地方主義和民族性不但有了彰顯的機遇,假以時日還有可能在文明的碰撞與交流中成為新的普遍主義與現代性標桿。
需要警覺的是,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和文化矛盾心理極易導致固步自封傾向,即強化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對立。這固然可以昭示民族自尊心,也可能激勵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自信心;但在某些歷史階段,更容易淪為專制者及其附庸的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典型論調,莫過于特殊國情論。如果動機出于文化情懷和學理探究,其民族感情應予肯定;但如果出于利益掠奪與權力維護,其虛偽性與無恥性就昭然若揭了。弱勢文明遭遇強勢文明的介入,所屬國民秉持民族本位立場和本土價值意識,應予理解與尊重,但不應成為抵制與抗拒的借口。學習與模仿,并不是一件令人羞愧與恥辱的事情。堂而皇之地享用資本主義文明的物質產品,卻又以維護傳統的名義抵制資本主義文明的精神果實,是不是顯得滑稽?魯迅的“拿來主義”在今天依然振聾發聵,只不過我們已經習焉不察。“拿來主義”不是實用主義手段,而是凝練概括了弱勢文明遭遇強勢文明時所應有的胸襟、氣度和立場。日本堪稱“拿來主義”的一個成功案例,它在充分吸收與借鑒普遍主義和現代性時,不但沒有喪失文化的民族本性和地方主義色彩,反而從文明等級的低端快速抵達了高端。當然其民族根性中“惡”的一面,也實現了現代轉換,這尤其值得引以為戒。弱勢文明在扭轉劣勢、實現復興過程中最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謂的普遍主義和現代性,而是固有文化結構中“惡”的因素沉渣泛起,尤其是“惡”以現代形式借尸還魂。在文化交流和學理探究層面探討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對立,可以通過鮮明的對比效應,凸顯文化更新與復興中遭遇的諸多具體問題。但如何避免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導致的價值偏離與情感抵觸,避免文化情懷與學理探究淪為利益與權力的附庸,是需要盡快解決的問題。談論中國現代文學“半殖民性”,不是激活民族恥辱感、歷史悲情意識,更不是強調文化殖民色彩,而是在學理和文化情懷層面,探究中國現代文學及其研究在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碰撞與交融中如何實現“會通”。必須看到,“半殖民性”帶來了民族恥辱感和歷史悲情敘事,更給中國社會和文學帶來了一個重大歷史發展契機。在今天的歷史境遇中,祛除民族自卑感和歷史悲情敘事,調適文化矛盾心理,更多關注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會通”,是現代學術體系能否拓展、創新的一個更為迫切的命題。
二、在“會通”視野中探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創新可能
邏輯分類和認知模式中的普遍主義和現代性,一般指向歐美強勢文明范疇內的各種觀念體系及其指涉物。從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譜系看,歐美文學及其觀念給中國文學帶來了一場至今仍在變動不居的革命性變遷;這場變遷的模仿與學習色彩,迄今依然強烈;所謂“半殖民性”,即是對這場革命性變遷的實際歷史狀態與情形的描述與概括。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重視:(1)發源于歐美民族性和地方主義的文學及其觀念,因為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貢獻了創造性經驗與價值,而具有了普遍主義和現代性面目;作為歐美地方主義和民族性在文學領域的具體呈現,它熔鑄的是歐美世界的區域性文學經驗與價值,并未充分容納和吸收其他地方與民族的文學經驗與價值;憑借資本主義歷史體系的擴張,這種創造性價值與經驗被賦予了模本和范型的作用與意義。(2)中國文學有著幾千年的連續性和不間斷性,文物典籍、文獻史料浩如煙海,精神遺產和文化心理博大精深,無論在古典時代還是步入現代進程,都體現和蘊含著人類社會在一個特定時空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3)中國現代文學是在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抗爭、對世界文學的借鑒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是在中國古典文學、世界文學和當時文學實踐的共存秩序中脫穎而出的;它實現了自我本質的確證,具有了“融匯古今、貫通中西”后的自足性和獨特性,初步孕育了自身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為中國文藝復興的展開打開了歷史之門。或許再過多少年,這些才能看得更為清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具有知識傳授、塑造審美能力、宣傳意識形態、增強社會凝聚力、提振民族精神、傳承民族文化和學術史延展等功能和效用。這些都無法繞開一個基點,即對中國現代文學創造性經驗與價值的挖掘、梳理、歸納、總結和闡發。因此,挖掘上述三個層面之間的差異、分歧和對立,有助于我們在對比視野中甄別和挖掘中國現代文學的自我認同與創造個性;但更應在比較視野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全面、細致地建構中外古今的“會通”機制與平臺,在世界文學的格局中,在中國文藝復興的延展中,探究中國文學已有和將有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最近二十年,創新的焦慮與疲憊困擾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不僅是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特殊問題,也是整個國家和民族創新能力普遍匱乏的一種具體體現。創新的實現,有賴于學術外部環境、學術內部事務和學術個體倫理意愿匯聚而成的合力機制能否發揮良性作用。但是,不能奢望有了一個寬松自由的外部環境后再去創新。如何在有限時空內,充分發揚學術個體的倫理意愿,重塑學術內部事務的動力源和創新機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更具操作性的路徑。因此,在“會通”視野中發掘“半殖民性”的內涵及其表現,重新考察一百多年來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實際歷史狀態與情形,就有可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具體創新點。
“反思西方、回歸傳統已然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個時代話題”①。這值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躬身自問。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反思與創新意愿,主要表現為:(1)反省西方文學的知識、理論和方法對中國文學研究的改造與影響;(2)呼喚回歸中國文學研究的本來狀態,倡導建構民族詩學。在反思移用西方理論弊端方面,有的觀點較為尖銳,有學者指出:“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學觀念、文體界限和文學創作方法,使中國固有的文學觀念和文體形式面臨消失的窘境。同時,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也漸漸變成了西方話語體系下的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中國固有的文學體系和價值范疇漸漸被拋棄”②。在呼喚回歸中國文學傳統、建構民族詩學方面,有學者認為:“構建一個以中國固有文學觀念為指導的中國古代文學史體系,發掘民族傳統文學的人文訴求和發展脈絡及價值,這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任務,卻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復興的迫切要求”③。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還從全局性研究視野,觀照和歸納已有研究弊端:“在百年來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中,將古代文學現代化、將中國文學研究西方化、將文學研究政治化,是最值得反思的三個方面”④。這種反思與重建趨勢,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學術針對性。我們可以從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中,得到一些啟示:(1)從“半殖民性”視野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創新訴求,主要指向研究主體而非研究本體。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古代文學本身具有“半殖民性”;即使有,也是周邊民族國家的文學遭遇天朝體系的強勢影響而具有“半殖民性”,更何況殖民、半殖民這類術語特指資本主義文明擴張的一種現象。(2)如果說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創新趨向的旨歸,是恢復和重建中國古典文學的本來面目,那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面臨的問題更為復雜,原因在于,中國現代文學是在“半殖民性”的社會形態與情境中生長起來的,本身就具有“半殖民性”;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本體的相對“純凈”相比,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本體是一個古今中外文學融匯后的“雜質”產物;緊隨其后的研究,更是主要依據西方的知識、理論和觀念展開的;顯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面臨對研究主體與研究本體的雙重梳理和甄別任務。(3)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反思西方”的趨向落腳于民族詩學建構,但問題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田園已經荒蕪不可歸,今人已經不可能用古典時代的思維和話語去再現古代文學的本真面目,民族詩學建構也不可能再局限于地方主義和民族性的價值資源和話語系統。這些難題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同樣是個拷問:反思現代性、建構內源性研究模式,來源和支點何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依據的已經是古今中外話語系統融匯后具有全球化色彩的話語系統,現代文學實踐本身更是早已大范圍系統運用普遍主義和現代性的話語和思維了。反思西方文學理論觀念的影響、建構內源型的原創性研究模式,來源只能是古今中外“會通”后產生的那種新的歷史狀態與情形,支點只能是中外古今文學知識、理論與方法的“會通”機制與平臺。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強勢文明對弱勢文明的侵略、剝削和同化,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人類文明全球化趨勢的一種“曲解”的歷史展現形式。各區域、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化及文學,是人類文明創造物的一個分支,因為地域、民族、宗教、習俗等原因而呈現出差異性和特殊性,但差異性和特殊性背后總是體現了人類文明創造物所具有的深層普遍性和共通性。西方文學及其觀念,借助于資本主義文明的崛起而具有普遍主義和現代性面目,未必具有絕對的普適性和通用性,但作為人類文明在現代時段孕育的一種創造性經驗和價值,最低效用也可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西方的文藝復興,持續數百年才開花結果。中國的文藝復興才剛剛展開一百多年,中經諸多歷史挫折,且大有岌岌可危之勢,要孕育出完整而獨立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需要更多的歷史積累。雖然有了一百多年的生長歷程,中國現代文學還沒有抵達獨立性和創造性的較高境界,有關研究更是沒有達到丟棄西方話語系統、建構原創學術體系的境界。完整與獨立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必然是在一個“會通”機制與平臺中才能得以完型。
前車之鑒,歷歷在目。在建構“會通”機制與平臺過程中,有一個問題需要我們長期警醒,即“全盤西化”和“特殊國情論”及各種變形話題帶來的周期性困擾。如果深入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深處和細部,尊重中國現代文學自然生長的歷史狀態,不難發現這類論調的偽命題色彩:運用單線邏輯和封閉思維,將復雜的歷史狀態和情形簡化為各執一端的結構性本質對立。以此觀照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犬牙交錯的狀態與復雜情形,就往往歸納為不兼容模式,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將會無數次復活。如果對這類命題信以為真,將會導致精神創造力的嚴重退化,導致研究主體胸襟、氣度和立場的萎縮。通過中國現代文學“半殖民性”的研究,把握歷史與文學的實際形態、情形與走向,正視它在“會通”機制中駁雜的自然生長性,有助于突破與摒棄這種極端和僵化的致思模式。強調中國現代文學的“半殖民性”,不是給中國現代文學定性質、下結論,而是把它當作開創新的學術研究空間的重要觀念,以之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有效“會通”機制,充分彰顯中國現代文學由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元素氤氳化生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為探索中國現代文學那些迷人秘密增添一個有效的學術空間。
作者:賈振勇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 上一篇:現代文學批評史的重寫范文
- 下一篇:幽默小說看現代文學的反審美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