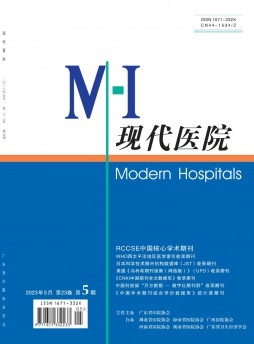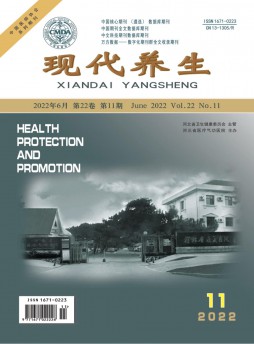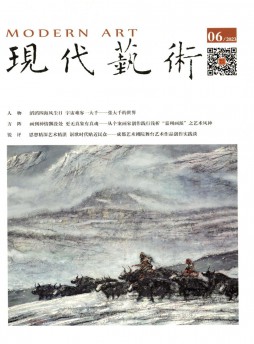現(xiàn)代西方體育在邊區(qū)的傳播探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現(xiàn)代西方體育在邊區(qū)的傳播探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文章闡述了現(xiàn)代西方體育在我國早期的傳播和影響,分析了現(xiàn)代西方體育在陜甘寧邊區(qū)傳播的脈象和特征。一是具有強(qiáng)烈的實用主義特征;二是體現(xiàn)了強(qiáng)大的組織力;三是以不同層次的體育活動和體育競賽吸引參加者和擴(kuò)大愛好者范圍。審視現(xiàn)代西方體育在陜甘寧邊區(qū)的傳播,對于當(dāng)代開展全民體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價值。
【關(guān)鍵詞】現(xiàn)代西方體育;陜甘寧邊區(qū);傳播特征;借鑒
現(xiàn)代西方體育是適應(yīng)社會化大生產(chǎn)和市民社會生活需要的文化形式。它源起于古希臘城邦間的生存空間競爭,因而,具有鮮明的尚武文化價值內(nèi)涵。這和我國傳統(tǒng)文化尚靜不尚力、尚文不尚武的文化價值觀是大異其趣的。西方現(xiàn)代體育是一種大眾化的文化活動,具有游戲的因素和超越性的精神內(nèi)涵,這和西方工業(yè)化社會的文化土壤和生產(chǎn)力條件是相映成趣的。這和封閉保守的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明有著不同的旨趣。西方體育文化的內(nèi)在價值訴求是文化的個體性展開,是將體育作為人追求現(xiàn)實幸福、快樂以及進(jìn)行競爭的平臺。這也是和我國傳統(tǒng)文化尚和不尚爭有著天壤之別。但就是這樣一個充溢著西方文化特質(zhì)和時代氣質(zhì)的文化形式卻在地居邊遠(yuǎn)、經(jīng)濟(jì)落后、文化保守的陜甘寧邊區(qū)廣泛傳播、蓬勃發(fā)展。陜甘寧邊區(qū)現(xiàn)代體育的發(fā)展,不僅實現(xiàn)了中共通過發(fā)展現(xiàn)代體育增強(qiáng)人民體質(zhì)、振奮民族精神的價值目標(biāo),而且實現(xiàn)了對西方現(xiàn)代體育精神內(nèi)涵的超越,賦予了其救亡圖存的中國功能。體育與增強(qiáng)人民體質(zhì)、振奮民族精神相結(jié)合,使之符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氣質(zhì)的中國化改造。這種體育發(fā)展思想影響至今。深入探討中共將一個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價值大相徑庭的文化形式,在一個時處落后、封閉且又以農(nóng)民為主體的地區(qū)蓬勃發(fā)展,并實現(xiàn)其文化精神超越和達(dá)致健民強(qiáng)身支撐抗戰(zhàn)的目標(biāo),對于當(dāng)代蓬勃開展社會大眾體育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和借鑒價值。
一、現(xiàn)代西方體育在我國早期的傳播和影響
現(xiàn)代西方體育在中國的傳播是兩種文化碰撞的過程,也是洋為中用的過程。鴉片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中國長期封閉的國門被打開。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商品、資本和人員的流入,體現(xiàn)西方社會文化價值內(nèi)涵的文化形式及生活方式也傳入中國,其中西方現(xiàn)代體育的傳入就頗具代表性。西方現(xiàn)代體育重技擊、面對面的競爭以及尚勝的文化氣質(zhì),完全不同于中國點到為止的傳統(tǒng)武術(shù)境界。在當(dāng)時舊中國整體封閉保守的文化氛圍中,這種基于西方文化價值觀的文化形式顯然難以被當(dāng)時的國人廣泛的接受。因而,在早期的通商口岸,隨著西方人的涌入,西方現(xiàn)代體育也以一種迥異于中國傳統(tǒng)武術(shù)的“武戲”方式展現(xiàn)在中國人面前,并對中國人的視界和精神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沖擊,但也僅限于此,并不能從根本上促動一種文化精神或文化形式的自新。因而,盡管很早就有西方現(xiàn)代體育在各通商口岸和租界中示范,但動眼而不動手就是當(dāng)時中國大眾對這種外來的“武戲”的基本反應(yīng)。
西方現(xiàn)代體育的傳播是西方文化強(qiáng)勢入侵的必然結(jié)果。一種價值觀迥異的文化形式被接受,一定出現(xiàn)在這種文化的強(qiáng)勢表現(xiàn)之后。西方現(xiàn)代體育被接受的過程誠如斯是。經(jīng)過兩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當(dāng)時的中國人逐步認(rèn)識到自身的器物不足,于是有了洋務(wù)運(yùn)動。洋務(wù)運(yùn)動思想準(zhǔn)備的不足和思想的局限性,以及現(xiàn)實層面的需要,體現(xiàn)在對于西方文明的學(xué)習(xí)必然是有選擇的。這種選擇就是重視對器物學(xué)習(xí)。西方現(xiàn)代體育最為外在和容易為人所辨識的特征就是強(qiáng)身健體功能,特別是作為西方軍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兵操,對于強(qiáng)兵具有顯著的效果,因而更是易于被接受。但是基于文化價值觀的不同,這種學(xué)習(xí)注定是一種不服氣的接受、羞澀的借鑒和不辨真假的效仿。[1]只有認(rèn)識到自身的文化不足,才能發(fā)自內(nèi)心深處地去學(xué)習(xí)和接受一種不同文化價值觀的文化形式。西方現(xiàn)代體育大規(guī)模地被學(xué)習(xí)和接受,出現(xiàn)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其時正處中國文化從自滿到自卑的轉(zhuǎn)折中。當(dāng)然,這個過程并不是一帆風(fēng)順的,期間會有對尚武、尚力的西方現(xiàn)代體育的鼓吹、推進(jìn)甚至反對。正如西方現(xiàn)代體育被廣泛引入學(xué)校教育后,仍然會出現(xiàn)一些發(fā)自文化深處的抵觸和不解。如“同文館的學(xué)生不愿意學(xué)習(xí)體育,認(rèn)為有失尊嚴(yán),他們只能慢慢度方步,中國學(xué)生是沒有粗野的游戲如足球棒球之類的”,[2]甚至其后的亦有同樣的觀測。“教者發(fā)令,學(xué)者強(qiáng)應(yīng),身順而心違,精神受無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也,蓋一體操之終,未有不貌悴神傷者也。”[3]作為不同文化價值觀的西方現(xiàn)代體育早期在中國的傳播注定是一個讓當(dāng)時的中國人感到心神俱疲的過程。
現(xiàn)代西方體育在中國的傳播,是其健身和強(qiáng)體功能與中國大眾挽救國難的現(xiàn)實需要的耦合,是西方現(xiàn)代體育在我國得以廣泛傳播的根本動力。體現(xiàn)西方文化“社會的教育”、“生活的教育”以及個體性價值的西方現(xiàn)代體育具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同的格調(diào)。這是早期西方現(xiàn)代體育被引入中國之后緩慢傳播的原因。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加深,救亡圖存成為不斷覺醒的中國人的緊迫目標(biāo)。拯救危殆的民族精神,強(qiáng)健孱弱的民族體魄,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是一種文化號召,更是一種救國路徑。這是傳播西方現(xiàn)代體育與挽救國難相結(jié)合最為根本的原因和最持久的動力。盡管存在著國民體育教育和自然主義體育教育的分野和爭論,但隨著國難的深入,發(fā)展體育、強(qiáng)健民族體魄卻是不爭的選擇。因而,在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西方現(xiàn)代體育以各種形式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得以快速發(fā)展和傳播。不僅有國民政府組織參加的奧運(yùn)會、亞運(yùn)會、遠(yuǎn)東運(yùn)動會,也有全國運(yùn)動會和各省的省運(yùn)會;不僅有政府組織的專業(yè)體育隊伍、蓬勃開展的學(xué)校體育,也有紅紅火火的大眾體育活動和多樣化的體育社團(tuán)。即使在當(dāng)時的井岡山和江西蘇區(qū)也逐步發(fā)展起了具有特殊意義和價值內(nèi)涵的紅色體育。西方現(xiàn)代體育在當(dāng)時中國熱絡(luò)的發(fā)展場面是時勢的發(fā)展需要,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家國情懷的價值擔(dān)當(dāng)在個體層面的體現(xiàn)。這已完全超越了西方現(xiàn)代體育的價值精神,是西方現(xiàn)代體育中國化的發(fā)展表現(xiàn);不是“為個人而體育,為少數(shù)人娛樂而體育,為少數(shù)人健康而體育”,[4]而是一為愛國,二是娛樂。[5]這種西方現(xiàn)代體育中國化的發(fā)展,不僅在當(dāng)時是蔚為普遍的發(fā)展方向,也是中共領(lǐng)導(dǎo)的各根據(jù)地舉辦和興辦西方現(xiàn)代體育的重要內(nèi)涵。只不過與民國其他地區(qū)的發(fā)展脈象有所不同而已。
二、現(xiàn)代西方體育在陜甘寧邊區(qū)傳播的脈象
陜甘寧邊區(qū)西方現(xiàn)代體育的發(fā)展,與同期民國其他地區(qū)體育大發(fā)展有著相似的原因,但又呈現(xiàn)著不同的發(fā)展脈象。西方現(xiàn)代體育在1930年代的大發(fā)展,是舊中國時勢的體現(xiàn),是基于這種時勢中國大眾從個體層面以西方現(xiàn)代體育形式做出的回應(yīng)。這種回應(yīng)已經(jīng)從價值層面超越了西方現(xiàn)代體育個體超越和娛樂的精神境界,而賦予了其拯救國家危難和民族振興的功能。這也意味著,西方現(xiàn)代體育所謂的游戲和個體超越的功能在當(dāng)時中國的時勢下,形成了向工具實用主義的轉(zhuǎn)化。這種轉(zhuǎn)化不僅體現(xiàn)在民國政府統(tǒng)治區(qū),也體現(xiàn)在江西蘇區(qū)、陜甘寧邊區(qū)。對于這種轉(zhuǎn)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的指示:“鍛煉身體,好打日本”。[6]不過與國統(tǒng)區(qū)發(fā)展現(xiàn)代體育相比,特別是與當(dāng)時一些大城市相比,無論是陜甘寧邊區(qū),還是江西蘇區(qū)發(fā)展西方現(xiàn)代體育的條件顯然是較為艱澀的。但就是在這樣艱澀的條件下,陜甘寧邊區(qū)卻蓬勃地開展起了西方現(xiàn)代體育,將西方現(xiàn)代體育強(qiáng)健體魄、進(jìn)而保家衛(wèi)國的功能發(fā)揮地更好,也收獲了更好的效果,充分體現(xiàn)了中共強(qiáng)大的組織能力和政治動員能力。這正是陜甘寧邊區(qū)與國統(tǒng)區(qū)發(fā)展西方現(xiàn)代體育的脈象差異。
以強(qiáng)大的輿論號召力,激發(fā)軍民進(jìn)行體育鍛煉。陜甘寧邊區(qū)是經(jīng)濟(jì)非常落后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體育鍛煉既不可能也沒有成為人們的生活習(xí)慣。隨著中央紅軍進(jìn)入陜甘寧邊區(qū),紅軍隊伍也將傳承的中央蘇區(qū)的紅色體育思想和形式逐步在邊區(qū)傳播,但邊區(qū)落后的經(jīng)濟(jì)生活和文化觀念卻始終是這些體育形式在陜甘寧邊區(qū)快速傳播和發(fā)展的瓶頸。為打破這一瓶頸,中共首先將體育鍛煉從個人層面提升到國家和民族的層面,使其和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中的家國情懷相聯(lián)系,從而實現(xiàn)個人思想瓶頸的突破。當(dāng)時具有代表性的口號就是:“鍛煉身體,好打日本”。其次,在廣泛采用各種宣傳手段和各種宣傳形式的基礎(chǔ)上,積極動員各種人員力量進(jìn)行現(xiàn)代體育的推廣和示范。其中具有代表意義的就是領(lǐng)導(dǎo)人的重視和率先垂范。著名的總司令是排球好手,同志是邊區(qū)著名的籃球運(yùn)動員。最后,將井岡山和江西中央蘇區(qū)的紅色體育實踐進(jìn)行復(fù)制和傳播。
以強(qiáng)有力的組織保障,推動軍民體育鍛煉。在一個不具備開展現(xiàn)代體育的文化保守地區(qū),發(fā)展現(xiàn)代體育必須依靠強(qiáng)有力的組織推進(jìn)。在這方面,中共具有很強(qiáng)的政策執(zhí)行力和組織動員能力。早在1937年中共就成立了“陜甘寧邊區(qū)體育運(yùn)動委員會”,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由李富春領(lǐng)導(dǎo)的“延安體育會”等組織,專門負(fù)責(zé)組織和推進(jìn)陜甘寧邊區(qū)的體育事業(yè)。為了推動群眾積極參加體育鍛煉,體育會經(jīng)常組織機(jī)關(guān)、學(xué)校、工廠、部隊進(jìn)行體育比賽,夏練游泳、冬練滑冰,春秋進(jìn)行球類比賽。每逢節(jié)假日還組織進(jìn)行“三八”、“五四”、“八一”、“九一”等不同類型的體育比賽。1942年又進(jìn)一步提倡開展“十分鐘運(yùn)動”,內(nèi)容包括多種多樣的西方現(xiàn)代體育項目。
推動體育場所的修建和開展不同層次的體育賽事。西方現(xiàn)代體育與中國傳統(tǒng)體育的重要區(qū)別在于它需要專業(yè)的體育場所和設(shè)施。為服務(wù)軍民有效開展現(xiàn)代體育鍛煉,陜甘寧邊區(qū)在財政資金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多方籌措資金推動了不同層次的體育場所和設(shè)施的建設(shè),為延安地區(qū)建設(shè)了一批最早的體育公共產(chǎn)品設(shè)施。其中比較著名的就有延安南關(guān)公共體育場、延安體育會滑冰場等大眾體育場所、抗日軍政大學(xué)體育場、中央黨校體育場等機(jī)關(guān)及學(xué)校體育場所。這些體育設(shè)施的修建極大地方便了軍民從事各項體育活動的開展,也為邊區(qū)開展各層次的體育競賽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賽場環(huán)境和條件。利用體育場所開展有規(guī)律的體育競賽是推動大眾體育最好的方式。陜甘寧邊區(qū)有規(guī)律的競賽一般有市縣級體育運(yùn)動比賽、地區(qū)級體育運(yùn)動比賽和全邊區(qū)體育比賽(包括著名的“全蘇區(qū)八一抗戰(zhàn)動員運(yùn)動大會”、“九一”擴(kuò)大運(yùn)動會)。通過這些競賽活動的開展,不僅使邊區(qū)的軍人體育活動得到廣泛開展,也吸引了延安的市民和一些社團(tuán)自發(fā)組隊參加體育競賽,促進(jìn)現(xiàn)代體育運(yùn)動從軍隊和學(xué)校向市民的擴(kuò)散和傳播。
三、現(xiàn)代西方體育在陜甘寧邊區(qū)傳播的特征
在陜甘寧邊區(qū)開展的西方現(xiàn)代體育活動,無論就其內(nèi)涵,還是價值訴求,已經(jīng)完全超越了西方現(xiàn)代體育固有的內(nèi)涵,而是被邊區(qū)軍民賦予了獨特的內(nèi)容和價值維度,呈現(xiàn)為獨特的中國化特性。陜甘寧邊區(qū)開展的西方現(xiàn)代體育運(yùn)動,不僅是新民主義革命時期紅色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發(fā)展成就最高和最具代表性的階段。西方現(xiàn)代體育在陜甘寧邊區(qū)的中國化開展,有賴于中共卓有成效的組織和傳播,呈現(xiàn)出鮮明的中國化特征。
西方現(xiàn)代體育在陜甘寧邊區(qū)傳播具有強(qiáng)烈的實用主義特征。陜甘寧邊區(qū)開展西方現(xiàn)代體育活動有兩個顯著的功能訴求。一是通過開展現(xiàn)代體育活動能夠增強(qiáng)軍民體魄,振奮軍民精神。二是在邊區(qū)落后的生產(chǎn)力條件和困難的生活保障條件下,通過體育活動的開展,增強(qiáng)軍民的體質(zhì),確保軍民在缺醫(yī)少藥的條件下,能夠以健康的身體抵御物資匱乏和病痛的侵襲,保持強(qiáng)大的戰(zhàn)斗力。另外,通過體育競賽活動的開展,也可以鍛煉和提高軍民在艱難困苦中的堅強(qiáng)意志,始終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直至革命的成功。
強(qiáng)大的組織力。陜甘寧邊區(qū)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水平與孕育西方現(xiàn)代體育的生產(chǎn)力水平有著較大的落差,而且也是兩種不同氣質(zhì)的文化。如何在西方文化語境下發(fā)展而來的西方現(xiàn)代體育克服生產(chǎn)力發(fā)展落差和文化的差異,顯然依靠個體示范和部分社團(tuán)的力量實現(xiàn)全民參與既是不現(xiàn)實的,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早在1920年代的上海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社團(tuán)體育組織和社團(tuán)體育活動,但并沒有有效地擴(kuò)展到中國廣大的中西部地區(qū)和經(jīng)濟(jì)文化落后的地區(qū)。顯然要想實現(xiàn)全民參與并普及這些異質(zhì)文化形式,必須既要有能引起共鳴的“意識”,也要有強(qiáng)有力的組織推動。中共從其理論掌握革命群眾的實踐中,顯然有著鮮活的經(jīng)驗和系統(tǒng)的理論作指導(dǎo),那就是要建設(shè)一個強(qiáng)有力的組織為依托,使各種體育文化形式落到實處。中共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成果也如其所望。
以不同層次的體育活動和體育競賽吸引參加者和擴(kuò)大愛好者范圍。異質(zhì)文化形式的傳播要取得有效成果,必須要在文化保守主義傾向較低的群體中開展,要有顯著的成果吸引和能夠引起人本然的共鳴。中共在陜甘寧邊區(qū)開展西方現(xiàn)代體育,首先選擇在學(xué)校(包括幼兒園體育、小學(xué)體育、中學(xué)體育和大學(xué)體育)和軍隊,它們的共同特征在于有著嚴(yán)格的組織紀(jì)律性以及較高的執(zhí)行力,推動成本較低。軍隊作為軍事戰(zhàn)斗組織,其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競爭,甚至是殘酷的競爭。在軍隊中開展體育活動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一種情境模仿,有利于軍人意志品質(zhì)和斗爭策略的實踐,因而比較易于實現(xiàn)。特別是在部隊內(nèi)部、部隊之間、部隊與地區(qū)之間組織的體育賽事,更能夠以組織化的方式體現(xiàn)出這種文化形式的獨特內(nèi)涵和價值。如中共領(lǐng)導(dǎo)的八路軍120師籃球隊,就取得了在陜甘寧邊區(qū)常勝不敗的戰(zhàn)果,從而在邊區(qū)掀起了強(qiáng)勁的籃球風(fēng)。[7]
西方現(xiàn)代體育在陜甘寧邊區(qū)的成功傳播,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創(chuàng)舉。它實現(xiàn)了在異質(zhì)文化條件下的跨文化的傳播,實現(xiàn)了在生產(chǎn)力條件存在巨大落差條件下的傳播,實現(xiàn)了在簡陋的物質(zhì)條件下同樣可以開展高水平全民體育活動的目標(biāo)。這些偉大的歷史創(chuàng)舉對于今天我們有效地開展大眾化社會體育具有及其重要的借鑒價值和啟發(fā)意義。這些價值和意義包括要根據(jù)中國國情,適時適地進(jìn)行中國化改造;將其和解決社會中存在的某些矛盾相結(jié)合,并使之有效地解決這些矛盾;要深諳我們民族文化的特征,并以符合其文化心理的方式開展這些活動,從而實現(xiàn)這些文化形式能夠較快地得以推進(jìn)。
【參考文獻(xiàn)】
[1]張曉軍.近代國人對西方體育認(rèn)識的嬗變[D].吉林大學(xué)文學(xué)院博士論文,2010.74.
[2]朱有獻(xiàn)主編.中國近代學(xué)制史料(第一輯上冊)[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3.186.
[3]轉(zhuǎn)引自全國體總文史資料編審委員會.中國近代體育文選[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2.33.
[4]轉(zhuǎn)引自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主編.中國近代體育文選[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2.265.
[5]蔣志和.民族資本家創(chuàng)建體育初探[J].上海體育史話,1986.2.25.
[6][7]王增明.陜甘寧邊區(qū)體育史[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3.16-19.
作者:韋統(tǒng)義;肖群;孫枝青 單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