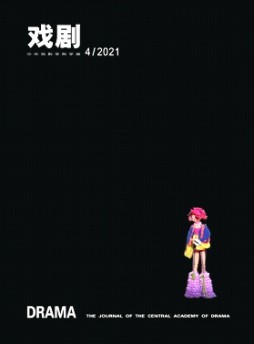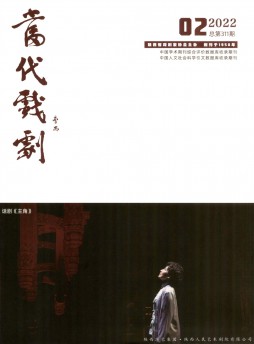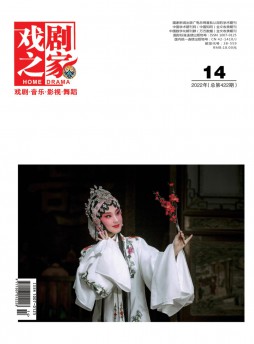晚明戲劇審美意識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晚明戲劇審美意識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陳才單位:廣東省文化館廣東廣州
明清戲曲遠承元雜劇,近受南戲啟示,隨著創作經驗的積累和戲曲理論的豐富,明清戲曲發展至晚明一變前中期的因襲模擬之弊,顯示出成熟的藝術特征,凸顯尚奇逐新的藝術風格。戲曲審美觀念的嬗變蘊含了時代的社會文化心理和文藝思潮,對后世戲曲的發展影響深遠。
一、戲曲審美觀念變化的緣由
明代程朱理學的束縛、八股取士的桎梏,造成了思想文化界保守。明中葉以后,王學左派異軍突起反對存理遏欲的說教,孕育出一個追求人格平等、呼吁個性解放、肯定私欲的文化氛圍。這種具有世俗性特征的文化思想,影響到社會風俗、社會心理、文學藝術等各個層面。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當“率性自為的人格理想和世俗享樂的精神傾向,升華為一種慕奇好異、獨抒性靈的審美精神。心學特長的內省傾向的思維方式,使人們重一己而輕外物,重冥會而輕實證,更多地追求超脫外物的束縛,滿足個人的生活情趣或主觀的精神境界。這就構成了明人崇尚新奇、標樹真情的審美精神。”[1]
伴隨著文人的慕新尚奇審美觀的形成,在文壇上也掀起一股慕新好奇的審美思潮,人們對傳統的文學觀念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逆反心理,希求掙脫奇正中和的審美規范的約束,作家在文學藝術創作中大膽地求新求奇,并總結出一套頗具體系的“新奇”觀,作為沖破傳統的守規范、嚴法律、套模式、遵典型的審美風范的手段。湯顯祖的尚奇主張,堪稱這種“新奇”觀的代表。他在《序丘毛伯稿》中說:“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士奇則心靈,心靈則能飛動,能飛動則上下天地、來去古今,可以屈伸長短生滅如意,如意則可以無所不知。”[2]
湯氏首先把文章的“新奇”歸因于文人主體的“心奇”,正是明中后期文人對慕新尚奇的人格理想的極力倡導和大膽追求,才鼓動文壇上的新奇時風。這種幕新尚奇的審美精神,在戲曲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倪倬在《二奇緣•小引》明確地宣稱:“傳奇,紀異之書也;無奇不傳,無傳不奇。”[3]
另外,明中期以來由于政治腐敗、仕途堵塞,導致文人在政壇上難以建樹,于是他們試圖構建新型文化的傳統職責便不期而然被置換為一種審美創造行為。晚明文藝新思潮,帶來了世俗性和享樂性的文化氛圍,文人士大夫在著書立說閑暇之余,將個人情致寄托于傳奇這種新型文體,于是豢養家班、蓄養家樂成為當時風尚,據清冒襄《同人集》卷九《王昔行跋》記載崇禎十五年(1642年)中秋冒襄、李雯、陳梁等復社、幾社文人在秦淮河畔聚會,召阮大鋮家班前來演戲,僅戲酬就是白金一斤,即銀十六兩,可窺阮氏家樂受歡迎程度。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情景中,劇壇上熔鑄著文人審美精神、滲透著文人審美情趣的傳奇,便逐漸取代了質樸的北雜劇和南戲,據傅惜華《明代傳奇總目》統計,僅明代有姓名可考的傳奇作家就有三百五十多人,他們創作了六百十八種傳奇,文人創作戲曲已成為燎原之勢,并以一種游戲社會、調侃人生的態度對待創作,力求情節翻新出奇,至此,戲曲創作中慣用偶然事件,如意外的巧遇、信物的巧拾來加深情節的奇異色彩。
二、戲曲尚“奇”審美趣味的藝術表現手法
明中晚以來,隨著劇論家對戲曲本質特征的認識,劇作家開始苦心經營戲曲結構,一改以往傳奇作家疏于結構的習氣,將結構的完整性和情節的生動性提到議程上來,以濃厚的文人審美趣味構置戲曲的敘事結構。明清劇作家常用錯認、誤會模式,信物模式,或兼用幾種敘事模式來設置故事情境,達到“奇”的審美目的,使故事情節的發展跌宕多姿,戲劇性迭出。
(一)巧合誤會敘事模式明晚期劇作家打破了曲本位的藩籬,重視結構等敘事技巧,在尚奇之風影響下,更多的審美趣味與戲劇化的要求漸相適應。根據戲曲體裁對舞臺性、敘事時間的要求,劇作家常利用巧合誤會等偶然性因素,創設生動的戲劇情境。巧合誤會可以將劇中人物置于偶然性事件中,使人物的內在性格表現出來,與外在行動形成矛盾對立,產生喜劇效果,喜劇人物的自我暴露和人物之間的互相揭露。人物言行不一、自相矛盾是喜劇人物自我暴露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如《綠牡丹》中,謝英到車尚公家,見門口無人,便進去找這家的大官人車尚公。車忽聽堂上有人,便在隔壁朝外偷看,見是謝英,不愿理睬。謝問“大官人可在家?”車捏著鼻子在里面說:“不在家”。《贗售》一折,沈重老先生把胸無點墨的柳希潛請人代做的詩誤認作柳的佳作,贊不絕口的說:“柳兄,你這樣的好文字,何處得來?”柳五愚蠢至極,聽不出這是贊賞的話,加之做賊心虛,誤以為沈先生已識破這首詩是冒牌貨,連忙辯解說:“其實是門生親自做的。”答非所問,令人忍俊不禁。沈老先生再次贊嘆道:“想別有神功,倩作天然巧?”柳五柳則更感局促不安,誤以為沈老先生已點破他作弊,連忙說:“門生并無倩作之弊,憑老師細訪!”這種互相誤會產生了強烈的喜劇效果,引起哄堂大笑。再如阮大鋮的《春燈謎》,《春燈謎》的幽默藝術是由陰差陽錯而造成的,由于十次錯認而鬧出了眾多的笑話。阮氏在《春燈謎自序》中稱“所以娛親而戲為之也”,“娛”之作用正在逗人發笑。劇中宇文彥和韋影娘來到黃陵廟中觀燈。突然下起春雨,吹起大風,觀燈的人群都飛快地往家里跑,于是就把宇文彥、韋影娘、春櫻沖散了。宇文彥喝了酒,便錯上了船,鉆進韋影娘的艙內和衣而睡;接著春櫻回來了,進了船艙,錯認為小姐,就轉入別艙睡覺去了。韋影娘是千金小姐,走得慢,歸船晚,也帶有幾分酒意,在黑夜中模模糊糊地誤上了宇文彥的船,也進入艙只能夠睡覺去了。當宇文彥醒來之后,發現不是自己的船艙,突然意識到,昨晚錯上了樞密使的船,心中害怕起來,馬上出艙逃跑。此時,心生一計,用桌上的粉黛抹成一個花臉,怕的是人們認出了真面目。等到逃出船艙,鉆進岸上的花樹叢中,洗了臉,欲回到自己的船上,卻被軍官捉住了。韋初平出來審問,宇文彥否認是賊。韋反駁到,既不是賊何以打花了臉。宇文彥無言以對,情急之下,為了不連累父親的官職,編造一個假名西川秀才于俊。韋初評恰好管理西川,手中持有秀才名冊,并未見于俊此名,于是就斷定他是盜賊,在背上批明賊名于俊,投入長江。宇文彥誤上官船,被判為盜賊,不免讓人同情傷心,但這一悲劇又是自己無意中一手造成的,自己打了花臉,把自己弄成賊樣,又捏造自己是成都秀才,恰撞著韋初平手里有西川秀才名冊,總之,宇文彥每一次行動都是在作繭自縛,打碎了黃連自己吞,有苦難言,觀眾在這啼笑皆非的劇中領會著一種特殊的苦笑幽默。
晚明傳奇大多取材于現實生活中普通的人、尋常的事,要想達到吸引人的目的,晚明傳奇作家在編排上苦下功夫,樂此不疲地采用巧合誤會手法來結撰故事,使劇情一波三折,使尋常的故事生發喜劇情調。讓劇中人物通過錯誤的判斷和事實真相產生矛盾,來造成戲劇沖突。觀眾在欣賞表演時,體察到劇中人物由于巧合而導致的與事實不一致的行動,由此爆發笑料,也使的全劇自始至終都洋溢著濃郁的喜劇氣氛。
(二)道具敘事模式
古典戲曲常以“砌末”來統稱舞臺表演時所使用的器物,即現在的道具。晚明戲曲家慣用一件極為平常普通的小物件翻新出奇,使得劇情出神人化,變幻無窮。晚明戲曲審美色彩的變化亦來源于道具的使用。如王元壽的《異夢記》中敘金陵秀才王奇俊體貌清俊,富有文章,欲往京城趕考,與園主顧促瑛之女顧云容在夢中離魂,互贈信物,云容以紫金碧甸贈王,王以水晶雙魚佩送云容。然而,信物又給王帶來的災難,劇敘李昌言交給他三封信,讓一一拜訪信中之人。誰知到了京城,卻未能蒙面。后又聞知科舉被取消,一氣之下將李昌言給他書信取出撕毀。王取信時不慎將紫金碧甸環失落,恰被張曳白看見,暗暗拾起。張又弄到李昌言給范夫人的信。張還從王的談話中知道了夢中的題詩及紫金碧甸環事。次日一早,乘王在睡中離店而去,冒名王欲騙云容,云容發現不是夢中情人,偷稅自盡。后兩人歷經坎坷,憑信物得以團圓。可見信物成為本劇結構情節的關鍵線索,它使男女主角相愛、遇害、重逢等,極盡變幻之能事。再如范文若的《花筵賺》以紈扇與題詩配合運用,劇寫碧玉見溫嶠年老色黑多須,溫好友謝鯤貌美,碧玉遂有意于謝鯤。清明時節,碧玉在樓偷賞春,春心蕩漾。
謝鯤潛入門內,躲在暗中窺視,被芳姿發現,芳姿誤認為謝鯤是溫嶠,便告訴了碧玉。而碧玉思戀溫嶠的心情更加迫切。一日碧玉寄扇傳,恰被溫嶠拾得,后謝鯤來訪戲竊紈扇,誦扇上詩,芳姿假扮碧玉,以為與溫嶠相戲,留情于謝鯤。碧玉姑母托溫嶠為女選婿,溫嶠假意為謝鯤作媒,自作新郎與碧玉成婚。劇中詩扇道具的使用,不僅將溫嶠與碧玉、謝鯤與芳姿主副兩條線索粘合,巧妙地實現了戲曲雙線結構模式,且詩扇在劇中的再三出現,猶如一根紅繩貫穿全劇始末,將劇情跌宕逆折,如詩扇被溫嶠拾得,打破了碧玉對謝鯤愛戀;謝鯤竊扇,破壞了芳姿與溫嶠、謝鯤與碧玉的愛戀,可謂一扇起三波,使得平淡見奇,懸念疊出。以信物為敘事模式取得登峰造極的藝術效果則莫屬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劇中從扇墜拋樓、題詩定情、血濺詩扇、以扇代書到裂扇擲地,串聯整個劇情,不斷推動情節曲折向前發展,達到“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母的。
據孫書磊《論明清之際戲曲敘述的類型化》研究,在現存的明清之際的劇作中,明確使用道具的劇作有89種,占現存劇作總數的26.3%,可見,晚明戲曲家比較多地利用道具來結構情節、串聯人物,并由道具的易遺生發種種枝節,引起戲劇沖突,打破原有事理發展進程,令故事生奇,懸念迭生。
三、尚“奇”審美觀念變化對戲曲發展的影響
審美觀念地潛移帶來了藝術創作手法的變遷,勢必將對戲曲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縱觀戲曲史,晚明戲曲突破了雜劇、南戲的創作藩籬,構建更為復雜的情節結構,在戲曲理論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一便是劇作家將目光集中在戲曲的敘事性和舞臺性特點。為了達到尚奇的創作目的,晚明戲曲家常借助誤會巧合模式、道具信物模式等,便于安排故事情節,嚴謹戲曲結構,克服了宋元南戲以來一生一旦的單純敘事結構,開始構建復雜結構的雙線敘事模式,劇作家利用巧合手法將并列的兩條敘事線索交叉、重疊,構筑曲折跌宕的情節。如沈璟的《紅蕖記》使用了兩種敘事模式。
講述了鄭德麟、韋楚云和崔希周、曾麗玉兩對情侶間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劇中通過兩次巧合性的相遇使兩二生二旦敘事線索交叉連接。一是有長沙鹽商韋淡成者,與老妻與女楚云乘船赴湘潭。途中,遇巴陵鹽商曾友直,攜妻與女麗玉亦乘船去湘潭。二船并行,楚云與麗玉拜為姐妹,因系順風,任船漂泊。二是鄭德璘于表兄家,多方提親,終無所成,準備返里。行至中途,遇風浪下船,至龍王廟,恰遇韋、曾二家亦來祈拜。正因第一相遇,楚云采得紅蕖,麗玉題詩,崔希周方才拾得紅蕖,求愛于麗玉。第二次巧遇,鄭德璘才得以結識韋楚云,產生一段感情。傳奇發展至明清之際,劇作家在兩組“生旦離合”的線索基礎上,進一步追求作品的布局精巧、結構巧妙。副線形式是他們最常用、最常見的形式,注重突出主線的地位,確保主人公活動為中心的主線清晰,副線穿插于主線之間,使劇情更富立體,敘事思路更為清晰。如王異《弄珠樓》中主線敘阮翰與柳椏枝的姻緣故事,中間穿插副線敘阮翰與柳枝的來往。劇中阮翰巧拾曠霏煙的詩帕而生愛慕之情,阮翰姑丈家有婢女柳枝因偶得阮翰所續詩箋,也萌生仰慕之情。恰巧阮翰姑丈曾想曠士借過千金,柳枝作為抵債,便入園與霏煙為伴。正因為柳枝的這次入園,將阮翰與霏煙、阮翰與柳枝兩條情節線索連接交叉起來。
巧合誤會模式、道具模式對于雙線結構型劇本的特殊意義在于,巧合更靈活地處理雙線結構中兩條線索的離合關系,解決雙線結構的功能缺陷,同時也能在保證劇本起承轉合緩慢均勻發展的基礎上,設下伏筆照應,在平行兩線間建立緊密的聯系,使雙線結構更細致精巧。
明中后期定型的傳奇劇本,通例篇幅在30—50出之間,形成形成“戲之好者必長”的普遍現象,如果演出全本戲,則觀眾必須具備充裕的時間。如《金瓶梅》第六十四回描寫西門慶有一次演出《玉環記》,頭晚演到三更天氣,又將《玉環記》“‘做不完的折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眾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明清傳奇過分追奇求怪,排場熱鬧,并且故意在情節上橫生許多枝節,加上體制的龐大,繁冗的缺點十分明顯,部分作品只適合案頭閱讀,無法搬演場上。于是,劇本創作與舞臺演出之間便出現了尖銳的矛盾。因此,傳奇作家首選“省略”敘事時間來講述故事始末。如何取舍“敘事時間”,成為劇作家必然要考慮的問題,正如李漁所說,要將筆墨放在主要人物和事件上,省略次要人物和事件,由于描寫的輕重不同,劇作中每條敘事線索的敘事時間長短不同,必然會造成敘事的不連貫,而誤會巧合模式、道具模式則以偶然性,體現著生活的必然性原則,滲透著觀眾對現象本質的理解,可以做到故事時間合理的省略,加快“敘事節奏”。如《燕子箋》演述唐代扶風秀士霍都梁與曲江妓女華行云、宦家女子酈飛云曲折離奇的婚姻故事。作者在安排霍生于飛云相識時,巧妙的設置了【拾箋】一出,用飛燕銜曲飛云詩箋,落在霍生面前。按照傳奇風情作品男女主人公相遇的程式化寫作,一般則會安排旦角一次游玩,不慎遺失隨身私物,而生則因游學或是趕考,于途中經過巧拾信物,而萌生相思之情,經過一番苦苦追尋,而得以蒙面,于是生旦遂生情事。如此套路,則勢必延長故事時間,而生旦相識于情節來講為次要內容,如果對此次要情節亦詳加贅述,則勢必增加傳奇篇幅。在《燕子箋》里,作者僅用一出來省略二人相識過程的故事時間,將劇情直接導入主要情節,即霍生與飛云的曲折戀情。
晚明戲曲家十分注意對敘事時間的省略,使時間的表現既以貫串的運動態勢維系劇情的向前發展,同時又在整個時間鏈上運用誤會巧合、道具等敘事模式,將敘事時間進程中次要事件發展所需時間縮短或是省略,體現出局部的活躍性,加快敘事節奏,使劇作家能集中筆墨與主要人物、情節的刻畫和描寫,省略次要情節,如此,有利于傳奇體制“縮長為短”的實現。
四、結語
晚明以來,除當時進步文藝思潮、社會經濟的繁榮等影響因素外,尚奇逐新的審美觀念所帶來的新的藝術表現手法,促進了古典戲曲的文學性與舞臺性相結合,使得戲曲真正做到了可觀可演,從根本上繁榮了演劇市場。從宮廷到民間,從士大夫到老百姓,奢樂之風漸漸流行開來,形成舉國若狂的晚明劇壇,戲曲成為大眾化的娛樂方式之一,據明范濂《云間據目抄》卷二《記風俗》[4]中記錄了萬歷年間,吳地松江一帶的廟會演劇光演員戲服、道具一項每日花費千金,可見民間演劇如火如荼之勢。戲曲演出成了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娛樂方式,據張岱《虎丘中秋夜》[5]的描述,“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孌童及游冶惡少、清客幫閑、傒僮走空之輩無不鱗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鵝澗、劍池、申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氈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可觀明晚期蘇州的虎丘演唱大會,是一種具有極大的廣泛性、然而又包含不同審美層次的群眾性戲曲活動,從蘇州一帶的戲劇演出的繁盛可窺見全國戲劇活動的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