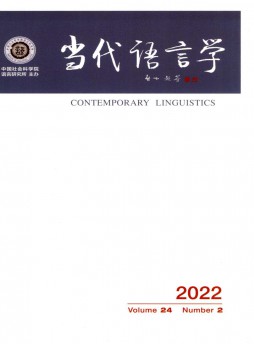語言學(xué)下漢譯佛典四言文體的形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語言學(xué)下漢譯佛典四言文體的形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漢文佛典中大量運(yùn)用的四字格形式一直以來都是一個(gè)值得探討的語言現(xiàn)象。本文嘗試從認(rèn)知語言學(xué)的角度,初步探究佛典中四言文體的形成原因。
[關(guān)鍵詞]
在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語言往往是最直接的施加影響者,也是最深刻的被影響者。佛教的傳入是中國歷史上持續(xù)時(shí)間最久、范圍最廣、影響最深的一場文化交流活動。佛教作為一種不同質(zhì)素的語言和文化系統(tǒng),在近兩千年的歷史中,經(jīng)歷了試探、依附、沖突、改變、適應(yīng)、融合種種階段,已經(jīng)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gè)階層和領(lǐng)域。自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安世高譯出《明度五十校計(jì)經(jīng)》始,直至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佛經(jīng)譯場停頓,其間八百八十六年是佛典的翻譯時(shí)代。這一場近千年的文化交流活動給后世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漢文佛教文獻(xiàn)。佛教文獻(xiàn)是一種既有別于書面語,又不同于口語的特殊文體,顯著特征之一就是四字格的大量運(yùn)用。朱慶之先生在博士論文《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匯研究》中指出,漢文佛典“刻意講求節(jié)律。通常是四字為一頓,組成一個(gè)大節(jié)拍,其間或與邏輯停頓不一致;每個(gè)大節(jié)拍又以二字為一個(gè)小節(jié)”。俞理明先生(1993)認(rèn)為,漢靈帝時(shí)支曜翻譯的《成具光明定意經(jīng)》最早開始大量使用四言文體,經(jīng)文中四言句與雜言句交替使用;而在東漢康孟詳譯經(jīng)中,通篇以四字句為主。根據(jù)顏洽茂先生的研究,六朝譯經(jīng)中四字句是最常見的句式。隋唐以后,經(jīng)文中已經(jīng)很少出現(xiàn)四字格之外的文體了。漢語是一種人文性極強(qiáng)的語言,四字格這種獨(dú)特的語言構(gòu)成格式,負(fù)載了許多語言層面以上的文化信息和內(nèi)涵,本文試圖從認(rèn)知語言學(xué)的視角,探討梵漢對譯中出現(xiàn)的大量四字格詞語和四言文體形成的內(nèi)在動因。
一、四字格符合語言的精確性和經(jīng)濟(jì)性原則,有利于佛教教義的傳播
從佛經(jīng)翻譯的根本目的出發(fā),漢譯佛經(jīng)必須同時(shí)滿足精確性和經(jīng)濟(jì)性兩點(diǎn)要求。由于佛經(jīng)是以傳達(dá)宗教教義為宗旨,字面上的謬誤和偏差很有可能導(dǎo)致意義上的分歧和謬誤。對于《圣經(jīng)》流傳的不同版本的信奉導(dǎo)致了眾多教派數(shù)百年的分歧和斗爭,可見以宗教原典不可動搖的權(quán)威性、豐富的內(nèi)涵性和可解讀性,“一字之差”產(chǎn)生的蝴蝶效應(yīng)是不可估量的。《荀子•正名篇》有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佛經(jīng)漢譯的過程伴隨著漢語從單音化發(fā)展到雙音化的過程,這一方面是大量口語進(jìn)入書面語導(dǎo)致的必然結(jié)果,另一方面也是詞語為了適應(yīng)表達(dá)信息量增加的需要。為了使詞義更加精確、明白,漢語選擇了詞的自身內(nèi)部自我注釋的方法,排除了雙音詞或單音詞的多義性。漢語詞匯雙音節(jié)化是產(chǎn)生四字格結(jié)構(gòu)必不可少的內(nèi)部條件。在此之前,漢語基本上是通過雙聲疊韻的語音手段產(chǎn)生新詞,但是語音構(gòu)詞的手段局限性比較大,而由雙音化引起的漢語構(gòu)詞手段的增加為四字格的發(fā)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由于雙音化大大增強(qiáng)了漢語詞匯表意的精確性和豐富的內(nèi)涵型,在佛經(jīng)翻譯的過程中被大量采用。
經(jīng)濟(jì)性原則是語言的一個(gè)重要特征。語言的經(jīng)濟(jì)性原則最早由法國語言學(xué)家Martinet提出,指的是:在表意明晰的前提下,為了提高語言的交際效率,盡可能采用經(jīng)濟(jì)簡潔的語言符號形式。(徐下考等,2008)語言使用中的經(jīng)濟(jì)性原則是所有語言使用的本質(zhì)需求。這種需求在佛經(jīng)原典被譯為漢語時(shí)顯得尤為重要和突出。佛典被翻譯成漢語的最終作用是宣揚(yáng)教義、教化民眾,使佛教在中國得以傳播和流傳。在知識分子集中在社會上層、普通大眾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前提下,佛經(jīng)文體必須便于誦讀和記憶,才能廣泛流傳。從心理學(xué)和認(rèn)知語言學(xué)的角度來說,四字格是一種非常符合人腦認(rèn)知記憶的語言結(jié)構(gòu)。心理學(xué)家研究發(fā)現(xiàn),人腦處理或記憶信息是以組塊為單位的。組塊可大可小,都是作為一個(gè)單位被處理和記憶的。人腦的記憶的第二層次即短時(shí)忘記,其信息處理區(qū)的容量一般為5個(gè)組塊,超過5個(gè),會給信息處理帶來困難①。“四字格”結(jié)構(gòu)正好適應(yīng)人腦認(rèn)知心理上的特點(diǎn)。因?yàn)榫渥犹L會超出人們的記憶,太短則無法準(zhǔn)確完整地表達(dá)出應(yīng)有的含義。“對于固定語來說,四字格的長度很適中,既不至于形成長串的音節(jié)而使人發(fā)音不暢便,同時(shí)又是可表示豐滿、復(fù)雜的意思和明晰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劉叔新,1990)這一現(xiàn)象在與漢語同屬漢藏語系、并且同樣深受佛教及其語言影響的藏語中可以得到印證。“藏語的四字格音節(jié)整齊、語調(diào)鏗鏘、組織嚴(yán)密、結(jié)構(gòu)對稱、表意巧妙、形象生動、言簡意賅、感染力強(qiáng)、能產(chǎn)性大”,“在早期作品中這種四字格出現(xiàn)得較少,但在十三、十四世紀(jì)以后的文學(xué)作品中,特別是在卷帙浩繁的偉大史詩《格薩爾王傳》中就用得多了”②。我們知道,十一世紀(jì)前后,佛教在西藏地區(qū)復(fù)興,藏族僧侶開始搜集、整理、編纂之前,《格薩爾王傳》都是以游吟歌手口口相傳、世代傳唱的方式流傳的。除此之外,吳海勇在《漢譯佛經(jīng)四字文體成因芻議》③一文中考查得出結(jié)論,佛經(jīng)四字文體形成的關(guān)鍵是受佛經(jīng)原典首盧偈的影響。文中認(rèn)為,出于忠實(shí)原典的原則,譯經(jīng)者極有可能用對等的漢字字?jǐn)?shù)翻譯梵文音節(jié)數(shù),因此是梵文原典中四音節(jié)一頓的行文特征促使了漢譯佛經(jīng)中大量四字文體的形成。書寫梵本佛典的語言是多音節(jié)文字,但是為了便于記憶、唱誦仍采用四音節(jié)一頓的停頓形式,那么作為單音節(jié)文字的漢字就更容易做到這一點(diǎn)。藏語和梵語中的這種現(xiàn)象,也證明了四字格符合語言經(jīng)濟(jì)性原則和認(rèn)知結(jié)構(gòu)的特點(diǎn)。在這一目的促使下,這種經(jīng)濟(jì)性原則在漢譯佛經(jīng)中對于句法規(guī)則的制約力極強(qiáng),甚至使一般的句法規(guī)則都為之讓步。因此,在佛典漢譯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既非散文,又非韻文,或者說散韻結(jié)合的新文體,朱慶之先生稱其為“混合漢語”。顏洽茂先生(1997)認(rèn)為,漢譯佛典采用四字格這種整齊劃一的文體,固然促成了誦讀的便利,增強(qiáng)了宣傳的效果,但同時(shí)也帶來了迥異于世俗文獻(xiàn)的語言面貌。具體包括:其一,語詞的割裂與省縮;其二,語詞的增擴(kuò)與添加;其三,外語詞的大量引進(jìn)與初步整飭。④
二、中華民族以偶為美、追求韻律和對稱的審美取向造成了佛典漢譯中語言選擇的偏好
心理學(xué)中的格式塔心理學(xué)明確地指出了對于對稱事物的認(rèn)知的傾向性和能動性。格式塔心理學(xué)研究人的模式識別,提出了幾條模式識別的格式塔原則,其中有一條叫作對稱性原則。這條原則認(rèn)為人們在模式識別中有個(gè)明顯的傾向———對稱的模式是個(gè)“好”模式,這種傾向可以影響人對模式的識別。⑤漢語是一種音樂性強(qiáng)的語言,要求音節(jié)平穩(wěn)、節(jié)奏和諧、結(jié)構(gòu)對稱是漢語的詩性內(nèi)核。四字格的語音,是漢語固定語最常見的語音形式,甚至可以說是固定語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語音形式。呂叔湘先生說“:四音好像一直都是漢語使用者非常愛好的語音段落,最早的詩集《詩經(jīng)》里詩以四音為主,啟蒙課本《千字文》、《百家姓》、《李氏蒙求》、《龍文鞭影》等等都是四音。亭臺樓閣常有四個(gè)字橫額,流傳最廣的成語也是四言為多。”在漢語中,三音節(jié)的結(jié)構(gòu)是不穩(wěn)定的結(jié)構(gòu),而四音節(jié)從形式上看是對稱的,這種對稱意味著平衡。所謂“偶語易安,奇字難適”,正是因?yàn)樗淖指窠o人以整齊、勻稱和穩(wěn)定的感覺。呂叔湘先生指出,“四音節(jié)好像一直都是漢語使用者非常愛好的語音段落形式,2+2的四音節(jié)是現(xiàn)代漢語里的一種重要的節(jié)奏傾向”。從歷時(shí)方面看,早在周代就形成的四言詩歌在文學(xué)領(lǐng)域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長達(dá)一千余年,對于四言文體的偏好已經(jīng)滲入到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從共時(shí)方面看,從東漢至魏晉,既是佛經(jīng)翻譯逐步走向繁榮的時(shí)期,也是中國文人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對于“駢四儷六”的形式美的追求達(dá)到巔峰的時(shí)期。而且,佛教存在著追求對稱和諧之美的哲學(xué)。對于對稱的認(rèn)知心理基礎(chǔ),以及對漢語、漢文化及佛教文化系統(tǒng)本身的認(rèn)知,使佛經(jīng)的譯者在語言選擇過程中表現(xiàn)出語言選擇的偏好。
三、四字格具有極強(qiáng)的模因性和造詞能力,在佛典漢譯的工作中能發(fā)揮極強(qiáng)的能產(chǎn)作用
模因論(Memetics)是近年來引入國內(nèi)的解釋文化進(jìn)化、語言發(fā)展的新理論,它是基于達(dá)爾文的進(jìn)化論思想發(fā)展而來的。該理論最核心的術(shù)語是模因(meme)。該術(shù)語最早出現(xiàn)于英國生物學(xué)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出版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1976)中,其含義是指“在諸多的語言、觀念、信仰、行為方式等的傳遞過程中與基因在生物進(jìn)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的那個(gè)東西”。也就是說,模因可以成為生物基因之外的又一復(fù)制因子,是一種“文化傳播單位”。它像基因那樣得到繼承,像病毒那樣傳播,可以更好地解釋文化進(jìn)化現(xiàn)象,為人類進(jìn)一步解釋文化進(jìn)化規(guī)律引入了一個(gè)新的概念,提供了一個(gè)新的思路。語言在社會交際中也是不斷地被使用者進(jìn)行模仿、復(fù)制和傳播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可以認(rèn)為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模因。事實(shí)上,語言作為一種模因,之所以能夠流傳至今與歷代語言使用者的不斷模仿、復(fù)制與傳播是分不開的。根據(jù)語用功能,模因分為強(qiáng)勢模因與弱勢模因。強(qiáng)勢模因指那些生命力強(qiáng)、被廣泛復(fù)制并在一定時(shí)期內(nèi)得以持續(xù)傳播的模因。強(qiáng)勢模因在物種文化進(jìn)化過程中發(fā)揮著積極的作用,其復(fù)制力、傳播性強(qiáng)。而那些隨著時(shí)間與環(huán)境的發(fā)展變化,不再活躍、逐漸為人淡忘、遺忘乃至消失的模因被稱為弱勢模因。四字格和四言文體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強(qiáng)勢模因的語言表達(dá)形式。這表現(xiàn)為兩個(gè)方面:第一是構(gòu)詞方式上的強(qiáng)勢模因。受語言的經(jīng)濟(jì)性原則制約,詞匯是不可能無限增加的。任何一種語言都不可能為每種新事物造出一個(gè)對應(yīng)的新詞。佛典在被翻譯成漢語的過程中,引入了許多中華文明的文化系統(tǒng)中從未有過的全新概念,大大豐富和發(fā)展了漢語構(gòu)詞法。而古漢語中四字格的構(gòu)詞方式除了常見的構(gòu)詞法,最多的就是概括寓言、故事和節(jié)縮、擴(kuò)展古書詞句⑥。這兩種構(gòu)詞方式都適應(yīng)了佛典漢譯的需要。孫艷在《佛經(jīng)翻譯與漢語四字格的發(fā)展》一文中總結(jié)了佛教成語的三種主要類型:凝練故事、概括教義和運(yùn)用比喻。在朱瑞文編寫的佛教成語中收錄的478個(gè)成語中,四字格成語有412個(gè)⑦,可見四字格構(gòu)詞方式在佛典漢譯這一方面的能產(chǎn)力之強(qiáng)。在大量引入外來概念的翻譯工作中,能產(chǎn)力更強(qiáng)的構(gòu)詞方式就會被更加普遍使用。由于佛教文獻(xiàn)的口語化和通俗化特性,使這一部分詞語具有更廣泛的傳播力和生命力。第二是文體上的強(qiáng)勢模因。大乘佛教的經(jīng)典常常以“evamayārutam”開篇,意為“我曾經(jīng)這樣聽說”。eva意為“如此、這樣”;mayā意為“我”,是全句的主語;rutam意為“聽到”,是句中的謂語。在西晉以前,這句梵語經(jīng)文幾乎都被譯為“聞如是”,只有個(gè)別西晉譯經(jīng)用了“如是我聞”。在東晉齊梁間的漢譯佛經(jīng)中,有的被譯為“聞如是”,也有譯為“我聞如是”或“如是我聞”的。隋唐以后,“如是我聞”已經(jīng)固定成為佛經(jīng)的開頭,后常接“一時(shí)佛在某處”。佛經(jīng)原典的文體、敘述方式、描法大部分是類似的,對應(yīng)的,經(jīng)過翻譯的漢文佛典也極有可能以某一種文體為典范,而產(chǎn)生大量模仿和復(fù)制的模因。四字格既能適應(yīng)人類的認(rèn)知系統(tǒng),又能滿足佛經(jīng)傳播的需要和受眾的審美情趣,被廣泛使用。
【注釋】
①《中國大百科全書•心理學(xué)》卷《普通心理學(xué)》單行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第l版.②胡書津.藏語并列四字格結(jié)構(gòu)初探[J].西藏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1989(4).③《青海社會科學(xué)》1999年第4期。④顏洽茂.佛經(jīng)語言闡釋[M].杭州大學(xué)出版社,1997.⑤于廣元.對偶的認(rèn)知解釋[J].揚(yáng)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4(9).⑥李索.古漢語“四字格”與語音修辭[J].邏輯與語言學(xué)習(xí),1994(3).⑦孫艷.佛經(jīng)翻譯與漢語四字格的發(fā)展[J].中央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5(1).
【參考文獻(xiàn)】
[1]顏洽茂.佛經(jīng)語言闡釋[M].杭州大學(xué)出版社,1997.[2]吳海勇.漢譯佛經(jīng)四字文體成因芻議[J].青海社會科學(xué),1999(4).[3]王繼紅.玄奘譯經(jīng)四言文體的構(gòu)成方法———以《阿毗達(dá)摩俱舍論》梵漢對勘為例[J].中國文化研究,2006(2).[4]李少虹.現(xiàn)代漢語并列四字格及其習(xí)得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xué),2009.[5]許杰然.漢譯佛典對漢語詞匯影響初探[J].甘肅高師學(xué)報(bào).2012(3).
作者:馬云鷺 單位:浙江大學(xué) 人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