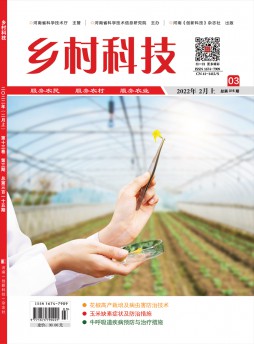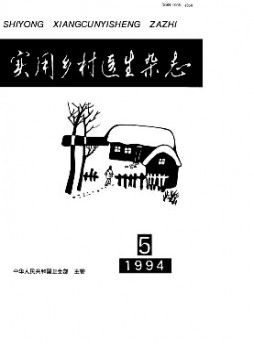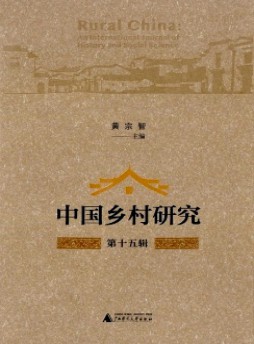鄉(xiāng)村宗教文化遺產保護策略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鄉(xiāng)村宗教文化遺產保護策略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我國的鄉(xiāng)村宗教文化遺產不僅數量大、分布廣泛,而且由于受社會變遷與城鎮(zhèn)建設的影響較小等原因,大多保留著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但另一方面,對這些文化遺產的保護程度較差、價值挖掘不夠深入等問題也十分突出。湖北省黃袍山蘭若寺便是我國鄉(xiāng)村宗教文化遺產的典型代表之一,本文運用歷史法與SWOT分析法,對這座鄉(xiāng)村小廟進行深入的探究與分析,進而嘗試對黃袍山蘭若寺的保護與發(fā)展提出針對性的策略,將對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鄉(xiāng)村宗教文化遺產保護范式有所裨益。
【關鍵詞】宗教文化遺產;鄉(xiāng)村小廟;黃袍山蘭若寺
2005年12月22日,國務院發(fā)出《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把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文化遺產整體進行保護的首個文件,明確提出了構建科學有效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的指導思想以及“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基本方針。[1]我國文化遺產中的宗教文化遺產具有的民族性、時代性和地域性尤為突出,使對宗教文化遺產的保護方法呈現多樣化、復雜化的趨勢,其中對鄉(xiāng)村地區(qū)的宗教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僅是宗教文化遺產保護的重點,更可以作為宗教文化遺產保護的典型。我國鄉(xiāng)村的宗教文化遺產不僅數量大、分布廣泛,而且由于受社會變遷與城鎮(zhèn)建設的影響較小等原因,大多都保留著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但另一方面,對其保護程度較差、價值挖掘不夠深入等問題也十分突出。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多次就堅定文化自信、保護文化遺產發(fā)表重要論述,他指出:“我們講要堅定文化自信,不能只掛在口頭上,而要落實到行動上。歷史文化遺產是祖先留給我們的,我們一定要完整交給后人”,“要保護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要保護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2]為我們保護與傳承好宗教文化遺產提供了依據、指明了方向。因此,對鄉(xiāng)村宗教文化遺產進行科學有效的保護既是對現實問題的解決,更是對歷史文化的傳承。本文選取湖北省黃袍山蘭若寺為研究對象,擬對該問題進行探討。
一、黃袍山蘭若寺概述
(一)黃袍山的自然與人文環(huán)境
蘭若寺(亦稱來佛寺)位于黃袍山望湖村高山湖西南,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與人文環(huán)境。就自然環(huán)境而言,黃袍山地處幕阜山脈中段,又名盤古大山、大盤山、仙圣山。《通城縣志》云:“黃袍山,俗呼黃茅山,幽泉怪石。舊傳有仙曬黃袍于此。”[3]《讀史方輿紀要》第76卷也有記載:“大盤山,(通城)縣東四十里。山嶺縈紆廣遠,因名。”[4]黃袍山是湖北十大名山之一、湖北省生態(tài)自然保護區(qū),主峰華羅寨海拔約1200多米,地形陡峭,風景秀麗。就人文環(huán)境而言,黃袍山處于湘、鄂、贛三省的交界處,地理位置優(yōu)越,古今名人輩出,人文古跡眾多。漢代,張良退隱于此,今黃袍山仍留存著其創(chuàng)辦的“伐桂書院”、古道觀等遺跡;唐初,黃袍山有父子兩侍郎金同慶、金興政,現存有幕阜書院、防御古監(jiān)樓、夜窩臺等遺跡;唐朝后期有地方鄉(xiāng)紳張十萬在華羅寨開山立寨,現存古兵寨遺址;北宋時期,方氏家族一門三尚書,現存方瓊紀念館、方瓊墓地,另還有黃庭堅退隱黃袍山的“魯直第”等;明朝有進士汪潤田故居與劉塘湖故居;現代以來,更有元帥早期革命紀念館(通城縣蘇維埃政府舊址)、湘鄂贛黃袍山革命烈士陵園、英雄母親黃菊媽陵園等紅色人文景觀。此外,黃袍山佛道淵源深厚,不僅有蘭若寺、福龍寺、白玉寺、普救寺、南臺寺等佛教寺廟,還有良山道觀、八仙道觀、吳芮祈天臺遺址等道教遺址。
(二)蘭若寺概況
廣泛查閱現存各縣志,僅清同治五年(1866)《通城縣志》第十九卷“廟宇”所載“巽宮汪坊圖”[3]對蘭若寺的所在方位作了簡單的記述。該縣志卷首的《圖考》[3]將通城縣疆域按照八卦的方位分為九宮,分別為乾宮、坤宮、巽宮、艮宮、震宮、兌宮、坎宮、離宮與中宮,“巽宮”指東南方位;在巽宮的大圖中即畫出了“汪坊”的方位,[3]第二卷“疆域”又記:“汪坊”“距城四十五里”(約23.895公里;清朝光緒以前沿襲隋唐制度,一里相當于現代的0.531公里)[3]。對當地歷史、地理進一步考察,可以查證“汪坊”是指汪姓家族聚居的地區(qū),即潤田村(因明代出了汪姓進士汪潤田而得名,明代又出進士汪宗翰)附近;“坊”和“圖”都是清代縣以下的行政區(qū)劃名[6]6,該縣志中另有佘坊圖、油坊圖等。時至今日,蘭若寺僅存重建于明清時期的中寺,寺門正上方有一近代人所掛牌匾,上書“蘭若寺”三個大字。又從當地居民及守廟人的口中得知,“蘭若寺”正是這座寺廟的真實名字。在通城方言中,“蘭”和“來”發(fā)音有相似之處,因而這座寺廟也有“來佛寺”之稱。《永嘉證道歌》曰:“入深山,住蘭若,岑崟幽邃長松下,優(yōu)游靜坐野僧家,闃寂安居實瀟灑。”蘭若是“阿蘭若”的省稱,梵文Aranya,為佛教名詞,原意是森林,引申為“寂靜處”“空閑處”“遠離處”,即躲避人間熱鬧之地,可供修道者居住靜修之用。由于深契佛理,我國多見以“蘭若”為名的寺廟,如河南省扶溝縣蘭若寺、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qū)赤橋村蘭若寺、山西省忻州市繁峙縣蘭若寺、大理蘭若寺和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蘭若寺等。
(三)廟內外石碑
黃袍山蘭若寺現存的中寺,其室內墻壁被白石灰粉刷過,右側的墻壁中嵌有一塊石碑,碑文大體清晰,主要記載了同治七年(1868)當地有識之士出資重修該寺并記述功德的事。經辨認如下(文中“□”為未辨明字):粵自漢明帝始立佛門,佛之由來久矣,吾境大盤山中,寺厥名蘭若。崇祀佛祖,諸神無地不恩,無微不顯,真所稱佛中之龍象也。奈僧不克善,盡以變賣,凡我首士等援邀各助馀伐之。費公存管積,修整廟宇,裝彩神光,兼之修造廂房兩間。至咸豐七年丁巳年,價買土名水口硚上田種五斗,大小四坵。上寺門首西邊日字塘水,長沖𡏉水蔭注,又買方家葭土地坵田種五斗五升,大一坵。承中𡏉水蔭注又買本寺門首棗樹丘田種三斗,大小二丘。下寺門前塘水蔭注,又屋右側土名小椿樹坵。下寺門首大椿樹,坵田四斗,大一坵。承上寺西邊塘水蔭注,又金銀沖泉水分派蔭注共田□石七斗五升。其田實秋叁斗五升□。合契內載明秋隨田完納以及田地一并付寺供奉。香燈之資有僧等屢年臘月初八,迎接頭目聚手盤歡而恭祝合堂。神圣千秋庶幾神其有感佑福不淺矣。謹序日后不許私忘。計□頭目于后。批典押。搃首黃谷魁所管契□。頭首:夏位華、黃正□、吳浚源、夏福章、丁以和、黃清香、黃裘凡、續(xù)見堂、黃立文、夏安國、黃印初、黃介爾、黃升平、黃俠□、夏浴文、夏特吾、夏星照。同治七年戊辰年興三月吉日。公□。在這塊石碑下面倚靠著另一塊獨立石碑,由于時代久遠和受風化的影響,磨損比較嚴重,但也有幾十個清晰可辨的文字,最上端是“永古千秋”四個字,下邊的文字經辨認應當是:“漢來廟宇維新□壯善,神之赫濯……因大盤山蘭若寺先朝建立至……□年奈僧命□難以保守,□僧明……圖圖內會□派□頭□損……廟宇穴□,栚一副上下前□左右……契內載明因而募化仁人解囊相助以保佛祖□香煙而神圣賜福無韁……目救后”,接著是寫的是人名和錢數,有“黃燕居一千”“黃慶云一千”等,最左端落款為“道光丙午年季冬”。據此推斷,記載的大概是道光丙午年即1846年冬募資修護這座寺廟并記述功德的事。在離該寺200米處山路邊的一塊巨石上,也豎立著一塊石碑,該碑有明顯斷裂后修復的痕跡,碑中出現“蘭若寺住持”“申甲年”“隆慶六年”等清晰字跡。經查證,隆慶皇帝為明朝第十二帝,隆慶六年為公元1572年,距1572年最近的甲申年是1584年,該碑大概是對明代重修蘭若寺的有關事項及功德的記載[5]。
二、蘭若寺的歷史興衰
漢武帝在位時,以開放之姿容納八方之物。大漢使者張騫遣副使出使大夏經身毒(今印度國的一部分),又因黃袍山地處皇城之偏遠,便由身毒人在此建設寺廟、宣揚佛教、施行教化,名為蘭若寺,是華夏四海九州最早的佛教寺廟之一。沿黃袍山大盤山來佛寺側的古道及山窩相繼建起了上寺、中寺、下寺、觀音(又稱東庵,女性佛教信士集聚之地)等四寺,寺廟建筑面積宏大,信徒眾多,香火旺盛。[7]唐宋時期,黃袍山蘭若寺受到名人雅士的推崇。據傳,唐朝臣相金興政、北宋詩人黃庭堅和北宋抗金英雄方瓊等歷史名人為蘭若寺書寫過“佛源”“佛宗”“佛祖”等石刻,[7]但現已遺失。之后,蘭若寺經歷了中國佛教史最嚴重的四次法難,即“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的滅佛活動,蘭若寺遭到嚴重破壞。北宋年間,蘭若寺又經歷一次重修,才得以恢復與繼續(xù)發(fā)展。黃袍山蘭若寺習武健身的歷史久遠,自漢到唐都有武僧的記載。黃袍山上一位夏姓村民這樣說:“少林寺第34代弟子釋延康是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女兒的武術教練,也是我們湖北通城人,但他也許不知道,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武術中有一支派是源于黃袍山的蘭若寺,作為少林武術發(fā)源地的通城人,我們今天卻要去河南學習武術,這就是中國人所說的‘30年河東、30年河西’吧。”這些無不見證著蘭若寺那段燦爛的歲月。[3]從北宋到清代,蘭若寺逐漸損壞衰落,房屋損毀嚴重、土地大面積縮減,幸于明隆慶年間和清咸豐道光同治年幾度重修。從廟內兩塊石碑,可見道光二十六年與同治七年當地士紳募資集地重修蘭若寺之事,但蘭若寺畢竟飽經風雨,難復當年。據守寺老人所言,近代以來的戰(zhàn)爭與動亂對寺廟造成一定損害。1958年,當地民眾將寺廟中的木質佛像燒毀,將金屬佛像熔化鑄鋼,最終只剩大殿上的三尊佛像,這一切對蘭若寺造成近乎毀滅性傷害。[7]目前,蘭若寺來客稀少、香火不盛,僅偶爾有零星游人前來瞻仰上香。保存相對較好的部分只有中寺,但中寺也有近一半房屋倒坍,另一部分于清朝后期重修,分上下兩層,現存正殿一間,廚房、住室數間,屋頂有破漏。正殿長桌正中間供奉著一尊較大的佛像,兩邊左右分布著數尊小的佛像,都受風化影響,掉色、磨損痕跡明顯,后側的墻壁上懸掛著幾塊殘破的紅布,上面有模糊的字跡,寫著“有求必應、西天如來佛祖、南無觀音上士、上界玉皇大天尊”等文字,應是用來祈福的。更令人惋惜的是,蘭若寺內已無僧人,暫由與它一墻相隔的一戶當地村民順帶照看。黃袍山蘭若寺不遠處有多棵至少1500年以上樹齡的紅豆杉、銀杏等古樹,也許是古時的佛教信士們所植,這些古樹也被稱為“黃袍山活著的歷史”。蘭若寺左側古道上行百余米,有一塊由后人修補過的千年古佛石碑,在古道附近可見古石橋、古石埂、古石梯、古石道、古石洞等遺存,但古道邊的古茶樓、古驛站、古街道、古客棧都已不見。[7]1985年,黃袍山蘭若寺被定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6年,縣委書記熊亞平、縣長劉明燈等縣領導在塘湖、黃袍調研,首次發(fā)出打造黃袍山國家3A景區(qū)強音,塘湖、黃袍多處景點啟動建設(蘭若寺列入規(guī)劃);同年,通城古裝美女與美景攝影活動在潤田大屋啟動開拍(蘭若寺納入拍攝范圍)。2018年4月,由政府招標、光合文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的黃袍山風景區(qū)PPP項目開工慶典隆重舉行。開工慶典上,光合文旅董事長王明榮強調:“我們有決心把黃袍山建設成為通城縣全域旅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建成一個數據旅游、行業(yè)旅游的典范。”這一項目占地面積約17.32平方公里,投資2.65億元,主體工程總建筑面積約44630平方米。建設了“一紅一綠”景觀帶,“一紅”為建設元帥廣場,包括羅榮恒早期革命活動紀念館、通城革命烈士陵園、通城革命博物館、革命傳統(tǒng)教育基地等;“一綠”為建設大盤山公園,包括大盤山門樓、蘭若寺、千年紅豆杉等旅游景點,并配套建設了中心廣場、康養(yǎng)中心等;建設種植灌溉、景觀照明、給排水、供電、消防等景區(qū)基礎設施及道路工程等。2019年6月,首屆中國·湖北黃袍山(通城)全國自行車戶外公開挑戰(zhàn)賽在黃袍山風景區(qū)開賽,吸引了全國各地600多名選手參加。湖北咸寧通城縣委書記熊亞平表示,將以此次自行車賽為契機,在黃袍山打造一條全國獨一無二的專業(yè)自行車體驗運動賽道,倡導“體育+旅游+扶貧+N”的模式,建設自行車運動小鎮(zhèn),使其成為全國有特色的鄉(xiāng)村旅游目的地。黃袍山風景區(qū)的開發(fā),使蘭若寺的周邊環(huán)境和基礎設施得到極大改善,知名度也得到較大提高。
三、SWOT分析
(一)優(yōu)勢分析
黃袍山蘭若寺作為我國典型的宗教文化遺產之一,不僅具有游賞娛樂、文化教育、慈善救濟等方面的發(fā)展?jié)摿Γ移渥陨硭邇?yōu)勢也較為明顯,具體可從文物本體和周邊環(huán)境兩方面進行分析。從文物本體來說,一方面,蘭若寺歷史悠久,底蘊深厚,有很多珍貴的歷史遺跡,值得我們去探究;另一方面,蘭若寺未經充分的開發(fā),不僅保證了其作為宗教文化歷史映像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使其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得到了較好的延續(xù),而且給我們對蘭若寺的探究留下了較大的空間。從周邊環(huán)境來說,一方面,黃袍山本身的自然與人文地理條件得天獨厚,自然和人文景觀資源豐富、種類多樣,有利于打造古色人文、紅色文化、佛道宗教、綠色生態(tài)等多個獨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另一方面,近年來政府開始重視對黃袍山風景區(qū)整體的打造與建設,并且初具成效,蘭若寺周邊的基礎設施得到極大改善,為進一步發(fā)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二)劣勢分析
蘭若寺地處偏遠、破敗嚴重,與輝煌時期相比十不存一,大大加重了保護與修繕的成本負擔,再加之蘭若寺距離經濟發(fā)達的大城市距離較遠,對于蘭若寺文化歷史底蘊的宣傳力度不足,難以形成較強的吸引力,充足穩(wěn)定的客源得不到保障,更難吸引投資商與其他社會力量的資金投入。另外,蘭若寺周邊各景點的分布得較為散亂,各景點間的山路陡峭,交通薄弱,周邊基礎設施的開發(fā)不夠完善,眾多資源亟待進一步合理有效的整合。從另一層面來說,佛教文化內涵較為晦澀難懂,需要較長的接觸與熏陶才能獲得認同,佛教文化的認同群體縮減成為佛教文化遺產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8]。無獨有偶,蘭若寺所面臨的修繕費用負擔嚴重、多景點未形成整體優(yōu)勢、得不到廣泛認同等問題也普遍存在于我國為數眾多的鄉(xiāng)村宗教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fā)過程之中。
(三)外部機會
近年來,國家對保護宗教文化遺產的重視、政府政策的支持、消費者收入的增加、文化旅游消費群體數量的增加、文物保護技術的提高等都成為利于蘭若寺保護與開發(fā)的外部機會。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積極推動宗教文化遺產資源普查,探索建立宗教文化遺產數據庫、保護名錄體系,探索設立宗教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專項資金,建立宗教文化遺產管理體制;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廳積極探索鄉(xiāng)村振興實際策略,開展鄉(xiāng)村文化旅游節(jié)、鄉(xiāng)村文化調研、文藝演出等形式的活動;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使人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并更注重享受型與發(fā)展型消費的投入,消費結構不斷改善,宗教文化旅游的需求有顯著上升;科學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并擴展到文物修復、建筑復原等領域。
(四)面臨威脅
現今蘭若寺面臨的最大威脅便是現有的保護力度不足、保護措施亟待完善,再加之近年來周圍環(huán)境的巨大變化,其仍難脫離完全沒落的可能。進一步分析原因,一方面是對于蘭若寺背后的歷史文化及經濟價值挖掘得不夠深入,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另一方面是受基礎差、地形險峻等原因影響,開發(fā)難度大、成本高。其次,近現代以來,蘭若寺本身僧人數量減少,與外界交流減少甚至基本斷絕,使佛教文化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受到阻礙,進一步削減了以佛教文化為特色和主題的蘭若寺的生命力。此外,宗教文化遺產具有本身的特殊性,必須把握好開發(fā)時的度,既要把宗教文化遺產展示好,又要防止造成“宗教熱”;既要利用好宗教文化遺產資源,又要尊重宗教的“神圣性”,防止過度商業(yè)開發(fā)帶來的庸俗化,堅決警惕“宗教搭臺、經濟唱戲”現象[1]。
四、保護策略
(一)良好的社會背景是蘭若寺保護的前提條件
通過對蘭若寺所經歷史變遷的研究不難看出,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統(tǒng)治階級的態(tài)度、具體的文化宗教政策、社會總體政治經濟狀況等都對蘭若寺的發(fā)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佛教文化作為一種社會特殊意識形態(tài),每當佛教的教義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時,佛教文化就得以興盛,蘭若寺常也得以發(fā)展;而在佛教的教義不能符合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時,佛教往往受到排斥,蘭若寺的發(fā)展也會停滯甚至倒退。特別表現在,戰(zhàn)亂和極端的政治環(huán)境造成了蘭若寺的破壞與衰落,而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及政府的重建與政策性傾斜等都促進著蘭若寺的發(fā)展。因此,構建良好穩(wěn)定的政治與社會生態(tài)、在政治與文化策略上重視對宗教文化遺產的保護是蘭若寺保護的前提條件。當前,國家加強對宗教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的探索與嘗試、政府對于地方文化歷史的尊重與傳承以及新的文物與建筑保護技術的發(fā)展等都能成為蘭若寺保護的良好契機。
(二)充分的價值挖掘是蘭若寺發(fā)展的關鍵與基礎
黃袍山蘭若寺名聲不顯進而得不到發(fā)展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對其價值的挖掘不夠充分,而實際保護與開發(fā)過程中,在保證良好社會背景與適宜政策環(huán)境的基礎上,重點同時也是難點便是要發(fā)掘蘭若寺自身的文化價值,賦予周邊環(huán)境豐富的精神內涵。結合蘭若寺的歷史背景與現實情況,當務之急便是指派專人對蘭若寺進行看護、邀請相關方面的專家對蘭若寺進行科學調研,充分發(fā)掘蘭若寺的歷史文化價值。同時,需要通過出版物、電視廣告、特色活動開展、大型活動承辦等多樣化的、切實可行的、長久有效的手段對其進行展示和宣傳,突出其作為一種文化歷史載體與象征的地位,使其長久地延續(xù)和發(fā)展下去。[9]在保護與開發(fā)時,除了注重蘭若寺自身的特色和蘊含價值,還要注意其與周邊自然人文環(huán)境間的協(xié)調統(tǒng)一,注重在充分尊重與保護原有地方鄉(xiāng)村特色的基礎上,構建具有秩序性、場所性和完整性的整體空間格局景觀。具體來說,可以加快構建以蘭若寺為核心之一的特色鄉(xiāng)村文化鏈,整合本鄉(xiāng)村的各個地方性文化旅游資源,以提升鄉(xiāng)村整體文化內涵、豐富參觀者的文化體驗。
(三)廣泛發(fā)動社會力量是蘭若寺保護與發(fā)展的有力保障
從上述碑文以及對其歷史角度的研究可見:社會力量在蘭若寺的建設、發(fā)展與維護過程中起過重要的作用。這里的社會力量不僅包括當地的有識之士、文化與旅游方向的投資者,還包括佛教愛好者、鄰近有影響的寺院、地方佛教協(xié)會等。新的時代背景下,社會力量具有數量大、資金多、選擇性強等特點,并且已經滲入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蘭若寺的保護與發(fā)展過程中,充分發(fā)動社會力量不僅有利于獲得充足的資金用于蘭若寺的保護與周邊基礎設施的建設,還可以起到普及宣傳蘭若寺佛教文化特色的作用。此外,佛教同仁、地方佛教協(xié)會以及周邊大型寺廟的慷慨援助,包括資財的施舍、佛法的傳揚、佛教人才的培訓等,都可以成為蘭若寺得以迅速恢復、更好發(fā)展的堅實保障。
五、結語
宗教文化遺產訴說著地方、民族乃至整個國家的歷史與文化,對其進行有效的保護、使其更好地發(fā)展具有深遠的歷史與文化意義。但現實情況是,我國的政府有關部門、社會組織以及相關學者大多將注意力放到大型寺廟的維護與提升上,鄉(xiāng)村宗教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fā)展則往往出現明顯的“缺位”。保護與傳承好宗教文化遺產不僅要抓好大型寺廟這些重點以更好帶動周邊地區(qū)的遺產保護與發(fā)展,更要補齊鄉(xiāng)村宗教文化遺產這塊短板,以實現我國宗教文化遺產保護的全面發(fā)展。本文側重于從理論層面對鄉(xiāng)村宗教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fā)展進行探討,還應注意在具體的鄉(xiāng)村宗教文化遺產保護與發(fā)展實踐過程中檢驗與發(fā)展這些策略,為構建科學完整的中國特色鄉(xiāng)村宗教文化遺產保護體系提供一些有效的實踐路徑。
作者:包鈺 王瑩 單位:安徽大學文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