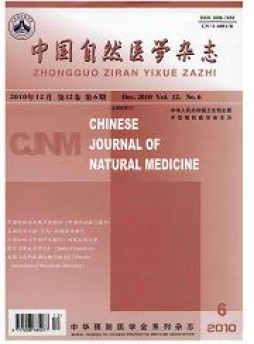自然教育觀的跨文化對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自然教育觀的跨文化對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愛彌兒》與《莊子》雖屬不同語境下的多維性專著,但它們都有自然主義教育的理論傾向。因文化時代背景各異,“自然”在他們各自的理論體系中有著特定的內涵。將盧梭與莊子的自然教育理念橫加比較,二者雖因文化上的差異表現出不同的思想訴求,但我們也會驚喜地發現盧梭和莊子的思想有著微契合之處。厘清兩位哲人的自然教育觀,對現如今教育事業的發展大有裨益。
關鍵詞:
《愛彌兒》;《莊子》;自然教育
教育本是一個多向度的概念,圍繞這個概念生發的一系列教育原則是教育施行的依據。藝術、社會、自然都是教育的向度,它們在潛移默化中對人情感的陶冶、健康審美力的培養與健全人格的塑造都起著重要作用。教育與審美發生聯系就具有了升華的維度,美育成為了現如今精神文化建設的重要議題,被人們全方位地解讀與發掘。自然教育是美育的一個扇面,自然教育原則在各種思想體系中又有不盡相同的內涵。筆者選取先秦時期道家哲學的代表性著作———《莊子》[1]與法國啟蒙時期思想家盧梭的作品———《愛彌兒或論教育》[2]來進行跨文化的探視,這對我們理解自然教育豐富的內涵有較大的啟示。
《莊子》與《愛彌兒》是分屬不同時代、文化背景的產物:在那個“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莊子•人間世》)的社會,《莊子》這本書的思想意旨本就是復雜的。它的確是一部哲學專著,莊子站在道家哲學元范疇之上提出了如何“體道”的主張。但《莊子》的富饒讓我們不得不對這樣一部寓意豐贍的書產生拓展性的理解與詮釋。在回歸自然的“體道”中,莊子以神話隱喻的獨特方式向讀者展示了一個怪誕的世界,美國學者愛蓮心就認為《莊子》中的神話與隱喻形象的使用并非莊子無意的安排與撥弄,而是莊子有意為之的哲學策略,以此來實現莊子所要達到的哲學目的。“《莊子》文本中的不連貫和十分難解的文學方式跟達到自我轉化的目的技術手段有一種系統的關聯”[3]。莊子假借一系列怪誕的意象是與實現讀者心靈轉化的哲學意旨分不開的。雖然莊子沒有明確提及此書是寫給受教者的教育專著,但我們有理由從教育的角度去解讀《莊子》。閱讀本就是人對德行的自覺追求,莊子也成為了邏輯上的教者。況且,莊子的思想是有教育訴求的,在《莊子》中充斥了大量人物對話與獨白,這往往給讀者以另類的啟示。特別是其以“游”的方式來完成對“道”的體悟,這種對人們直覺(詩性智慧)的喚醒與自然美育的原則暗中契合。盧梭的《愛彌兒或論教育》是啟蒙語境下的產物,盧梭所處的時代是崇仰理性的時代,理性主義的過度猖獗讓盧梭生發了培養“自然人”的想法。在盧梭看來,社會的“種種成見、權威、強迫、規范,以及壓在我們身上的所有社會制度都將扼殺人的自然天性”(《愛彌兒》)。那么,回歸自然,用自然教育的原則來培養作者假想的兒童———愛彌兒就顯得尤為必要。我們發現,盧梭明確地表示這本近小說似的作品是他對教育的論述,較之《莊子》有著更為明確的寫作目的,即對教育的看法與評解。
1762年,在相繼發表了早期兩篇論文之后,盧梭發表了《社會契約論》和《愛彌兒》。盧梭也多次強調《愛彌兒》在他思想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在致友人馬勒薩爾伯的信中,盧梭說:“我的全部精神智慧分散于前兩篇論文和《倫教育》中,三部著作不可分割,構成一個整體。”[4]前兩篇論文指《論科學與藝術》和《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尤其在《論科學與藝術》中,盧梭就敏銳地洞見了那個時代技術與文明對人類早期純樸情感的破壞,充滿了盧梭對科學啟蒙及其后果的審慎思考。所以,我們在解讀《愛彌兒》的同時應該注意到《論科學與技術》和《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這兩篇論文對《愛彌兒》的思想預設,這是進一步理解《愛彌兒》的先行前提。早在《愛彌兒》出版之前,《社會契約論》就出版了。此書一出版盧梭旋即被指控是在“攻擊各國政體”。然而,盧梭卻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社會契約論》不過是緊隨其后出版的《愛彌兒》的注釋性附錄。還說《愛彌兒》與《社會契約論》應該是一個完整的主體,《愛彌兒》引用和改變了了《社會契約論》的許多東西[5]。由此可以想見,《愛彌兒》絕非一部單純的教育論著,而是和其政治思想緊密相聯的(《社會契約論》明顯談的是民主政體及其法律制度建設的問題,因此是關于政治制度設計和立法的書)。況且,一般認為,《愛彌兒》在有意模仿柏拉圖的《理想國》。在書的開篇不久盧梭就寫道:“你要想懂得公共教育的理念嗎?讀柏拉圖的《理想國》吧。這可不是一部政治作品,像僅憑書名來判斷的人所想的那樣。它是從不曾有人寫過的最佳教育論。”
我們可否斷定,盧梭寫作《愛彌兒》和柏拉圖寫作《理想國》有著相反的意圖。《愛彌兒》不僅是一部論教育的小說,而且也是一部闡揚盧梭政治主張的專著。由此觀之,《愛彌兒》中的自然教育至始至終都秉承面向社會、面向政治的教育原則,盧梭成為了自然教育原則的操控者。自然的教育,是《愛彌兒》的行文起點。在第一卷盧梭就告訴我們,他這部小說主要論述“自然人”的培養。他說“:一句話,必然了解自然的人。我相信,人們在看完這本書后,在這個問題上就可能有幾分收獲。”所謂“自然人”是將古代的忠誠、勇敢、道義等“自然的情感保持在第一位的人”,而與之相反的是“社會人”(即“文明人”)。我們應該注意到,盧梭“自然人”觀念的提出是有一定啟蒙語境的,“自然人”本就是那個時代哲學的公共產物。在《論不平等的起源》的本論中盧梭告訴我們,為了探究社會的基礎及其政治性質,當今時代的哲人們提出了“自然狀態”及其“自然人”的假設,以此作為研究政治制度或優或劣的參照系數。盧梭是贊成這種分類方法的,但他同時代哲人們對“自然人”假設的表述還差強人意,其結果必然是曲解人類社會的基礎以及應該追求的完美政治的性質。在盧梭看來,古代人是“自然人”,而當代人是“社會人”,是一種被封建專制制度所腐蝕了的人。在《論科學與藝術》中,盧梭極力倡導回歸自然的理念,《愛彌兒》在這方面必然有思想上的承襲性。自然的狀態在盧梭看來是最理想的。他說“:自然讓人曾經是多么幸福而善良,而社會卻使人變得那么墮落而悲慘。”[6]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變壞了。”盧梭在暗指科學和藝術的進步沒有帶來人類道德的提高,反而帶來普遍的墮落與罪惡。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非常早的對“文明”的反思。“社會人”已經被人類社會的種種成規陋習所污染“,回歸自然”必然成為盧梭教導愛彌兒的首要原則。那么,如何培養“自然人”,如何“回歸自然”呢?盧梭的回答是“:遵循自然,跟著它給你畫出的道路前進。”盧梭為愛彌兒制定了一系列的培養計劃,從幼兒時期的愛彌兒到情竇初開的愛彌兒,作者“細數了一生的苦難”[7],相應的采取培養策略,他認為這樣才是自然教育應該做的。不難發現,“自然”在《愛彌兒》中顯然參雜了“人為”的因素———那就是盧梭本人。盧梭從“社會人”相反的維度去思索“自然人”應然的存在狀態,這只能導致主觀化的自然。盧梭對自然的理解也帶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狹隘性。
較之《愛彌兒》,《莊子》在行文中所言及的“自然”具有不同的內涵。“自然”以純哲學的姿態出現,顯示出形上哲理色彩。以此生發的“自然教育”也顯得難以為人所操控。道家處處言及“自然”,“自然”成為得道者的一種處事方式和行為準則。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高于“道”的存在物,“道”也可以說是“自然”的一種概括與描述。道家的“自然”近“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運行”[8],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簡言之,“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它排除了一切可操控的因素,涵融萬有,凌駕于萬類之上,產生在萬有之前(“象帝之先”,“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道家從純哲學的角度來表述“自然”,這是形而上的哲理思辨。以此“自然”觀導出的具有教育傾向的“體道”方式就與盧梭的自然教育原則大相徑庭。我們注意到,不論是老子還是莊子,都沒有明確表示自己在論如何教育,他們只是在表述如何以最淳樸的姿態歸順自然。在他們的思想中我們體察到了靠“自然”來實現自我教化的可行性。老子云“:我無為,而民自化。”這成為道家教化的首要原則———不去向外訴求,而是順自然發展。那么,到底如何自我育化?《莊子》以“體道”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自育之法。《莊子》的首篇《逍遙游》以“鯤鵬”神話開場,這是暗指了讀者直覺思維應該重啟,而邏輯思維暫告休假[9]。“游”是一種態度,這是直覺對“道”的體悟,是純娛樂性、非功利性的審美活動。以“游”的方式來完成對“道”的覺解,這是莊子美育的基本訴求。
游戲的心態本就是童真心靈所具有的基本特點,理性邏輯的思維方式宣告癱瘓,審美直覺被喚醒,這本身就是自我育化的自覺追求。莊子中“心齋”“、坐忘”,都是體道的具體途徑。“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心齋”讓人摒除雜念,心境純一,通明大道,以虛空之心集道于懷,這是入道的關鍵,也是進入審美之境的起點。在《大宗師》中,莊子還提出了“坐忘”的修心方式,這是對身體感官機能的拋棄,也是對理性思維的揚棄:“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大宗師》)“心齋”、“坐忘”是“悟道”的過程,“悟道”的主體是自我而非他人,也即是自我育化。我們發現,這種自然育化的過程是自我的修心活動,我是自在且自為的存在主體。莊子沒有刻意地去接近“自然”,其美育策略本就自然而然,無須人為的操控。這種哲學范疇的自然教育觀與盧梭從政治社會的反面提出的自然教育觀是有很大不同的。
盧梭所處的時代是唯理論占據優勢的時代,用洛克的著名說法“:我們生而自由,也生而具有理性……年齡帶來自由,同時也帶來理性。”[10]理性成為了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的助推器。但唯理論的過度發展必然導致獨斷論,導致另一場思想與文明的危機。在唯理論蓬勃發展之時,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這一理論模式興起于法國,盧梭力批理性,推崇感性,顯現其不同凡響的哲思。他批判了當時頗為時髦的“用理性去教育孩子”的觀念,他說:“用理性去教育孩子,是洛克的一個重要原理;這個原理在今天最時髦不過;然而在我看來,他雖然時髦卻遠遠不能說明它可靠;就我來說,我發現,再沒有誰比那些受過過多理性教育的孩子更傻的了。”他認為,理性教育不符合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只能起到負面效用。以此相對,盧梭卻對感性教育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將感性看作人生存的基礎與前提。他認為,在人身上“首先成熟的官能就是感官”,然而,“唯獨為人們所遺忘,而且最易于為人們所忽略的,也是感官”。他說“:由于所有一切都是通過人的感覺而進入頭腦的,所以人的最初的理解是一種感性的理解,正如有了這種感性的理解做基礎,理智的理解才得以形成,所以說,我們最初的哲學老師是我們的腳、我們的手和我們的眼睛。”由此觀之,在那個理性主義占統領地位的時代,盧梭對感官和感性教育的推崇可謂空谷足音,他將感官和感性提到人“存在的本身”與最有意義的生活的高度來認識的確是從未有過的。較之盧梭的美育觀,直覺與感性在莊子看來是極為重要的,對“道”本體的體悟本身就非理性邏輯可以達到的,而是靠“體驗”,這個過程是對人內在感性能力的一種培養與操練。而且,在《莊子》中,以神話和寓言形式出現的具有隱喻特點的故事俯拾即是,它們以不太連貫的方式串聯成文本全部。然而,神話似的場面本就是摒除邏輯理性思維模式的,“以便平息心靈的分析功能同時又喚醒其直覺功能。”[11]
莊子在《逍遙游》一開場就選取“鯤”與“鵬”作為自己理念的寄托物絕非偶然;《齊物論》蝴蝶夢也是借蝴蝶原型(本喻)來闡釋“轉化”之旨;《人間世》和《大宗師》中畸形的智者,癲狂的哲人都饒有趣味,極富暗示性與啟發性;在《至樂》中,“骷髏”意象的運用既表現出莊子看破生死喜樂的豁達,這也是一個具有象征意蘊的可怖意象;《秋水》中的“水”意象,它本身就是中國古典哲學常見的“本喻”體[12],“水”是“道”最恰切的表現形態。隱喻與象征藝術是莊子的文學選擇,也是他有意為之的語言設計(“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只有形象思維能力才能較為妥帖地接納這些有著象征性的哲學啟示。這種古老的、埋藏在人類童年期的智慧在閱讀《莊子》時被重啟,如“童真之心”的復蘇一樣,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受直覺、感性的哲學操練。所以,盧梭與莊子雖用不同的教育策略來達到自然美育的目的,但他們對人感官能力、直覺能力、感性能力都是極為重視的,在“理性”肆意猖獗的當時,他們都力求一種向人類原始情結(感性能力,詩性智慧)的回歸。這既是盧梭尋找原始淳樸文明的思想根源,也是莊子對老子哲學藝術化的繼承與闡揚.
作者:陳辭 單位:四川師范大學 文學院
- 上一篇:金屬商品交易中的互聯網安全文化管理范文
- 下一篇:后現代語境下的斯坦貝克研究意義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