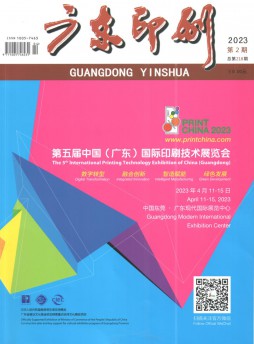印刷出版與中西文化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印刷出版與中西文化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由上述可知,米憐一行甫抵馬六甲,即創辦《察世俗》。印刷所成立后,更是積極開展印刷出版。馬六甲時期英華書院的出版品主要有:1.中英文報紙期刊。1815年8月創刊的《察世俗》是米憐主持創辦的第一份中文月刊報紙,被譽為“中國近代雜志的第一種”、“中國近代報業的開山鼻祖”[6]。其編務由米憐全盤負責,所刊載的文章也多出自他之手,封面書“博漢者纂”,“博漢者”即米憐的筆名,馬禮遜、麥都思和梁發給最后幾期寫了稿[7]。《察世俗》至少出版到1822年2月至3月,因米憐去世而停刊。《察世俗》在中文印刷、出版、新聞、傳教以至中外文化關系等方面,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它不僅對基督教在華人中的傳播,對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且在中國近代報刊發展史也占有重要地位。在清廷禁止傳教士在華公開布道的情況下,《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創辦,可以說是新教傳教士開展文字傳教的一次成功的嘗試。《天下新聞》(TheUniversalGazette)是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的另一份中文刊物,由英華書院院長吉德(SamuelKidd,1799-1843)在1828年創辦并編輯[1]。它的出版資金是由兩名英國商人馬治平(CharlesMarjoribanks,1794-1833)和馬地臣(JamesMatheson,1796-1878)提供的,因而其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一份完全宗教性的刊物了,所載內容有中外新聞、歐洲科學、歷史、宗教與倫理等[2]。該刊的式樣也突破了過去的書本式而改為散張,并用活字印刷,實際上是最早采用中文鉛活字排版、機械化印刷的中文雜志。但該刊僅維持了一年,1829年底,由于吉德夫人身體欠佳,吉德偕夫人移居新加坡,在那兒小住后返回英國,《天下新聞》亦因此遭遇停刊[3]。《天下新聞》共出版4期,4期的發行量超過4250份,每期約有1000份上下[4]。對于英華書院與中文報刊之間的關系,卓南生曾經指出:“如果我們查閱教會早期報刊創刊人的履歷,就可以知道他們幾乎都出身英華書院或與該院有某種密切的關系。”
《印中搜聞》(TheIndo-ChineseGleaner)[6]是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的一份英文季刊,它創刊于1817年5月,由米憐編輯,他同時也是重要的撰稿人。《印中搜聞》是一份宗教性刊物,目的在于“促進印度各傳教會的合作,促進基督教互助、互愛美德的實施”[7]。《印中搜聞》出版到1822年6月停刊,持續近六年時間。它所刊載的大量有關中國的報導,加深了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和認識。白瑞華認為馬禮遜和米憐既把《印中搜聞》看成實現恒河外方傳教計劃的工具,也把它看成一個有關漢學的重要刊物[8],實非臆說。2.宗教類書籍。一是《圣經》中文直譯本。馬禮遜在翻譯中文《圣經》的過程中,邊翻譯邊出版,但由于清政府嚴厲禁止出版宗教書刊,所以有些就被馬禮遜送到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1817年,馬禮遜將譯畢的《新約》在馬六甲出版,題名為《我等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1823年,包括《舊約》和《新約》的全套《圣經》中譯本以木板雕刻方式在英華書院印刷所全部刊印完畢,題名為《神天圣書》,達21卷[9]。二是勸教書,如馬禮遜的《古時如氐亞國歷代略傳》、《神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本》、《問答淺注耶穌教法》、《年中每日早晚祈禱敘式》、《神天道碎集傳》、《古圣奉神天啟示道家訓》;米憐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記》、《崇真實棄假謊略說》、《進小門走窄路解論》、《幼學淺解問答》、《祈禱真法注解》、《諸國異神論》、《圣書節注十二訓》、《圣書節解》等。三是圣史、傳教史及傳教士回憶錄,像米憐的《古今圣史記集》、《新教傳教會在華第一個十年回顧》(ARetrospectofthefirsttenyearsoftheProtestantMissiontoChina)、馬禮遜的《米憐回憶錄》(MemoirsofRev.WilliamMilne,1824)、柯大衛(DavidCollie,?-1828)的《圣史簡本》(AnAbridgmentofSacredHistory)等。《新教傳教會在華第一個十年回顧》是米憐根據馬禮遜的手稿寫成,包括許多關于新教傳教士在華最初活動的珍貴史料[1]。3.世俗類書籍。涉及語言學、歷史、地理、倫理等,內容極為豐富。語言學方面,法國漢學家馬若瑟(JosephdePremare,1666-1736)的《漢語札記》(NotitiaLingaeSinicae,1728)[2]1831年由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馬若瑟與宋君榮(AntoineGaubil,1689-1759)、錢德明(Jean-JosephMarie,1718-1793)并稱法國早期漢學三大家。他1698年來華后,“即專心于兩點,質言之,傳布教務,精研漢文是也”[3]。經過30年辛勞,著成《漢語札記》。這是一本研究漢語的專著,被法國著名漢學家雷慕沙(JeanPierreAbelRémusat,1788-1832)認為是“若瑟著述中之最重要而堪注意之著述,亦為歐洲人所據此類著述中之最佳者”[4]。方豪認為:“其書于漢字之構造及性質,論列頗詳,舉例一萬三千余則,為西人研究我國文字之鼻祖”[5]。日本著名學者石田干之助稱它“是一部最先將中國語言的性質與其構造,正確地傳之于歐洲人的專書”[6]。但是,由于種種原因,該書長期沒有出版,而是以手抄本在西歐學者中流傳。直到1831年才由英華書院印刷所公開出版。甫發行,即引起廣泛注意。《中國叢報》(TheChineseReposito⁃ry)刊載的評論文章指出:“作為漢語的研究者,沒有一個外國人可以超過馬若瑟。他的著作不是一部簡單的語法書或修辭學著作。他擯棄了拉丁語法的模式,建構起一套全新的漢語分析框架。”[7]1847年,裨詹姆(JamesGrangerBridgman,1820-1850)又將其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在廣州出版,于是影響更大,成為來華傳教士學習漢語的必讀書之一。此外,像馬禮遜的《中文會話與凡例》(DialoguesandDe⁃tachedSentencesintheChineseLanguage;withafreeandverbaltranslationinEnglish)也是為了幫助外國人學習中文而出版的。米憐的《張遠兩友相論》是公認的第一部公開發行的傳教士中文小說,1819年在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它模仿中國傳統章回小說寫法,以張與遠兩個好朋友的系列答疑對話,來闡釋基督教教義,迎合中國讀者的閱讀與審美習慣,閃現著作者對中國文化、民間習俗的觀察與思考。同時,其中融入了西方的思想觀念、小說技巧與語言表達方式,帶給讀者獨特的審美體驗。該書的流傳跨越了整個19世紀,版本眾多,并經多次改寫、修訂,受到中國中下層讀者喜愛,并為傳教士一致推崇。以它為成本,出現了許多仿作。傳教士中文小說由此大行其道,為中國傳統小說創作同時帶來了危機與契機,對中國小說由古代到近現代的過渡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8]。由于采用對話形式,內容也是西方人極為熟悉的,很適宜作為中文學習的入門讀物。一位名叫弗利歐(Phlio)的作者極力推崇《張遠兩友相論》:“這些對話以簡明的風格寫成,包含了大量普通人經常使用的詞匯。我之所以在學習之初就選擇此書,是因為據我所知,沒有一本書比它所含的詞匯更為豐富了。我會與老師一起將它研讀兩三遍,學習之余,還請老師把它抄在空白的簿子上,欄與欄之間間隔開來,一頁或許能寫兩欄以上。”[9]郭實獵也提到1829年3月他在曼谷時,一個非常貧窮的人去拜訪他,說自己罪孽深重,經常冒犯上帝,但自從讀了米憐的《張遠兩友相論》后,感覺從書中受益匪淺[10]。據裨治文1833年10月統計,當時這本書的單行本發行數已達5萬冊,遍及中國沿海、蒙古、琉球[1]。直到1907年,這本書仍然被看作是用中文著述的最有價值的基督教書籍之一[2]。而據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韓南(PatrickHanan,1927-2014)最新統計,《張遠兩友相論》至少有30個版本[3]。足見此書影響之大。
歷史方面,以麥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1796-1857)的《東西史記和合》(ComparativeChro⁃nology)最為著名。其摘要最初刊載于《天下新聞》,1829年在巴達維亞出版單行本,1829和1833在馬六甲又兩次重印。《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從1833年8月1日創刊起,分11次轉載了《東西史記和合》。從麥都思自定的英文書名看,《東西史記和合》屬于編年體史書,它也是一部東西歷史共時性對照的史書,將東西歷史上同一時期不同地區歷史過程中的一些穩定單位的時間,進行對比敘述。當然,這里的“東史”并非今天意義上的東方史,而是特指中國史;“西史”主要是指古代西方歷史和英國王朝史。所以,該書“確可被認作中文著作中比較敘述中西歷史的首次嘗試”[4]。全書分上下兩欄,列出中西歷史大事,東史為“漢土帝王歷代”,起于盤古開天地;下欄西史為“西天古傳歷記”與盤古相對應的是關于亞當的故事。與夏商周相對的西史記述,大多是《圣經》等傳說中的故事,與東史秦朝和西漢相對應的是埃及的托勒米王朝。《東西史記和合》的記述有詳有略,而關于耶穌的誕生和基督教與佛教,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述。用比較的歷史方法,來考察中國和西方歷史發展的演變,《東西史記和合》可能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嘗試。這種對比分析,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歷史闡述的狹隘性,將中西歷史發展放到了更廣闊的背景下,改變了歐洲史學中的孤立主義傾向,擴大了中國學者的歷史視野,有助于全面地認識西方和東方。《東西史記和合》不僅是19世紀面世的第一部中西比較的編年體史書,可能也是有史以來第一部中西比較歷史的著述。地理方面,出版有《全地萬國紀略》(SketchoftheWorld)和《地理便童略傳》(GeographyCate⁃chism)。《全地萬國紀略》由米憐執筆撰寫,在1820至1821年間,分11回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連載,主要內容介紹了地球的歐、亞、美、非四個大板塊,介紹了許多國家的情況,包括京城、人口、人種、政治制度、物產和語言的不同。各國詳略殊異,略者不足一行,詳者如美國則多達17行。還專辟一回,論述美洲發現經過,多達50多行。1822年又以單冊印行。
《地理便童略傳》為麥都思所著,初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上連載。《地理便童略傳》介紹了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埃及、德國、英國、美國等的疆界、范圍、物產、人口、宗教等。該文還有4幅地圖,即世界地圖,中國、亞洲和歐洲地圖各一幅。1819年作為小冊子單獨出版,成為教會學校的教科書[5]。《地理便童略傳》是晚清新教傳教士所編寫的第一部面世的漢文地理學通論,該書不僅介紹了世界自然地理的一般知識,而且注意介紹西方的人文地理,特別是首次為中國人帶來了西方君主立憲、兩院制度和三權分立的觀點。這些漢文地理學著述,事實上對中國人開始了一場關于“世界意識”的新的啟蒙[6]。還有就是漢語經典西譯的出版。1828年,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了柯大衛的一本名為《中國經典》的書,一般被稱之為《四書》的著作。這可能是《四書》最早的英譯本。柯大衛為英國傳教士,1822年奉倫敦傳教會之派到達馬六甲布道站,隨馬禮遜學習中文。1824年開始擔任英華書院校長直至去世。1828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由他翻譯的這本《四書》由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柯氏坦言其從事翻譯經典的目的是“獲得一些關于中國語言的知識”,便于英華書院的中國學生掌握英語,藉此“引導他們認真反思其至圣先師教誨中的致命錯誤”,進而皈依基督教[1]。由于此前英語世界儒家典籍翻譯極為匱乏[2],因此該譯本在英語世界得到一些學者的重視。美國著名漢學家衛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97)在撰寫《中國總論》(TheMiddleKingdom)時,所用的就是柯大衛譯本[3]。據學者統計,1842年以前,傳教士出版中文書籍共147種,英華書院印刷出版的即達47種[4]。
二、香港時期英華書院的印刷出版活動
1843年英華書院遷往香港,更名為英華神學院,隨遷至港的印刷所設在英華神學院內,仍積極從事出版工作。王韜初到香港,即觀察到英華書院不僅“教以西國語言文字,造就人才,以供國家用”,還“兼有機器活字版排印書籍”[5],并注意到印刷所擁有印工七至八人[6]。尤其1856年英華書院停止教學活動,專事出版。據統計,此時期其出版品超過70余種[7]。現擇其要者簡介如下:1.中文期刊。香港時期英華書院出版的最重要的中文期刊是《遐邇貫珍》(TheChineseSerial),創刊于1853年9月3日,為鴉片戰爭后香港出版的第一個中文期刊,它由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Ed⁃ucationSociety)出資。第一任主編是麥都思,次年就轉交給香港殖民政府官員、也是麥都思的女婿奚禮爾(CharlesBattenHiller,-1856)負責,1855年起由理雅各主持,翌年5月停刊。《遐邇貫珍》雖由傳教士主辦,但實際上是新聞性刊物。《遐邇貫珍》以傳播西方文明為重點,目的是在贏得中國人對外國人及西方文明尤其是英國好感的同時,不失時機地進行宗教滲透。因此,《遐邇貫珍》在內容上以西方近代文明及時政要聞為主,其次才是宗教。《遐邇貫珍》對西方近代文明的宣傳和介紹,涉獵極其廣泛,囊括政治學、歷史學、文學、地質及地理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醫學、生物學等領域,可謂19世紀中葉介紹西學最集中、最有影響的中文刊物。反映時事政治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是《遐邇貫珍》的另一重要內容。該刊設有新聞專欄“近日雜報”,并發表新聞評論。其刊載的新聞信息量大,內容豐富,覆蓋西方各國、中國大陸以及香港,涉及政治、經濟、外交、宗教、軍事、教育文化等。該刊發表的一些有關中國內政的報道,敢說敢言,保留了歷史真相。如對太平天國、小刀會以及其他會黨起義的報道,公正客觀,至今為史學界所重視。以研究中國新聞史而享譽海內外的新加坡著名學者卓南生即指出:“《遐邇貫珍》所載內容,前半部分主要是介紹西洋文明的長篇文章,后半部分是新聞。所謂西洋文明的介紹,從傾向看,最初是以政治、歷史為中心,后來則把重點轉為西洋醫學、地理與化學等知識性文章。”
在新聞業務上,《遐邇貫珍》也做出不少開創性的貢獻,它是我國近代第一個以時事政治為主的刊物。在新聞編輯上,它以新聞標題簡明扼要來反映新聞內容,是我國近代報刊在新聞編輯業務上的一個飛躍。《遐邇貫珍》也是我國最早刊載新聞圖片的中文報刊,有科普插圖及為配合新聞報道而繪制的插圖[2]。總之,不管是在編輯內容、版式設計、商業經營,還是在新聞報道方面,《遐邇貫珍》對后來的華文報刊均產生過重要影響。2.宗教類書籍。香港時期的出版品中,宗教書刊仍占相當比重。《圣經》的第四個中譯本,也就是“委辦本”(Delegates’Version)就是在英華神學院印制的。為適應鴉片戰爭后基督教在華傳教的新局面,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英美傳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1801-1861)、文惠廉(WilliamJonesBoone,1839-1891)、施敦力(JohnStronach,1810-?)、克陛存(MichaelSimpsonCulbert⁃son,1819-1862)、理雅各、麥都思及米憐之子美魏茶(WilliamCharlesMilne,1815-1863)等十二人在香港開會,組成“委辦譯本委員會”,決定翻譯出版新的《圣經》中譯本。但是在翻譯過程中,發生了譯名爭執:一是對宇宙主宰God究竟應該譯為“神”或“上帝”,在英美傳教士之間無法達成一致;二是浸禮會和其它差會對Baptism如何漢譯也存在不同意見。面對爭執不休的局面,浸禮會傳教士首先退出翻譯委員會,接著公理會傳教士也退出。留下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和理雅各,在王韜等中國學者的協助下,1852年出版《新約全書》,1853年《舊約全書》亦告完成,1854年由英華神學院印刷所出版。這個中譯本被稱為“委辦本”或“代表本”。因有中國學者參加,翻譯文筆比以前都“大見進步”,其出色的譯文風格贏得了高度贊譽[3]。但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委辦本”《圣經》譯本“犧牲了許多準確的地方,所用的名辭近乎中國哲學上的說法,而少合基督教義的見解”[4]。盡管如此,該譯本后來還是多次再版重印,直到20世紀20年代依然流行。除《圣經》外,還印行大量與傳教有關的宗教小冊子。3.世俗類書籍。世俗類書籍以理雅各翻譯的《中國經籍》(TheChineseClassics)影響最大,該書首版就是在香港英華神學院印刷所印制的。理雅各是倫敦傳教會傳教士,1839年7月奉派來華,1840年1月抵馬六甲英華書院學習中文。同年伊云士校長(Rev.JohnEvans)去世,理雅各接任為英華書院校長。1843年英華書院遷往香港后,仍由理雅各擔任校長。他熱心對華傳教事業,寫出了18種漢文新教布教書籍。他是第一個系統研究、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人,從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間,將“四書”、“五經”等中國主要典籍全部譯出,共計28卷。當然,在這一翻譯過程中,理雅各也得到了其他傳教士如湛約瀚(JohnChalmers,1825-1899)、麥高溫(JohnMacgowan,?-1922)、合信(BenjaminHobson,1816-1873)以及華人王韜、黃勝等的協助。從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對中國典籍也曾多有譯述,但都只譯片斷,且因漢語不精,或對于儒學經義鉆研不透,或請學養淺陋的華人合譯,譯文往往辭句粗劣,語義欠通,謬誤百出。而理雅各的《中國經典》是傾注其幾十年心血并得到中國學者的幫助才得以完成,陸續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轟動,使歐美人士得以了解東方文明和中國文化以及中國民族倫理道德。理雅各的英譯本直到今天仍被公認為標準譯本。理雅各所以在漢學研究方面有這樣的成就,恰如卓南生所說,“與他長期主持英華書院的事業是密切相關的。可以這么說,理雅各在中國文學方面的學術成就,是他從1840年接任英華書院院長開始,到該書院關閉為止主持該書院院政的同時,發奮研究的結果”[1]。
此外,英華神學院印刷所還曾出版教科書,像《智環啟蒙塾課初步》(GraduatedReading)。該書為理雅各為英華書院編譯的一部教科書,它由24篇200課構成,中英文對照,上段為英文,下段為中文,內容涉及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和西方的基礎知識。1859年香港官學把該書作為標準教材,1862年、1864年分別在廣州、香港重版。1859、1864年再版,再版時刪除了英文對照部分的中文版。此書后被列為香港公辦學校所采用的教科書[2]。1873年在上海也出版了刪除英文對照部分的中文版。該書在漢語新語詞的創制方面也有一定貢獻。理雅各在翻譯該書時,除借自其他傳教士的漢譯西書的語詞外,還創制一些新語詞。像“公侯院”(houseoflords)、“百姓院”(houseofcommons)、“水蒸”(steam)、“陪審”(jury)、“老人院”(almshouse)、“福音教師”(Preachersofthegospel)等。雖然這些新語詞“有些被后來的新譯詞所替代,有些在原詞形的基礎上發生了變化,在現代漢語中已看不到了。但這些新詞語的研究,對于理清現代漢語詞匯的源流演變,揭示近代中日間詞匯交流的過程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3]。此書不僅在香港影響極大,在日本也流播甚廣。據日本學者尾佐竹蒙研究,《智環啟蒙塾課》于1860年經長崎傳入日本,1862年就開始出現了刪除英文部分的漢文翻刻版[4]。從1862年起到明治初期,日本出版的《智環啟蒙塾課》各種版本多達十余種。從用途來看,可分為英語教科書用和啟蒙書用兩類。作為英語教科書用的《智環啟蒙塾課》,主要有1862年江戶開物社翻刻的中英對譯版和1870年由廣島洋學所翻刻的刪除了中文對譯部分的英文版。而作為啟蒙書用的《智環啟蒙塾課》,分為漢文版和日文版,兩者均將英文部分刪除。總之,《智環啟蒙塾課》在日本各地被翻譯或翻刻,被許多小學采用為教科書,對日本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日本學者小澤三朗即指出:《智環啟蒙塾課》作為“西洋新知識的入門書”及“小百科辭典”,對引進西學具有啟導的作用[5]。增田涉也指出:“此書作為西洋知識入門的啟蒙書,或作為英語教科書,對明治初年為我國開發新文化立下的媒介之功,必須給予高度評價。”[6]除《智環啟蒙塾課》外,英華神書院的其他出版品也極為日本學界重視。陳湛頤指出:“英華書院所出版的部分書籍和報刊,在幕末時曾為專門負責翻譯的機構‘蕃書調所’所重印,在日本知識界中廣泛流傳,因此,歷次使節團:包括1860年、1862年、1867年以至1872年的使節團訪港時,不少團員都慕名前赴這所學校參觀。”[7]采購英華神學院出版品是他們接踵而往的主要目的。
三、英華書院與中文鉛活字印刷術的引介與推廣
英華書院在引介近代西方印刷術方面也發揮過重要作用,這就是鉛活字的研制與推廣。馬禮遜初抵中國時,對中國的木刻版印極為欣賞。1813年,與馬禮遜友情甚篤的東印度公司職員、正回英國休假的斯當東(GeorgeThomasStaunton,1737-1801),特意給他寄來一位叫休斯(Hughes)的印刷工研制的中文鉛字樣本與價格時,他沒有任何回應[8]。1814年7月,為印刷馬禮遜的《華英字典》(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inThreeParts),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印工湯姆司(PeterPerringThoms,1790-1855)來華,成立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TheHonorableEastIndiaCompany’sPressinMacau)。由于《華英字典》需采用中英文夾排,馬禮遜提出印刷時中英文都采用金屬活字,這樣每面可以一次印成,印好拆版后的活字亦可以重復使用,不但美觀,而且也降低印刷成本。經湯姆司嘗試后,發現中英文都以金屬活字印刷的效果的確比雕版和活字并用要好得多,遂由其負責制成鑄模用以制造活字柱體,柱體上面再以人工逐字雕刻成中文活字,漢字高度、大小以配合英文活字,從而鑄成了中國境內最早的一套中文鉛活字[1]。但馬禮遜對木刻板印的看法沒有因此改變。1816年2月,在一封信中,他仍強調板刻印刷的優點[2]。1817年,馬禮遜出版英文著作《中國大觀》(AViewofChina,forPhilo⁃logicalPurposes),堅持認為活字絕對無法與中國人的木刻板印相提并論[3]。很可能基于馬禮遜的這種識見,馬六甲傳教基地初期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及其他中文出版品均采用木刻板印。但是,馬禮遜對木刻板印的欣賞并沒有堅持到底,1820年代中期,他已改變了對木刻板印的態度,轉而認為鑄造活字才是根本之道[4]。1824年,馬禮遜利用回國休假的機會,呼吁為增進歐洲對中國的了解,必須改善中文印刷,英國應成為第一個鑄造出中文活字的國家[5]。他的呼吁雖未使英國造字工廠從事鑄造中文活字,但卻吸引一位英國青年畢生從事中文鉛活字的研制,他就是戴爾(舊譯“臺約爾”,SamuelDyer,1804-1843)。戴爾出生在倫敦附近的格林威治,1820年全家遷往帕丁頓(Paddington)。1822年萌生成為律師念頭,進入內殿(theInnerTemple),接著又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Hall)學習法律、數學等課程。1823年7月,他突然致信其父,表達了要成為海外傳教士的強烈愿望。1824年6月23日,戴爾向倫敦傳教會提出請求,獲得允準,同年夏進入高斯坡神學院(theSeminaryatGosport)學習神學和中文,后又進入馬禮遜創辦于倫敦的語言傳習所(LanguageInstitute)研習中文。在此期間,受馬禮遜呼吁之影響,戴爾開始注意中文活字問題。通過仔細計算,他發現馬禮遜中文《圣經》包含3600個不同的字,其中《新約》大約2600個[6]。
1827年,戴爾被按立為牧師后東來,他到達的第一站是檳榔嶼。在那里除繼續學習中文、傳教布道外,從1828年初開始,致力于完善中文金屬活字,“先由他的的中文教師在檳榔嶼寫好字樣,再送到馬六甲由那里的刻工上版照刻,送回檳榔嶼檢查后,再運到倫敦鑄版鋸字,然后送回檳榔嶼”。戴爾的這次試驗共刻了55塊版片,一直到1831年3月這批鉛活字才回到他的手中[7]。但具體多少字,現今已無法得知。戴爾認為,要鑄造活字,首先要確定一副中文活字究竟要包括多少個字。這次他擴大了計算范圍,既包括《勸世文》、《靈魂篇》、《新增圣書節解》等宗教性書籍,也包括《三國》、《朱子》、《國語》、《西游》等世俗類書籍,共計14種。通過兩年多的逐日計算,戴爾得出這14種中文著作所使用的漢字為3000個,其中的常用字約1200個,而一副完備的中文活字的數目是13000至14000個[8]。同時,戴爾經過前揭鑄版造字的試驗,認為只有按照歐洲的傳統方法,即“字范-字模-活字”,才可視需要隨時鑄出活字,他說:“字范是永久性的基礎,只要一副字范便可以供應馬六甲、廣州、英國或任何地方的任何活字需要。”[1]1833年6、7月間,戴爾以1827年馬六甲木刻印刷的中文圣經宋體大字為藍本,雇傭數名中國工匠開始打造字范。但最初進度很慢,導致成本很高,戴爾難以承擔,他遂發傳單向南洋、印度和廣州的外國人募捐到100鎊,并致信倫敦傳教會總部對其計劃予以資助,保證用400鎊便能刻鑄3000個鋼模。倫敦傳教會總部被其計劃打動,不僅資助100鎊,而且把戴爾的鑄字計劃向英國民眾公布,致使戴爾兩年間收到英國各地寄來的捐款達200余鎊[2]。在經費問題得以解決后,戴爾便開始刻制鋼模。1834年9月間,戴爾排印一部名為《耶穌登山寶訓》的小冊子,這是以戴爾的中文活字印刷的第一部出版品。1835年初,戴爾報道說他正生產四副活字,除一副自用,其中兩副分別為倫敦傳教會的巴達維亞布道站和美部會的新加坡布道站訂購[3]。
1835年9月,戴爾根據倫敦傳教會總部要求再度來到馬六甲,負責英華書院印刷出版,繼續進行活字的研制。鑒于法國人勒格朗(MarcellinLegrand)打造中文字范的成就,為與其競爭,倫敦傳教會要求戴爾打造大小各一副活字。收到總部要求后,戴爾嘗試性的打造出一些小的字范。1839年,戴爾陪同生病的妻子回英國,順道巴黎參觀了勒格朗用鋼模刻制的中文字范與字模。1841年,戴爾夫婦再度離英東來,1842年3月被派往新加坡布道站,與施敦力兄弟(AlexanderandJohnStronach)等一起從事鑄字印刷,且以鑄造小字模為主。1843年7月,戴爾與施敦力兄弟被派往香港。此時已完成大字1540個,小字卻只有300余字。戴爾于1843年10月24日病逝后,施敦力兄弟決定繼承戴爾的遺志。1846年,施敦力兄弟離開香港前往廈門,當時完成的大小字范已累積到3891個[4]。1847年,香港布道站雇用美國人柯理(RichardCole)繼續戴爾的工作,他是一位熟練的印工兼活字雕工,因而鑄字的速度加快,1850年時大小兩副活字都已完成約4500字,1857年時達到5584字。這兩副活字字體清晰文雅,社會需求量很大,小字尤為報紙及出版家所歡迎。因其制售于香港,又稱為“香港字”。由戴爾等研制的中文鉛活字,從1850年代初起成為中文印刷市場上最主要的活字。各傳教會、俄國、法國、新加坡政府、太平天國、兩廣總督、上海道臺、清廷總理衙門等,都先后購買過英華書院鑄造的中文鉛活字,或全套活字銅模,“他奮斗十余年的中文活字志業,確已深深影響此后一百五十年間中文印刷出版傳播的方式”[5]。華花圣經書房和墨海書館的中文活字,有些就是從香港英華書院購進的。1871年,王韜和黃勝在香港購進英華書院印字局全部排印設備和活字,籌建中華印務總局,并在此基礎上創辦世界上第一家華資中文日報——《循環日報》。至此,鉛印技術在中國迅速發展。
作者:譚樹林單位: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 上一篇:概念書書籍設計論文范文
- 下一篇:多維度書籍設計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