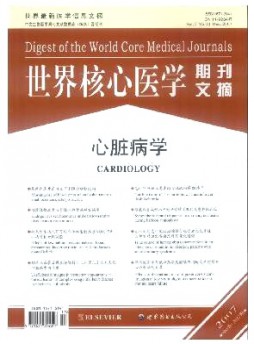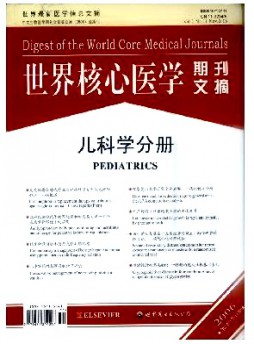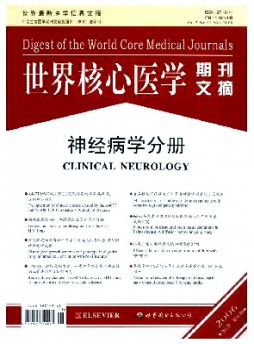核心價值觀中西文化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核心價值觀中西文化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中國與西方不同的文化基因
為了深入把握“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這一重要范疇,我們在此有必要比較系統(tǒng)地考察一下歷史學(xué)家許倬云關(guān)于“中西文明的對照”的論述。對于中西不同文化基因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許倬云認為,中國新石器文化逐步發(fā)展,從星羅棋布的農(nóng)業(yè)村落逐步融合成為幾個大的文化區(qū),再形成中原龐大的核心地區(qū),從原始的部落一步步發(fā)展到商代大規(guī)模的王國以及西周封建體制的王國,其整體的發(fā)展過程,是內(nèi)聚,是融合。這一地區(qū)面對的外來文化干預(yù)不大,外來的移民也不多,是土生土長的文明體系。西方文明的發(fā)展則遵循了另一路徑,農(nóng)業(yè)文化是外來的,不是內(nèi)聚型的融合,而是外來者的取代和演變。作為早期歐洲歷史重要組成部分的希臘文明顯示,歐洲的歷史就是一個武裝移民開拓的故事。靠掠奪、占領(lǐng)和征服,將歐洲轉(zhuǎn)化成白人的大陸。從而,“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兩者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新石器文化時代以后,中國的發(fā)展使農(nóng)村居民安土重遷,因此容易形成核心。而歐洲的傳統(tǒng)則是戰(zhàn)斗群統(tǒng)治土著居民,戰(zhàn)斗群一定要保持長期的戰(zhàn)斗精神。戰(zhàn)爭、掠奪和占領(lǐng),使印歐民族體的歐洲社會具有強大的進取心和積極性。……尚武好勇的傳統(tǒng),一直到今天仍是西方社會和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農(nóng)業(yè)社會的生活缺乏這一誘因,沒有發(fā)展出同樣的好武精神,也沒有經(jīng)常遷移和掠奪的傳統(tǒng)。”[7]此外,希臘殖民城邦以商業(yè)為主的傳統(tǒng)也成為中、歐統(tǒng)治形態(tài)差異的原因,不同于東方王國的領(lǐng)土擴張,其遠程的商業(yè)活動、殖民組織以及繁密的交通網(wǎng)等特質(zhì),在歐洲的發(fā)展史上成為一個長期繼承的傳統(tǒng)。總之,“對比中國古代的面貌和歐洲印歐化過程中發(fā)展的面貌,我們看到,其間各自保存的傳統(tǒng),終于在后來兩三千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各自發(fā)展相應(yīng)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
二、中西文化基因的歷史命運
中國進入定居的農(nóng)業(yè)社會,歐洲的古代人類則是不斷地征服和擴張,在確認了中國和歐洲兩個地區(qū)的古代人類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之后,許倬云接著考察他們?nèi)绾蝿?chuàng)造了不同的社會價值。就中國的歷史發(fā)展而言,他指出大禹治水的傳說表明,當(dāng)時家庭組織的穩(wěn)固已經(jīng)成為一個制度,而商代考古學(xué)和古代數(shù)據(jù)顯示,商人應(yīng)已發(fā)展了對親人組織的重視、對傳統(tǒng)的重視、對知識的重視三種價值觀;至于周人將天命觀念與祖先崇拜合二為一則更為重要:“周人用道德觀念來解釋政權(quán)的合法性:天命垂愛那些照顧百姓的王者。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意味著國家領(lǐng)袖必須具有道德修養(yǎng)和能力。……周人理想的‘王道’,意味著這一社會必須尊重別人,也必須容忍別人,才能建構(gòu)一個注重和諧與合作的新秩序。”[9]進一步說,夏、商、周三代陸續(xù)建構(gòu)的這些社會價值觀念留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達數(shù)千年之久,后來的諸如孔子、老子等思想家,又將這些重要的社會觀念闡釋為中國思想系統(tǒng)。與此不同,希臘文明則是建構(gòu)在壓迫和侵略的基礎(chǔ)上的。“若是跟隨著荷馬史詩分析的話,也可以說希臘人輝煌的戰(zhàn)功和歷史上的擴張乃是出于欲望,欲望轉(zhuǎn)變?yōu)樽运降膭訖C,然后又激發(fā)出強大的動力。……求更快、更多、更好、更大,永遠進取,動力非凡但不懂節(jié)制,從而對其他人造成了傷害。”[10]當(dāng)然,希臘文化確實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非常可貴的貢獻,希臘的文學(xué)和藝術(shù)成就非凡。但必須看到:“假如沒有一無牽絆的自由,假如沒有身為公民的自尊,這些成就便很難達到。”[11]在確立了中國和歐洲文明的真正開始,初步界定了中國與西方的不同文化基因之后,許倬云接著以分析中西思想的分野為基點探討中西文化基因的歷史命運。就中國而言,他強調(diào)儒家思想是中國思想體系的主軸,在西周封建制度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致力于重建超越時空限制的價值觀念,并被后儒歸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思想落實在人間事務(wù)上,是主導(dǎo)人間關(guān)系的大原則,確立人和人之間相處的尺寸與尺度。孔子將中國后世幾千年來的思想脈絡(luò)一錘定音,這是一個人間與社會的學(xué)問,而非今天學(xué)術(shù)界的認知學(xué)問。這個特點我們必須記得,它乃是中國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異。”[12]而西方思想傳統(tǒng)的來源則相當(dāng)復(fù)雜,除了兩河流域、埃及和猶太文化之外,希臘文化成為其最重要的源頭,整合成型的時間當(dāng)是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成為主流之后。“我們對比中國和西方的傳統(tǒng)可見,中國文化關(guān)注的是人間的秩序、人生在世的意義;西方關(guān)注的是超越自然和人心的理性。中國思想的二元觀,甚至多元并存的觀念,都會綜合變成辯證式的演化,成為光譜上的延續(xù);西方的二元對立則是兩元分化的永遠對抗,其間缺少折中的余地。中、西思維方式明顯分野:中國文化關(guān)心人在人間和宇宙的秩序,歐洲文化關(guān)心自然;中國的心態(tài)是追求和諧于宇宙之中,歐洲的心態(tài)則是從對抗中求得勝利。”[13]從古至今,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不斷涌現(xiàn),也常常決定了難以避免的誤解。在當(dāng)今全球化時代,如何在共存中彼此影響、相互學(xué)習(xí),一起發(fā)展出融合各方特色的共同文明,是當(dāng)代人類的使命。就中西文化圈的分合與擴展而言,許倬云強調(diào)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有復(fù)雜而高效的管理系統(tǒng)、市場化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和包容共存的多元文化,而羅馬帝國只是一個松弛的復(fù)合體,中世紀的神圣羅馬帝國更談不上具備有效的行政系統(tǒng),缺乏整合的城市和莊園兩種經(jīng)濟形態(tài)并存、排他的基督教文化的形成,勾勒了當(dāng)時中西文化基因的不同特點。在中、歐面對歷史轉(zhuǎn)折的關(guān)頭,即中國在唐宋以后,也是由于所謂蠻族入侵,重新尋找自己的秩序,文化的古代淵源再次復(fù)興。可是中國的儒家卻走向了理學(xué)的僵固結(jié)構(gòu),這一正統(tǒng)思想和政權(quán)的結(jié)合,將中國帶向內(nèi)斂,并喪失了唐宋時代多元的活力。而在中古時代晚期,歐洲發(fā)展的形態(tài)可謂是脫胎換骨,從僵化呆板的宗教專權(quán)和粗糙的封建制度,到思想、經(jīng)濟、社會各個方面都經(jīng)過掙扎,擺脫舊日的包袱,創(chuàng)造了后世歐洲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契機。這就構(gòu)成了近代以來中國遠遠地落在后面的深遠歷史背景。以歐洲為主體的近代世界,在17世紀以來的幾百年間,有了非常迅速和巨大的改變。這些改變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文明,也引發(fā)了許多問題。總之,中國和歐洲兩大文化系統(tǒng)起起伏伏,終究各走各的路。16世紀以后,東方和西方能夠直接接觸了。從現(xiàn)在看將來,“中國要從衰勢回頭的時候,歐美卻從盛況轉(zhuǎn)向衰退。……中國挾其蓄勢待發(fā)的‘動能’,‘接過’歐美留下來的制度和觀念,然而問題在于,中國人接過來的是一個正在腐爛的‘現(xiàn)代文明’,我們怎么能盼望,已經(jīng)衰敗的種子能長出優(yōu)良的果實?”[14]許倬云的上述概括說明,自古以來就走著完全不同方向的中國和歐洲,其文化基因各有千秋,其命運往往取決于自身開放或僵化的選擇,中國古代的輝煌文明和近代衰落就是一個顯證,當(dāng)代中國人應(yīng)該自覺地吸取其中蘊涵的深刻歷史教訓(xùn)。以上概括了許倬云關(guān)于中西不同文化基因及其歷史命運的論述,雖然在一篇論文中多了些,但基于“一個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傳的民族精神中來進行基因測序”的道理,鑒于為實現(xiàn)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同中華民族和中國的歷史文化相契合的要求,必須講清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淵源、發(fā)展脈絡(luò)、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chuàng)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fā)展壯大的豐厚滋養(yǎng),講清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yōu)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但由于目前我國學(xué)術(shù)界和思想界還缺少相關(guān)參考性論著的狀況,筆者這么做還是有一定理由的。上述許倬云關(guān)于中西不同文化基因的論述,盡管只是一家之言,但啟發(fā)我們認識到,中國和西方文化的不同,根源于舊石器時代,作為安定內(nèi)斂的農(nóng)耕民族,其文化基因始終不同于武裝移民、擴張征服的印歐民族。由于自秦漢以來就有了復(fù)雜而高效的管理系統(tǒng)、市場化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學(xué)作為主體的多元文化,使得中國長期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近代以來,相對于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文明的西方國家,清朝統(tǒng)治下中國將近三百年的閉關(guān)和停滯,居然能夠逃過瓜分和覆滅的危機,確實是歷史上的一個奇跡,究其原因,中國有一批“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正是這批士大夫們,以文化的力量挽救了中國,也推動中國一步步走向現(xiàn)代。據(jù)此,中國有著獨特的、綿延五千多年的文化基因,它不僅使中國長期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且即使在面對西方挑戰(zhàn)的三千年未有之巨變時,也能夠為中國人提供“挽浩劫而拯生靈”[15]的信念和力量。而一百多年來一度對自己的文化基因喪失自信、全盤西化、全面改弦更張的教訓(xùn)也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國只能走中國自己的路,中華民族只能走中華民族自己的路,中華文明只能走中華文明自己的路。借鑒和吸取所有外來的成功的經(jīng)驗,歸根結(jié)底,都必須使之能和中國的根柢、中華民族的根柢、中華文明的根柢相容、相融,而不是相悖、相害。”[16]這就是說,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作為區(qū)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biāo)識,即使在西方文明主導(dǎo)的現(xiàn)代世界,仍然是中國人堅持其精神獨立性,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獨立性的文化根基,是中國人汲取外來文明有益成果的文明根柢。在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的進程中,中國人當(dāng)然要與時俱進、勇于創(chuàng)新,推動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但這樣做的前提首先是要自覺地延續(xù)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努力傳承和守護其文化基因,否則就有可能淪為邯鄲學(xué)步。從理論上講,這實際上是一個文化基因的“返本”和“開新”辯證統(tǒng)一的過程:“所謂‘返本’,是指在復(fù)興傳統(tǒng)文化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傳承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謂‘開新’,是指在堅持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基礎(chǔ)上在全球化的新形勢下適時地開拓創(chuàng)新。因此‘返本’與‘開新’兩者互為促進的關(guān)系,‘返本’能‘開新’,‘返本’最重要的是為了‘開新’。”
三、中國文化基因與當(dāng)代治國理政
進一步說,就妥善處理中國和西方不同文化基因的關(guān)系而言,我們在確立對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自信的同時,也必須自覺地汲取雖然已經(jīng)出現(xiàn)“從盛況轉(zhuǎn)向衰退”的趨勢,但仍然在當(dāng)今世界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西方文化基因的積極成果。如果說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的文化基因安定有余、動力不足,那么我們就有必要積極引進近代以來首先在西方發(fā)展起來的科學(xué)技術(shù)、市場經(jīng)濟體制;如果說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文化基因維護社會秩序有余、保障個人權(quán)利不足,那么我們就有必要積極引進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內(nèi)部政府和公民關(guān)系中的人權(quán)、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雖然上述科學(xué)技術(shù)、市場經(jīng)濟體制和政治民主等理念是在西方社會中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來的,有其不可避免的現(xiàn)實和歷史的兩重性,但作為整個人類文明積極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都應(yīng)該在立足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基礎(chǔ)上,把它們吸收進來,揚長避短,使其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機組成部分,并達到使其既同中華民族和中國的歷史文化相契合,又同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奮斗相結(jié)合,同中華民族、中國需要解決的時代問題相適應(yīng)的要求,不僅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創(chuàng)造國內(nèi)價值觀基礎(chǔ),而且也為整個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和完善作出中國人應(yīng)有的貢獻。回顧近代以來的歷史,這樣的目標(biāo)實際上也就是梁啟超早在近一個世紀前就明確提出的:“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zé)任橫在前途。什么責(zé)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18]這樣,本文以上首先確認了“核心價值觀必須同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的思想日益為我國公民所接受的事實,并提出了為實現(xiàn)這一相契合必須有更多的人確立起“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已經(jīng)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之文化基因自信的觀點,接著用較大篇幅引證了許倬云關(guān)于中國與西方不同文化基因及其歷史命運的論述以闡發(fā)上述看法。如果這些判斷、觀點、引證和闡發(fā)言之成理,對于人們理解“價值觀是人類在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的過程中產(chǎn)生與發(fā)揮作用的。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由于其自然條件和發(fā)展歷程不同,產(chǎn)生和形成的核心價值觀也各有特點”的思想有所助益的話,那么筆者就能夠以此為基礎(chǔ)進一步探討“核心價值觀必須同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思想的基本內(nèi)涵,即什么是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當(dāng)前我們應(yīng)該最關(guān)注哪些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問題了。對此,筆者認為,在當(dāng)前能夠看到的相關(guān)文獻中,國務(wù)院副總理的一段論述給出了一個堅定而明確的回答,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國家’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獨有的概念,國與家緊密相連、不可分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為首要,治國從治家開始。只有修好身,才能理好家、治好國。中國人講的家既指家庭,又包括家族,家族內(nèi)外長幼有序,講究道德禮儀。中華傳統(tǒng)文化是倫理文化、責(zé)任文化,為國盡忠、在家盡孝,天經(jīng)地義。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些就是中華文化的DNA,滲透到中華民族每一個子孫的骨髓里。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人敢挑戰(zhàn)這八個字。家國情懷和修齊治平、崇德重禮的德治思想,把社會教化同國家治理結(jié)合起來。”[19]筆者這么說的根據(jù)在于,關(guān)于“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就是中華文化的DNA”的命題,如果完全用漢語來表達,那么這個句子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就是中華文化的基因。”由此,在當(dāng)前學(xué)術(shù)界和思想界還在就什么是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我們應(yīng)該最關(guān)注哪些基因的問題進行探討和爭論時,這一命題已經(jīng)對此給出了直接的、明確的回答,并且直指核心。從實現(xiàn)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同中華民族和中國的歷史文化相契合的要求來看,如果確立對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自信解決的是其文化自主性和根基性問題,那么“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就是中華文化的DNA”的命題解決的則是其文化規(guī)范性和影響力問題。在初步澄清了“核心價值觀必須同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之后,筆者認為,現(xiàn)在更有必要著重闡發(fā)“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就是中華文化的DNA”的命題對于深化認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規(guī)范性和影響力問題的啟示。毋庸諱言,對于什么是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對于我們應(yīng)該最關(guān)注哪些基因,即使在認同“核心價值觀必須同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的人士中間,其認識也未必充分到位。例如,盡管筆者原先已經(jīng)確立了擺脫西方中心論歷史哲學(xué)的束縛、達到文化自覺的目標(biāo),但還是認為,“儒家思想的當(dāng)代價值主要在于為當(dāng)代道德建設(shè)的一個部分——‘整個社會的道德教化系統(tǒng)’(公民德性)的建構(gòu)——提供‘傳統(tǒng)的道德根基’;至于對于當(dāng)代道德建設(shè)的另一部分,‘健全完備的政治法律制度’(制度道德性)的確立,也許應(yīng)該更多地吸取西方的文化思想資源”,[20]即認為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當(dāng)代價值主要在于其人生哲學(xué)和自然哲學(xué),而非政治哲學(xué)。因此,基于實現(xiàn)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同中華民族和中國的歷史文化相契合的要求,僅僅從其人生哲學(xué)和自然哲學(xué)而非政治哲學(xué)的角度來肯定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當(dāng)代價值,雖然已經(jīng)明顯好于過去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那種反傳統(tǒng)的狀況,但對于確立中華民族和國家的精神獨立性,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對于確立作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總根源的“文化自信”,還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承認,一談到政治哲學(xué)和國家治理問題,當(dāng)前學(xué)術(shù)界和思想界的一些人士往往會不由自主地想把西方現(xiàn)代政治哲學(xué)的“普世價值”直接、全盤地搬到中國來,成為當(dāng)代中國人在確立對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文化自信時的最后一塊短板。因此,為真正地、全面地確立當(dāng)代中國人的文化自信,為真正地、全面地實現(xiàn)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同中華民族和中國的歷史文化相契合的要求,我們不僅要充分肯定體現(xiàn)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傳統(tǒng)人生哲學(xué)和自然哲學(xué)的當(dāng)代價值,而且也更應(yīng)該充分肯定其政治哲學(xué)的當(dāng)代價值。鑒于在我國“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學(xué)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的文化基因中,原本就有人生哲學(xué)、自然哲學(xué)和政治哲學(xué)相結(jié)合的傳統(tǒng),在近代以來歐風(fēng)美雨的嚴峻挑戰(zhàn)下,雖然有學(xué)者主張孔子、《論語》和儒學(xué)的“倫理與政治的混同必須解構(gòu)”,但現(xiàn)在看來,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人生哲學(xué)、自然哲學(xué)和政治哲學(xué)相結(jié)合的文化基因并非一定要拋棄,我們完全有可能在堅持這一結(jié)合的基礎(chǔ)上汲取人類政治文明的積極成果。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會比較容易理解關(guān)于“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豐富哲學(xué)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shè)提供有益啟發(fā)”[21]的論斷。如果上述“認識和改造世界”屬于自然哲學(xué),“治國理政”屬于政治哲學(xué),“道德建設(shè)”屬于人生哲學(xué),那么就對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理解和吸取而言,顯然不僅把自然哲學(xué)、政治哲學(xué)和人生哲學(xué)都包括在內(nèi),而且特別強調(diào)了治國理政的政治哲學(xué)。例如,2014年10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xué)習(xí)時,強調(diào)要牢記歷史經(jīng)驗、歷史教訓(xùn)、歷史警示,為國家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提供有益借鑒:“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些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數(shù)千年來,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fā)展道路。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tǒng)決定的。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當(dāng)然要學(xué)習(xí)和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yōu)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國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從我國的現(xiàn)實條件出發(fā)來創(chuàng)造性前進。”[22]聯(lián)想到2014年11月11日同奧巴馬在中南海會晤時所說的,“要了解今天的中國、預(yù)測明天的中國,必須了解中國的過去,了解中國的文化。當(dāng)代中國人的思維,中國政府的治國方略,浸透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因”,[23]我們確實應(yīng)該更多地理解中國文化基因與當(dāng)代治國理政密切關(guān)系的重要性了。
四、結(jié)語
綜上所述,就深入和全面理解“核心價值觀必須同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的思想,并且在當(dāng)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過程中自覺實現(xiàn)其同中華民族和中國的歷史文化相契合的要求而言,雖然也有一些學(xué)者提出了富有啟示意義的觀點,如姜義華關(guān)于“政治大一統(tǒng),家國共同體,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強大精神支柱”[24]的觀點,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充分吸取既對中國歷史有過深入研究,又具備廣闊的世界歷史視野的歷史學(xué)家許倬云關(guān)于中國與西方的不同文化基因及其歷史命運的論述,以幫助我們確立起對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文化自信。當(dāng)然,作為一種學(xué)術(shù)研究,這畢竟只是一家之言,不應(yīng)把其成果凝固化。因此,筆者在此盼望有更多、更好的相關(guān)論著問世,使當(dāng)代中國社會能夠盡快地確立起對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文化自信的廣泛共識。而在確立了對中華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文化自信之后,我們還得解決什么是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當(dāng)前我們特別應(yīng)該關(guān)注和堅持哪些文化基因等問題。在此,筆者認為,等領(lǐng)導(dǎo)人關(guān)于“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tǒng)密切相關(guān)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就是中華文化的DNA”等命題的提出,不僅以其無與倫比的影響力,[25]而且在觀念本身方面也遠遠地走在了一些學(xué)術(shù)界和思想界人士的前面,為我們正確解決這一問題指出了方向、提供了線索。
作者:陳澤環(huán)單位:上海師范大學(xué)哲學(xué)學(xué)院
- 上一篇:唯物史觀中國文化論文范文
- 下一篇:文化差異下的中西文化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