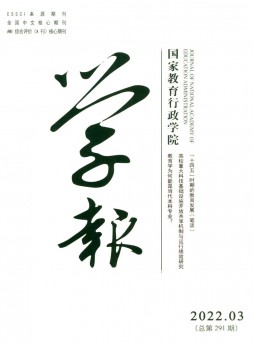教育行政的內外合作與現代化教學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教育行政的內外合作與現代化教學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蔡元培、范源濂于1912年4月26日正式上任,至7月14日蔡元培辭職獲準,時間雖不及3個月,但二人的密切合作產生了豐富成果。首先,按“能者在職”原則完成了人事重組,聘用部員67人,以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人員和學部舊員為主,奠定了民國前期教育部的人事基礎。①蔡元培回憶:“一半是我所提出的,大約留學歐美或日本的多一點,一半是范靜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經驗的多一點,卻都沒有注意到黨派的關系”②,“我(即蔡元培)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實踐,以他所長,補我之短”③。這既能保證中央教育行政的民主改革方向,又能保障教育部的有效運轉,可以說是共和政治初建時期較為理想的人事搭配。其次,地域、黨派、教育背景的不同使教育部員存在各種矛盾和派系分野,但在蔡、范二人的通力合作下,依然形成了民主、高效的工作氛圍。范源濂回憶:“在我們的合作期間,部里的人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討論很多,卻沒有久懸不決的事。一經決定,立刻執行。所以期間很短,辦得事很多。”④著名政論記者黃遠庸也非常肯定這一時期教育部的新形象:“教育部新舊雜用,分司辦事,已確有規模……蔡鶴卿君富于理想,范源濂君勤于任務,總次長實具調和性質,亦各部所未有。”⑤最后,促成臨時教育會議的召開。蔡元培視召開臨時教育會議為“全國教育改革的起點”⑥。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已有所籌劃和準備,他不僅提出了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方向的教育方針,并且帶領部員擬定了以學制為中心的各項法令草案。北京教育部重組之后,開始分司設科,部員們分工合作,進一步修改、完善了法令草案,積極籌備臨時教育會議。7月10日,在蔡、范二人及教育部員的密切合作下,召開了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臨時教育會議,它不僅標志著民國教育奠基工作的順利進行,而且為其后教育部決策樹立了典范。1912年7月26日,范源濂首次被正式任命為教育總長,至次年1月28日去職。⑦范氏之所以能夠出任教育總長,可以說是完全受惠于與蔡元培的通力合作。當時,握有內閣成員否決權的國會尚在革命派的控制之中,同盟會有推舉蔡元培出面組閣的動議,內閣中其他同盟會總長也視蔡之進退行事,由此可知他在同盟會內的地位。⑧正是蔡氏的主導,使同盟會在與袁世凱的拉鋸戰中認為“教育為范源濂人望尚符”,決定由其來擔任教育總長。⑨1912年7月26日,范源濂被正式任命為教育總長。范氏上任之時,正值臨時教育會議召開,全面籌劃全國教育大業的進程才剛剛開始,教育正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范氏雖系進步黨人,其政治主張與蔡元培并不相同,但他對蔡元培的教育理念產生了高度認同。他此次出任得到蔡元培跨越黨派的支持,加之對發展教育的執著,因而在被正式任命后即在臨時教育會議大會上聲明:“教育宗旨及行政大綱,業由蔡總長宣布或規定,悉當遵行,”表明了“蔡規范隨”的執政思路。
在這一思路指導下,范源濂堅持“能者在職”的人事原則,以“維持和擴充”為主基調,保證了人員的穩定,并對主事以下人員進行了擴充,陸續增加近70人,增強了中央教育行政機構的行政力量。執政思路的承繼和人事的擴充保證了教育部行政活動的高效率和各項工作的持續進行。1912年7月,在范源濂的努力維持下,臨時教育會議繼續加緊討論各項議題,并提前開議重點議案,最終完成了大部分議程,于8月10日順利閉幕。此后,教育部以采納臨時教育會議議決案為中心工作,出現了第一波活動高峰。此番活動并沒有因范源濂的去職而驟停,而是歷經劉冠雄和陳振先兼署時期,直至教育次長董鴻祎部務期間均得到延續。先后頒布了涵蓋教育宗旨、學校系統及各級各類教育事業的42項法令規程,初步構建了民國教育體系,①保障了政體變更之后教育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可以說,范源濂在其第一個任期里完成了對蔡元培開創民國教育事業的承繼,共同奠定了民國教育的根基,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1916年7月,范源濂第二次出任教育總長,至次年11月30日去職。其間經歷張勛復辟,但中斷時間甚短,沒有對他的執政形成實質性的沖擊。②當時的中國社會剛剛經歷過帝制之痛,傳統文化心理和尊孔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教育又處在向何處走的緊要關頭,身處進步黨陣營的范源濂的執政方向又一次歷史性地決定著教育走向。范氏上任伊始即表示要“切實實行元年所發表的教育方針”,在重要時刻明確了教育部的行政方向,為民國教育撥正了方向。③為了貫徹落實這一執政思路,范氏以“恢復和調整”為主基調,對進步黨人汪大燮和湯化龍任內形成的趨向保守的人事格局進行了大幅調整。參司以上人員方面,先是延請曾任普通教育司司長、教育部次長的袁希濤重任次長,又將辭職南下的蔣維喬重新請回部內出任參事。在秘書主事等中下層人員的任用上,范源濂收到“各方面薦書三千封之多”,④始終堅持“能者在職”原則,錄用人員以文官考試及格分部人員為主,即使秘書人員也均系對教育素有研究之人,且不問黨派出身,⑤這與汪大燮、湯化龍任內培植私人勢力和維護黨派利益形成鮮明對比,使民初良好的部風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人事恢復和調整的同時,各項工作也漸次得到開展。1916年9月7日,教育部通知各省區撤銷1915年頒布的《教育綱要》和《預備學校令》。11日又通知各省一律廢止《教育綱要》原規定之高等小學以上學校考試摘默辦法。10月9日,教育部修正了1915年頒布的《國民學校令》、《高等小學校》和1916年頒布的《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高等小學校令施行細則》,刪去“讀經”及有關內容。⑥上述舉措較好地恢復了民國初年確立的教育方針,有力地清除了帝制復辟的影響。在范源濂的主持下,承繼蔡元培的執政思路,教育部于1916年11月和1917年10月分別召開了全國教育行政會議和全國實業學校校長會議,積極采納有關議決案,推進初等教育和實業教育等,進一步完善了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建設,促進教育事業的迅速恢復和發展。⑦傅增湘近承范源濂之思路,遠紹蔡元培之余緒,并有所充實和發展,使恢復和發展教育事業的勢頭一直延續到前夕,形成了教育發展的第二個高峰。這一高峰離不開范源濂的努力及其對蔡元培執政理念的承繼和發展,是二人合作持續影響的結果。
1920年8月11日,范源濂第三次任教育總長,次年5月14日去職。⑧新文化運動和后,文化教育界思潮激蕩。能否順應這一文化發展潮流推進教育改革,成為中央教育行政部門決策成敗的關鍵。同時,中央政府更迭頻繁,中央教育行政處于弱勢,而民間教育力量則迅速加強。基于這一客觀形勢,范氏人事調整的主基調為“溝通和提效”,反映了其應時順變的用意。后,教育界的民主意識增強。范氏一方面吸收北京教育界資深人士,增強與北京教育界的溝通;另一方面裁汰教育部冗員以提高行政效率,①使教育部雖處亂局卻仍保持了正常有效的運轉。直到1926年任可澄上任后,這一時期形成的居于教育部核心決策地位的參司人員格局才有了實質性變動。從這一點來講,蔡、范二人合作對教育部人事的影響幾乎貫穿了整個民國前期。這一時期,教育部的活動特點也隨外部環境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之后,北京政府對教育界特別是高等教育界開始采取強硬政策,教育部全面推進教育事業的勢頭受阻,改為重點推進的策略。范源濂領導下的教育部把大力整頓高等教育作為工作重點,主要是成立專門以上學校視察委員會,制定相關規程和細則,順應教育文化界推進教育和文化普及的要求,積極推進義務教育和國語運動。他還延續民初應對教會學校的思路,支持民間要求對教會學校采取措施的呼聲,積極致力于收回教育主權等。
②范源濂堅持民初的人事原則和教育方向,積極應對社會環境的變化,使教育部在動蕩時局中形成了第三次行政活動高峰。范源濂在三次任期內均堅持、繼承和發展了蔡元培在民初所確立的諸多行政原則和所進行的各項教育改革,從而對這三個時期的中央教育行政活動和全國教育事業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由于范氏這三次任期均處于民國前期的重要歷史節點,使其任內的舉措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后續效應,從而擴大了蔡、范二人合作所產生影響的時空范圍。三范源濂第二次任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后,面對帝制干擾和兵燹沖擊下滿目瘡痍的教育事業,積極開展恢復和整頓工作,其中一項重要舉動就是1916年8月26日致電遠在歐洲的蔡元培,邀其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實現了蔡、范二人中央教育行政內外的合作。③對范源濂而言,邀請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并非一時沖動,他主要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是蔡元培對高等教育向為看重并素有研究,恰好與范源濂注重普通教育形成互補,二是高等教育在民初發展緩慢而急需整頓。當然,兩人之所以能實現再次合作,更重要的是在第一次合作中形成的超越黨派和個人利益的“肝膽相期”的關系使然,是為民國教育樹立百年大計的合作在新形勢下的延續。④蔡元培接到邀請后,于10月初即啟程返國。
12月26日,總統黎元洪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⑤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開始了蔡、范二人的再度合作。⑥這一合作標志著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整頓高等教育的真正開始,拉開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雖然蔡、范二度合作的成果主要是在范源濂第二次任期內完成的,集中體現在大學改制的成功進行。蔡元培上任之后,立志“使大學為全國文化的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⑦。1917年1月27日,蔡元培即向京師國立高校校務討論會提交了大學改制議案。蔡元培認為,德國和日本高等教育中的普通大學與專門學校的科目無差別而僅是程度不同,而中國仿效德、日的高等教育制度時間不長,所以這種現象在國內尚未顯現。為使中國高等教育力避上述弊端而健康發展,他主張“大學專設文理兩科,其法、醫、農、工、商五科,另立獨立之大學,名曰法政大學、醫科大學、農科大學等”,一則改變民初大學設學門檻過高之弊,二則明確區分普通大學及分科大學之功用,強調學科設置上的互補以避免重復。他還主張將“大學均分為三級:(1)預科一年,(2)本科三年,(3)研究科2年,凡6年”,意在整體縮短大學教育的年限,力圖讓更多的大學畢業生進入研究科學習。30日,與會校長公呈教育部核準了這一提案。①教育部高度重視這一大學改制案,2月23日召集專門會議進行討論。
“列席者總次長、參事、專門司司長、北洋大學校長,及具呈各校長”,核心人員全部出動,足以顯示教育部的積極態度和迅速行動。與會人員對改制案第一條“無異議”,但“于第二條,則多以預科一年之期太短,又有以研究科之名為不必設者”,建議付京師國立高校校務討論會復議。25日,京師國立高校校務討論會議決“大學均分為二級,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凡六年”。3月5日,教育部又召開專門會議,與會人員對第二條改正意見均無異議。3月14日,教育部發出部令:“改編大學制年限辦法,經本部迭次開會討論,應定為預科二年,本科四年。”②快節奏的議決,表明范源濂領導下的教育部對蔡元培牽頭所形成議決案的高度重視和密切配合。由于修正大學法令規程尚需時日,而大學改制工作又刻不容緩,6月28日,教育部規定:“各大學在規程未經修竣公布以前,欲照改定年限辦理者,應將各科詳細課程斟酌妥訂,呈部核定再行遵辦。”③與此同時,相關法令規程的修改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9月27日,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學令》:“一,凡設兩科以上者皆可稱大學;設一科者,稱某科大學。二,大學本科修業年限改為四年,預科二年。三,大學教授改分正教授、教授、助教授三等,講師仍舊。四,廢止各科教授會,凡各科事項必須開會審議者,由各科評議員自行議決。”
④蔡元培的提議大多被采納。修正《大學令》必然要求相應修正《大學規程》。蔡元培認為原有規程中“分年級之制,與小學校無異,大學當純擇一科完全之編制法”,“至于輔助學科則聽學子之自擇”,大力提倡選科制,并向教育部報送極為詳細的說明。為集思廣益,教育部延請法科大學、法政專門學校的教員,于11月15日召開專門會議討論《大學規程》之修正,而具體修改內容以選科制為中心。⑤大學改制最直接的影響是促發了專門學校升格潮,改變了高等教育的整體格局,擴大了高等學校的分布范圍,也影響了教育部高等教育政策的走向。據統計,1917—1925年,中國大學由10所增加到47所,各類專門學校則從96所減少到58所,⑥大學與專門學校出現了此消彼長的態勢,“學”、“術”分立和互補的高等教育格局形成。因應大學數量的發展,教育部將全國分成7個大學區域,每區各設分科大學一所,以引導大學改制之下出現的專門學校升格潮。⑦至1925年,高等學校雖然仍集中于京滬地區,但分布范圍已經拓展至全國,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各省區對高等教育的需求。⑧大學改制使大學數量激增的同時,引發了質量下降的問題,教育部遂開始整頓高等教育,這一努力一直進行至北京政府結束之前。修改和頒布《大學令》后,1918年10月教育部召開專門以上學校校長會議,會上與大學教育有關的交議19件,其中教育部17件,北京大學2件,可見此時高等教育改革仍有賴于北京大學與教育部的合作。會后,教育部采納有關議決案,出臺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法令規程,逐步完善高等教育各項制度建設,對大學及專門學校的新生招考、學科設置、學術研究、師資管理等作出更為詳細的規定,①保障了大學改制之后高等教育改革的順利推進。1919年4月,教育部又組織了教育調查會,由蔡元培、范源濂擔綱,對教育存在的問題尋求解決辦法,主要規定了大學規程及各類專門學校規程、專門學校學科設置以及高等教育學位授予等,并且形成了相關議決案,直接推進了高等教育制度建設。②1922年,教育部頒布了“壬戌學制”,全面確認此前大學改制的成果,大學采用選科制,使高等教育開始注重學生的個性發展,還建立了男女平等的單軌教育體制。③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公布了《國立大學條例》,進一步吸收了大學改制以來高等教育的變革成果,④“標志著中國高等教育在經歷了新文化教育運動以來近十年的改革,新的體制最終完成”⑤。蔡、范二人的合作對這一過程的推進具有重要意義。有關法令規程在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的貫徹落實也是大學改制的重要影響。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學率先進行改制工作。首先是重新組織大學評議會,把民初未能施行的“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落到實處,并通過頒布北京大學《學校內部組織試行章程》,從行政上確立教授治校的基本格局。
⑥其次實行“廢門改系”,意在打通文理界限,進行通才教育,培養高層次學術人才,這些舉動“逐漸被界內人士所認同,而且廢門設系成為各大學20世紀20年代以后學科結構體系變化的基本趨勢”,推進了學科設置的現代化進程。⑦此外,北京大學于1918年開始試招女生。對此,最初教育部采取慎重的態度,⑧但1919年后“國內各大學多數予女生以求學權利”⑨,女子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最終得到實現。北京大學還率先實行選科制和學分制,尊重和保障學生個性和潛力的發展。在蔡元培領導下,北京大學通過上述改革措施率先完成了向現代大學的轉變,其他大學也紛起效仿,中國高等教育早期現代化得了巨大進展。總體而言,蔡元培和范源濂秉承教育救國的堅定理念,實現了跨越黨派的精誠合作。在中華民國前期艱難復雜的社會環境中,蔡、范二人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教育樹立百年大計的目標付出努力,詮釋著動蕩時局下學人追求教育救國的信念,其跨越黨派的合作精神和對教育事業的忠誠態度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輝,值得我們在推進當代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征程中繼承和發揚下去。
作者:田正平閻登科單位:浙江大學教育學院
- 上一篇:公共選擇概念下的教育行政探析范文
- 下一篇:高校教育行政行為探討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