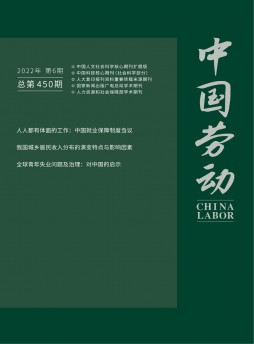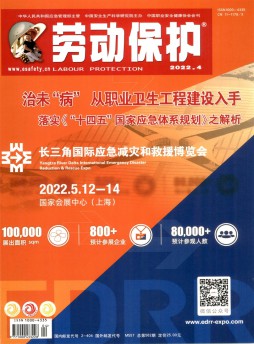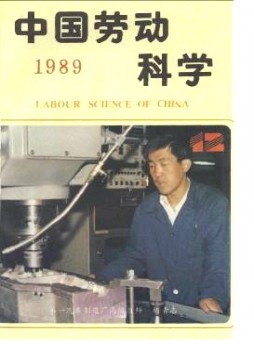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完善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完善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作為化解勞動爭議的一項重要制度,憑借其程序簡便、成本低廉、方式靈活等特點,成功地解決了大量的勞動糾紛。然而該制度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和效果,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非專業性,包括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的非三方性和勞動爭議調解組織的調解員的非職業性;其次是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的設立比例低,并且其受理范圍有限;再次,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公信力不強;最后,各勞動爭議調解組織之間對勞動爭議存在管轄問題。基于此,應組建獨立的、中立的勞動爭議調解機構,確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具體規則,把集體爭議納入勞動爭議調解的范圍等。該制度的完善能夠使更多的勞動爭議在進入仲裁之前便能得到解決,從而減輕我國仲裁機構和人民法院的壓力,節約司法資源。
關鍵詞:勞動爭議;調解制度;調解組織
一、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界定及發展
(一)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界定
隨著勞動法律法規的紛紛出臺,我國基本確立了以協商、調解、仲裁和訴訟為內容的勞動爭議處理體系。在這個體系當中,協商程序和調解程序不是必經程序,而仲裁程序是訴訟程序的前置程序。勞動爭議調解制度,是由勞動調解組織針對勞動爭議雙方當事人,通過充分溝通和民主協商,促進相互之間的理解,自愿達成調解協議,最終解決勞動爭議的一種制度。本文研究的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特指勞動爭議案件進入仲裁程序之前的調解,包括企業內部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基層人民調解組織的調解和鄉鎮、街道調解組織的調解。
(二)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發展
1987年,國務院頒布了《國營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暫行規定》,規定企業在內部設立調解委員會,初步確定了“三方代表”原則,有力地推動了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發展。1993年,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和勞動部頒布的《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組織及工作規則》,標志著現代意義上的勞動爭議調解制度開始建立并發展。1994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71條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確定了“一調一裁兩審”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將勞動爭議的范圍延伸到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并擴展到事實勞動關系中發生的爭議。2007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對勞動爭議調解制度進行了具體規定,該法將勞動爭議調解組織的范圍擴大至三個。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第76次部務會審議通過的《企業勞動爭議協商調解規定》,對勞動爭議調解制度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該規定對企業調解委員會的設立、組成、職責、調解員擔任條件及其職責、調解程序、調解協議等均作出了明確規定。
二、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非專業性
一是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的非三方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了企業調解委員會由內部職工代表和企業代表組成,并沒有中立的第三方參與其中,這便使得調解制度脫離了其本質屬性,即調解應是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進行。而企業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人員都是企業內部人員,他們同勞動爭議雙方不可避免地會有親疏遠近之分,難以保證其能站在中立的立場上去開展調解工作。二是我國勞動爭議調解組織調解員的非職業性。勞動爭議能否調解成功往往在于調解人員能否發揮關鍵作用。所以勞動爭議調解制度能否發揮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調解人員的職業性。我國目前相關法律法規對勞動爭議調解員的任職條件的規定還比較寬泛,主要強調的是政治素養,而忽略了其調解的專業性[1]。
(二)企業調解委員會設立比例低,受理范圍有限
我國目前的勞動爭議調解機構有三種,由于權威性不高和專業性不強等原因,使得基層人民調解組織和鄉鎮、街道的調解組織不能有效處理大多數勞動爭議。企業調解委員會是當前勞動爭議的最主要調解組織,但是依法設立調解委員會的企業比例很低,或者雖然設立了但不能有效地開展調解工作。《企業勞動爭議協商調解規定》在調解委員會的設立方面,規定大中型企業“應當”設立,而小微型企業“可以”設立。企業內部設立的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欠缺開放性和中立性,使得其受理勞動爭議的范圍受到限制:它只負責處理發生在企業內部的個體爭議,不能處理勞務派遣引起的勞動關系較為復雜的勞動爭議,且由于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以及企業調解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使得調解委員會不能處理集體勞動爭議。
(三)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公信力不強
一是我國勞動爭議調解沒有行政權力的介入。因為沒有最有影響力和公信力的政府部門作為第三方介入勞動爭議的調解,使得勞動爭議調解的結案成功率不高、達成的調解協議得不到完全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雖然將勞動爭議調解組織擴大至三個,從形式上建立了橫向化的調解模式,但這種橫向化的調解模式難以在實踐中發揮應有作用。二是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問題未能有效解決。如果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能夠得到法律的確認和保障,那么勞動爭議雙方當事人就會嚴肅對待并積極履行已達成的調解協議,從而使得調解結果能夠得到全面落實。但在現實中,由于法律未明確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即使雙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已達成的調解協議,也不會有任何不利后果。正因為我國調解制度的公信力不強,導致勞動爭議調解成功的數量不多,很多未經調解直接進入或者調解未成功轉而進入仲裁程序。
(四)勞動爭議調解組織之間的管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將勞動爭議調解組織的范圍由一個擴大至三個,即該法確立了橫向式的調解模式,使勞動爭議當事人如果想以調解方式解決勞動爭議,既可以向企業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也可以向外部調解組織申請調解。從法理上說,如果某類案件有多個管轄組織,那么法律就一定得規定這些組織之間各自管轄案件的范圍。橫向式的勞動爭議調解應當確立企業調解委員會與其他調解組織之間的調解勞動爭議的范圍[2]178。但該法沒有確定這三種勞動爭議調解組織各自的案件管轄范圍。如果勞動爭議雙方當事人均向同一調解組織申請調解,不會涉及管轄范圍問題,但如果一方當事人向企業調解委員會提出調解申請,而另一方當事人向外部調解組織提出調解申請,那么就存在誰有權進行調解的問題。
三、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完善對策
現行勞動爭議調解功能的弱化,主要是由企業內部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的的內部性和結構上的封閉性造成的。由于沒有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目前大多數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和三資企業,并未建立內部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而且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的組成往往包括工會,所以也不適宜由其處理集體爭議。因此,建立專門的、獨立于企業之外的勞動爭議調解機構應當是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并由法律法規確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具體規則。
(一)組建獨立的、中立的勞動爭議調解機構
按照“三方原則”,由政府行政部門(勞動保障部門)牽頭并作為中立方,與用人單位組織代表(企業團體代表)和勞動者組織的代表(工會代表)一起,組建勞動爭議調解機構。該調解機構分為三級:省級、市級和縣級,大量勞動爭議由縣級調解機構處理,部分勞動爭議由市級調解機構處理,具體受理范圍由法律法規加以確定,省級調解機構不負責調解具體的勞動爭議,只是行使對下級調解機構的業務指導和人員培訓工作。獨立于企業之外,由政府行政部門負責管理的勞動爭議調解機構,實際上可以稱為企業之上的勞動爭議調解機構,由于政府行政權利的影響,對于企業而言具有權威性和震懾性,因此調解成功的可能性很大[3]149。該勞動爭議調解機構雖由勞動保障部門主導,但獨立于勞動保障部門和政府之外,其地位應當由法律法規加以確定,成為勞動爭議調解的主要機構。
(二)確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具體規則
調解相對于仲裁和訴訟的優勢,在于其所具有的靈活性、多樣性和非正式性等特點,使得勞動爭議能夠迅速快捷地得到處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無規則可循[1]。對于按照“三方原則”組建的勞動爭議調解機構,由法規或規章制度來明確其調解制度的適用規則,并適當考慮道德、習慣以及公序良俗。首先,是關于勞動爭議調解程序的規定,調解機構需要依照規定的程序來進行調解,畢竟程序是保障公平正義的前提,但是該調解程序不必像仲裁或訴訟那般嚴苛,并規定勞動爭議當事人在調解活動中享有的權利及應履行的義務。其次,要明確勞動爭議調解人員的任職資格條件,選拔專業性的勞動爭議調解人員,并由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定期對其進行業務培訓。再次,要增強勞動爭議調解協議的效力,可以仿效2010年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對調解協議的規定,即經調解機構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后,爭議雙方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經司法確認的調解協議具有強制執行力,且爭議雙方可在達成的調解協議中約定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已生效調解協議的一方將向另一方支付約定數額的違約金。最后,在調解費用方面,實行調解完全免費的政策,從而最大程度地降低當事人解決勞動爭議的成本,使越來越多的勞動爭議在調解程序就得到解決,從而能夠減輕仲裁和訴訟的壓力[4]。
(三)把集體爭議等納入勞動爭議調解的范圍
在現行法律制度下,企業調解委員會的受理范圍有限,這使得某些勞動爭議,如勞務派遣爭議、集體勞動爭議,在調解環節得不到解決。對于集體爭議,我國現行處理體制并沒有將其納入調解機構調解的范圍,只是規定雙方發生集體爭議后,應當通過協商和政府主管部門協調解決,對于能否進行調解以及由何機構調解并沒有作出規定。在現行企業內部的勞動爭議調解機構組織調解的模式下,集體爭議確實不應當由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組織調解。因為集體爭議一般由工會代表勞動者發起,如果由企業調解委員會組織調解,會發生工會既是當事人又是調解活動組織者的尷尬局面。在組建了獨立的、中立的勞動爭議調解機構之后,把集體爭議納入其調解范圍,使集體爭議從談判、簽訂到履行過程中發生的爭議都能夠得到及時調解,對于集體合同制度的健康發展是很有意義的。新組建的調解機構的受理范圍將得到擴大,使得幾乎所有的勞動爭議都能在調解環節得到有效處理。
參考文獻:
[1]李雄.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理性檢討與改革前瞻[J].中國法學,2013(4):158-168.
[2]蘭仁迅.勞動爭議解決機制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
[3]侯海軍.勞動爭議調解、仲裁和審判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王劍.我國現行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分析及重構[J].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56-61.
作者:袁亞萍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
- 上一篇:探析行政事業單位財務內部控制范文
- 下一篇:大數據在交通優化上的運用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