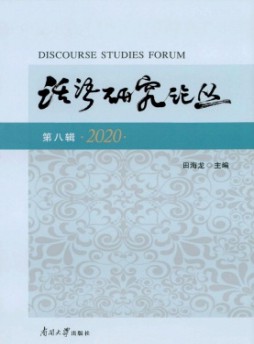話語創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話語創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詩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例證。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推動者,對傳統詩詞進行了馬克思主義改造,在話語創新上表現為:詞中抒情主體的嬗變和壯美詞境的開拓,從而開創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格律上繼承性與創新性有機統一;秉承“詩言志”,又眼光向下;“文藝為大眾服務”的生動實踐;豪放大氣等美學特質。
[關鍵詞];詩詞;話語創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2013年3月1日,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許多老一輩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學素養,在詩詞歌賦方面有很高的造詣。”[1]同年底,在紀念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大量地引用詩詞,用“詩人的語言”去闡釋生平和思想。不難理解,是“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新中國開國功勛子嗣,自幼熟讀詩詞,在其治國理政的系列重要講話中,引用詩詞的地方同樣不勝枚舉。如2012年2月14日,在出席中美企業家座談會時,引用“風物長宜放眼量”(《七律•和柳亞子先生》),對兩國的企業家提出殷切希望,勉勵他們要心存大局,摒棄“小我”,推動中美兩國經濟的長期共榮和發展。2012年11月29日,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引用“雄關漫道真如鐵”(《憶秦娥•婁山關》),回顧了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砥礪前行;用“人間正道是滄桑”(《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闡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得來不易,飽含艱辛、玉汝于成。本文主要探討詩詞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聯系和辯證關系,以及其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話語創新。
一、詩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例證
作為早期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理論先行者,不僅誕生出如《矛盾論》《實踐論》等煌煌理論巨著,作為一個國學功底深厚的文人,他的這種情懷一樣也體現在詩詞中。詩言志,歌詠言。如果從早年的《無題•孩兒立志出鄉關》算起,到1975年的絕筆之作《訴衷情》,所存詩詞不僅數量可觀①,而且時有精品問世,可謂詩人情懷、無詩不歡,樹立起一個“經綸外,詩詞不輟”的詩人形象,令后人高山仰止。斯大林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2]列寧說:“沒有‘人的感情’,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對于真理的追求。”[3]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質上講,就是要把德國舶來的馬克思主義入鄉隨俗,講民族語言、說鄉間俚語。這一點,的造詣無人能及,舉凡文章、詩詞,無不表現出一種別開生面的“中國氣象”,特別是詩詞“極為生動形象地體現了作者本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思想”。概而言之,詩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例證”[4]。然而,現存詩詞作品中,詞的數量和質量又略勝于詩。曾說自己“偶爾寫過幾首七律”,“(但)沒有一首是自己滿意的”,“對于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5]。換言之,他似乎對于詞更情有獨鐘。日本學者竹內實甚至認為,應該叫“詞人”更恰當一些[6]。盡管詩詞的形式是傳統的,但詩詞的內容卻是馬克思主義的,達到了一種鹽溶于水、運化無痕的至善境界。
二、對傳統詩詞美學特質的馬克思主義改造
如前所述,創作的“詞”要略多于“詩”,而“詞”作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匯,在馬克思主義原典語言中并不存在一個相應的語匯來直接對譯,在日語里,“詩”與“詞”的發音差別不大。可以說,唯有“詞”,是土生土長的地道中國語言。從對舊體詩詞的改造,更可以透視出其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用臻于至境的功力。
(一)詞中抒情主體的嬗變
傳統詞興起于隋唐時期,是在近體詩確立之后,逐漸出現的一種“新變”的產物。作為當時最為流行的文學形式之一,詞的主要功能在于吟唱,是由伶工依律創作后,交付“十七八女郎”“手執紅牙檀板,淺斟低唱”。到了柳永,詞的意境又為之一變,舉凡城市風光、歌伎生活,無一不可入詞,尤其長于抒寫羈旅行役。詞至蘇軾又一變,他將詞這種“詩余”的文學地位進一步提升,堂堂正正走進文學殿堂,成為可以抒寫性情的“士大夫之詞”。從這個意義上講,蘇軾的出現把“詞”男性化了。而作為后起巨擘的,并不滿足于此。他客觀冷靜地指出“婉約”“豪放”兩種創作風格之短長:“婉約派中的一味兒女情長,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鐵板,讀久了,都令人生厭的。”[7]下文以時間為序,擷取寫給發妻的三首詞,《賀新郎•別友》(1923年)、《蝶戀花•答李淑一》(1957年)、《卜算子•詠梅》(1961年)作一分析。與妻子情意篤厚,但這種情感又非“昵昵兒女”,是一種“丈夫志四海”的職業革命家情懷。這在《賀新郎•別友》中流露得淋漓盡致。毛與楊雖是新婚小別,情所不忍,但為了革命前程,青年拋家舍業,毅然與妻子離別,“汽笛一聲腸已斷”,顯然是新時代的新氣象。1973年,已屆古稀的“舊事重提”,把上闕結尾“重感慨,淚如雨”,改為“人有病,天知否?”;把下闕結尾“我自欲為江海客,更不為昵昵兒女語。山欲墮,云橫翥”,改為“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臺風掃寰宇。重比翼,和云翥”[8]51,對原句進行了較大語義上的修改,從而徹底摒棄了傳統婉約詞的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但“重豪放,又不偏廢婉約”,兩者情韻兼而有之。在《蝶戀花•答李淑一》中,作者的情感呈現出“悲慟—紀念—高興—寬慰”這樣的脈絡。對于發妻和戰友柳直荀的犧牲,已沒有了早年的“心有戚戚”,而是洋溢著一種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后來章士釗問:為什么把稱作是“驕”?答道:“女子革命而喪其元,焉得不驕。”[8]56-57對妻子的英年早逝遺憾中充滿崇敬,想象著他們在彼岸世界始終關注著中國革命的前途,就連嫦娥仙子、神仙吳剛都為英雄所折服,舒廣袖、捧美酒,熱情招待。在《卜算子•詠梅》中,將美麗的化身為“凌寒獨自開”的梅花,她不驕不躁,卻壓倒群芳,令人心折。詞的節奏和色彩皆明快、曉暢,令人不禁對女革命家的形象嘆服。
(二)壯美詞境的大力開拓與抒情
主體相對應,傳統的詞境偏于旖旎柔美,是一種“男子作閨音”,詞的境界格調不高。詞至稼軒,始出現壯美的意境和金戈鐵馬的真英雄。該詞通過工筆描繪的幾個軍旅倥傯的場景,刻畫出一位久經戰陣、驍勇善戰的英雄形象,或許也是詞人自況。這種英雄可惜在后世的詞作中并不多見,要么是文弱書生強作豪強之語,頓覺突兀;要么是赳赳武夫文白交雜,詩味闌珊。可以說,只有兼具“文采”和“武功”二美,才能寫出這樣的英雄之詞。世所罕見的軍事生涯和過人的詞學功底,很好地繼承了稼軒詞的這一衣缽,又能多出藍之作。這里我們以長征途中創作的7首詩詞為例:《十六字令三首》(1934至1935年)、《憶秦娥•婁山關》(1935年2月)、《七律•長征》(1935年10月)、《念奴嬌•昆侖》(1935年10月)、《清平樂•六盤山》(1935年10月)、《六言詩•給同志》(1935年10月)、《沁園春•雪》(1936年2月)。可以說,這七首詩詞高度紀實地還原了長征途中的波瀾壯闊。有行軍途中踏遍千山的滄桑感,對山之高、山之險峻、山之綿延的譬喻無不貼切、生動。據不完全統計,長征中一共翻越了二十多座大山,包括江西雷嶺,廣東苗山、大小王山、大盈山,廣西永安關、白茅隘,貴州紫金關、婁山關,四川小相嶺、冕山、大相嶺、夾金山、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拖雷崗、臘子山、分水嶺,甘肅朵扎里、岷山、六盤山。有激烈的戰斗場面,“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令人感到戰爭肅殺之氣氛。婁山關位于遵義城北的最高峰,是拱衛遵義的天然屏障。當年參加過這場戰役的成仿吾回憶:“我軍猛攻婁山關高地點金山,經過肉搏,占領了這個制高點,然后連續沖鋒,把敵人完全擊潰,傍晚占領了婁山關關口。”后來回憶這首詞的創作緣起:“萬里長征,千回百折,順利少于困難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8]112有對紅軍大將的獎掖之詞,鼓舞士氣、提振人心。后來回憶:“戰斗結束后,我回來時看到桌子上寫的這首詩。詩的第一句恰好是電報里的那一句,只是把其中的‘路險’寫成了‘路遠’,把‘溝深’寫成了‘坑深’,我當即拿起筆來,把最后一句‘唯我彭大將軍’,改成‘唯我英勇紅軍’,又放回了原處。”[8]122據說在1947年轉戰陜北的時候,率西北野戰軍取得米脂縣沙家店大捷,重新書寫了這首詩贈與。有兼濟天下的普世情懷,“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環球同此涼熱”。昆侖山,主脈位于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交界處,東段分三支伸展,其南支向東延伸后與岷山相接。因此紅軍長征時所經過的岷山,也可看作是昆侖山的一個支脈。后來回憶:“昆侖:主體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別的解釋不合實際。”[8]120也有勝利后的喜悅,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其后自注道:“蒼龍:,不是日本人。因為當前全副精神要對付的是蔣不是日。”[8]121更有三軍會師的笑顏逐開。長征勝利會師后,當年的親歷者吳玉章回憶道:(過岷山那天)“天氣特別晴朗,……我們很快登上了岷山的山頂,從山頂遠望山下的田野,牛羊成群,農民在田間辛勤勞動,大家很愉快地像潮水般涌下山去,到了大草灘宿營地。在漢族人的熱誠歡迎中,我們很快進入了村子。”[8]117這與“三軍過后盡開顏”寫的是一樣的心情。還有指點江山、舍我其誰的雄蠻之氣。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創作的這一組長征詩詞,以其壯美意境的開拓,也足以橫絕古今,為20世紀的中國詩詞留下一座高峰。
三、詩詞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
王國維有言:“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9]郭沫若評價的詩詞是“經綸外”的“余事”。可以說,正好是把詩人和政治家的眼光統一起來,把詞人的婉轉綢繆和政治家的經世致用統一起來,在語用主體上變才子佳人為職業革命家,在風格意境上變旖旎綺麗為壯美闊遠,從而突破了傳統詞的“情”“理”糾葛和意境藩籬,成為近代以來詞的集大成者。
(一)格律上繼承性和創新性的有機統一
有著豐富的詩詞創作實踐,他一貫主張詩詞創作應秉持民族的傳統形式:“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10]認為,格律不是束縛詩人創作的“鐐銬”,而是授人以法的“向導”,“掌握了格律,(詩人)就覺得有自由了”[11]。有國學功底,這使得他在創作舊體詩詞上游刃有余。以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毛譯東詩詞集》中的“正編42首”為例,大多經過其本人的親自審定和校閱。這部分詩詞大體上能夠嚴格按平仄、對仗等格律要求來創作,讀來音韻和諧、朗朗上口,這是他能夠繼承傳統詩詞平仄格律的一面。另一方面,與生俱來的革命家氣質,又使得他不拘泥于格律的束縛,體現出創新性的特點。有時甚至不惜打破音律,防止簡單的“以文害義”。如“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中的“仍”字為平聲字,按格律此處應用仄聲;“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中的“八”字按“平水韻”系仄聲,“八萬里”成了“三仄尾”;《蝶戀花•答李淑一》上片用的是“平水韻”上聲中的“二十五有”韻,下片用的是“平水韻”上聲中的“七虞”韻。其實,只要大家熟讀詞史就會知道,就連蘇軾和辛棄疾這樣的大家,在部分詞作的音律方面也會有不嚴謹的地方。關鍵是要處理好“求正”和“容變”的辯證關系:“求正”即盡可能恪守音律;“容變”即必要時可根據內容對格律作適當調整。為此,曾提議:現代人寫舊體詩在詩韻上要適當放寬,時機成熟時有必要編一部新時期的詩韻表,供大家寫詩時參考使用。
(二)兼濟天下眾生的入世情懷
詩詞能夠秉承“詩言志”,又眼光向下,具有強烈的入世精神和現實懷抱,實現了傳統詩詞從“小我”向“大我”的躍升。近代以來,傳統詩詞同華夏文明一樣,曾一度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戰和沖擊,面臨著“無用之學”的拷問。這種舊的文學創作形式,能否與時俱進,挾歷史潮流而涅槃重生,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沉重話題。詩詞的出現,使傳統詩詞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他的詩詞緊扣中國革命、建設脈搏,與人民群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彰顯出傳統詩詞的現代生命力,傳統詩詞的面貌為之煥然一新。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古典詩詞的現代轉型,用它來反映戎馬生涯,反映軍事戰爭,這在過去的詩詞創作中是不曾有過的。可以說,是用詩詞來寫史,他的詩詞與史事做到了雙璧合一,也即詩史合一,是繼承了杜甫精神的史詩作品,成為至今傳誦不衰的重要原因。曾幾何時,詩詞家弦戶誦、婦孺皆知,成為宣揚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工具,同時也推動了傳統詩詞的普及,使詩詞真正成為土里長出來的果實,老百姓喜聞樂見,從“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三)“文藝為大眾服務”的生動實踐和有力注腳
如前所言,詞中的語用主體已經發生了重大嬗變,首次把人民的主體地位貫穿其中,成為一種“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學創作形式。有了這樣的創作宗旨,詩詞那些詩意盎然、膾炙人口的美言佳句,無不是以謳歌和贊賞人民群眾為主要內容。如“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嘆服工農群眾所蘊藏的無窮力量。“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詮釋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樸素的道理。“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對在舊社會罹患疾病的人民群眾恫瘝在抱。“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贊美人民當家作主的今非昔比。在《賀新郎•讀史》中,更是通篇貫穿著歷史唯物主義和群眾觀點,“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蹻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對人民力量的贊美溢于言表。
(四)豪放大氣的藝術風格
曾對自己詩詞的藝術風格有過這樣的評價:“我的興趣偏于豪放,不廢婉約。”是湖南人,的詩詞特色,如用湖南話的一個詞來概括就是“霸蠻”,即豪放大氣。少年時曾手書一首七絕《詠蛙》: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成功地塑造出青蛙性格耿介、嫉惡如仇的莊稼衛士形象,其中“如虎踞”“敢作聲”等措詞充滿霸氣,試想一個少年竟然有如此氣量,令人不敢小覷。通觀詩詞,喜歡用表現豪邁情懷的大詞,名詞上喜歡用天、海、山;量詞上喜歡用億、千、萬,特別是“萬”字,引用頻率較高。如“看萬山紅遍”“萬里雪飄”“一萬年太久”“萬類霜天競自由”。使用大詞比較集中的如《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這首詞僅62字,卻用了3個“天”、3個“萬”、2個“千”,還有“沖霄漢”“紅旗亂”“風煙滾滾”這樣的大詞,真是讀后令人酣暢淋漓!再如《沁園春•長沙》,“萬山”突出山之多,“萬類”突出大自然的生機勃勃,“萬戶侯”突出青年的蔑視權貴,“百侶”突出同儕人數之眾。這些大詞的使用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營造出一種豪放、開闊的意境和氛圍。從詞的發展脈絡來看,詩詞的橫空出世,正好處于傳統詞的深刻變革期。前有秋瑾、柳亞子的鼓噪作勢,以運斤成風的巨擘風范,成功解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無法解決的傳統與創新的分野。通過對傳統詩詞話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改造,以新的意境、新的語詞開創出一代詞風,成為傳統詩詞與時俱進、與時偕行的光輝典范。
[參考文獻]
[1].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J].理論視野,2013(3):7.
[2]斯大林.斯大林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75.
[3]列寧.列寧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17.
[4]靳書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問題、視野與范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56.
[5].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21.
[6]竹內實.的詩詞、人生和思想[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9.
[7].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4.
[8]陳晉.文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9]王國維.人間詞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5.
[10].詩詞集[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264-267.
[11]鄭廣瑾,楊宇鄭.詩話[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172.
作者:海珍1;張瓊2 單位:1.太原工業學院,2.忻州師范學院
- 上一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當展范文
- 下一篇: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啟示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