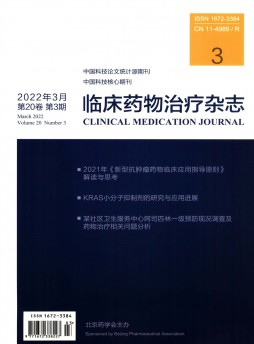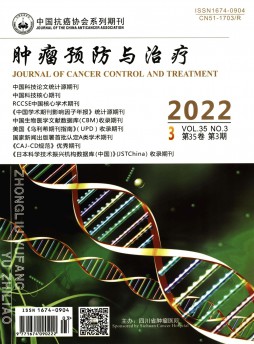益腎蠲痹法治療中風的臨證應用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益腎蠲痹法治療中風的臨證應用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2015年第六期
益腎蠲痹法是國醫大師朱良春教授(以下尊稱朱老)治療痹證的獨特療法。關于痹癥,中醫醫籍論述如下:《靈樞•五變》“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痹”;《濟生方•痹》“皆因體虛腠理空疏,受風寒濕氣而成痹也”;張景岳曰:“痹證大抵因虛者多”。朱老發煌古義,承前納賢,認為病之所成,是先因體虛,主要是腎虛,復加病邪深入經隧骨骱使然,并總結出頑痹的特點是“久痛多瘀,久痛入絡,久痛多虛,久必及腎”[1],故朱老從腎虛立論,提出了益腎壯督以扶正、蠲痹通絡以祛邪的治療理念來治療痹證。其代表方為益腎蠲痹丸,主要用于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中風與痹癥有類似的中醫病理機制,以下試探討益腎蠲痹法在中風中醫治療中的應用。
1中風病機從腎虛立論的理論基礎
1.1中風從腎虛立論的學術淵源中風從腎虛立論,最早可追溯至《內經》。《內經》認為,中風之發生,為正氣不足,復中風邪所致。《素問•脈解篇》曰:“內奪而厥則為痱,此腎虛也”。《靈樞•刺節真邪篇》曰:“虛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之后,諸家論治中風都考慮其病理基礎為“正虛”,如漢代張仲景《金匱要略•中風歷節病》中,首現中風之名,并提出了“正虛邪中”之論;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曰:“偏風者,風邪偏客于身一邊也,人體有偏虛者,風邪乘虛而傷之”;金元大家李東垣強調中風病機為“正氣自虛”;明代張景岳倡導“內傷積損”論;清代名醫沈金鰲在《雜病源流犀燭》中指出:“曰火曰痰,總由于虛,虛為中風之根也”等等。綜合《內經》及各家之說,其所謂“正虛”,應當以“腎虛”為主,正如清代名醫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中風》所云:“……水不涵木,木少滋榮,內風時起”。清代名醫王清任專從氣虛立論,并強調“虧損元氣是其本源”;清代名醫懷抱奇在《古今醫徹》中更明確指出:“……,而究其根,則在于腎元不足所致”。可見,中風從腎虛論治,有其充分的理論依據。
1.2中風病機與腎虛相關一項流行病學調查資料表明,中風的發病率、死亡率隨年齡增長而升高,50歲以上者上升明顯[2]。另有資料發現,50歲以前,動脈硬化性腦梗死的發病率僅占8%[3]。可見,中風好發于老年人。《靈樞•衛氣失常》說:“人年五十已上為老”,認為人在50歲以后即進入老年期。《素問•上古天真論》明確指出,老年期衰老的主要原因為腎衰。多發于老年人的中風之病,通常都有腎虛存在。有研究表明,腎虛是老年缺血性中風的病機特點之一[4]。現代研究認為,腎虛與神經內分泌系統關系密切,可表現出兒茶酚胺類神經遞質及其降解產物的異常釋放,進而影響神經信息的傳導[5]。實驗研究表明,溫腎陽類中藥能增加腦內乙酰膽堿及單胺類神經遞質的含量,增加神經遞質受體的數量,從而促進神經功能的恢復[6]。可見,中風之發生多與腎虛相關。
1.3肝腎不足為中風的病理機制朱良春教授對中風病機的認識,在承古納賢之時,力推明代張景岳之論:“凡病此者,多以素不能慎,或七情內傷,或酒色過度,先傷五臟之真陰,此致病之本也”。朱老在《章次公醫案》中風案按語中進一步指出:“中風多由肝腎虧于下,氣血并走于上,肝陽偏亢,內風時起”;“中風遺留偏廢,多由肝腎陰血不足,不榮筋骨,內風襲絡”。所以朱老認為,中風之發生,源于肝腎陰血不足。中醫學認為,中風之本在于“虛”,肝腎不足為其根本[7]。中風病機雖較復雜,但歸納起來,不外乎虛、火、風、痰、氣、血六端。其中,“虛”即是肝腎不足,經絡空虛,是致病之本。經絡是運行氣血、聯絡臟腑肢節、溝通上下內外、調節人體功能的一種特殊網絡。其生理功能的健全與否,決定于氣血之盛衰。經絡之血,源于肝藏之血的注入;血之運行,依賴于腎之元氣的促動,經絡之氣血的盛衰,依賴于肝腎功能之強弱。所以,肝腎不足則脈絡空虛,此時易致風、火、痰、瘀之邪閉阻經絡,即成偏枯。治療時,益腎養肝及滋水涵木即能充實脈絡,有助于祛邪通絡。
2益腎蠲痹法在中風治療中的應用
2.1中風與痹證治則同而治法稍異比較中風與痹證,在病機方面具有共同點。兩者都有“虛”的一面,都與腎虛相關。兩者又都有實的一面,在“虛”之基礎上,復加邪氣閉阻經隧。病性均為本虛標實,虛實夾雜,肝腎不足為其本,邪閉經絡為其標。共同的病機特點決定了兩者的治療應遵守相同的原則。因此,筆者認為朱老“益腎蠲痹”之學術思想可用來指導中風的治療,此即異病同治。所不同的是,痹證之“益腎”,主要是指溫腎陽,因痹證多寒濕也;而中風之“益腎”,主要是滋腎陰,滋水涵木,肝腎同補。所謂蠲痹,即剔除閉阻之邪,實屬祛邪之法,有祛邪之力更加迅猛之寓意。朱老認為,由于腎根不堅,痹證與中風之邪均已深入經隧,伏藏難卻,故主張用蟲類藥治療,其祛邪之力猛悍效著。朱老對于中風的治療,亦現蠲痹之法跡。
2.2益腎蠲痹法治療中風的具體應用臨床實踐中,筆者在正確辨證施治的同時,充分運用朱老益腎蠲痹的理論,靈活化裁加減,對中風的整個診治過程,始終堅守扶正祛邪的原則,療效明顯。具體方法如下:
2.2.1分期治療分清標本緩急急性期(2周以內),多以標實為主,按照急則治其標的原則,側重祛邪蠲痹,佐以益腎扶正以充實脈絡。朱老認為,急性期主要有兩種證型。一是肝陽上亢,內風肆擾;二是痰熱壅盛,蒙竅阻絡。所以,常用的治法應當是平肝潛陽、搜風化痰、泄熱通腑、化瘀通絡等。這些方法,無非是剔除閉阻經絡之邪,即所謂蠲痹。常用藥物有:天麻、鉤藤、全蝎、地龍、水蛭、炮穿山甲、羚羊角粉、生大黃、芒硝、陳膽南星、全瓜蔞、鮮竹瀝、石菖蒲、桃仁、紅花、丹參、黛蛤散、豨薟草、威靈仙等。恢復期(2周以上,6個月以內),標實已去六七,此時應當益腎與蠲痹并舉,兩者不可偏廢,才能互為作用,形成合力,促成康復。益腎常用生地黃、熟地黃、枸杞子、楮實子、桑椹子、龜甲、山藥、紫河車等,蠲痹常用蟲類藥,如地龍、僵蠶、全蝎、蜈蚣、地鱉蟲、水蛭、露蜂房等。后遺癥期(半年以上),本虛為主,余邪未盡。重點補益肝腎,益氣養血,充實脈絡。余邪纏綿難清,當以蟲蟻搜風剔絡。常用人參、黃芪、熟地黃、當歸、白芍、枸杞子、楮實子、桑椹子、龜甲、山藥、紫河車、鹿角膠等,蠲痹常用穿山龍、桂枝、桃仁、紅花、赤芍、生三七、路路通、雞血藤、牛膝以及蟲類藥。整個治療過程,按照標本緩急的治療原則,適時調整益腎扶正與蠲痹祛邪的藥物權重。特別在中風恢復期、后遺癥期可以酌情使用益腎蠲痹法調治。
2.2.2益腎重在辨明陰虛陽虛益腎蠲痹丸的組成有熟地黃、當歸、淫羊藿、全蝎、蜈蚣、露蜂房、骨碎補、地龍、烏梢蛇、延胡索等。臨床資料顯示,本方對痹證屬寒濕型、痰瘀型者療效較顯著,而對于陰虛或濕熱型痹證療效欠佳[8]。從其組方特點分析,不難看出,其中淫羊藿、露蜂房、骨碎補有溫腎助陽之功,故益腎蠲痹丸是偏溫性的,這是因為痹證多屬寒濕,這里的益腎,僅指溫腎助陽。對于陰虛型痹證或濕熱型痹證,朱老常加用滋陰清熱類藥,如天冬、麥冬、生地黃、知母、玄參、石斛等,或清熱化濕類藥,如黃連、黃柏、苦參、龍膽草、澤瀉、六一散等。中風之虛,主要責之于肝腎陰虛。肝腎同源,故筆者在采用益腎法治療中風時,認為應當與朱老益腎蠲痹丸之“益腎”有所區別,不能完全照搬。這里的益腎,應當具有更廣泛的外延,包括補益陰陽氣血。當然滋養肝腎之陰為其根本,所謂滋水涵木,肝腎同補,并達滋陰熄風之目的。常用藥物:生地黃、熟地黃、楮實子、桑椹子、枸杞子、女貞子、山萸肉、白芍、何首烏、龜甲、鱉甲。中風之虛,少部分責之于腎陽虛。喻昌《醫門法律》:“偏枯不仁,要皆陽氣虛餒,不能充灌所致。又如中風卒倒,其陽虛更甚。設非陽虛,其人必輕矯便捷,何得卒倒耶”。有學者認為,中風后期即后遺癥期多見腎陽虧虛、氣虛血瘀、腦絡痹阻的病機特點[9]。也有學者認為,腎陽虛是中風后遺癥的常見證型之一[10]。臨證中遇見此類證型時,可用朱老的培補腎陽湯(淫羊藿、仙茅、懷山藥、枸杞子、紫河車、甘草)加減,或直接另服益腎蠲痹丸8g,每日2次。綜上,中風之益腎,主要指腎陰,涉及肝陰,即所謂肝腎不足,應當滋水涵木。當然,臨證時還應當正確辨證,對于腎陽不足者,可按照朱老治痹證之益腎,主要指溫腎助陽之本意施予湯藥加減,或直接予益腎蠲痹丸。
2.2.3常用蟲類藥祛邪通絡痹者,閉也,阻塞不通之意。蠲痹,即指祛邪通絡。中風之病,實質亦為邪氣閉阻經絡,經氣不利使然,故祛邪通絡,實則亦為蠲痹,只是祛邪作用不如后者強烈而已。其方法包括:祛風、化痰、降火、通腑、活血化瘀、行氣通絡。由于風邪存在于中風之病的全過程,無論病情輕重,均見風證之候[11],并且朱老認為,中風之“風”,根起于腎,而蕩于肝,又由于腎為五臟之根,故中風之風邪為虛邪賊風,根痼難祛,亦非一般草木之力所能達。因此朱老治療中風,亦喜用蟲類藥以搜風剔絡即所謂蠲痹,而非一般程度上的祛風通絡。常用:全蝎、蜈蚣、地龍、僵蠶、水蛭、烏梢蛇、龜甲、鱉甲。在常規辨證施治的基礎上,盡量使用蟲類藥,常能明顯提高療效,這正體現了朱老創制益腎蠲痹丸時配伍蟲類藥的指導思想,“組方用藥時,又根據蟲類藥‘搜剔鉆透祛邪’的特點,集中使用之,有協同加強之功”[8]。唐宋之后,中風以內風學說為主流,目前依然。肝腎不足、經絡空虛為其本,邪閉經絡為其標。病性為本虛標實、虛實夾雜。治療原則當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扶正祛邪,標本兼治。治本當從腎虛立論,補益肝腎,滋水涵木為主。治標當平肝潛陽、搜風化痰、泄熱通腑、化瘀通絡等。臨證中,筆者分別針對風、痰、瘀、火、熱、虛等,在正確辨證的同時,充分應用朱老益腎蠲痹的學術思想指導中風的治療,并善用蟲類藥,取得了較為顯著的療效,這不僅是對朱老學術經驗的繼承,同時將之推廣應用,亦是對朱老學術經驗的進一步發展。
作者:田華 單位:南京中醫藥大學南通附屬醫院
- 上一篇:桂林抗戰藝術研究思考范文
- 下一篇:佐劑性關節炎大鼠骨代謝標志物探討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