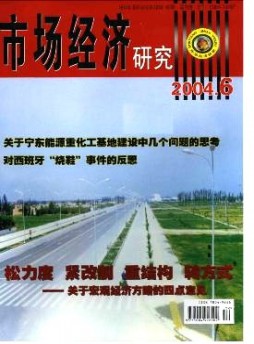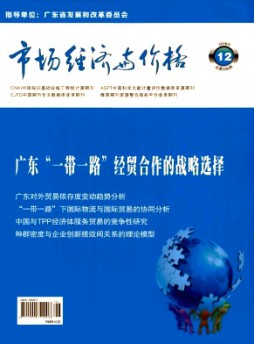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自由秩序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自由秩序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自由的形態(tài)
人類(lèi)文明的歷史亦即人性從異化到不斷解放的歷程,意味著人之自由的不斷進(jìn)步。可以說(shuō),自由的發(fā)展過(guò)程,就是人類(lèi)更接近他自身實(shí)現(xiàn)的過(guò)程(弗洛姆,1988)。法律被視為正義之物,而“整個(gè)法律正義哲學(xué)都是以自由觀念為核心而建立起來(lái)的”(博登海默,1987)。而自由為何物,無(wú)論是在哲學(xué)領(lǐng)域,還是在法哲學(xué)領(lǐng)域抑或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都是眾說(shuō)紛紜。法律視角最直接關(guān)注的是人的行為,法律作為社會(huì)關(guān)系的調(diào)節(jié)器,通過(guò)規(guī)范人的行為以影響社會(huì)關(guān)系,進(jìn)而規(guī)整與塑造社會(huì)秩序。因此,法律關(guān)注的自由,首先是描述某種行為或活動(dòng)狀態(tài)。自由首先就是行為之自由,雖然這不是自由的全部。即使,我們經(jīng)常可以將自由或不自由的狀態(tài)還原為諸行為的自由或不自由,但二者畢竟具有不同的價(jià)值。如:自由選擇是行為自由,但其結(jié)果并不必然使自己處于自由的狀態(tài),而這種不自由的狀態(tài),并不能因其源自自由的選擇而符合自由價(jià)值觀。因此,正如哈耶克所言,不能將具有因果關(guān)系的自由行為與不自由狀態(tài)相混淆(哈耶克,1997)。但“行為自由”過(guò)于寬泛,理解行為自由還需要理解法律視角下行為的特質(zhì)。
不同學(xué)科從自身學(xué)科的視角出發(fā),對(duì)行為進(jìn)行了不同的界定。受哲學(xué)思辨影響的人,會(huì)將“行為”定義為“受思想支配而表現(xiàn)在外面的活動(dòng)”(《現(xiàn)代漢語(yǔ)小詞典》,1982)。而在倫理學(xué)領(lǐng)域,由于其強(qiáng)調(diào)行為目的之合理性,行為是指“人類(lèi)自覺(jué)的有目的的活動(dòng)”(宋希仁等,1989)。行為科學(xué)家由于從“人和環(huán)境交互作用”出發(fā),主要強(qiáng)調(diào)行為的社會(huì)性,因而關(guān)注那些與社會(huì)發(fā)生互動(dòng)的行為(劉鳳瑞,1991)。馬克斯·韋伯就是將社會(huì)學(xué)定義為“解釋性地理解社會(huì)行為……的科學(xué)”(韋伯,2006),從而將“非社會(huì)行為”排除在社會(huì)學(xué)研究之外。但毫無(wú)疑問(wèn),行為包括兩個(gè)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表現(xiàn)部分,另一方面是內(nèi)在的主觀方面。行為自由必須從這兩個(gè)方面進(jìn)行思考。
從語(yǔ)言分析的角度來(lái)看,正如叔本華所言,“在我們的思想中,自由的概念總是動(dòng)物的賓語(yǔ)”(叔本華,2004)。因此,自由總與人或動(dòng)物的主觀狀態(tài)相關(guān)聯(lián)。就人之行為而言,意志構(gòu)成行為的內(nèi)在方面,內(nèi)在方面的行為自由,即通常所謂之意志自由。但是,在現(xiàn)代法律中,若無(wú)外在的表現(xiàn)或表達(dá),意志自由,在規(guī)范意義上,沒(méi)有實(shí)質(zhì)性?xún)r(jià)值。內(nèi)在的意志不表達(dá)于外,就失去其社會(huì)性特征,那么從社會(huì)規(guī)范的角度,就失去意義。行為的外在方面,即為行為人客觀可觀察的舉止,其為人之器官的各種活動(dòng)或不活動(dòng),其作用于外,方產(chǎn)生行為的社會(huì)性,才具有規(guī)范價(jià)值。但是,若脫離行為的內(nèi)在方面的自由,行為的外在舉止的自由,僅意味著在功能上無(wú)障礙,這顯然不是倫理或價(jià)值論意義上的自由。因此,行為自由包括兩個(gè)不可分割的部分:意志自由以及意志表達(dá)與實(shí)現(xiàn)上的舉止自由。行為自由表現(xiàn)于社會(huì)關(guān)系之中,表現(xiàn)為不受他人意志的強(qiáng)制。自由原本就是“僅指涉人與他人間的關(guān)系”(哈耶克,1997)。荒島上的魯賓遜無(wú)所謂自由與不自由,因?yàn)橥浒l(fā)生關(guān)系的他人意志是不存在的。
二、組織體的行為自由
通常,傳統(tǒng)法學(xué)理論上所謂的行為自由往往指?jìng)€(gè)體的行為自由或者說(shuō)是與政治權(quán)威相對(duì)的被管理者或被統(tǒng)治者的行為自由。這一傳統(tǒng)信念與民事法律行為理論相切合。但在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不僅僅有公權(quán)組織的存在,還有眾多的非公權(quán)的經(jīng)濟(jì)組織,而這些組織的行為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的影響遠(yuǎn)遠(yuǎn)超出自然人。因此,“組織行為”的自由狀態(tài)就顯得尤為重要。但組織行為的自由在內(nèi)、外兩個(gè)方面顯得相當(dāng)復(fù)雜。傳統(tǒng)的行為自由理論對(duì)于組織行為在以下兩方面缺乏解釋力:
首先,人為地割裂了兩類(lèi)組織體的行為自由。就私法人而言,我們常常用權(quán)利和自由來(lái)對(duì)其行為進(jìn)行描述;對(duì)于公法人,通常用權(quán)力來(lái)描述其行為,而幾乎不談其行為的自由問(wèn)題。就自由的本來(lái)涵義而言,行使權(quán)力的行為與權(quán)利行為同樣是意志自由的表現(xiàn)。如果說(shuō)私權(quán)組織具有意志,而且是自由的,那么公權(quán)組織就不存在意志?其意志在行為時(shí)與他人意志發(fā)生關(guān)系,在這一關(guān)系中它是非自由的?
其次,對(duì)于公權(quán)力行為問(wèn)題,通常是用“職責(zé)理論”來(lái)進(jìn)行闡述的。如果用“職責(zé)理論”來(lái)反對(duì)公權(quán)力行使中的“行為自由”,則混淆了此等行為中的內(nèi)外部關(guān)系。
組織行為依賴(lài)于自然人的軀體活動(dòng),但這些特殊的人的軀體活動(dòng)確是“組織”的而非“活動(dòng)著或不活動(dòng)著的人”的行為。這原本是“非自然的”,是因?yàn)樯钪械募s定俗成或法律的設(shè)定而使之如此。是什么因素決定著一個(gè)外在表現(xiàn)為自然人的舉止被視為一個(gè)組織的行為呢?顯然,是其內(nèi)在的主觀方面的因素。“我以...的名義”,這樣的開(kāi)場(chǎng)白,顯然表達(dá)了行為的內(nèi)容為被代表者的意圖,而非行動(dòng)者的意圖。但是,實(shí)際的困難是:對(duì)于行為的受眾來(lái)說(shuō),其直觀感覺(jué)到的是舉止者的軀體活動(dòng)。無(wú)論任何,作為行動(dòng)承擔(dān)者的舉止者,在進(jìn)行軀體活動(dòng)時(shí),同樣表露著其自身的主觀色彩,包括思想、情感、態(tài)度或情緒。因此,對(duì)于行為受眾來(lái)說(shuō),兩個(gè)方面的因素都對(duì)其產(chǎn)生影響,一方面是,通過(guò)作為代表者的自然人的舉止表達(dá)出來(lái)的組織的意向,另一方面是,代表者在表達(dá)組織的意向時(shí),自己表露在外的思想、情感、態(tài)度與情緒。因此,在組織行為中,行為受眾受到兩個(gè)方面意向的影響,而不是“組織”的單一意向。
同時(shí),實(shí)際的舉止者在從事代表行為的時(shí)候,他的內(nèi)心意志中已經(jīng)與被代表者發(fā)生內(nèi)在的聯(lián)系。而這內(nèi)在的聯(lián)系本身也是這一行為的要素或邏輯前提。因此,就行為及其社會(huì)關(guān)系而言,組織行為蘊(yùn)含如圖1所示的三種關(guān)系。
作為組織的代表,自然人的舉止,一方面基于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受制于其與組織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所產(chǎn)生的某種要求;對(duì)于行為受者,舉止活動(dòng)的主觀意向不屬于舉止者,而屬于組織,因此,在舉止者與舉止受者之間形成的主要是一種外在活動(dòng)所表現(xiàn)的物質(zhì)互動(dòng)關(guān)系。而行為受者的意志與組織的主觀意志發(fā)生關(guān)系,因此組織與行為受者之間發(fā)生了一種意志上的關(guān)系。而正是這種意志上的關(guān)系,被我們視為真正重要的關(guān)系。但有必要聲明,并非是說(shuō)圖示中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和“物質(zhì)關(guān)系”與人的主觀意志無(wú)關(guān),正如上文中所說(shuō),舉止者的思想、欲望、情緒等都對(duì)行為受者產(chǎn)生影響;而且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本身又是另一行為所產(chǎn)生的具有意志內(nèi)容的關(guān)系。
“職責(zé)理論”忽視了這種復(fù)雜的關(guān)系,要么將舉止者的“行為”解釋為職責(zé)之所在,而非意志自由引導(dǎo)的系列變化;要么將組織的“行為”解釋為職責(zé)使然。前一種解釋?zhuān)@然混淆了組織行為關(guān)系體系中的“物質(zhì)關(guān)系”與“意志關(guān)系”。組織行為所產(chǎn)生的真正社會(huì)關(guān)系是“意志關(guān)系”,考察行為是否自由的重點(diǎn)實(shí)質(zhì)為組織意志及其展開(kāi),而非舉止者的意志狀態(tài)。后一種解釋則是混淆了意志源起與意志自由的關(guān)系。無(wú)論公法人組織或私法人組織的行為自由,都表現(xiàn)為組織意志的自由表達(dá)與實(shí)現(xiàn)。我們不難想像私法人意志在源起上受到法人制度及其運(yùn)行體系的束縛,但這并不意味著私法人在行為時(shí),意志是受到強(qiáng)制的。而且,“職責(zé)理論”同樣忽視了自然人意志在源起上也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有些是法律制度之外的,而另一些則是法律制度之內(nèi)的。意志自由意味著,在行為所產(chǎn)生的特定社會(huì)關(guān)系中不受對(duì)方意志的強(qiáng)制束縛,而并不意味著受其組織機(jī)構(gòu)制度的影響以及受到社會(huì)的一系列條件的限制。公法人本身也是出于公法人體系的制度性機(jī)構(gòu)體系之中,其意志的產(chǎn)生與源起同樣受其置身于其中的機(jī)構(gòu)體系的影響。但公法人在行使職責(zé)時(shí),其行為相當(dāng)于相對(duì)人來(lái)說(shuō),其意志是不受強(qiáng)制的。可見(jiàn),公法人與私法人、甚至是自然人,在行為的意志自由方面沒(méi)有區(qū)別,而區(qū)別僅在于行為過(guò)程的外在表現(xiàn)以及行為過(guò)程的復(fù)合關(guān)系。
三、經(jīng)濟(jì)自由與經(jīng)濟(jì)秩序
經(jīng)濟(jì)自由作為自由的一個(gè)組成部分,通常與政治自由相對(duì)應(yīng)。并且,在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觀中,兩者往往也被認(rèn)為是可以分開(kāi)的。雖然,經(jīng)濟(jì)自由對(duì)政治自由具有特殊的功能性作用,甚至是必要的條件。但經(jīng)濟(jì)自由不僅僅被當(dāng)作是一種現(xiàn)象的描述,而且被視為重要的價(jià)值目標(biāo)。正如弗里德曼所言,“經(jīng)濟(jì)自由本身是一個(gè)目的”(弗里德曼,1986)。作為價(jià)值目標(biāo)的經(jīng)濟(jì)自由,無(wú)疑就與社會(huì)的價(jià)值體系密切相關(guān)。從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視角來(lái)看市場(chǎng)行為,其本質(zhì)上是自由的,這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運(yùn)行規(guī)律所要求的。
自亞當(dāng)·斯密《國(guó)富論》以來(lái),經(jīng)濟(jì)自由的理念長(zhǎng)期以來(lái)一直引領(lǐng)著西方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乃至成為西方個(gè)人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的重要組成部分。經(jīng)受凱恩斯主義短期沖擊后,自由主義在上個(gè)世紀(jì)70年代以后再次主導(dǎo)著西方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觀點(diǎn)。有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甚至呼吁“古典自由主義……一定不能從世上絕跡”(布坎南,1988)。自由主義堅(jiān)持市場(chǎng)的自發(fā)作用,作為交換經(jīng)濟(j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必然要求經(jīng)濟(jì)行為的自由。經(jīng)濟(jì)自由乃是由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本質(zhì)結(jié)構(gòu)決定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意味著交換,“看不見(jiàn)之手”的調(diào)節(jié)機(jī)制基于無(wú)數(shù)平等自愿的市場(chǎng)交換得以實(shí)施。意志自由的交換主體是這一機(jī)制的細(xì)胞,而自由的交換就是這一機(jī)制的動(dòng)脈。
經(jīng)濟(jì)行為的自由主要表現(xiàn)為契約自由與競(jìng)爭(zhēng)自由,而作為這兩者的邏輯前提是私有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因此,經(jīng)濟(jì)自由包括如下幾個(gè)方面:首先是追求個(gè)人經(jīng)濟(jì)利益最大化的自由。雖然亦受到一些學(xué)者的質(zhì)疑,“經(jīng)濟(jì)人”假設(shè)始終是主流經(jīng)濟(jì)學(xué)最基本的假設(shè)之一。“經(jīng)濟(jì)人”意味著市場(chǎng)中的參與者都是理性的、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私利角逐者。作為單個(gè)交換主體,獲利是其根本目的。而自由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必須以此為邏輯起點(diǎn),那么,意志上的自由就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制度環(huán)境下的必需品。從微觀上看,這就是前文所述之行為自由的內(nèi)在方面,即自由的經(jīng)濟(jì)行為的意志自由。其次是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自由。從“經(jīng)濟(jì)人”的假設(shè)出發(fā),市場(chǎng)主體都是逐利者,依據(jù)自己對(duì)自己利益的判斷,進(jìn)行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而商品生產(chǎn)的目的在于交換,基于自由的交換,市場(chǎng)機(jī)制所發(fā)揮的資源在社會(huì)成員間的配置功能才得以實(shí)現(xiàn)。交換通過(guò)當(dāng)事人之間契約而完成,因此交換的自由亦可謂之契約自由。因此,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自由包括了商品生產(chǎn)與交換的全部過(guò)程中的行為自由。再次是競(jìng)爭(zhēng)的自由。資源的有限性和市場(chǎng)主體的逐利性,必然產(chǎn)生市場(chǎng)主體之間的競(jìng)爭(zhēng)。自由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要求按照市場(chǎng)規(guī)律調(diào)節(jié)主體之間的競(jìng)爭(zhēng)行為,由競(jìng)爭(zhēng)主體根據(jù)自己對(duì)自己利益的判斷,自由選擇。自由的競(jìng)爭(zhēng)導(dǎo)致市場(chǎng)主體在自我發(fā)展上的自由。一言以蔽之,經(jīng)濟(jì)自由,在傳統(tǒng)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理論中,即為市場(chǎng)主體的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之自由。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消費(fèi)自由。商品的終極價(jià)值體現(xiàn)于消費(fèi)使用,而且人人皆為消費(fèi)者。因此,消費(fèi)自由具有兩個(gè)方面的重要意義:它不僅決定著物質(zhì)享受過(guò)程的心理愉悅狀態(tài),而且這一消費(fèi)過(guò)程是人人都參與的過(guò)程,因此關(guān)涉到所有社會(huì)生活中的個(gè)體。消費(fèi)自由最常見(jiàn)的障礙是壟斷,一些壟斷構(gòu)成對(duì)消費(fèi)者意志自由的強(qiáng)制,導(dǎo)致不自由;而一些則僅僅構(gòu)成行為的物理障礙,而不構(gòu)成消費(fèi)者的不自由(哈耶克,1997),如自然壟斷。
與經(jīng)濟(jì)自由一樣,經(jīng)濟(jì)秩序亦構(gòu)成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所謂秩序,至少包括以下一些基本面:首先,秩序表現(xiàn)為人們一致的、至少是相對(duì)一致的行為或具有一致價(jià)值取向的行為所產(chǎn)生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其次,此等社會(huì)關(guān)系之所以不具有明顯的或不可調(diào)和的沖突,原因在于其內(nèi)在的價(jià)值體系相互可以協(xié)調(diào)或利益沖突在相當(dāng)程度上可以調(diào)和。再次,秩序意味著行為規(guī)則的當(dāng)然存在,而且構(gòu)成秩序的行為規(guī)則構(gòu)成一個(gè)有效的調(diào)節(jié)人們行為的體系,此一體系相對(duì)而言具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或價(jià)值體系上的一致性,其適用于人們的行為,不至于產(chǎn)生不可調(diào)和的沖突,或者即使產(chǎn)生沖突也可以通過(guò)規(guī)則體系內(nèi)部的調(diào)整而有效地消除沖突。這就意味著形成秩序的規(guī)則體系不是一個(gè)封閉的體系,而是一個(gè)自身可以不斷適應(yīng)外界變化的開(kāi)放體系。最后,至于秩序本身也是一個(gè)可變的動(dòng)態(tài)的人類(lèi)關(guān)系體系。其可變性源自人類(lèi)物質(zhì)生活狀態(tài)的不斷演進(jìn)以及由其而引發(fā)的人類(lèi)價(jià)值體系的不斷演化。而對(duì)于一個(gè)局部社會(huì)來(lái)說(shuō),其秩序的演化可以是內(nèi)在力量的推動(dòng),也可以是外在力量作用的結(jié)果,而對(duì)于整個(gè)人類(lèi)來(lái)說(shuō),無(wú)論是來(lái)自多數(shù)人的意志還是來(lái)自少數(shù)人的意志,其都是內(nèi)生變化的,除非持創(chuàng)世觀,沒(méi)有人類(lèi)以外的智力引發(fā)或誘導(dǎo)社會(huì)生活的變遷。因此,無(wú)論是內(nèi)生的秩序演化,還是外在的秩序變遷,秩序都具有歷史現(xiàn)實(shí)性。
由此我們可以斷定,經(jīng)濟(jì)秩序首先是一個(gè)歷史性和地域可分性的社會(huì)現(xiàn)象。經(jīng)濟(jì)法意義上的經(jīng)濟(jì)秩序,應(yīng)當(dāng)界定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的經(jīng)濟(jì)秩序,或者說(shuō)我們所謂的經(jīng)濟(jì)秩序乃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秩序,而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經(jīng)濟(jì)秩序。就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秩序而言,從不同的角度可做不同的區(qū)分:
從形成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秩序的規(guī)則來(lái)源的角度,可分為私人自發(fā)的經(jīng)濟(jì)秩序和調(diào)控的經(jīng)濟(jì)秩序。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源于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本源于私人自發(fā)的物質(zhì)生活需要而產(chǎn)生的愿望,千百萬(wàn)自發(fā)的交換行為形成了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最原初的秩序。此等由于人們自發(fā)的物質(zhì)需求而導(dǎo)致的行為,由于其具有內(nèi)在的同質(zhì)性,因而表現(xiàn)為相對(duì)一致的行為模式,從而產(chǎn)生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秩序中最基礎(chǔ)的部分。當(dāng)然,在國(guó)家還是當(dāng)今人類(lèi)社會(huì)最根本的組織形式的前提下,此等自發(fā)秩序要得到有效的運(yùn)行,離不開(kāi)國(guó)家權(quán)力的有效保護(hù),因此,此等經(jīng)濟(jì)秩序?qū)嶋H上也是被法律制度化了的。與自發(fā)的經(jīng)濟(jì)秩序相對(duì)應(yīng)的是調(diào)控秩序。自發(fā)的經(jīng)濟(jì)秩序即使在法律保護(hù)下,亦不能免于走向自身的反面。任何事物都有向其反面發(fā)展的內(nèi)在傾向。因此,當(dāng)自發(fā)的經(jīng)濟(jì)秩序發(fā)生有悖于其自身的要求或?qū)е伦陨淼谋罎ⅲ瑖?guó)家作為社會(huì)的組織者,毫無(wú)疑問(wèn)將進(jìn)行干涉,國(guó)家對(du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進(jìn)行干預(yù)而形成了不同于自發(fā)秩序的經(jīng)濟(jì)秩序,此等經(jīng)濟(jì)秩序明顯具有國(guó)家意志的特征。當(dāng)然,國(guó)家干預(yù)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而形成的調(diào)控秩序與自發(fā)秩序是交織于一體的,就具體的單一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而言,其中的自發(fā)因素和國(guó)家調(diào)控因素相互起作用。因此,這一區(qū)分是理念形態(tài)的,在實(shí)際社會(huì)關(guān)系中,此二者共同并存于特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之中,或者說(shuō)同一經(jīng)濟(jì)社會(huì)關(guān)系體現(xiàn)著二者的意志。
從經(jīng)濟(jì)秩序所體現(xiàn)的價(jià)值而言,我們認(rèn)為經(jīng)濟(jì)秩序至少可區(qū)別為效率秩序與正義秩序。在漢語(yǔ)中,經(jīng)濟(jì)的另一日常含義即為效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微觀方面是通過(guò)交換各取所需,而宏觀方面就是通過(guò)交換而有效率地配置資源,從中觀角度來(lái)看,經(jīng)營(yíng)者的經(jīng)營(yíng)應(yīng)當(dāng)具有盡可能的高效率以獲得盡可能高的利潤(rùn)。因此,那些與效率要求相一致的經(jīng)濟(jì)行為與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就形成了效率經(jīng)濟(jì)秩序。當(dāng)然,效率不能解決人類(lèi)生活關(guān)系的一切方面,更不是經(jīng)濟(jì)秩序的惟一目標(biāo)。正義的生活是人類(lèi)矢志不渝的理想,正義的要求同樣適用于人類(lèi)的經(jīng)濟(jì)生活。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在歷史上的一系列挫折和危機(jī),都不可避免地使人們更加關(guān)注經(jīng)濟(jì)生活的正義問(wèn)題。經(jīng)濟(jì)法視角下,國(guó)家對(duì)市場(chǎng)的干預(yù)處處體現(xiàn)著正義的原則要求。消費(fèi)者保護(hù),體現(xiàn)正義要求的實(shí)質(zhì)平等;反壟斷與反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體現(xiàn)著符合正義要求的自由競(jìng)爭(zhēng);社會(huì)保障與社會(huì)福利,反映了正義所要求的對(duì)人的基本保護(hù)與人道主義關(guān)懷。效率與正義不至于像有些理論家眼中那樣處于格格不入的尖銳對(duì)立之中。果真如此,要么,現(xiàn)實(shí)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就不可能延續(xù);要么,道德水平始終是令人不堪忍受的。然而不能因此就說(shuō)效率與正義始終處于和諧與相互一致的狀態(tài)。在特定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過(guò)程中,二者的暫時(shí)性對(duì)立是在所難免的。
霍布斯對(duì)原始叢林中導(dǎo)致每個(gè)人對(duì)每個(gè)人發(fā)生戰(zhàn)爭(zhēng)的自由與權(quán)利的描寫(xiě),似乎表明:自由意味著就是撕裂秩序之網(wǎng)的利刃。在集體主義者與社群主義者眼中,個(gè)人自由即使不是對(duì)立于秩序的和諧,也與之發(fā)生著緊張的關(guān)系,因此就產(chǎn)生了集體優(yōu)先于個(gè)人的教義或民主主義(多數(shù)人的統(tǒng)治)。而自由主義者,在堅(jiān)持自由精神與追求的同時(shí),其不可能否認(rèn)自由與秩序的并存。如果,自由果真導(dǎo)致每個(gè)人與每個(gè)人發(fā)生戰(zhàn)爭(zhēng),任何嚴(yán)肅的理性學(xué)者都不會(huì)倡導(dǎo)自由。而恰恰是自由主義者堅(jiān)持自由與秩序的并存,堅(jiān)持這種并存狀態(tài)——“自由秩序”的價(jià)值。自由主義旗手哈耶克,反對(duì)將基于自由選擇或被動(dòng)接受而產(chǎn)生的使人處于奴役狀態(tài)的秩序視為自由(哈耶克,1997)。在其眼中,自由不僅是人的不受奴役的狀態(tài),而且是一種值得過(guò)而且應(yīng)當(dāng)去追求的社會(huì)秩序。在具有集體主義傾向或民主的思想中,秩序的形成不成問(wèn)題,多數(shù)人的意志或集體的意志決定了秩序的建構(gòu)。但在自由主義者的理論框架中,秩序的形成卻不折不扣是個(gè)難題。
四、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自由秩序的形成
“如果要保存或恢復(fù)一個(gè)自由社會(huì),我們必須傳播的是信念。”(哈耶克,1989)即使是在堅(jiān)持自由秩序的自發(fā)生成觀的哈耶克看來(lái),人的主觀性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如此一來(lái),這種自發(fā)生成的自由秩序觀,不僅意味著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自由秩序由意識(shí)自由的人的自由的市場(chǎng)行為衍生出來(lái),還意味著這種市場(chǎng)秩序需要一種對(duì)某種自由的市場(chǎng)秩序的信念作為基礎(chǔ)。問(wèn)題在于:這樣信念下的自由觀仍然是一種具有主觀上的構(gòu)建性質(zhì)。很明顯,哈耶克所持的自由秩序原本就不是客觀現(xiàn)實(shí)中的一種真實(shí)自由秩序。至少哈耶克,從反對(duì)理性建構(gòu)的立場(chǎng)出發(fā),又不可避免地卷入另一形態(tài)的建構(gòu)主義。哈耶克的憲政改革顯然是基于自己的自由主義信念,而非一種客觀的自由秩序。
如果從主觀介入的角度來(lái)看,人類(lèi)社會(huì)任何秩序的形成,都不可能避開(kāi)有意識(shí)的主觀行為。從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角度來(lái)看,這種人的有意識(shí)的行為主要是“計(jì)劃行為”。無(wú)論是各個(gè)純自然人的計(jì)劃、國(guó)家或政府的計(jì)劃,還是競(jìng)爭(zhēng)組織的計(jì)劃,都是主觀知識(shí)的一種運(yùn)用,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建構(gòu)作用,這從“計(jì)劃”一詞的意涵即可得以明證。即使在哈耶克的語(yǔ)境下,無(wú)數(shù)個(gè)人的自由計(jì)劃衍生了真正自由的經(jīng)濟(jì)秩序,屬于內(nèi)生性的。但問(wèn)題在于:這樣的思考,其前提假設(shè)就是政府或國(guó)家是市場(chǎng)秩序之外的。這根本就不符合與建構(gòu)理論相對(duì)立的真正意義上的混沌理論中秩序的“涌現(xiàn)”或“生成”理論(沃爾德羅,1997)。政府或國(guó)家這樣的組織本身也是“涌現(xiàn)”或“生成”的結(jié)果,其與市場(chǎng)都是同一涌現(xiàn)過(guò)程的產(chǎn)物,是人類(lèi)社會(huì)秩序的自發(fā)涌現(xiàn)的現(xiàn)象。兩者的區(qū)分只是理論上的,實(shí)際上不存在相互分離的市場(chǎng)與國(guó)家。
因此,那種強(qiáng)調(diào)由千百萬(wàn)個(gè)個(gè)人自發(fā)的自由市場(chǎng)行為生成自由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秩序,這本身就是:首先,人為地割裂了人類(lèi)生活秩序。我們從理性認(rèn)知上可以將市場(chǎng)秩序與公共生活尤其是國(guó)家組織體之下的公共生活區(qū)分開(kāi)來(lái)。但實(shí)際上這兩種被人為割裂的社會(huì)秩序是交織在一起的。抽象的區(qū)分適宜于智識(shí)上的理解與認(rèn)識(shí),但歪曲了事實(shí),作為復(fù)雜“涌現(xiàn)”的社會(huì)秩序具有整體性。這一整體性表現(xiàn)為人類(lèi)社會(huì)中的各種因素,其作用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社會(huì)秩序是這些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因素共同演繹而“涌現(xiàn)”出來(lái)的。
其次,這種理論忽視了一個(gè)重要的事實(shí),那就是人類(lèi)歷史上,國(guó)家從來(lái)就沒(méi)有從經(jīng)濟(jì)事務(wù)中完全超脫出來(lái)。以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為例,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最終形成是通過(guò)政治斗爭(zhēng)。在這一過(guò)程中,政治、軍事都起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英國(guó)漸進(jìn)式的憲政改革、圈地運(yùn)動(dòng),美國(guó)的獨(dú)立戰(zhàn)爭(zhēng)以及一系列的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沒(méi)有政治上的勝利,資本主義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根本無(wú)法形成。而在“自由”的資本主義確立以后,資本主義國(guó)家從來(lái)沒(méi)有做過(guò)真正的“守夜人”。海外殖民與關(guān)稅壁壘就是明證,由其導(dǎo)致的武裝沖突更是極端的表現(xiàn)。
而且,這樣的理論也割裂了自然人的自由與政府以及其他國(guó)家機(jī)構(gòu)的自由。正如本文一開(kāi)始分析的那樣,任何組織體,在社會(huì)生活中同樣是自由的。那么國(guó)家在市場(chǎng)秩序中所表現(xiàn)的自由同樣是存在的,這并不能僅僅以“守夜人”這樣的職責(zé)來(lái)表達(dá)。這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現(xiàn)實(shí)。以職責(zé)來(lái)替代自由,僅僅是另一層次上的理論構(gòu)造,是一種至今未曾證實(shí)的信念。
那種反對(duì)國(guó)家對(duì)市場(chǎng)進(jìn)行積極干預(yù)的理論,還做了另一個(gè)“歧視性”對(duì)待。那就是允許個(gè)人在不完全知識(shí)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計(jì)劃,而堅(jiān)決反對(duì)有缺陷的國(guó)家進(jìn)行的計(jì)劃。允許千百萬(wàn)個(gè)個(gè)人有缺陷的計(jì)劃,以至于造成大危機(jī)也堅(jiān)信“自發(fā)的市場(chǎng)力量”能夠重新恢復(fù)秩序,卻不能容忍有缺陷的國(guó)家干預(yù)。索羅斯認(rèn)為美國(guó)政府拯救雷曼兄弟公司,將使政府面臨“道德風(fēng)險(xiǎn)”。而資本主義在原始積累過(guò)程中的海外殖民,也決不因?yàn)榈赖聠?wèn)題而從未發(fā)生過(guò)。兩惡之間誰(shuí)更惡,這根本就不清楚,那么反對(duì)國(guó)家的“介入”的理由也就只能置于信念或社會(huì)的道德觀上了。然而道德觀是有民族性和歷史性的,在中國(guó),“有問(wèn)題找政府”,似乎就是老百姓天經(jīng)地義的信條。
因此,人類(lèi)的任何秩序都是內(nèi)生的,因?yàn)闆](méi)有人類(lèi)以外的智慧在安排計(jì)劃我們的生活,人類(lèi)社會(huì)完全就是一個(gè)“自組織”的過(guò)程,有意識(shí)的自由的行為不僅是這一過(guò)程的細(xì)胞,還是這一過(guò)程的動(dòng)力。就自由的市場(chǎng)秩序而言,不僅僅表現(xiàn)為個(gè)人的自由,組織的自由也是客觀存在的,這其中包括國(guó)家和政府的自由。而市場(chǎng)秩序的形成,正是無(wú)數(shù)自由相互競(jìng)爭(zhēng)、相互作用的結(jié)果。
擴(kuò)展閱讀
精品推薦
- 1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專(zhuān)業(yè)導(dǎo)論論文
- 2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專(zhuān)科論文
- 3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環(huán)境論文
- 4市場(chǎng)開(kāi)發(fā)的重要性
- 5市場(chǎng)監(jiān)管綜合行政執(zhí)法
- 6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本科畢業(yè)論文
- 7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策劃論文
- 8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實(shí)訓(xùn)報(bào)告
- 9市場(chǎng)開(kāi)發(fā)工作計(jì)劃
- 10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學(xué)專(zhuān)業(yè)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