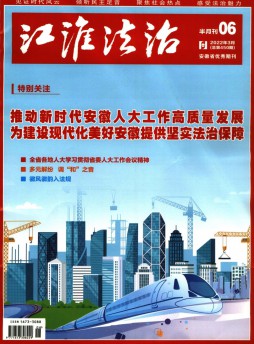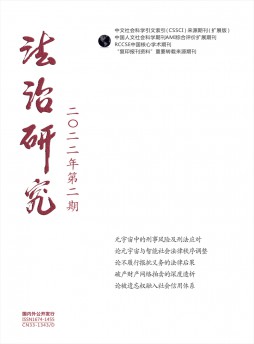法治現代化與理性淺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法治現代化與理性淺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法治現代化
有的著作中,法治化與工業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民主化、社會階層流動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識科學化、信息傳播化、人口控制化等被列為主要的現代性因素。[2]法是作為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與工業化等相適應的體制構建。而法的現代化是指與現代化的需要相適應的、法的現代性因素不斷增加的過程。簡而言之就是使社會生活中的法,具有更多的現代性(現代化的特征)。而法的現代性又有那些內容呢?經過學者的歸納,基本上包括以下內容:公開性、自治性、普遍性、確定性、可訴性、合理性及權威性。這八個法的現代性因素,概括起來就是理性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體現,或者說,法的現代性就是法的理性化。那么現代化背景下的理性,應該是怎樣的理性呢?鑒于筆者的閱讀量限制與學識的淺薄,在此介紹的是貝克的觀點。他認為應該把現代化區分為簡單的現代化與反省的現代化。他指的是:“簡單的現代化指傳統的理性化,反省的現代化指理性的理性化。”對此,筆者對這樣的觀點做如是理解。在20世紀后半期,中國人對法的理解是一種國家意志,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當時,在處理公權力與私權利的關系時,社會所倡導的服從國家的安排。即在20世紀90年代,“民告官”是一種難以想象的事情,最簡單的行政訴訟都將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新聞。或者在刑事案件中,“壞人”與“好人”是要嚴格區分的,壞就是要受到嚴厲的懲罰。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不會得到合法權利的關注的。還可以討論的就是,在大街上,運氣不好被逮到的小偷將是過街老鼠,人人可打。以上種種都是被世人認為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這些問題不再是專業法律人所壟斷的問題了。還記得在“藥家鑫”案件中,輿論的作用以及案件審理后社會對藥家父母的同情,再到政府“強拆”事件的不斷升級和社會輿論所關注的各種司法程序正義問題。法的現代性問題———理性化,其實存在于社會大眾之間,只不過法學家們用更理論、更系統的方式將其闡述出來。我們可以看出,這就是法律理性在發揮作用。
(二)理性與科學的意識形態
科學是理性精神的集中體現,科學進步是知識論思想傳統的直接成果,甚至現代文明本身也是完全依賴科學技術并且是以科學技術的進步為標志的。筆者認為,我們已經認定,現今的時代特征是一種“知識經濟”。由此看出,科學不僅代表的是技術的先進,更是一種先進的思想方式。乍看之下,我們的法律理性與科學也許相差甚遠。“科學”的思想觀念和方法論正是我們法律理性化所不可或缺的。正如馬克思主義法學所描述的,“科學”在于發現和揭示真理,目的在于使人的有機體在尋求更美好的世界的過程中發現、發明、改造新的環境,這要重要的多。由此可見,法律的理性就要求法律能更符合正義、公平、公開的理想境界。這必須是以科學的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所以,理性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就是要不斷貼近人們所期望的法律的理性。不論是在實體法還是程序法上。首先,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來反映客觀現實。人們所追求的法律都是為了解決最現實的問題,如果法律不能有效的反應客觀事實并提供有效的運行程序,那么理性將沒有存在的前提。其次,要用科學的方法論來形成系統完善、涵蓋面周全的法律體系。在理想理性的狀態下,法律運行能在法治的環境中,形成完美的形式,確定的內容,并具有有效的執行以適用法律。第三,不能缺少理性的法律人士。法律的理性來源于人的理性。基于前述的前提與條件,高度理性化的法律文件和適用法律的制度機制,形成專業知識的領域。于是,一個經過系統法律訓練的高度專業化的法律職業群體就必然要應運而生。這樣的狀態,就是在脫離了宗教神學的價值理性控制后的法律的全面理性化(工具理性)。
(三)理性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挑戰
有的學者認為,法學和民族志,如航行術、園藝、政治和詩歌,都是具有地方性意義的技藝,因為它們的運作憑靠的乃是地方性知識。這表明這些學者認為法律不可能具有一般普適性。若再作進一步的思考,法律是沒有全社會的普適性的,那么人們就是不具有統一的理性的,而是依賴于其他更能決定法律內容的事物。這樣,我們所堅持的理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還有學者,如弗蘭克、盧埃林等對法律的確定性表示懷疑。如果說現代法治的基本精神之一,就在于通過公開的法律文本宣告,用規范的、明確的、詳盡的文字形式告之公眾其權利義務,以建立理性化的行為預期,那么,對法律的確定性的否定必定將動搖近代以來形成的法治基礎。而對于法律職業的專業化所存在的問題,也是學者爭議的焦點。他們認為:隨著法律的日益復雜化、技術化、專業化和職業化,頗具核心功能的法律解釋已經出現精英文化的話語統制,這使現代性法律知識預設的民主與法治、正當與合法之間的緊密關系出現了較難克服的內在危機。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法律理性提出了質疑。這就不能不促進我們關注這樣的質疑了。從理論的角度來說,也許不是因為法治出現了問題,而讓我們審視它的理性基礎,而是理性基礎出現缺點,才迫使學界反思理性。
二、中國法治現代化與理性
(一)中國法治之困境
百年來中國法律制度從來沒有真正徹底進入現代化的狀態,因為它從來沒有超越自己,甚至也從來沒有認真想過對這個束縛中國人數千年的內外有別的思想界限的超越。因此,這就導致了中國法的現代化的一種特殊形式:一方面,我們強化了法律的工具理性化。這種自上而下的法制現代化模式必然對國家和政府權力極其依賴,因而,這種建立在法制現代化也必須依賴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表述政府命令,依賴一支職業化的法律專家隊伍有效地貫徹政府命令。這表明,中國法律在制度上對專業知識的依賴可能導向形式合理化;另一方面,我們并沒有把理性作為法官,寓于界限之內,缺乏把理性轉化為法律的精神條件。在意識的支配下,法律僅僅是貫徹統治者意志的工具,遠不是理性的主體之間可以以理性的方式加以討論、評論、論證的對象。所以,中國法制具有一種追求形式、忽略實質的形式主義,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表象。我國的法制仍然停留在效仿西方法治的層面上,并不曾讓理性深入國民骨髓,使得許多法律問題的解決只能是治標不治本。例如在民訴的理論分析中,我國的糾紛解決與西方法治國家的糾紛解決是不同的,即使存在同樣的訴訟制度。在美國,民事案件以調解結案的比例高達90%,而我國的調解率卻成為法官們的頭疼業績。在西方,調解之所以如此行之有效,就是在于當事人在正當的程序中,能有效的預見訴訟結果,并誠實守信的尊重各方主體。因此,調解成為了有效的糾紛解決方式,使當事人能回復到良好的關系。這就是一種理性的體現。由于中國只將法律當做一種工具,只能在形式合理性的層面上使用法律,所以,當事人在接觸到法律時,是一種不得以,甚至是帶著懷疑的態度進入司法程序。在這樣的前提下,裁判的效力是不能得到當事人的尊重的。如此而來,國家只是機械的運用法律,民眾也不能在法律中感受理性。
(二)對理性之堅持
在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下,我們認為社會本質上是客觀的。存在這樣的一種客觀規律,并且這樣的規律是理性的,是能被人們所感知并利用的。而法律是要反映這個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是人的意識產物。法律能否體現和反映客觀規律,就必須借助人的理性認知。這就是說,人是理性的,而社會規律也有它的內在理性規律。那么,法律成為了這兩者之間的橋梁,建造橋梁的工具就應該是理性。還記得在中國法制史中,清末法理派與禮教派之爭,表面上是要不要法治之爭,實際上還是中國是否具備法治的條件。由此看來,中國人是意識到了法治的必要性的,并且也是承認法的現代性———理性的。如今我們已經進入了世界現代化的浪潮,條件具備了,那么自然也就沒有理由反對法治。所以,把法的現代化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相聯系,無論什么目的,都是相當的。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以后,客觀規律決定法律的見解就被意識形態化,并且為法制建設提供了一個具有相當說服力的根據。它不僅提供了一個法制建設的系統化的理論根據,即社會處于永遠地有規律地發展變化之中,人的理性能力能夠揭示這種客觀規律,從而利用這種規律,把無意識的自然規律上升為國家法律;而且還根據這個規律使法制現代化具有了正當性。而且中國法制現代化也表現出了形式合理性的趨勢。但是,中國的法律遠遠不能稱為理性的,也不能是工具理性。因為工具理性是指形式意義上的法律的絕對權威,是強調規則的治理和統治。所以,中國法的現代性,在各種表現之下來看,是理性不足的。因此,在這樣前提下,對中國法治發展的理性堅持是絕對必要的。
(三)中國法治現代化之動力———理性
中國的法律傳統一直都缺乏理性。中國古人強調自律,而非他律。即使在當代社會,中國的法治建設也不可能與西方社會相同。中國的法治發展不是由內在的動力所激發,外在壓力才是法治思想進入中國文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國法治建設不可能回避自身的特殊問題。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問題,換一個角度就是法治的理性化。這是法作為理性的實踐要求。它要求立法、執法、適法和守法都應當體現理性,并把理性作為最高原則。這就要求我們在生活中時時以“法的最高理性”作為標桿來理解和適用法律。
第一,在法律、道德和政治的關系上,堅持法是理性的原則。法的理性來源自然法學派,所以法律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孤立的。法律、道德與政治必須要在理性的指導下,形成良性的關系。比如,見死不救、拾金不昧或見義勇為,當代是否將其上升為法律,已經激起了學者們的熱議。這其實是一種價值的選擇,不同社會、不同背景下的人都會對此有不同的選擇。價值本身是一種理性,而選擇價值的行為也是一種理性的體現。根據羅爾斯的觀點,設計制度時,允許價值沖撞,從中產生價值平衡,是一種理性的表現。對于政治而言,是同理可證的。中國當代一直不斷的在修改法律或增設法律,其中就包括對各種道德與政治的決定。此時,理性就應該是這種選擇的標準。只有符合理性標準的價值以及選擇行為才能決定法律的存在與否。
第二,社會必須要在法律的前提下理性的發展。當然,在法律成為最高理性時,尊重法律也就成為了理性。在法治國家,信仰法律和信仰理性具有同樣的意義。還記得亞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人們遵守的法律應該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反過來說,如果不是良法,就不應該獲得人們的信仰。這對我們中國社會是十分重要的。在法律制定的前提下,我們應該要學會信仰法律。不然,制定法律又不信仰它,這樣的法律勢必會阻礙社會的發展,成為社會運行的絆腳石。因為此時的法律不是最高原則,在問題處理時,法律會與其他事物相矛盾,利益雙方永遠得不到解決。
第三,理性原則同樣也是一種實施原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法律要想獲得廣泛而忠實的遵守,因為它能體現人民的利益,具有理性。這是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要求。但除了法律內容的理性化,當代法治社會強調“程序正義”,這不得不給法律理性披上了一層新衣。運用法律也是理性要求的范圍。司法實踐中,只有真正的理性程序才能說服人,才能使司法活動在普遍的尊重中獲得真正的權威。人們在遇到糾紛時所期盼的是法院能成為一個說理的地方,而法律的規定也使法院成為糾紛的最終解決地,因此,理性的程序性要求必須要充分表現在適法的過程中。在中國,各種起訴難、申訴難的問題,辯論在判決中的影響力以及干涉處分權等問題比比皆是。法律理性在適法中被阻斷。法律理性不能只提留在字面上,而是一種以法律體系為載體的全方位的最高原則。
本文作者:劉柳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