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文明對國際政治的塑造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淺析文明對國際政治的塑造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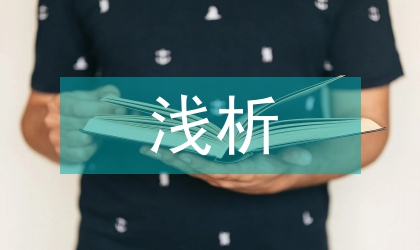
文明這一文化的集大成者在所謂蘇聯共產主義已然崩潰的后冷戰時代的今天,理所當然地取代了意識形態而成為人們判別自身所屬陣營的新標準。在這樣一個立論基礎上,《文明的沖突》進一步闡明了其關于未來世界秩序的核心思想:不同種類文明之間的沖突是國際沖突的根源,文明間的關系將在極大程度上決定未來國際格局的走向。從地區范圍的微觀層面上看,“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而上升到世界范圍則“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亨廷頓為了能確切地勾勒出其關于當今及未來國際格局的藍圖,甚至對他所列出的八大文明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致的定性,諸如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及伊斯蘭文明之間的沖突性較重,東正教文明與印度教文明之間的沖突性較輕等等。亨廷頓的這一“看待全球政治的……[新]范式”在解釋不少國際事件特別是一些熱點問題上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它對波黑問題的解釋更是近乎完美。穆族、克族、塞族在波黑地區的血腥戰爭便是活脫脫一副“文明沖突”的畫面,而且三大種族還得到了各自所屬文明之“核心國家”的支持。亨廷頓形象地稱之為“文明斷層線上的戰爭”。此外,亨廷頓的理論還有助于人們理解諸如北約東擴、印巴沖突、東帝汶獨立、車臣戰爭等重大事件。然而,人們也不難發現“文明沖突論”在解釋其他許多重要的國際事件上并不靈驗,一如亨廷頓本人在書的前言中所承認的,它并不能說明“正發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事情”。就以北約東擴為例。總的來看北約東擴可以解釋為西方文明在軍事上對東正教文明核心國家俄羅斯的遏制圍堵,總體上驗證了“文明沖突論”的觀點。但既然“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國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則分道揚鑣”,為什么像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這些有著“斯拉夫”文化背景的國家竟然最熱衷于加入北約?此外亨廷頓對于當下中日關系的認識也是缺乏洞察力的。他從中華文明與所謂“日本文明”乃親族文明的觀點出發斷定日本遲早將“順應中國”,從而未能在根本上把握住將極大影響未來亞太地區乃至世界格局走向的中日關系之本質。但盡管如此,“文明沖突論”還是以其新穎的視角第一次將文明與國際關系的關系呈現在了一切關注國際政治走向的人們面前。它至少激發了人們的思考,即文明是以怎樣的方式,在一個怎樣的程度(及層次)上參與了對國際政治的塑造。事實上,亨廷頓并非第一個深刻認識到文明對國際格局的演變施加了強烈影響的人,對這一關系的認識至少還可追溯到20世紀西方杰出的歷史學家湯因比。湯因比藉以理解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思維方式就是“文明”的。“歷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說明問題(self-intelligible)的單位既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也不是一個極端意義上的人類全體,而是我們稱之為社會[即文明]的某一群人類。”因而湯因比對屬于人類社會活動的國際政治考察也是站在“文明”高度上進行的。
令人欽佩的是,湯因比早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冷戰正酣之時便能超越“意識形態論”的思維窠臼深刻洞察到美蘇冷戰的真正本質。湯因比并不認為美蘇間的冷戰是基于意識形態上的爭執,相反,美蘇沖突有著強烈的“文明”背景。在湯因比看來,整個世界近現代史實質上就是一部西方文明的全球擴張史,是一部西方文明利用其無與倫比的經濟技術優勢強行將其余諸文明納入到一個巨大的全球性經濟、技術之網中的歷史。世界上所有的非西方文明,無論情愿與否,都或多或少地卷入到了這場全球化的浪潮中來,并且被迫作出各種選擇以適應這一全新的環境。于是,整個世界近現代史也可以理解為一部西方文明與其余諸文明的“互動”史。而對于冷戰期間美蘇關系的理解若離開了這一世界近現代文明史的大背景則必定不可能抓住其本質而流于淺顯。表面上看,美蘇冷戰似乎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然而實質上蘇俄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斯拉夫東正教文明對全球西方化挑戰的應戰。蘇俄之所以認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僅有政治信仰方面的原因,其根源更在于,“共產主義雖來源于西方,但在西方人心目中卻是一種可憎的異端”。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學說作為對近現代資本主義的深刻批判,從根本上就是對工業資本主義的西方文明的反叛。蘇俄社會主義模式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展開的冷戰不僅體現了意識形態的爭執,更是以蘇俄為代表的東正教文明試圖向全世界其余諸文明指出西化以外的另一條出路,一條他們認定必將成功應對由西方文明所帶來之全球化挑戰的光明大道。對這一本質的把握也有利于人們理解為什么冷戰后的今天俄美關系仍舊是一種不尷不尬、由冷戰趨于“冷和平”的狀態。整個世界歷史的進程實質上就是世界諸文明發展演變的歷程,而國際政治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理應被放置到“文明”的高度上加以考察。事實上,當前整個國際政治的現狀就其本質而言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各大文明板塊經年累月的互動在國際關系中的反映。“文明沖突論”的啟示在于,它為國際政治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使國際政治研究在繼意識形態、國家利益、綜合國力、民族心理等等之后又獲得了一個嶄新的研究維度———“文明”的維度。它使得人們認識到,國際政治不僅僅是國與國之間的事,而且也涉及“文明”這一“能夠自行說明問題的歷史研究單位”,從而為國際政治研究獲得一種真正的歷史縱深。
然而,“文明沖突論”的巨大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它雖然站在了“文明”的高度上,但卻沒能進一步洞察文明在塑造國際政治方面的復雜作用。在亨廷頓那里,文明所起的作用僅限于作為人們自我認同,界定敵、我、友關系的尺度。且為了充分展示文明的這一作用,亨廷頓甚至不惜對各大文明間的關系作了一番充滿主觀臆測的定性。他炮制的所謂儒教—伊斯蘭文明聯盟只能用“牽強附會”一詞來形容,而所謂的“非洲文明”、“日本文明”則更像是他一手捏造出來的,至于書中所描繪的未來儒教—伊斯蘭教—“日本文明”的聯盟與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展開的文明大戰則更是不能不令讀者懷疑自己是否在閱讀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亨廷頓在涂寫這樣一幅“文明大戰”的圖景時所表現出來的隨意性與煽動性不由使人感到,他似乎并不具備一名卓越的國際政治學者應有的“世界主義”胸襟。很顯然,亨廷頓之所以會得出這樣一幅與事實并不相符的“文明組合圖”,其根源還在于他過分簡化了文明在國際政治形成與演化過程中所起到的極其復雜的作用。文明絕不應僅僅作為界定國與國之間之敵、我、友關系的尺度而被納入到國際政治的研究領域中來,文明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要遠比這深刻得多。就以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斯拉夫”國家在北約東擴中的表現為例。這些國家就其文化傳統而言照例應劃歸東正教文明的行列,但在外交上它們卻并不是捍衛其“核心國家”俄羅斯,而是積極充當北約東擴的急先鋒。在這里我們發現“文明沖突論”的邏輯喪失了效力。誠然,文明的不同確是西方與俄羅斯之間互不信任的深刻原因,并且這種隔閡還由于基督教在羅馬天主教廷與東正教會之間上千年的分裂而變得根深蒂固,但在北約東擴的這個例子中,文明對非核心國家或所謂“亞文明國家”的外交走向的影響卻是另一種性質的。上文曾經談到,當今的世界歷史實質上即是西方文明在其全球擴張的過程中與諸非西方文明的“互動”史。而東正教文明在應戰由西方文明所帶來之全球化的過程中卻以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徹底失敗而告終,這一失敗的“文明”的含義是:它被世界其余諸文明國家(亦即冷戰期間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理解為東正教文明應戰全球化(某種意義上即西化)的一次重大失敗。它不僅對所有正蹣跚于現代化道路上的其余諸文明國家是一個教訓,更重要的是,它給所有的東正教文明國家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文明的核心國家俄羅斯作為昔日的“現代化的指路人”威信一落千丈;其余東正教國家除了白俄羅斯仍舊緊隨俄羅斯外只有南聯盟和希臘仍然在感情上親近俄羅斯;烏克蘭介于西方和俄羅斯之間;至于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則干脆公開要求加入西方陣營。在這里,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嚴格按照文明(或文化)的屬性進行切割的,但卻同樣可以用“文明”的觀點加以解釋。匈、保、羅諸國雖屬東正教國家,但從蘇聯解體及俄羅斯國力的長期不振中它們看到的是蘇俄模式適應全球化嘗試的失敗,而在它們眼中,加入北約、融入西方陣營將使自己搭上當今世界最強勢文明的現代化班車。至于純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雖然與它們的東正教文化背景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但這顯然不是作為亞文明國家的它們最優先考慮的問題。
另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日本。嚴格說來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日本文明”。在《文明的沖突》中,“日本文明”是與拉丁美洲文明甚至東正教文明一道作為西方文明抗衡其想象中的所謂儒教—伊斯蘭聯盟的“統戰對象”而炮制出來的:西方文明對“日本文明”所要做的就是“延緩日本脫離西方而順應中國”。因為日本作為一個獨立文明出現畢竟還有成為其“統戰對象”的機會,而如果僅僅是作為儒家文明圈中的一個亞文明國家,那么按照“文明沖突論”的邏輯則只有與中國站到一起的份了。然而歷史地看日本的真實身份卻只能是一個成功實現了現代化的儒家文明圈中的亞文明國家(地區),并且,它的“文明”身份也并非是獨一無二的,與其同屬一個文明圈的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香港、臺灣地區亦屬此列。誠然,日本歷來在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都能保持其文化的獨特性,但這種獨特性與文明核心國家如中國、印度的文化在世界歷史中的獨特性相比則顯然不在一個層次上。并且,于日本本島發展起來的日本本土文化其發展形態根本不足以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更何況在塑造日本人格的傳統價值觀中除了其本土的“神道教”文化外還有根深蒂固的儒、佛甚至道家的思想淵源。如果要將具有一定獨特性的確實存在的日本文化硬性提高到“文明”的層面,是否也可以因為韓國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也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性而把“高麗文化”稱之為“高麗文明”呢?我們是不是還能生產出諸如“美國文明”、“土耳其文明”、“澳洲文明”呢?將日本文化誤會成“日本文明”,只能是因為沒有充分領會文化與文明之重大區別的原故。文化是人類創造的從根本上有別于動物的生存方式(當然包括人類的精神生活),文化的出現標志著人類可以“不用經過生理上的突變便能很好地應付周圍的[生存]環境”,從而使人根本有別于動物。文化是一個內涵遠大于文明的概念,并且更多的是地域性和群體性的概念。我們可以說每一個地區或每一種類型的人群都有屬于自己的文化,小到一個村莊,大到一個民族國家,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并且我們還可以有茶文化、戲劇文化、旅游文化等類型文化。但文明則不同,文明乃是文化的集大成者,是無數地域、群體、類型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果,是文化發展到了極高的形態才上升到的高度。文明意味著從根本上塑造人格的,在價值觀、倫理觀、審美觀、根本世界觀上形成的偉大傳統,它所牽涉到的絕不僅僅是某個地域(甚至民族國家)或某個階層的人群,而是影響到在一個極為廣闊的地域內所有受到這一傳統規范的跨國家的人類群體。日本與其說因其文化的獨特性令人矚目,不如說是由于它在現代國際關系中的獨特處境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日本之獨特性在于,它是世界近現代史上第一個成功實現現代化的非西方國家,并且其社會發展水平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西方國家(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是一個極其善于吸收外來文化的國家,歷史上它曾是古代中國文明的門生,今天它又是西方文明之核心國家美國的追隨者。日本國民性的這一特點使之能夠在不同歷史時期都能搭上強勢文明的便車,站在文明的最前沿,但恰恰又正是這一特性決定了它永遠只能做一個一流的“亞文明國家”。
日本是一個夾在儒家與西方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民族國家,它雖然自明治維新以來長期施行所謂“脫亞入歐”,但其“文明”的靈魂卻仍舊屬于儒家文明圈。作為率先實現現代化并與西方文明關系親密的儒家文明的亞文明國家,日本正經受著民族精神的深刻分裂。這種分裂表現在國家政策上就是所謂“脫亞入歐”與“脫歐入亞”之爭,以至于人們至今不知該將其劃歸為西方國家還是亞洲國家。因而今天日本外交面臨的一個根本窘境是,隨著整個東亞地區諸儒家文明圈所屬國家和地區的紛紛崛起(先是韓國、新加坡、香港、臺灣等亞洲四小,而后是整個東南亞地區及中國大陸),日本意識到“文明”的風向似乎正在發生變化,并且最為重要的是,日本面臨著這一地區理所當然的文明的核心國家中國徹底崛起的前景。以日本列島地域之狹小,文化原創力底蘊之淺顯,日本對它的這個西部大鄰國的重新崛起在“文明”的層面上意味著什么心知肚明,并深知在最終的將來與之爭奪該文明地區的主導權將是十分不智的。然而日本的尷尬在于,曾經因率先實現現代化而自詡為所謂東亞經濟發展“雁形陣勢”之領頭雁的它面對中國可能重新主導該地區的前景,其民族心理自然是苦澀而又焦慮的,因而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何日本在多年前綜合國力尚強于中國的情況下仍要與另一文明的核心國家美國結盟以抗衡中國了,這乃是其焦慮和不自信心理的真實表露。事實上,對當前中國崛起的壓力最有切膚之感的還不是大洋彼岸的美國,而是與中國同屬一個文明圈的日本。未來中日關系的走向將因此而極為引人注目,并將因為兩國巨大的國家實力對亞太乃至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中日關系的極其復雜性表明,文明在對國際政治的塑造中并非僅僅是作為劃分敵、我、友關系的尺度起作用的,文明對國際政治的塑造常常是通過由文明間的遭遇所導致的相關國家的社會文化變革而發生的。在世界近現代史上,除西方文明外其余諸文明均面臨著一種弱勢文明遭遇強勢文明的局面,并且這種遭遇還具有強制性。弱勢文明遭遇強勢文明對該文明所屬國家和人民而言意味著他們不得不同時面臨兩個文明的傳統,由于強勢文明是以一種強者的姿態降臨的,它的傳統價值觀勢必對弱勢文明的國家和人民產生巨大的沖擊,并使之對原有的文明傳統產生懷疑和動搖,這一切必將導致弱勢文明原有之價值觀傳統的分裂,而這一分裂不可避免地將體現在民族國家的外交政策上,并造成同一文明圈內核心國家與亞文明國家外交走向的分野。一般而言,核心國家總是更趨于固守原有的文明傳統,而亞文明國家在面臨外來強勢文明的強權時總是更易于產生離心傾向。因之,人們就不難理解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之要求加入北約,19世紀后半葉日本的“脫亞入歐”,凱末爾的土耳其之有別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國家……
此外,在當今多元文明并存的條件下,從一個更根本層次上參與塑造國際政治的將是由各文明的交融互動所催發的文明自身的演變興衰。顯而易見,在國際政治中只有大國關系(很大程度上是文明核心國家間的關系)的整合才是推動國際格局演變的直接誘因,其中對各大國間戰略關系的走向起決定性作用的乃是各主要大國綜合國力的消長。保羅•肯尼迪認為:“經濟[國力]增長速度不平衡,對于國家體系中許多成員國相對的軍事力量和戰略地位都產生了決定性的長期影響。”我國學者黃碩風在其綜合國力研究專著《大較量:國力、球力論》中也明確提出:“新時期戰略格局變化的基本動因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其引起的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換言之,國際關系體系中各大國的力量消長必將使各主要大國的力量對比態勢發生深刻變化,從而最終導致大國關系的重新組合。然而世界歷史在當前的一個主要特征是,“當今世界實質上是歐洲[西方文明]的擴張和全球霸權的產物,也是這種擴張和霸權所激起的反應的產物”,因而整個人類歷史的前景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今世界之強勢文明———西方文明與諸非西方文明“互動”的結局如何。一方面是諸非西方文明如何應戰由西方文明的擴張引發的全球化并因此發生深刻變革,另一方面則是西方文明自身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由于受到諸非西方文明的挑戰而受到深刻影響。這樣一種互動的結局將極大地影響到諸文明自身的興衰演變,并因此直接關系到其各自所屬民族國家特別是核心國家的興衰。因而民族國家綜合國力的消長就絕不僅僅只是民族國家自身的事,民族國家的興盛從來都是與該國所屬之文明的發展興衰息息相關的。中國在近代歷史上的積弱積貧其根源在于它所代表的傳統農業文明相對于西方工業文明的衰敗,而不是一句“由于清王朝的腐敗無能”就能夠輕易打發的。同樣,與近代中國有著類似命運的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國,也無不是因其所屬文明的衰落而遭致西方列強的欺凌。而在當今這個多元文明并存的世界里,除了東亞的日本、新加坡等極少數國家外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均為西方國家,這也絕非偶然。
西方文明自文藝復興以來就一直以其勃勃的生機和不竭的創造力而逐漸后來居上,不僅超過了原先遙遙領先的古代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以及以古羅馬帝國正統繼承人自居而固步自封的拜占庭文明(今日東正教文明的前身),而且還將它們遠遠拋在了后頭。因此,文藝復興的意大利,大航海時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的“海上馬車夫”荷蘭,18、19世紀的英國,以及從20世紀初直至今日的美國,作為最強勢文明西方文明的核心國家也無一例外都是它們各自所屬時代國際政治中的最強國。因此,在人類社會已進入多元文明共存互動時代的今天,國與國尤其是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與消長都顯然與其所屬文明的發展態勢密切相關。今后,任何對大國力量對比及其走向的考察若撇開了對當今世界諸文明發展狀況的比較研究都將是有欠深刻的,因為民族國家尤其是各主要大國的興衰無一不是從根本上源于其所屬文明的興衰成敗。因而整個國際政治戰略格局也就與體現各文明發展態勢的“文明的格局”有著根本關聯。當今世界的“文明的格局”是:西方文明雖然仍以其無與倫比的經濟技術力量保持其最強勢文明的地位,但它的這一地位由于受到來自其余諸文明的有力挑戰而正變得相對衰落。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屬于儒家文明圈的東亞地區通過在經濟科技上的巨大進步而開始改變數百年來西方占絕對優勢的傳統格局。當今世界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全球性發展趨向———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崛起,并且這一趨向極有可能由于中國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參與者(李光耀語)的逐步崛起而得到根本加強。中國作為儒家文明圈之核心國家的崛起是周邊諸亞文明國家和地區相繼獲得大發展之后的一個必然,先是日本,而后是新加坡、香港、臺灣、韓國等亞洲四小龍,繼而波及東南亞各國,最終是核心國家中國。中國作為文明的核心國家文化傳統自然最根深蒂固,社會文化轉型自然最為艱難,因而它的崛起在東亞各國和地區中最晚并非偶然,然而一旦這個幅員遼闊、底蘊深厚,有著數千年文化原創力傳統的泱泱大國成功步入現代化軌道,它所爆發出來的能量將遠非日、韓等國所能企及。
中國的最終崛起將不僅僅意味著一個民族國家的興起,它有著深刻的“文明”義涵,它標志著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就開始的儒家文明圈的全面復興。這一復興將向全世界表明,除西方文明外的其余諸文明在應戰全球化、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上完全能夠取得成功。以中國的最終崛起為標志的儒家文明圈的全面復興將是對西方文明數百年來統治地位的真正挑戰,它將永久改變世界的文明格局,并徹底改寫國際政治格局。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們當能理解為什么當今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是中美關系。中美關系不僅僅是兩個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它更是兩個文明核心國家之間的關系,代表著一個正在全面復興的文明與當今最強勢文明之間的關系。美國和中國的外交走向意味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一個代表著對現有文明秩序的根本否定,另一個則力圖維系數百年來的文明格局,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視中國為其最大的“潛在對手”。因而,現今所有文明的核心國家都始終應當是國際政治研究應予以重點關注的對象,因為它們作為各自所屬文明在國際關系體系中的當然代表將始終具備徹底改寫整個國際政治格局的潛能。在當代多元文明的條件下,任何對國際政治的深刻理解都應當建立在對“文明”的深刻理解的基礎之上。
本文作者:陳一鳴單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 上一篇:認知心理學在國際政治中的應用范文
- 下一篇:經貿局黨建思想工作意見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