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心理學在國際政治中的應用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認知心理學在國際政治中的應用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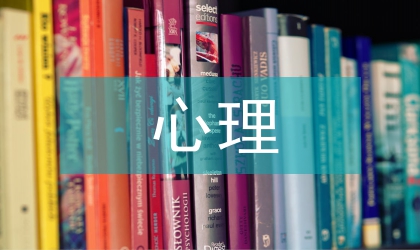
一、研究國際沖突的個人視角
相對于個體概念而言,國家事實上是一個抽象的實體,國家作為這樣一個客觀實體的抽象性便決定了國家行為作為一個分析變量時似乎難以把握。然而,國家行為終歸是要通過人的個體行為表現出來的,個人在國際政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國際關系心理學流派個體心理分析理論的主要理論預設是個體作為國家行為的行使主體,一國的國家領導人與政策精英才是抽象國家行為的具體實踐者。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個體尤其是領袖或重要的領導人建構了一國的國家行為。在此基礎上,杰維斯提出的理論假設為:在不確定的國際條件下,國家決策者事實上很容易發生錯誤知覺,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傾向于將其他國家視為具有沖突意圖的對手,并夸大對方的敵意。因為互動的雙方都趨向于發生這樣的錯誤知覺,國際沖突的幾率將會明顯大于合作的幾率。因此,作者抽提出兩個研究變量:決策者的知覺(自變量)與國家之間的沖突行為(因變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即是:國家決策者之間的錯誤知覺很可能會加劇國家之間的沖突,甚至會導致國家之間的戰爭。
二、錯誤知覺的生成機制
在提出理論假設之后,杰維斯將心理學中幾個重要的導致錯誤知覺的機制運用到國際關系研究中,并運用大量的歷史數據證實自己的假設,分析了為什么決策者會發生錯誤知覺。錯誤知覺的產生機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分別是認知相符現象、誘發定式及歷史學習和類比。首先是認知相符現象,即人們總是傾向于保持自己的原有知識,希望能將新的信息融入原有的認識框架。如果新信息與原有知識不一致時,他們往往會對其視而不見甚至曲解誤斷,以使新信息與原有的知識保持一致。其次是誘發定式。人們在接收到外來信息時,往往會以他們即時關注及考慮的問題為定式,并據此來認識和解讀接收的信息。即便在信息完全溝通的情況下,雙方也很難理解發送信息者的意義。如果處于相互敵對和有限溝通的情況下,加之由于政府內部信息的不平衡、雙方關注點不同等因素的影響下,錯誤知覺就更常發生。第三是歷史包袱。人們往往從歷史事件中吸取教訓,但如果機械地將現實同歷史相比,則會由于人的認知局限產生誤導,將一些實質上不相同的現實事件同歷史事件牽強地聯系在一起,出現嚴重的錯誤知覺。在從理論層面探討了錯誤知覺的種種生成機制后,杰維斯繼續剖析了四種常見的錯誤知覺。首先是國家決策者往往傾向于將其他國家視為團結一致、高度令行禁止的行為體,在這種設定下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是對方有計劃的而絕對不是無意或偶然的。其次,決策者往往過高估計自己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和自身作為目標的重要性。假如對方國家的行為與己方期望一致,那么決策者往往容易高估其自身政策對結果產生影響的程度;但如果對方國家的行為與己方期望不相符,決策者往往認為這是對方的敵意預謀,而非對其自身行為的一種反應。第三是一廂情愿(wishfulthinking)的認知陷阱。由于期望和懼怕塑造著個體的知覺,行為體所感知到的往往是他們(潛意識里)所希望感知到的東西。最后是認知失調,即決策者總是為自己的既定政策尋找理由,以自圓其說。
三、評介與思考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心理學界興起了一場認知革命。之后,國際關系研究中也大量借鑒了認知革命的成果,包括心理學中的社會學習理論、信息處理加工、意象與信念體系及知覺與錯誤知覺等在國際關系的理論分析中得到了廣泛的領會和運用。其中,羅伯特•杰維斯無疑成為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進行了將心理學的概念和方法運用到國際政治研究的開創性嘗試,揭示了一個理性行為體是如何由于心理機制和認知過程中的偏差而帶來難以避免的非理性決策。同時,杰維斯的理論成果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認識到個體知覺的根源將有助于減少國際關系實踐中大量存在的錯誤計算與誤解,有助于學者和決策者對其他國家的意圖進行更為精確的分析,從而能制定或提供比僅僅依靠“國家利益”分析框架對國際關系的分析更有效的政策。
當然,杰維斯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研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第一是理論解釋力的不足。國際沖突和戰爭的原因是國際體系、國家內部及決策者多個層次上不同的變量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僅僅單純從心理學角度去分析是難以完全說明戰爭產生的根源的。正如美國學者沃納•利瓦伊(WernerLevi)教授指出的那樣“,在這些關于戰爭的心理根源的生動猜測中,總是缺少一種把人的根本天性同戰爭的爆發聯系起來的環節。……正確的做法往往是把人的心理因素和人類本性歸納為戰爭的條件,而不是戰爭的根源。”第二是理論模型與個案研究的問題。杰維斯運用心理學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論范式和研究方法等)進行國際關系層面的實證研究,而理論研究和創新略顯不夠。所以,這種研究取向客觀上將導致國際關系心理學的理論說服力不足并大大限制它的發展空間。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政治現象往往具有煙云的特性,是多種因素和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心理學研究中一般注重運用的是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杰維斯借鑒的很多結論也都是實驗室的結果。這些結論在應用到國際政治事務的分析時是否足夠客觀及有效,尚有待驗證。第三是政治心理與國家政治文化問題。政治心理研究是與一國的政治文化研究緊密相連的,但現有研究在兩者的結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現有對個體心理的研究、國家決策和國際危機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歐美文化情境。有學者就認為杰維斯僅局限于分析“大國間關于戰爭以及雙方意圖的議題。……但對于國際談判以及南北關系則幾乎沒有涉及。”這種背景之下的理論成果能否超越時空的局限而具有普遍相通的適用性,至少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確證。其次,杰維斯“僅僅討論了個人經歷是如何影響觀念預期的,但忽視了整個官僚文化、社會背景等對個體認知起到的作用。”這說明我們需要把個體心理與社會心理的研究高度統一起來,需要進一步解釋歷史事件和社會實踐對個體的身份、思維、個性與認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構作用。
總之,“杰維斯的著作填平了外交決策理論與認知研究之間的鴻溝。……對個體信息處理與認知重建之間的互動做了迄今為止最好的分析。”因此,我們應重視個體層次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運用前輩學者業已取得的成果進行更多的實證分析乃至于理論的創新。
本文作者:徐瑤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 上一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意見范文
- 下一篇:淺析文明對國際政治的塑造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