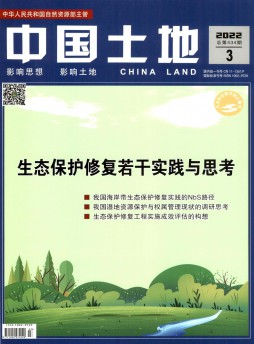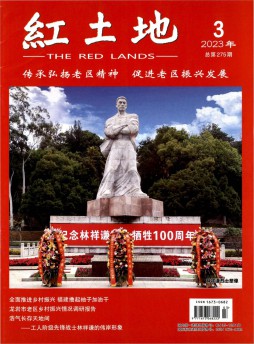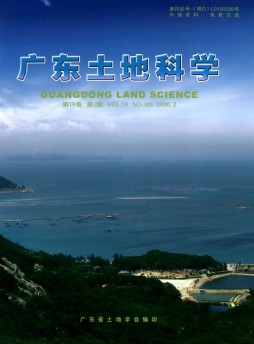土地行政復議的檢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土地行政復議的檢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雜志》2014年第三期
隨著土地行政管理改革的深入,柔性行政行為和過程性行政行為進入大眾視野,土地行政復議機構在面對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裁決、信息公開和歷史遺留等復議申請時往往猶豫不決,現行法律法規中關于“何為具體行政行為”的界定已跟不上時代變遷的步伐,復議受案范圍的狹窄和封閉狀態嚴重制約著土地行政復議的長遠發展。《行政復議法》在第二章規定了行政復議的受案范圍,其中第6條采用列舉法試圖窮盡行政機關可能影響行政相對人的各種具體行政行為,該條文最后一款進行兜底,概括出行政復議的受案范圍涵蓋“行政機關作出的、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所有具體行政行為”;第7條的規定普遍認為是行政復議相比較行政訴訟的一大進步,該條文指出行政相對人可以在提起對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的復議申請時一并提出對支持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規定(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即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但該條文最后一款同樣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外延作出了限縮性解釋,排除了規章(包括國務院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和國務院制發的規范性文件,導致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偏于狹窄,且附帶于具體行政行為審查的要求間接抬高了復議門檻;第8條是否定式列舉,將行政機關的人事處理決定等內部行政行為和民事調解行為排除在行政復議的受案范圍之外,分別交由申訴、仲裁或訴訟來救濟。由于《國土資源行政復議規定》等下位法沒有對土地行政復議的受案范圍作出新的排他性規定,所以在土地行政復議案件的處理中同樣適用《行政復議法》的有關規定。通過上述解讀不難發現,土地行政復議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和土地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對接,即土地行政復議在受案范圍上與土地行政訴訟的列舉驚人的相似,沒有擺脫土地爭議訴訟在受案范圍規定上的局限性,似乎是單純為了替訴訟“分擔壓力”而存在,其自身獨有的制度價值難以體現。受案范圍的界限需要法律來劃定,而受案門檻的高低則掌握在土地行政復議機關手中,它們肩負著進一步降低受案門檻,方便群眾提起土地行政復議的職責。近年來,各級土地行政復議機關積極探索,總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降低受案門檻的工作方法,值得整個行政復議系統學習和效仿。第一“,從寬受理”的原則。河北省國土資源廳在土地行政復議辦案中確立了從寬受理的辦案指導原則,對于復議申請人的復議申請,符合法定條件的一律受理;基于行政機關之間業務界限的模糊,介于可受理和可不予受理之間自由選擇的案件也予以受理;對于非行政行為相對人或非利害關系人提出的復議申請,本著“有訴求就可能有侵害”的審慎心里,根據從寬受理的原則也予以立案受理。從寬受理的原則打破了以往土地行政復議機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懶政”心理,促使復議工作人員以更加積極開放的心態向老百姓敞開復議救濟的大門,盡可能最大限度地吸納人民群眾對于土地行政管理行為的各項利益訴求。第二“,反向排除”的方法。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在處理土地行政復議案件時不再拘泥于《行政復議法》關于行政復議受案范圍“肯定式列舉”的方法,而是采用“反向排除”的判斷方法,遇到復議申請首先看是否處于受案范圍的法定剛性“禁區”,若在“禁區”之內的,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不予受理并及時告知復議申請人尋求其他途徑的救濟,除此之外一律受理。逆向思維的判斷方法不僅客觀上降低了受案門檻,縮短了復議機關的審核時間,也節省了復議機關的審核工作量,一舉兩得。第三“,履行告知”的舉措。各級土地行政主管機關越來越注意保護相對人的知情權,告知當事人對具體行政行為不滿享有提起復議的權利;若當事人提交的復議申請材料不齊全或申請書格式有紕漏的,海南省國土資源廳一次性告知申請人補正;對于符合土地行政復議申請條件的涉地信訪和違法舉報事項通過“履行告知”的舉措積極引導當事人通過復議的法定渠道尋求救濟。可見,“履行告知”的方式無形中拓寬了行政復議的受案范圍。
二、土地行政復議之問責體系
責任意識是依法行政的前提,沒有責任的明確劃分和侵權后的有力追責,土地行政復議的權威性就不復存在,土地行政行為也就缺乏強有力的約束,長此以往必然導致土地行政管理機關行政作風的散漫和侵權事件的頻發,土地行政爭議層出不窮而無法得到緩解。只有強化國土資源系統的責任意識,貫徹“有權必有責”“,違法必追責”的理念,才能更好地保證土地行政復議的效果。土地行政復議法律法規對于復議不作為或違法復議的責任規定較為匱乏,為數不多的責任形式也十分原則和籠統,局限于內部行政處分的偏多,而關于如何對行政相對人的損失進行合理賠償(或補償)以及賠償(或補償)標準和程序的規定卻只字不提。對此,筆者認為應當引入外部責任的相關規定,豐富法律責任的形式和懲罰梯度的設計,同時借鑒行政賠償的法律原理,達到既能保證問責力度,約束土地行政復議人員,又能合理補償行政相對人的損失,實現權利救濟的目的。土地行政復議不僅存在問責形式單一和問責力度孱弱的弊端,對問責主體和問責對象的設計也存在明顯不足。問責主體方面,法律沒有明確復議行為的監督主體,導致土地行政復議機構的復議行為缺乏監督和制約;復議機構雖然可以審查被申請人的具體行政行為,對被申請人的違法之處提出處理意見,但復議機關卻不享有問責的最終決定權和實際操作權,同時基于復議機關與監察、審計、紀委等實際問責主體之間問責銜接的不暢,出現了問責主體“空洞化”的現象。問責對象方面,關于土地行政復議的法律法規中存在過多諸如“責令限期改正”、“責令重新履行”的規定,針對部門的“團體問責”較多,針對機關領導和直接責任人的“個人問責”偏少,而“團體問責”的模糊性又決定了其對個人的實際影響較小,以至于容易成為復議分管領導和具體責任者規避個人責任的“保護傘”。為此,在土地行政復議的責任體系中,我們要分清各自的定位和歸屬,復議機構要肩負起化解行政爭議的“終結責任”,引發行政爭議的土地管理機關則要承擔避免類似爭議再次發生的“預防責任”。被申請人(一般為爭議引發機關)收到復議決定后要自覺履行,若原行政行為被撤銷、變更或被確認違法的,要在積極進行足額賠償(或補償)的前提下追究分管領導和具體責任人的法律和行政責任,必要時可向具體責任人員追償。
作者:馬迅單位:山東大學法學院
- 上一篇:刑事和解制度的新思考范文
- 下一篇:環境資源保護法制建設研究范文
擴展閱讀
- 1土地調查落實計劃
- 2土地糾紛
- 3土地資源及土地經營分析
- 4土地財政與土地城鎮化互動關系
- 5土地巡查報告
- 6集體土地
- 7土地買賣合同
- 8農業土地流轉研究
- 9農村土地流轉分析
- 10探索土地流轉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