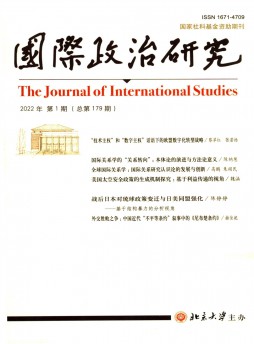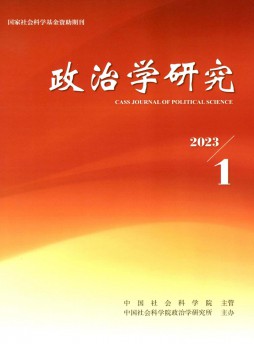政治演變的內在邏輯及其當代啟示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政治演變的內在邏輯及其當代啟示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中國政黨興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生俱來肩擔著整合社會、創建國家和振興民族的歷史使命。中國政黨政治歷經了從多黨競爭制、一黨壟斷制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的歷史演變。縱覽中國政黨政治的歷史與實踐可見,政黨是推動近代中國進步的重要工具,政黨政治并不存在定于一尊、一成不變的實踐模式;中國共產黨是推動中國政黨政治不斷變革、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的關鍵力量,必須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
關鍵詞:中國政黨;政黨政治;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厘清當代中國政黨政治①內在邏輯是當前我國學術研究領域一項重要課題,而探析中國政黨的興起緣由及其肩負使命、考察中國政黨政治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脈絡與實踐狀況,又是此項研究課題的重要任務。鑒于國內學術界對此問題的認識和研究至今仍然存在諸多不足,因而主要選擇從歷史與實踐這兩個層面對中國政黨政治研究課題作補充探討。在一定程度上,這不僅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論”給中國造成的思想桎梏,同時可為中國政黨政治的深入實踐提供有益啟發。
一、近代中國政黨的興起緣由及其肩負使命
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到特定階段的歷史產物,政黨不僅是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政治權力的執掌者,還是現代外交的政治行為主體之一。這種政治現象被統稱為政黨政治,以此區別于此前的神權政治或帝王政治。當代中國也是政黨政治國家,國家政治權力是交由現代政黨而不再是傳統的“天子”執掌的。但揆諸歷史,“吾國古無所謂政黨也,披覽史乘,只有朋黨之可稽”②。那么,政黨是緣何出現在中國的?其歷史使命又是什么?這是厘清當代中國政黨政治內在邏輯必先回答的重要問題。
1.中國政黨的興起緣由作為歷史悠久的東方國家,中國數千年史乘只有“朋黨”可稽查而未見“政黨”之影跡。雖然兩者在詞形上僅一字之差,但“朋黨”在中國卻長期飽蘸貶義色彩。“黨,不鮮也,從尚從黑。”③《說文解字》對“黨”(黨)字本義的前述解說,較好地道出傳統中國對朋黨的拒斥態度,以至于人們通常因此忽略了“黨”作為量詞使用時的另一層含義,如“五族為黨”④。進一步說,傳統中國對“黨”的這種拒斥態度又與孔子“吾聞君子不黨”“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⑤的儒家教化密切有關,因此長期把“結黨營私”視為一撮小人牟取私利的無恥之舉。在傳統政治領域,“朋黨”更是朝野群臣忌諱之辭,但歸根到底,在于帝王政治強烈的排他性和封閉性,因而不擇手段地厲行“黨禁”以保王權長治久安。由于鴉片戰爭爆發以及隨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近代中國由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之故,“救亡圖存”匯集成為時代最強音并掀起了洋務運動、和立憲運動等。在此過程中,一些有識之士不僅熱衷學習“洋技”,還傾心西洋“政制”,如清朝首任駐英大使郭嵩燾就較早留意到西方國家“設朝黨野黨,使各以所見相持爭勝”⑥的政治現象,其后出使西洋四國的洋務派代表薛福成對“英國上下議院,有公保兩黨,迭為進退,互相維制”⑦的政治機理作過細致考察。“天下者,黨派之天下也;國家者,黨派之國家也。”⑧鑒于諸如洋務運動、和立憲運動的改良主義皆無法“扶大廈之將傾”,1905年,孫中山聯合黃興等人在日本東京創建了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政治綱領,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政黨由此正式誕生。從歷史背景看,無論是中國同盟會還是后來的中國共產黨,它們皆是興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為正是由于近代中國主權淪喪、國土破碎、經濟凋敝和民不聊生,甚至淪為眾多侵略者互相爭利的硝煙戰場,而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卻甘當政治附庸,乃至聯合帝國主義竭力維持其統治,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批先進之士希冀效仿異域做法成立政黨以拯救危局。從全球視域看,中國政黨是伴隨著新生的強勢的西方工業文明對東方中國傳統的衰落的農耕文明進行野蠻入侵和殘酷解構之過程出現的。19世紀以來,以英美兩國為樣本的政黨政治思想伴隨著西方國家海外殖民地的開拓播向東方,經由日本傳入“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仁人志士之視野,這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同盟會和其他早期政黨的誕生,其后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在新文化運動猛烈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潮影響下創建的。
2.中國政黨的歷史使命如前所述,中國政黨興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此一來,中國政黨從誕生那一刻起,就與生俱來肩負著如下特殊的歷史使命。一是整合社會。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社會秩序是由“君權神授”的邏輯而構建的,其權威象征是作為“真龍天子”的皇帝。鴉片戰爭以來,由于清政府在御敵過程中節節敗退,皇權威望逐步衰微。加之,當局為巨額的戰爭賠款持續搜刮民眾,失控的政治腐敗不斷加劇社會矛盾,還爆發了歷時十余年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內憂外患之下,中國社會的“向心力”開始渙散,孫中山、都曾經將此期中國社會稱為“一盤散沙”。也正因如此,對中國政黨而言,其必須肩負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先設法整合形如“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進而重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否則難以獲取中國社會大眾的支持,甚至政黨本身也會因此而走向衰亡。二是創建國家。“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謀幸福,人民謀樂利”⑨,孫中山對政黨要義的認知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中國政黨所肩負的“建國”使命,這是國強民富的基本前提。因為時至近代,中國政治運轉的合法性基礎在較長時間內仍是“奉天承運”,傳統的“君—臣”綱常倫理仍是整個社會的固有遵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⑩,土地和臣民皆仍依附于帝王一身,缺乏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意識和社會公民權利。但從全球角度看,19世紀以來,構建現代主權國家、賦予社會公民權利已是人類政治發展的大趨勢,簡言之,即國有“國權”、民有“民權”,而清政府在內憂外患之下卻甘當殖民者的政治附庸工具,乃至“借師洋人”共同鎮壓中國人民,如何由帝王政治轉型邁向政黨政治成為近代中國的時代訴求,而這種訴求客觀上要求政黨必須在整合社會的基礎上構建起一個主權獨立的現代國家。正因如此,孫中山創建中國同盟會時就以“創立民國”作為其政治綱領,且強調這是順應“浩浩蕩蕩”歷史潮流的必然選擇,而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也同樣主張要創建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三是振興民族。中國歷時悠久的華夏民族觀念與近代西方興起的民族主義內生契合。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西方掀起了民族主義運動,“民族”超越了傳統的鄉土、地域和宗教藩籬,引發了西方社會深刻的政治變革,對近代中國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倘若說,近代中國把西方殖民統治視為“外族入侵”、洋務派把“師夷長技以制夷”作為變革中國之道、康有為和梁啟超創建的強學會以“保種”為宗旨只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萌芽,那么到了20世紀,在內憂外患的不斷累積之下,以“振興中華(民族)”為口號的中國民族主義則已澎湃。因此,孫中山和黃興等人把“民族主義”作為中國同盟會的核心綱領,且其后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再經改組的“中國國民黨”,都自覺繼承了中國同盟會“振興中華”的政治理念。即便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它在革命時期也頻繁提到“振興中華”或“民族復興”,這在的著作當中并不鮮見。從世界范圍看,19世紀以來,遭受西方殖民的國家或地區所誕生的大部分是民族主義政黨,與此相應,喚醒民族意識、爭取民族獨立和實現民族復興,則是這類政黨的一項重要使命。這種情形與近代中國政黨的興起極為相似,即便是時至今天,中國共產黨仍然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由上可見,盡管中國的政黨思想由西方傳入,但無論是其興起的社會環境還是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皆與西方政黨有著顯著區別。因為在西方,政黨主要興起于主權獨立國家之議會,其主要功能是政治選舉,策略選擇自然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而在“人人平等”“天賦人權”的時念下,政黨通常只是“嵌入”社會大規模開展的競選動員,說服民眾給本黨投票從而獲得執政的政治合法性,再以此實現本黨所代表階層的根本利益。瑏瑡而在中國,政黨興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的政黨的主要功能是整合社會、創建國家和振興民族,其任務相應主要是“反帝反封建”以重新構建近代中國的社會秩序,這進而決定了其策略選擇也必然是“革命”而不是“改良”。上述這些特殊情況決定了中國政黨政治的道路選擇,只是囿于時代所限,早期的政黨精英們對這一特殊情形的認知并不深刻,因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造成了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曲折迂回。
二、中國政黨政治的歷史演進及其特征
近代中國在政黨的推動下由帝王政治轉型邁向政黨政治,并在政黨政治道路上先后探索施行多黨競爭制、一黨壟斷制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至今已有共百余年歷史。整體上看,這三種不同類型政黨制度的基本特征分別是權力競爭、權力獨裁和協商合作,在20世紀上半葉實現了歷史更替。
1.民國初年的多黨競爭制20世紀初期,孫中山和黃興等人領導“革命黨人”發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統治,創建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政黨國家即中華民國。為防止中國再次出現君主獨裁,南京臨時政府除了通過約法賦予“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瑏瑢,還推出“內閣制”,規定內閣由議會中占多數議席的政黨組成,對議會負責且受議會監督。受此推動,民國初年的中華大地“集會結社,猶如瘋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為數幾至近百”瑏瑣,中國由此邁入“政黨林立的時代”或“多黨競爭制時代”瑏瑤。整體上,民國初年的政黨主要是圍繞議會席位競選而開展活動的,此期政黨政治的基本特征是權力競爭。為此,各政黨除了積極奔走游說社會名流加入本黨,還盛行以“改組”的方式迅速壯大力量,如共和黨、和統一黨聯合改組成進步黨,中國同盟會聯合數個小型政黨改組成國民黨,而宋教仁則干脆直接要求國民黨人“停止一切運動,專注于選舉運動”瑏瑥。然而,這種政黨政治實踐卻誘發了系列政治亂象。首先是盛行“跨黨”黨員,即一個人可以加入多個政黨,如黎元洪、陸建章跨黨9個,熊希齡、趙秉鈞跨黨8個,張騫、唐紹儀、于右任跨黨7個,瑏瑦甚至“跨盡各黨者,亦有其人”瑏瑧。民國風云人物趙秉鈞曾經感慨:“我本不曉得什么叫做黨的,不過有許多人勸我進黨,共和黨也送什么證來,同盟會也送得來。我也有拆開來看的,也有撂開不理的,我何曾曉得什么黨來。”瑏瑨政黨此時已蛻變為少數精英撈取政治資本的工具。其次是盛行金錢交易。民國初年政黨的“黨綱”大都無明顯區別,甚至有些政黨并無“黨綱”,議會競選在很大程度上變相淪為了金錢交易,如有政黨明碼標價,以每張選票5000元到1.2萬元的賄金選舉湯化龍當選為眾議院議長,以酒宴款待、轎船迎送、贈送金徽章、燕尾服和鴉片等方式進行賄選的現象更是普遍。瑏瑩更有甚者是不擇手段侮辱、恐嚇乃至暗殺競爭對手,國民黨總干事宋教仁南下選舉途中被刺身亡便是例證。民國初年這種以權力競爭為基本特征的多黨政治所引發的政治亂象,使得原本積極提倡多黨競爭的孫中山睹之都不由感慨“中國人多不明白黨字之真義”,甚至根本“不知黨與黨之關系,非仇讎,是對黨”。瑐瑠這種政治紛爭不僅招來社會輿論“黨爭亡國”的指責,也為袁世凱復辟帝制提供了極大的回旋空間,致使近代中國由政黨政治滑向軍閥政治,而后者是史學界公認的黑暗混亂時期之一。
2.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一黨壟斷制一黨壟斷制乃近代中國為矯正多黨競爭之弊所作的一種選擇,其歷史起點是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憑借北伐革命勝利之威,中國國民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南京國民政府在創建之初就申言“黨外無政,政外無黨”,強調中國在“訓政時期”只能夠存在“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瑐瑡為此還不遺余力地軍事“圍剿”曾經的政治盟友中國共產黨,即便在民族危機空前加劇的抗戰關頭,仍按照既定的“反共”方針策劃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然而,南京國民政府這種“矯正”之策此時卻是一股時代逆流。這就是說,以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政治浪潮洶涌澎湃,而“精誠團結”實乃“救亡圖存”時代的所趨大勢,這必然要求中國各政治力量緊密團結一致共同抵御外敵,但起初南京國民政府卻態度漠然。進一步說,早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前,中國為了“救亡圖存”早已成立了多個政黨,如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等,它們代表著中國不同社會階層的時代訴求。“九一八事變”以來,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其后中國又產生了諸如民盟、民建等以“抗日救國”為任的政治力量。作為中國對外合法的主權代表,此時南京國民政府對內卻選擇一黨壟斷制,在抗日戰爭的民族危難關頭仍不忘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毋庸贅言,這種選擇與“救亡圖存”的時代大潮顯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這種政黨政治道路選擇不僅在中國國民黨內部遭受質疑,還受到其外部政治力量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強烈抵制。囿于時代的特殊性,這種強烈抵制又是以“革命”與“反革命”的名義進行,其因正如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所指出的是“背叛孫中山,拿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專政作為壓迫中國平民的工具”,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反革命的專政”,因此他將之視為是一場關乎“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的較量。瑐瑢因為在看來,以1919年的“”為分水嶺,中國革命已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領導力量是中國的無產階級而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前途是建立“聯合政府”而不是“一黨訓政”。因此,早在抗戰時期,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就曾經多次“要求國民黨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是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瑐瑣。抗戰勝利之后,雖然中國各政黨(主要是國共兩黨)就和平建國事宜進行談判,并依據“雙十協定”精神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但由于中共和民盟關于“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未能獲得國民黨“一黨訓政”獨裁政策的兼容瑐瑤,第二次國共內戰最終爆發。1949年4月,伴隨著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南京,中國一黨壟斷制壽終正寢。
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之形成與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是近代中國對“一黨主義”黯淡前途進行反思的歷史產物,實踐雛形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推行的“三三制”瑐瑥政權,正式形成標志是1949年“新政協”召開。抗戰時期,鑒于中國革命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鞏固和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據地貫徹執行“三三制”政權,探索與其他政黨展開政治合作。瑐瑦對此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既不贊成別的黨派的,也不主張共產黨的,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瑐瑧。伴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五一號召,倡議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國是。對此,各派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瑐瑨。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順利召開,臨時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表決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選舉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等機構。以“新政協”的召開為標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正式形成。根據這一新型政黨制度安排,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其他派是參政黨,參政黨的基本職能是“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瑐瑩。由于這種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政黨進行“聯合革命”和“協商建國”的歷史總結,因而也成為了和平時期中國政黨進行“合作治國”的基本政治保障,至少有著如下特點。其一,基本特征是“協商合作”。就是說,它既不同于中國歷史上的多黨競爭制和一黨壟斷制(上文已述及),亦不同于蘇俄的一黨政治。盡管中共長期注重“以俄為師”,但早在革命時期就明確表示中國“不學俄國的一黨制度”,強調“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于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瑑瑠其二,價值導向是以“人民”為中心。這種價值導向在根本上取決于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身深蘊的“人民性”,即堅信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實現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其“人民性”不僅體現于始終信仰人民,密切依靠人民,堅持走“群眾路線”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還蘊含在由其領導探索的新型政黨制度之中,它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其他政黨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正如在革命時期所指出的,“不論什么政黨或社會集團,也不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在“有關中國的問題上”必須“尊重”中國共產黨,“誰要是不尊重中國共產黨,誰就是在實際上不尊重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誰就一定要失敗”,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意見,符合于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
縱而觀之,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價值導向的協商合作型政黨政治,因而不僅成功克服了中國過去兩類政黨政治存在的脫離人民群眾之弊,還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社會的“黨爭亡國”之虞,攜手與其他政黨進行“聯合革命”和“協商建國”,合力推動中國歷史前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在“合作治國”的實踐當中獲得了新發展。明確指出,派在革命時期的作用“不是一根頭發的功勞”,而是“一把頭發”,從長遠和整體看只能重視“不可藐視”。瑑瑢他不僅反對一些政黨自行解散,還在中共八大前后探索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合作方針,強調既要“共產黨萬歲”,也要“派萬歲”。瑑瑣因為在他看來,“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瑑瑤,派的存在對共產黨大有裨益。這些創造性探索尤其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合作方針的確立,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國政黨制度發展完善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實現了新的發展。中共中央除了確立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合作方針,還把這一政黨制度載入國家憲法。這是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進程當中取得的一個標志性成果。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至今至少取得了如下兩方面創新發展:一是理論層面,作出新的重要論述,為新時代我國政黨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新指南。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體現,強調“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勢和特點充分發揮出來,為人類政治文明進步作出充滿中國智慧的貢獻”瑑瑥,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首次從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的戰略高度提出推動我國政黨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二是實踐層面著力推進政黨協商。中共十八大以來,提出必須統籌推進政黨協商,強調“政黨協商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并領導制定中共歷史上首個《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不僅確定了“政黨協商的科學定位、內容和形式、主體和責任、特征和主題”,而且采取系列措施實現了政黨協商的“科學化、制度化、程序化”。瑑瑦諸如此類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有效地推動了我國政黨政治的向前發展。
三、中國政黨政治百年實踐的當代啟示
以1905年中國同盟會的創建為開端,政黨在中國已經存在一百多年,縱覽中國政黨政治百余年的歷史與實踐,可為當代中國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第一,政黨建設是一項關乎中國發展進步的時代課題。近現代中國發生了三大標志性歷史事件:一是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成立,中國由此告別了數千年的帝王政治,轉而邁向政黨政治的新征程;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讓近代中國徹底改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為當代中國的一切進步發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三是中國改革開放,這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瑑瑧。這三大歷史性事件都是由政黨領導進行的,在此意義上,近現代中國歷史也是一部政黨史,政黨當之無愧是推動近現代中國進步最重要的政治工具。然而,政黨畢竟是一個“舶來品”,中國社會起初對政黨的認知水平整體上是相對偏低的,主要體現為早期的政黨領袖們尚未能夠重視政黨自身建設以及沒有深刻意識到這項工作對中國發展進步的極端重要性。中國最早的政黨中國同盟會長期存在組織松散、紀律松弛和派系林立等問題,辛亥革命勝利以后,國內政治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但政黨理論卻未能及時得以更新,因而部分黨員誤以為民國創建意味著革命已經成功,開始坐享革命果實,甚至有的黨員主張解散政黨,理由是清朝已被推翻、民國已經建立,黨的目標已經實現,中國同盟會再也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這在極大程度上導致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最終被封建軍閥勢力篡奪,乃至極大地滯緩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即便是中國共產黨,它在幼稚時期也是不擅長政黨建設問題的。在遵義會議以前,王明和博古等人熱衷推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黨內斗爭路線,致使全黨執行了錯誤的政治路線,讓共產黨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遭受慘敗從而不得不開啟行程兩萬多里的戰略性轉移。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確立了以為核心的領導集體,“黨的建設”才被視為一項“偉大工程”加以重視。除了“特別著重從思想上建黨”,在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還尤其注重黨的組織、紀律和作風建設。這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之蓬勃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力量支撐。也正因如此,“黨的建設”被認為是中共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其余是“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即便是在革命勝利以后也常抓不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短短幾十年時間里取得了舉世矚目成就的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鑄造中國共產黨這個堅強“領導核心”的奧秘之一,就在于它在改革開放新時期能夠繼續把黨的建設視為一項“新的偉大工程”加以推進,且能夠在原先的思想、組織和作風建設之基礎上,審時度勢加以創新發展,如提出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反腐倡廉建設”“政治建設”,并把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和“提升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當作一項重要的建設任務。“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于黨”。面向未來,政黨建設仍然是一項關乎中國發展進步的時代課題,因此必須繼續深入推動政黨建設特別是加強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以政黨建設推動中國進步既是歷史教訓也是實踐啟發,應當成為中國未來發展進步的應有參照。
第二,政黨政治并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實踐模式。外界通常是以“西方中心論”而不是從中國歷史與實踐的角度審視中國的政黨政治,這種要求中國必須以英美國家政黨政治模式作為“標準答案”的做法乃一種文明傲慢,不僅在邏輯上講不通,而且有悖于中國的歷史事實。從邏輯上講,任何事物的發生必定有與之相適應的環境,即便是同一事物,在不同環境當中也相應有不同的變化,而不是必然的千篇一律。政黨雖然最早興起于西方,但其功效在傳入中國之初就已經發生了轉向,即中國政黨最初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不是類似西方那樣源于議會,且遭受著本國封建統治和外來殖民的雙重壓迫,這進而決定了中國政黨只能選擇以“革命”作為旗幟來整合社會和創建國家,而無法像西方政黨那樣能夠在主權國家范圍內以“改良”的方式和平開展政治競選。不僅如此,中國政黨還必須植根于中華優秀的文化傳統,通過汲取本土的“中華民族”觀念作為其政治動員口號和奮斗目標,以此源源不斷獲取社會支持并驅動中國向前發展。歷史經驗證明,當代中國政黨制度是適合中國國情的、行之有效的政黨制度選擇。在此意義上,政黨政治并不存在定于一尊、一成不變的實踐模式。換言之,如今評判中國政黨制度應當結合特定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而不是抽象地以西方標準作為必然的“參考答案”。進一步說,當代中國政黨制度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一種政治創造,為當今世界政黨政治發展提供了一番新的實踐圖景,是一項值得稱贊的“中國方案”。
第三,中國共產黨無愧是推動中國政黨政治不斷變革、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的核心領導力量。歷史證明,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發起的“社會性質問題”的大論戰,中國社會才逐步認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瑑瑨。“我們懂得了中國社會還有半殖民地的性質,那末就要反帝”,“革命的任務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瑑瑩這是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進行“聯合革命”和“協商建國”的思想前提,而由此開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則是中國政黨政治發生根本性變革的實踐基礎。若非如此,中國政黨就無法徹底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也正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政黨政治才形成了“新型政黨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種新型制度在“合作治國”的新環境下不斷實現創新發展,最大限度調動起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國家,讓積貧積弱的中國能夠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為目前全球擁有重要影響力的世界大國。上述歷史與實踐啟發我們,中國共產黨當之無愧是推動中國政黨政治不斷變革、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的關鍵力量。因此,要推動中國政黨政治不斷變革、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就必須繼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源自歷史、實踐和理論的共同“答案”。
作者:廖皇珠;石德金
- 上一篇:黨內政治生活思想的三重維度范文
- 下一篇:政治儀式與紅船精神的孕育及傳播范文
擴展閱讀
- 1生態政治與政治生態化
- 2政治處思想政治總結
- 3時事政治在初中政治中的應用
- 4時事政治融入政治課堂
- 5思想政治
- 6思想政治途徑
- 7思想政治
- 8醫院思想政治
- 9生態政治生態化
- 10思想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