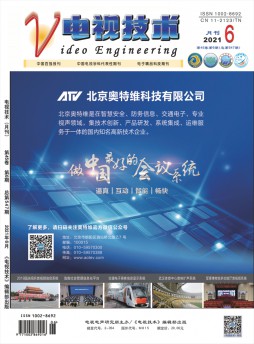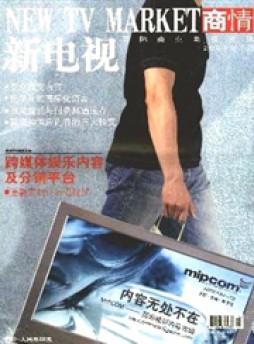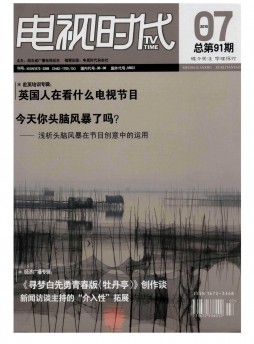電視紀錄片中主持人的作用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電視紀錄片中主持人的作用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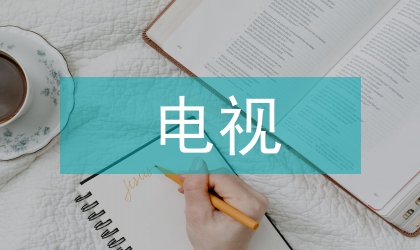
《世紀橋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紀錄片中主持人的優勢作用
采用主持人介入紀錄片的敘事在心理學上也有跡可循,“紀錄片創新出許多新的元素,‘主持人效果’就是這些元素中最有分量的一種”。[5]紀錄片是一種對認知過程的體驗,當我們在認識一件事情的時候,如果和所認知的事物過近就很容易厘不清自己和對方之間的關系,恰如意大利新聞工作者卡爾維諾所說,“要把地面上的人看清楚,就要和地面保持距離”。[6]如果說第三人稱不容易建立觀眾的信任感,那么第一人稱則過于容易博取觀眾的信任,從而產生博取同情之嫌。主持人面對鏡頭以第二人稱直呼觀眾,不缺乏第一人稱的親和力,也不缺乏第三人稱的流暢清晰,同時還能用可視的現象來進行闡述。比如《焦點訪談》的《收購季節訪棉區》一期中,主持人在觀察過程中握住一只茶杯并迅速撒手然后說“還很熱”,并接著下判斷“他們應該剛走不久”,要比空鏡帶到茶杯再到走廊,或者解說直接敘述“相關人員剛剛得知消息并迅速撤離”要真實可信得多。其實電視紀錄片受到主持人化的影響已經比較深入,觀眾在收看的時候往往抱著一種好奇的求知的心理,這時一個主持人是很容易做到使紀錄片易于接受,輕松氛圍,又便于理解的。
二、主持人和紀錄片的配合
在中國高校教育的培養下,播音主持專業畢業的學生自身觀念中有許多扔不掉的包袱,比如字正腔圓,責任,道德等等,這導致紀錄片采用主持人的效果并沒有預期當中那么好。杜憲曾經在《試論電視紀錄片主持人的基本能力——兼憶鳳凰衛視三部電視紀錄片的拍攝》當中說,“在主持這個節目之前,我平時說話和播報新聞配音解說時的用聲是不一樣的……因為在采訪現場為了拉近和被采訪者的心理距離,最好用通俗的口語與各種人交流……這時候已經無暇顧及聲音問題了”。[7]講究用聲方法是我國主持人最大的特點,但是心里面總要惦記吐字歸音,在交流過程中就必然要分神,而對老百姓,一口流利的播音腔恐怕也并未必利于心里好感的建設。主持人最應該是自然的,就如竇文濤所說,“上升到社會責任和道德良心都非常可怕,其實腦子里應該忘掉這些詞,越想這些詞就越不真實了。還是最本能的良知吧,用第一個念頭。第一個念頭就是人人內心的良知喚起的,這樣的東西最好,最真,最寶貴。”[8]除了主持人口語,成片配音也呈現出和主持人的交流語言同樣的效果。我們期待著作品能夠創新,采訪能夠深入,但脫離了全片整體的解說有時卻影響著影片的獨立性。使用同一播音藝術家的播配,配音者的特點,往往容易使得解說詞語產生同一化的弊端。比如由于《動物世界》欄目的深入人心,趙忠祥老師播配任何片子都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非洲的大草原”——在這一點上,鳳凰衛視就很有前瞻性,“鳳凰衛視歷史題材紀錄片的解說詞對配音的要求是要“業余”……絕對不能字正腔圓,語氣決不能慷慨激昂,不能義憤填膺。”
[8]如果你去認真看《鳳凰大視野》,你會發現自己沉浸在那些戰爭風云的故事當中,完全忽視掉很多影片配音的普通話基本和主持人口播要求相去甚遠的。這些沙啞的男低音,有的出自錄音專業學生,有的可能是導演專業畢業生,但他們的聲音并沒有顯得和影片格格不入,反而因為配音者本人參與了大量影片制作而更具融合性。我國電視上的主持人不僅要求聲音無懈可擊,更將形象標準提高到和演員一樣,其選拔標準可以從每年播音主持專業藝考大軍中略知一二。但一味追求主持人或出鏡記者的長相也難免會讓觀眾產生抗拒的心理。觀眾希望在電視上看到的形象是和自己平行的,這也不難理解為什么海清會在眾多天仙女演員中脫穎而出倍受觀眾喜愛。
長期出現在電視熒屏上的主持人會逐漸積累固定的觀眾群,成為明星主持人。明星主持人現象還表現為柴靜在《新聞調查》中采訪時真情流露蹲下來給孩子擦眼淚被很多人吐槽為作秀,而臺風“海燕”來臨,央視一名男記者在安慰一個失去親人的當地居民時親切的撫摸對方的頭發卻并沒有引起多大關注。有些紀錄片為了收視和噱頭干脆用明星來當主持人,2013年韓庚出任紀錄片《人口販運(中國)》主持人,2012年藤原紀香出任日本朝日電視臺紀錄片《西安紀行》主持人……電視越來越像“居高臨下的教育、宣傳工具”,觀眾和電視里面的人之間有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離當初陳虻先生對《東方時空》的定位“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已經越走越遠了。和電視播出的其他節目不一樣,紀錄片的觀眾需要的是向他講述新聞事件的人,并不是在看演員的表演。在紀錄片中過度消費明星效應,觀眾會將注意力從紀錄片的主題偏離到對明星個人的關注,這和紀錄片拍攝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在BBC的系列紀錄片中有很多倍受觀眾熟知的主持人,比如主持紀錄片《宗教音樂》的演員SimonRussellBeale,專注于探索宇宙和生命奇跡的物理學家兼搖滾青年BrianCox,熱衷于研究各國藝術史的藝術評論家AndrewGraham-Dixon,還有作家RichardMiles……他們都因為在各自領域上的成就被導演請來坐鎮某一部或某一系列影片,離開主持人這個身份,他們各自都有一條成熟的認知坐標系。觀眾“在接受信號時,常常會收到潛在的、隱形的文化代碼的影響,因此……要把更多地關注投入他的文化層面。而把握這個文化層面的關鍵之一,應是電視紀錄片的主持人所具有的文化層次以及他所表現出的文化底蘊”。
這些主持人他們沒有年輕的面孔,卻有著雄厚的專業背景,對觀眾來說也就意味著強烈的信任感——這幾乎是國外主持人公認的選擇標準,新聞節目主持人也是要做幾十年普通記者才有資格去坐演播室,之前那些后天的努力是他們讓人產生好感的重要原因,這和看病投醫我們喜歡掛專家號是一樣的道理,主持人閱歷的資深,對觀眾來說具有天然的信服感。中國電視觀眾的流失與這點原因也不無關系,中國的主持人因為沒有專業,所以和他們播出的稿件之間有著看不見的陌生感,對觀眾來說,他們的聲音也就如過眼云煙,稍縱就逝了吧。在中國的紀錄片創作環境下,雖然由于環境限制,使主持人難以在紀錄片中發揮作用。但除外在原因之外,我國電視主持人自身現狀也存在著很多與紀錄片表現之間的矛盾。如果我們能夠打破固有思維,跳出對已有的主持人的思維定式,抱著尋找一個好的講述者和引導者的態度去操作,對紀錄片的創新和發展會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
作者:崔新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
- 上一篇:大學校園體育文化的展望范文
- 下一篇:社會主義農村文化建設的可行之路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