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的美學與政治學論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街道的美學與政治學論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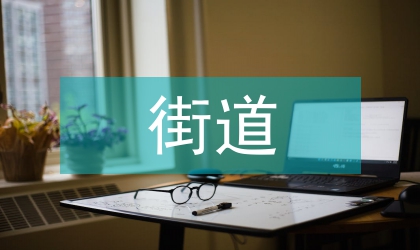
在德•塞托那里,街道、城市與日常生活極為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而對于資本主義城市而言,正是這種日常生活本身恰如其分地展示了城市消費主義和商品的歷史。“一部街道的發生史也是一部商品的變遷史,商品的展示史。街道的歷史是被商品逐漸包裹和粉飾的歷史。”就此而言,街道既是人群集合的場所,也是商品、物的集合場所。在這個意義上,街道成為了“人與物之間的中介,……在街道上,主體和客體,觀看櫥窗者和娼妓、精神空虛者和匆匆過路人、夢想與需求、自我克制與自我標榜在不斷交替”。遍布街道的人群,以艷羨的目光打量著城市櫥窗中琳瑯滿目的充滿魅惑氣息的商品。法國自然主義小說家左拉在《婦女樂園》中曾對巴黎街道上百貨公司的櫥窗有過細致的描寫,其作品堪稱資本主義物欲時代的生動寫照。其間,“街道”的風景所蘊含的物質主義震撼令人心醉。而在本雅明筆下,巴黎的浪蕩子和“拾荒者”所游走的“街道”本身,更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抒情的詩意所在。由此可見,街道的面孔其實蘊含著資本主義的秘密:商品展示和物質主義的欲望。在此消費社會的文化格局中,“街道”本身無疑蘊含著商品的美感、詩意的格調,又裹挾著幾分資本主義的罪惡。然而,對于1950至1970年代的中國文學而言,它究竟如何與社會主義政權及其文化格局相適應,這成為了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
一、《霓虹燈下的哨兵》與“城市行走”
創作于1960年代的話劇作品《霓虹燈下的哨兵》,亦是一幕講述“街道行走”的城市故事,只不過從中體味的是解放后社會主義的文化矛盾和危機。作為一部反映“南京路上的好八連”的作品,《霓虹燈下的哨兵》描寫了城市的進入者在城市所面對的吸引與誘惑,并著力呈現了新城市的主人———解放軍,在面對昔日資本主義的繁華所在———南京路時,所展開的意識形態爭斗與搖擺的過程。正如彼時其他城市題材作品一樣,《霓虹燈》中的城市生活也以妖魔化的身份,在批判性話語之中展現出來。如作品中所言,剛進上海的城市接管者就被警告:“我們解放軍除西藏之外,全國都到過,可是說不定到上海就被人打倒在地上。……在上海你隨便進入人家,就可能會被人弄死。所以,我們進城后越小心越好。……在城市我們可能要上當,要謹慎才好。”正是面對城市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警惕和焦慮,使得八連戰士們在南京路上的“行走”具有了非凡的象征意義。在這部話劇(而后改編成電影)之中,解放初期作為舊上海城市消費主義象征的南京路,明顯體現出“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對抗”。這種“對抗”并非以“暴力”、“沖突”等方式進行,而是以潛移默化的形式滲透。劇中,魯大成、路華與陳喜有這樣一段對話:魯大成:你這兒有什么情況?陳喜:情況?沒啥,一切都很正常。魯大成:照你看,南京路太平無事嘍?陳喜:就是,連風都有點香。魯大成:(驚訝)什么,什么?你說什么?陳喜:(嘟噥)風就是有點香味!(走去。)魯大成:你!你……路華:(自語)連風都有點香……魯大成:不像話!路華:是啊!南京路上老開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惱的倒是這股熏人的香風!魯大成:這種思想要不整一整,南京路這地方———不能待!“爵士樂聲蕩漾,霓虹燈耀眼欲花”,這便是南京路及其資產階級“香風”的意義所在。在此,“香風”作為紙醉金迷的資產階級生活的表征,它與其它資產階級文化形式一樣,讓人無法防備。事實也證明,行走在南京路上的解放軍果然陷入了資產階級“香風”和“毒霧”的糾纏。在反動派“紅的進來,不出三個月趴在南京路上完蛋”的叫囂中,排長陳喜開始迷戀城市的“物質主義”。他開始鐘情“花襪子”,而嫌棄“老布襪子”,并忘卻象征著“部隊的老傳統”,“解放區人民的心意”的“針線包”。城市的“香風毒霧”讓他“思想深處發霉”,“出現腐爛的斑點”。他鼓勵童阿男和林媛媛的約會,認為“你是個解放軍,大方些,別叫上海人笑話!”另外,對趙大大的“黑臉”也極盡揶揄之辭,“黑不溜球的,靠邊站站吧!”這都體現出對無產階級“土”的厭惡和自卑。在他眼中,上海繁華的城市空間,使得鮮明的無產階級特征恰恰成為城市的嘲諷對象。在此至關重要的是,妻子春妮兒連同她那“破舊”的“支前扁擔”、“紅布包袱”,都激起了陳喜“致命”的自卑感。因此,盡管文本之中“老布襪子”的象征意義在于,“結實、耐穿,穿著它,腳底板硬,站得穩,過去穿著它能推翻三座大山,今天穿著它照樣能改造南京路!”但陳喜對春妮兒的“無意識”的“摒棄”,連同上海這一花花世界的背景,便具有了意味深長的內涵。故事最后,盡管排長陳喜最后在指導員的教育下幡然悔悟,從而突顯出“拒腐蝕”的時代主題與國家意識形態話語,但他對“春妮兒”的堅守,毋寧說只是對解放區人民的道德承諾,而社會主義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賴這種“超我”結構維系著的。
導演黃佐臨在談到電影主題時曾這樣說道,“經過十多次瞄準和射擊”,最后選定了“沖鋒壓倒香風”作為全劇的主題思想:“我們感到象‘保衛大上海’、‘保衛游園會’、‘站馬路’、‘爭奪上海陣地’等等,都太小,太實,太具體,太片面,但是這是很必然的過程,因為我們初讀劇本,必定經過一個感性的認識階段,只看到劇本中的情節、事件。”因此,作品本身也極為貼切地契合了抵御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拒絕腐蝕,防止和平演變的時代主題。為了成功表達革命的意識形態主題,《霓虹燈下的哨兵》竭力營造了舊上海的消費城市景觀,“全劇用一個襯景,全部是高樓大廈,好像在外灘,又像在日升樓一帶。”電影版《霓虹燈下的哨兵》對城市場景有豐富的表現。影片在實地拍攝過程中刻意地復原了1949年南京路上的街景,“行人的穿著是西裝、旗袍,報童叫賣的是美國Life畫報,連長背后的櫥窗里擺著‘MaxFactor’(蜜斯佛陀)的化妝品,劇院放映的是好萊塢電影,軍營窗外是嘁喳作響的爵士樂,臨街房間里飄出來的是憂郁的鋼琴奏鳴曲,頭頂的霓虹燈是‘派克’金筆廣告,小商店擺著花花綠綠的糖果,就連街頭的公共汽車上也畫著‘無敵牙膏’和‘美麗牌’香煙的招貼,閃爍的霓虹燈在電影中更是被反復給以特寫的處理。”這些消費符號和電影場景中出現的《出水芙蓉》廣告、爵士樂一起,共同構成了舊上海的資產階級色彩。而且就電影和話劇而言,街道中所呈現的城市物質生產和消費的高度發達,也直觀地象征著資本主義腐朽的生活方式。在此,作品中“革命劇《白毛女》”與“好萊塢電影《出水芙蓉》”之間的爭斗,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面對資產階級消費城市的誘惑,處于文化匱乏狀態的無產階級終究難以抵擋。這種致命的吸引構成了“革命之后”社會主義城市的焦慮所在。這也從另一方面體現出“進城”的無產階級政權,不斷面臨一種文化抗爭的命運。然而“游園會”與爵士樂,《白毛女》與《出水芙蓉》之間的爭斗,背后蘊含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文化領導權的宏大主題。面對敵特分子的叫囂,“叫他趴在南京路上,發霉、變黑、爛掉!”無產階級戰士必須“站馬路,站崗放哨,守衛大上海”。在此之中,除了自覺抵制資產階級的誘惑之外,還必須創造出自己的文化空間和產品。在這個意義上,燈紅酒綠的南京路便成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的前線,而這場戰爭的殘酷性較之剛剛過去的那場戰爭更為嚴峻。就這樣,“街道的行走”連同街道的美學與政治學一道具有了生死攸關的意義。在此,南京路這個頗具舊上海消費社會特色的資產階級美學空間,成為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爭奪的對象。在此爭奪之中,城市街道便頗有幾分列斐伏爾有關“空間的生產”的意義。“空間在其本身也許是原始賜予的,但空間的組織和意義卻是社會變化、社會轉型和社會經驗的產物。”
在列斐伏爾看來,空間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同時也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再生產;圍繞空間進行的政治斗爭是社會問題的核心。對于新興的無產階級來說,要打破既有的資產階級消費主義對城市空間的壟斷,不僅要拒斥舊的空間生產方式對人的控制,更要創造出新的屬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反映到《霓虹燈下的哨兵》中,不僅要突出“拒腐蝕”,抵制資產階級“香風”的思想主題,還要創造出諸如“群眾秧歌”和“游園會”等街道文化活動,來對抗好萊塢電影和爵士樂。于是,在歌劇《白毛女》對抗美國電影《出水芙蓉》的背后,街道的美學和政治學意味被突出地表現了出來。同樣是面對街道櫥窗,在電影的開始,排長陳喜為陳列于其中的一雙“花襪子”所誘惑,然而通過教育,他又重拾了革命警惕性,繃緊了階級斗爭的神經。而同樣是街道的霓虹燈,當群眾歡送志愿軍出發時,它適時地閃爍出“萬歲”的政治標語,證明這個曾經被認為是“墮落象征”的物質現代性標志,完全服務于新的革命現代性的精神需要了。盡管在這種“虛張的正義”背后,有關“洗腦筋”和政治宣傳的指責不絕于耳,但它畢竟是無產階級對城市文化領導權艱難爭奪的開始。
作者:王亞平徐剛單位:湖北科技學院教育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科研處
- 上一篇:民事權益刑法發展的背景概述范文
- 下一篇:內科護理存在的問題分析及策略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