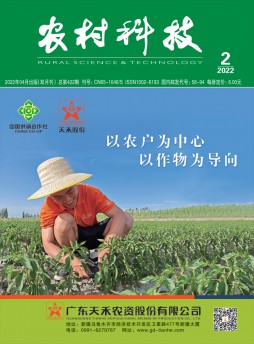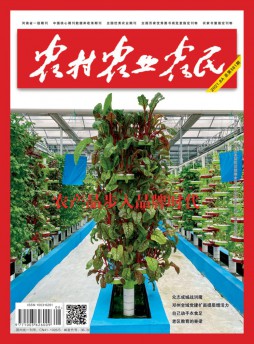農村征地領域職務法律適用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農村征地領域職務法律適用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與土地征用補償款相關的爭議
村級組織的資金主要有自有資金(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財產)和有關部門撥入的專項資金及社會捐助。為了避免打擊面過大,《解釋》將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對象限定在協助政府從事征地拆遷等七項事務管理中的資金,排除了原本屬于貪污賄賂犯罪對象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等,而實踐中難以區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用產和協助七種公務中的財產,導致司法實踐中爭議頗多。(1)土地補償款性質認定爭議。有觀點(階段說)認為,以政府向村委會和村民發放或分配土地征用補償費作為分界點,之前“村干部”的管理活動屬于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行政管理活動,“土地征用補償費用”被依法發放或分配入村財務賬后,即成為村集體財產(但依法應發放的安置補償費以發放到農民手中為分界點)。有觀點認為,只要村干部占用、侵吞、挪用的錢款涉及到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和使用,就符合《解釋》的規定。還有觀點認為,凡國家劃撥的有關土地征用的補償費不分階段、不分內容均應認定為國家財產,對其所有的管理行為均屬國家公務。(2)土地征用補償款與自有資金混同的認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對土地征用補償款中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的性質作了明確的規定,但在實踐中土地征用補償款往往一次性由政府拔給鄉鎮會計核算中心的村級財務帳戶,和村集體的所有資金混同,由村里按照用途向會計核算扣、領取使用。當村干部侵吞、挪用該賬戶里的資金時,認定資金的性質就會發生困難。
1.1與客觀行為相關的爭議
《解釋》中第七項是兜底性條款,因規定的模糊性,實踐中爭議很大。有觀點認為,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系村民依法選舉產生,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和行使自治權利辦理本村事務的所有行為均應認定為公務。有的觀點認為只有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解釋》所規定的七種行政管理工作方可認定為依法從事公務。因對兜底條款認識不一致,導致對實踐中一些行為性質的認定也不相同。如,村干部沒有協助人民政府進行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但收受他人賄賂后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提供關照的行為定性。有觀點認為應按照土地轉讓方式來確定,如果以出讓方式轉讓的,則行為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如果是劃撥方式轉讓的,則構成受賄罪。有觀點認為無論是劃撥方式還是出讓方式都構成受賄罪,也有觀點認為,《解釋》第七項屬于兜底條款,沒有明確指出此類協助工作屬于該種情形,不能擴大解釋。此外,如果村干部既協助政府迸行征地工作,同時作為村務負責人在征地中也承擔了許多職責,那么收受賄賂所利用的職務便利是利用哪一種身份便利,此類行為性質的界定存在難度。
1.2與管轄相關爭議
征地拆遷領域的管轄爭議體現為主罪和次罪之爭、此罪與彼罪之爭。(1)主罪與次罪之爭。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征地拆遷中的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和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分別屬于公安機關和檢察院管轄,對于管轄爭議,六部委《關于實施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規定》對于司法實踐中案件管轄爭議確立了“次罪隨主罪管轄”的基本原則,但不完善,操作還存在困難:一是判斷主罪和次罪的標準是什么;二是主罪和次罪在案件未查清之前還存在著轉化的可能;三是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之間需要移送案件時,移送主體不明、對象不明、法律責任不明、時機不明,更無如何配合的規定;四是當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都認為自己(對方)管轄的是主罪,對方(自己)管轄的是次罪時,如何協調,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2)此罪(職務侵占、挪用資金)與彼罪(貪污、挪用公款)交叉融合引發管轄沖突。《解釋》僅限于七種行政管理行為中涉及的財產,而村(居)委會還有其他自有資金。實踐中,村委會的財務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亂,就某一挪用或侵吞行為而言,難以區分自有資金還是七種公務行為中的資金,造成案件管轄權難以確定。
2農村征地領域職務犯罪法律適用與思考
2.1犯罪主體認定
黃太云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一文中指出:“村委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主要是指村黨支部、村委會和村經聯杜、經濟合作杜、農工商聯合企業等掌管村經濟活動的組織的人員。因為,他們是農村中掌握權力、可能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員。”該文已明確指出村黨支部屬于農村基層組織,同時對于認定其他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提供了理論支持,但此解讀只是學術性質,不具有法律效力。筆者認為,應當以立法解釋的形式,明確規定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包括村民委員會及其下屬委員會、村黨支部和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及依法律法規設立,或者經村民授權的各種村民自我管理組織的人員,如村民小組等自治組織的成員,同時應包括村會計和村出納。當前在法律尚未進一步完善前,在司法實踐中應當按照立法解釋的本意執法辦案,正確適用《解釋》要把握兩個基本原則,一是要堅持限制原則,凡是司法解釋中沒有列舉的事項,不能擅自作擴大解釋。二是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我國各地農村的實際情況又是各異的,農村基層組織的狀況極為復雜,差異很大,在司法實踐中對同一類問題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仔細分析。
2.2土地征用補償款性質認定
關于土地征用補償款的性質,我們贊同階段說:(1)劃入村集體賬戶之前,以及劃入村集體賬戶但未分配的土地征用補償款屬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對象;(2)劃入村集體賬戶并實施了分配,除應發放給農民的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安置費等屬于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對象,其他資金屬于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罪的犯罪對象。針對司法實踐中,土地征用補償款與自有資金混同,我們認為除了要考慮土地征用補償款所處的階段外,還要考慮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故意:(1)若有證據證實行為人主觀明確指向土地補償款等,如一些村干部在鎮會計中心開票據時,編造發放土地補償款的借口,以貪污、挪用公款罪認定;超過土地補償款的部分認定為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2)沒有證據能夠證實行為人主觀意圖指向土地補償費用等資金的,以職務侵占或挪用資金罪認定,資金數額超過村集體資金、屬于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部分,以貪污罪或挪用公款罪認定。(3)如果侵吞、挪用的資金數額大于集體自有資金(土地征用補償等費用),超出的部分認定為貪污罪、挪用公款罪(職務侵占、挪用資金罪),但如果超出部分的數額尚不足以單獨定罪,則計入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數額,或者作為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量刑情節。(4)如果貪污、挪用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數額與侵占、挪用集體資金的數額均未達到構罪標準,即使總額達到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構罪標準的,也不作犯罪處理。當然,不作犯罪處理不利于征地領域職務犯罪的打擊,建議法律進一步完善。
2.3客觀行為性質的認定
關于兜底條款認定,我們認為應當從公務行為的本質來看,公務的基本特點是關系到多數人或不特定人的利益,具有裁量、判斷、決定性質。在沒有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要把握四個關鍵點:一是屬于協助人民政府行使的管理工作;二是該事務有相關行政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屬政府部門有權管理的范疇;三是協助的內容應與前六項具有相當性。四是基層組織人員實施的行為是其本職工作以外的事務。征地拆遷款的管理、發放等具有管理性質的工作,應認定為“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而純粹的動員、宣傳等事務性工作,不具有公務性質。因而針對實踐中的村干部沒有協助政府管理土地征用補償費,但是收受賄賂后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提供關照的行為定性。我們認為,應按照認定公務行為的四個關鍵點來確認是否屬于“協助政府從事其他管理工作”。如果村干部是協助政府工作,從事的工作內容屬于法律規范規定的政府部門職責范圍,與《解釋》規定的前六項情形相當,可以認為“協助政府從事其他管理工作”,其行為構成受賄罪;反之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村干部作為村務的負責人,無論是否協助政府從事征地事務都會在征地中起到重要作用,如果不加以區分而一律認定構成或不構成受賄罪是不妥當的。
2.4管轄爭議的解決
征地拆遷領域職務犯罪管轄分工存在的沖突,是由于刑事訴訟法以案件性質作為職能管轄分工的依據,使得偵查管轄權劃分絕對化,缺乏包容性所導致的。2012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第111條僅僅解決了立案環節的消極管轄沖突,而對于“不應當立案而立案”的積極管轄沖突,目前仍無法可依。目前解決農村征地領域職務犯罪沖突,我們認為,可以考慮在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之間就職務犯罪案件管轄建立聯席會議制度,通過雙方互相通報一定期限內的管轄沖突問題、移送問題,對交叉管轄的案件進行協商、研究,并達成切實可行的管轄爭議解決方案,真正實現公安、檢察之間的協調與配合。但從長遠來看,可通過賦予檢察機關更加寬泛的機動偵查權來應對管轄之爭。1979《刑事訴訟法》賦予了檢察機關寬泛的機動偵查權,只要認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就可以立案偵查。而1996、2012《刑事訴訟法》對機動偵查權適用范圍作了嚴格的限定,必須滿足重大犯罪和省級以上檢察機關決定兩個條件,實踐中難有職務犯罪案件與之匹配。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城鎮化的推進,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執行公務的數量、國家投入農村資金數量會進一步增多和加大,涉農職務犯罪數量極有可能上升。筆者建議,在農村職務犯罪查辦上,可以賦予基層檢察院更為寬泛的機動偵查權,避免因管轄爭議影響案件辦理,以此推動農村職務犯罪查辦,服務城鎮化建設的有序推進。
作者:陳云高鄭瓊單家和單位:臨安市人民檢察院
- 上一篇:城鎮稅務局工作總結和工作計劃范文
- 下一篇:綜述水利工程項目前期籌備工作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