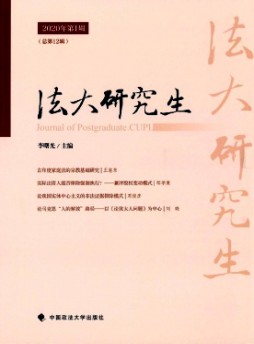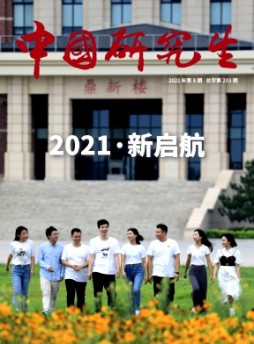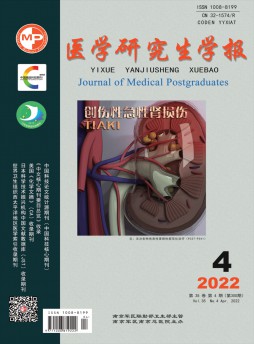研究生生源區域流動案例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研究生生源區域流動案例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引言
流動性是人才資源的固有特征,是人才開發的重要前提。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曾經指出,促進人口和生產要素合理流動,是縮小區域間、城鄉間收入差距最為有效的辦法。高等教育作為培養高素質人力資源的主要場所,理應在提高勞動力綜合素質并促進其合理流動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1]就博士生的流動而言,主要包括生源流動和就業流動兩個方面。其中,對于博士生就業的流動,筆者在前期研究中發現,學源地在中部地區的博士生更多地選擇到東部地區就業,而其他學源地博士生首選在學源地就業[2]。因此,博士生生源流動最終會通過就業流動的“傳遞效應”對人才流動帶來重要影響。此外,研究生生源的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動對提高生源質量、優化生源結構,進而對研究生教育質量的整體提高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濟大學徐佩珍曾撰文指出,若一個學生常年只在有限的地域、空間從事同一個學科、專業,那么他所接觸的研究者和研究課題都會相對單一,其知識視野和思維方法無疑會受到地域文化、學科條件、導師人格等因素的框箍和限制,與外界更廣闊、更精彩的世界缺少交流和更新,在行為方式上缺少不同模式的沖擊和磨合,個性得不到應有的張揚,怎么可能成為富有創新精神、全面素質的人才呢?[3]去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特別強調,2010-2012年要“基本建成較完備的國家級和省級教育基礎信息庫以及教育質量、學生流動、資源配置和畢業生就業狀況等監測分析系統”。一些培養單位也開始了促進研究生生源流動的實踐探索。例如,中南大學2010年推出博導自主選拔博士生新政,規定導師自主考核選拔的對象為外校應屆碩士畢業生,其中改善學緣結構、促進高校之間人才流動及交叉培養是主要著眼點之一。2011年4月1日,中南大學等18所高校代表就加強優秀生源互推工作達成共識,簽訂了《高水平大學優秀研究生生源互推聯盟框架協議》。由此可見,研究生生源流動狀況是非常值得關注和研究的。但目前有關人才流動問題以高校教師隊伍的學緣結構和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流動研究最為常見,而研究生生源流動方面的研究特別是大樣本的實證研究還比較少見。研究生生源的流動大致包括跨專業流動、跨學校流動和跨地區流動三種類型,本文利用2006年博士學位授予信息數據庫,重點對碩士到博士階段的跨地區流動進行實證分析。
二、樣本說明
本文采用數據來源于2006年博士學位授予信息數據庫,選擇入學前具有碩士學位的博士畢業生作為統計樣本,直接攻博和碩博連讀的樣本不包括在內,并對博士培養單位信息缺失樣本進行了剔除。實際樣本總計22376人,占當年實際博士學位授予人數(33305人)的67.2%。實際樣本中,籍貫缺失26人(占0.1%),大學培養單位缺失2404人(占10.7%),碩士培養單位缺失2007人(9.0%);海外大學畢業43人(0.2%),海外碩士畢業113人(0.5%)。本文對所在地的界定以省(自治區、直轄市)為計量單位,選取學生培養單位的實際所在地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學位授予單位所在地進行統計,如,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歸入上海市。樣本博士培養單位的地區分布如表1所示。表1樣本博士培養單位地區分布
三、博士研究生跨地區流動的統計描述
(一)流動類型學生完成博士學業,一般情況下會產生籍貫地、大學所在地、碩士所在地和博士所在地四個以省份為單位的不同空間組合,見表2。總樣本中在籍貫地完成從大學、碩士到博士整個學習過程者3740人,約占1/6;在籍貫地獲得博士學位者5826人,約占1/4;在大學所在地獲得博士學位者8083人,略高于1/3;在碩士所在地獲得博士學位者11259人,約占1/2。數據表明,博士學習地區選擇上對碩士所在地的依賴性明顯高于大學所在地和籍貫所在地,如果考慮到樣本中沒有計入的碩博連讀生,三者之間的差距將更大。表2不同階段同一所在地人數比例統計英國學者菲戈安(AlessandraFaggian)等根據大學生家庭所在地、學校所在地和工作所在地的各種可能的組合情況將大學畢業生的流動分為不動(Stayer)、前期流動(Sticker)、后期流動(LateMover)、返回流動(ReturnMigrant)和繼續流動(RepeatMigrant)五種類型。[4]借鑒該分類方法,同時為簡化分析,本文僅選擇大學所在地、碩士所在地和博士所在地進行具體考察,則博士學位獲得者從大學到博士階段的流動過程可以分為以下五種類型:(1)不動:是指學生在大學所在地繼續完成碩士和博士學習,未發生任何流動;(2)前期流動:是指學生由大學所在地流動到其他省(市)就讀碩士,而后留在碩士所在地獲得博士學位;(3)后期流動:是指學生留在大學所在地就讀碩士,而后流動到其他省(市)獲得博士學位;(4)返回流動:是指學生首先由大學所在地流動到其他省(市)就讀碩士,而后又返回大學所在地獲得博士學位;(5)繼續流動:是指學生首先由大學所在地流動到其他省(市)就讀碩士,又流動到大學所在地和碩士所在地之外的省(市)獲得博士學位,共發生了兩次流動行為。五種流動類型的特征和流動次數如表3所示。表3博士學位獲得者空間流動的五種類型根據以上分類方法,如表4所示,總樣本中不動者7207人,占32.2%;前期流動者4052人,占18.1%;后期流動者6834人,占30.5%;返回流動者876人,占3.9%;繼續流動者3407人,占15.2%。數據表明,盡管在大學所在地獲得碩士學位者高達62.8%,但在此后的博士階段有近一半人選擇了離開;而碩士階段一旦離開大學所在地,再返回該地攻讀博士學位的比例非常低,大有“一去不回頭”之意。表4博士學位獲得者五種流動類型的統計描述
安全提示:如果聊天中有涉及財產的操作,請一定先核實好友身份。發送驗證問題或點擊舉報
編輯部-蔣雪蓮 17:34:06
(二)流入流出統計本文將博士流入界定為外地碩士畢業生到本地就讀博士,流入率等于“非本地碩士生源人數÷本地博士總數×100%”;將博士流出界定為在本地碩士畢業后到外地就讀博士,流出率等于“本地碩士畢業后在外地獲得博士人數÷本地碩士總數×100%”。同時,考慮到寧夏、海南、貴州、西藏4個地區沒有博士授予樣本,而青海和河南的樣本數僅分別為8人和21人,故下文僅對我國上述6個地區之外的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統計分析。首先,從流入來看,選定25個省區的平均流入率為49.7%,即外地生源占博士總人數的一半。根據流入率的高低大體可以劃分為高流入地區(流入率60%以上)、較高流入地區(流入率在40-60%之間)、較低流入地區(流入率在30-40%之間)和低流入地區(流入率30%以下)四種類型。其中,高流入地區包括上海、浙江、廣東和北京四個地區,平均流入率為65.2%;較高流入地區包括江蘇、四川、天津、遼寧、福建、安徽和重慶七個地區,平均流入率為49.9%;較低流入地區包括江西、云南、湖北、湖南、陜西、山東和甘肅七個地區,平均流入率為34.9%;低流入地區包括山西、河北、吉林、廣西、黑龍江、內蒙古和新疆七個地區,平均流入率為20.1%,見表5。表5按流入率的區域劃分其次,從流出來看,選定25個省區的平均流出率為42.6%,即到外地讀博的碩士占碩士總人數的四成以上。根據流出率的高低大體可以劃分為高流出地區(流出率80%以上)、較高流出地區(流出率在60-80%之間)、較低流出地區(流出率在40-50%之間)和低流出地區(流出率40%以下)四種類型。其中,高流出地區包括江西、廣西、新疆和內蒙古四個地區,平均流出率為88.9%;較高流出地區包括云南、山西、河北、甘肅和山東五個地區,平均流出率為71.6%;較低流出地區包括安徽、重慶、湖南、遼寧、福建和四川六個地區,平均流出率為47.7%;低流出地區包括陜西、上海、吉林、湖北、浙江、黑龍江、廣東、江蘇、天津和北京十個地區,平均流出率為31.7%,見表6。表6按流出率的區域劃分依據流入率和流出率的綜合表現,可以將選定的25個省區劃分為高流入低流出地區(Ⅰ類)、較高流入較低(低)流出地區(Ⅱ類)、較低(低)流入較低(低)流出地區(Ⅲ類)、較低(低)流入較高(高)流出地區(Ⅳ類)和低流入高流出地區(Ⅴ類)五種類型。其中,Ⅰ類地區包括上海、浙江、廣東和北京四個地區;Ⅱ類地區包括天津、江蘇、遼寧、安徽、福建、重慶和四川七個地區;Ⅲ類地區包括湖北、湖南、陜西、吉林和黑龍江五個地區;Ⅳ類地區包括山東、甘肅、云南、河北、山西和江西六個地區;Ⅴ類地區包括新疆、廣西和內蒙古三個地區,見表7。表7按流入流出率的區域劃分在上述各地區中,新疆、內蒙古、廣西、江西2006年的博士學位授予數都不超過100人(見表8),但這四個省份的碩士教育都有一定的規模,其碩士授予數/博士學位授予數之比分別為51、37、89和44,這些省份的碩士畢業生必須向外流動才有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因此這些地區的高流出率是可以理解的。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湖北、陜西、吉林、黑龍江四省2006年的博士授予規模均超過1000人,湖南省博士學位授予數也接近1000人,但流入率和流出率均比較低。廣東、浙江兩省的博士學位授予數與上述五省基本相當,但卻屬于高流入地區;四川、遼寧的博士學位授予數也與上述五省相當,但屬于較高流入地區。由此可見,影響生源流動的因素既包括教育資源分布情況,也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廣東、遼寧、浙江均為經濟發達省份)。山東省的情況比較特殊,其博士教育資源相對豐富(2006年博士學位授予數為1030人),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2006年GDP排名全國第2,人均GDP排名全國第7),但卻屬于較高流出率和較低流入率地區。
四、結論及建議本文基于2006年全國博士學位獲得者樣本的流動性分析表明:
第一,博士生源整體流動率較高,但流入、流出率在地區間存在較大差異。雖然生源流動是改善學緣結構、培養學生創新素養的重要途徑,但鑒于直博、碩博連讀等長學制對博士生培養質量也有諸多優勢,流動率的合理區間尚無定論,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也非常有限。根據美國科學基金會、國立衛生研究院、教育部等機構對1999年23153名可獲得信息的美國本土博士學位獲得者的調查,在出生地(州)完成從高中、大學直到博士整個過程并且計劃在本地就業的比例為13.4%,在大學所在地獲得博士學位的比例為31.2%。[5]如果考慮到美國有50個州和1個特區,遠多于我國的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我國博士生源流動率與美國相比并無明顯差異。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在分析時選擇出生戶口所在地代替籍貫所在地更為合理;其次,本研究中的流動專指跨省流動,校內跨學科流動和省內跨學校流動包括在不動者中,如果完整考慮這些因素,則流動者的比例應該更高。
第二,學生在選擇博士培養單位時對碩士所在地具有更強的依賴性。為什么在博士學習地區選擇上對碩士所在地的依賴性明顯高于大學所在地和籍貫所在地?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相對大學和碩士而言,博士教育資源相對集中;其次,對于原本有流動需求的部分學生而言,經過大學和碩士階段兩次選擇,可能既定的流動需求已經得到滿足,如在大學所在地獲得碩士學位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選擇繼續在該地攻讀博士學位;再次,相對大學和碩士來講,導師在博士招生中擁有更大的自主權,考試科目基本都由本單位命題,選擇報考碩士所在地的培養單位,獲取信息的渠道更便捷、成本更低,被錄取的可能性也更大。
第三,教育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生源流動的主要因素。在解釋人口流動的原因方面,人口學上最重要的理論是“推拉”理論。最早系統提出這一理論的美國人口學家唐納德•博格(D.J.Bogue)認為,勞動力遷移可能是因為有利的經濟發展而形成的“拉力”造成的,也可能是因為不利的經濟發展而形成的“推力”造成的。[6]就博士研究生的跨地區流動而言,“推拉理論”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不同地區流入率和流出率的差別可看作是教育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水平共同作用的結果。博士教育資源充足、教育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高,就會形成吸引生源的“洼地”,產生對外地碩士的拉力;相反,博士教育資源匱乏、教育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低,就會形成排斥生源的“高地”,產生對本地生源的推力。
第四,政府在促進研究生生源流動中應發揮更大的宏觀調控作用。要引導博士畢業生向經濟欠發達地區合理流動,一方面要加強這些地區自身在人才引進、使用等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流動能力、流動機會、流動成本等方面的影響,學校所在地就業往往是博士畢業生的首要選擇,研究生生源的合理流動無疑是促進畢業生就業流動的重要環節和保障。因此,鑒于我國目前博士生教育的區域分布比碩士生教育更不均衡[7],是否需要在堅持博士生教育主要集中在研究生院高校培養的前提下適當調整博士研究生教育資源的空間布局,是否需要借鑒碩士招生中的地區傾斜政策,是否需要實行獎助學金的地區傾斜政策等等都是政府層面值得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