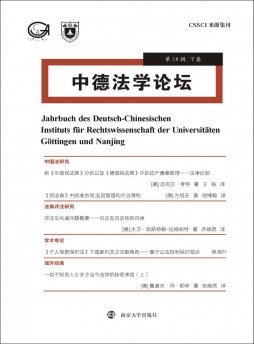德法治世反省與現實面向歷史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德法治世反省與現實面向歷史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春秋戰國時期政治上的分裂無序和文化上的多元爭鳴,使得當時思想家對曾經創造過輝煌文明的“德治”進行反思與取舍,先秦儒家的“以德治國”與法家的“依法治國”是其典型代表。先秦孔孟積極倡導的“以德治國”是對上古“德治”之繼承,其基本指向是修己安人、以德治國,此進路與后來法家所推行的“依法治國”形成鮮明的對比。法家亦反省歷史、繼承歷史,但法家更多地強調“民道弊”“世事變”與“行道異”的現實面向。春秋戰國時期孔孟“德治”與法家“法治”之博弈與最后之結果,深刻表明了反思歷史、汲取智慧,必須面向社會現實,才能解決現實問題,擔當時代大任,完成時代任務。
[關鍵詞]以德治國;依法治國;理想性;現實性
人的思想既可以為現實社會的合法性提供論證,也可以被現實社會的運行而蕩平滌凈。孔孟面對其生存時代所存在的問題,對上古三代的道德治世進行了反省、思考和總結,積極倡導“德治”理念以求解決當時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強調道德修為,尤其是為政者的道德對現實政治與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性。“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省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1]651-652孔孟“德治”遠離社會現實,其“德治”理想無法在現實社會中得以實現。與此同時,代之而起的是法家“法術”思想的推行。就歷史的演進與變遷而論,法家的法術之所以能被當時社會所認同而得以推行,并解決當時社會所存在的問題,是因為法家思想對歷史的反省建立在現實社會面向的基礎之上。汲取歷史經驗,必須面向現實的需求。
一、先秦德治思想的歷史變化
在先秦諸子以前,存在著一個以“德”治世的時期,并且經歷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演進過程,這是“德”內涵的形成和奠定時期,它是孔孟“德治”理念的基礎。早期的氏族公社或部落聯盟時期,人類生存面臨強大自然力的威脅和物質財富的極度匱乏,部落或氏族內部成員之間形成了均分財富、團結平等的關系,這種關系的維系與平衡是依靠德高望重的部落首領或氏族酋長來調和與維持的。從今天的史料,我們可以看到五帝時期的“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2]25-27的歷史變遷,證明了人們意識到“德”在族群生存中的重要性并進而求“德”,將“德”內化成為一種政治操守和政治理念,即以德治理族群。到了商周時期,不管是作為人格神的“帝”或“上帝”給了現存政治體制多少合法性論證,但在政治的運作層面,仍強調為政者的人格魅力和德性修養,將政治層面的德行與實行德治作為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根據。“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2]89“好生之德,洽于民心。”[2]91“伊尹申浩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常無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2]213“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2]216這些記載中的“天”與“帝”,其重要性已不及“德”,將“德”置于“天”之上。周武討伐商,是商紂無“德”,其誓師宣言之核心就是控訴商紂的“無道無德”而帶來的災難。王國維說:“夫商之季世,紀綱之廢,道德之隳極矣。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3]98此時“帝”與“天命”之觀念較前相比,在于賦予其“德”之內涵。傅斯年說:“一個因保天命之方案,皆明言在人事之中。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人民,在慎刑,在勤治,在無忘前輩艱難,在有賢輔,在遠儉人,在秉遺訓,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無一事合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為‘惟德之用’。”[4]158西周時期“德”之觀念第一次達到高度的自覺,成為現實政治的存在原因和合理性依據,其內涵包括為政者要明德慎罰、保民裕民、天道王制和自我修養四個方面。明德慎罰就是為政者應以德服人,注重教化百姓,勤于政事、效法先王、任用賢人,保民、惠民、安民;保民裕民就是為政者作為上天在人間的代表,要克制欲望,愛民如子,使人民富足安康;天道王制就是為政者的作為要順天道、循物理、定秩序;自我修養就是作為為政者應具備為政的道德品行,能為天下民眾做楷模。但此時之“德”,在面向現實的政治,僅強調現實政治運作過程中為政者的個人道德的作用,也就是以“德”治世的實現僅靠為政者的個人道德修為來實現,將現實政治的好壞、國家興衰、個人生活狀況都安置放到為政者個人道德修為上。就此而論,在當時對現實政治運作層面的為政者其道德品行,既沒有內在的規制標準,也缺乏外在的約束機制,很容易走向暴政而“禮壞樂崩”,西周以厲王暴政而結束正是此德治之弊所生。孔孟融“名分”于“德治”理念,要人找到各自在社會中的位置,循名分立身處世,方治“禮壞樂崩”,實現以德治國,達此面向而建立理想國家。
二、“德治”理想之現實面向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發生劇烈的大變動、大改組,給當時人們帶來了極大地苦痛與折磨。社會精英們面對政治上的分裂無序以及文化上的多元爭鳴,使得他們對曾經創造過輝煌文明的“德治”理念進行重新的反省與思考。春秋末年的孔子認為,亂之因在于禮壞樂崩,也就是西周禮樂“德治”的式微,故而他承繼西周以來的禮樂制度,以復興三代“德治”為己任,堅信“德治”為最高的政治理想,慨言“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5]234他一生奔波,游說諸侯,問政求官,“累累若喪家之狗”。[6]1921對于自己的理想的不曾實現,直到晚年依舍不得、念戀不去,“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5]85其所倡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因其失去貴族政體現實面向而不合時宜、四處碰壁。當時的政治現實,不再是體現個人德性的“敬德保民”,而是物質力量維度的“富國強兵”。孔子將當時的社會無序、混亂,其根本原因歸結為當權者的德性欠缺,強烈的要求“正名分”、施仁愛,以行“德治”,醫治“禮壞樂崩”,成就理想社會。“德治”優于“法制”,治標治本,“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5]15在為政的進路上,為政者應該是道德的表率,德應為為政的綱領。“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5]166“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5]166“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5]173“茍正其身矣,于從政者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5]175“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5]14孔子身體力行、四處周游,積極倡導“以德治國”,醫治“禮壞樂崩”的社會現狀,孔子“以德治國”的核心旨趣在于用“道德”對權力進行的約束和規整。孔子對上古因失德而“亂政”分析得很清楚,問題找得也很準確。但其將“德治”的社會政治理想之實現寄托在統治階級個人的道德修為上,其缺陷在于它既沒有內在的制約,亦缺少外在的約束和有力保證。就此而論,孔子終身奔波,抱有美好的愿望,聽之給人力量,使人振奮,思之讓人向往與追求。但缺乏有效機制約束的“德治”,軟弱而無法真正實現。戰國中期孟子生活的時代,“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7]202孟子以繼承孔子“德治”思想為己任,要求為政者行“仁政”、愛民惠民而得天下之心。他認為:“地方百里而可以為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7]15“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7]198對西周禮樂文明的“德治”理想,孔子將其提升具體的“仁”,而孟子更進一步,將其外化為“仁政”的政治操守。但無論是“仁”還是“仁政”,不管它內在的合理性有多少,因為政治的現實性,當它缺乏一種行之有效的內在機制和外在約束時,它只是理想而無法得以真正的實行。梁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這個典型的時代性問題,明確指向當時時代的主題是物質利益豐富和國家實力的壯大。孔孟的德政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著無法調和的矛盾,政治現實的復雜性,從本質上決定了政治秩序的建立和規范,無法通過個人自我的修養來完成,春秋戰國歷史的變遷,證明了孔孟“德治”理想背離時代需求的現實面向。
三、“德治”之式微與法術之推行
孔孟“德治”理念在現實政治中的博弈、式微,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家“富國強兵”法術思想發展、見用并最終取得成功。商鞅見秦孝公,先講王道理想而不被理睬,轉述“富國強兵”而被大加贊許并委以重任,反映出現實的時代面向的重要性。西戎小邦秦國因商鞅變法推行法術而迅速崛起。在法家看來,“德治”的問題實質在于“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得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8]113也就是具備道德修養的人,即使可以能將自己的仁義德性施諸于人,但他無法保證使接受者亦具有仁義的德性。按其人之本性很容易走向為惡的通徑,而“法”就是要堵住此為惡之門的基石。孔、孟一生勤勉、四處奔走,理想難以推行,只是“敬見孔子,不問其禮”,[6]1911或是“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9]1661的自我安慰與心里平衡。晏嬰給齊景公的建議是儒者不可用、禮樂不可興,將“德治”國家治理理念和持這種理念的人都徹底否定,原因是“德治”僅是理想,離現實相去已遠;禮樂制度,那也是圣賢的東西,周王室衰微,“禮樂缺有間”。拋卻現實面向的理想,既不為時代所容也無法見行于世。法家對儒家的批判以及儒家“德治”理想的式微,其核心在于儒家所極力倡導的禮樂制度已失去現實的需求,孔、孟津津樂道、孜孜以求而法家卻極力反對、嗤之以鼻。“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守。國以十者治,敵至必消,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畏。”[8]23“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憂不勞而功可立也。”[8]66戰國末年的荀子,雖以儒家自居,但在現實社會巨變中,其國家理念認為,“德”“法”“王”“霸”雖對立但可調和,他追求國家“富強”,承認“法制”而霸,但認為不“德”而“霸”非理想之途,也非最終追求,他倡導王霸并用、德法兼行、各有高下而互為犄角、相互補充,正是出于對現實面向的考量。基于此,儒法兼綜的國家理念成為現實,他的學生韓非子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為現實政治所青睞,推行法制,解決春秋戰國社會變遷的時代問題,建立強大的國家。人的思想既可以為現實社會的運行提供合法性的論證,也會被現實的社會面向所絞殺。從春秋末年的孔子到戰國中期的孟子,再到戰國末年的荀子,最后到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儒家“德治”國家理念在現實歷史演進中的式微和變化,就其學理而言,被韓非子徹底粉碎;就其現實而言,被秦始皇大一統集權政治徹底打翻。戰國法家始終能夠面對現實、立足現實面向的需求,就歷史演進而言,孔、孟“德治”的現實面向是“丈夫不耕,草木之食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則養足,人民少而財余,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1]649的特定的歷史時期,而現在卻已變成財用不足、人情澆薄、爭斗不已的時代,還求以“德”醫治“禮壞樂崩”,在法家看來“皆守株之類也”。面向現實以合時代之需、以順時代之變、以解時代難題是法家思想的現實基礎。韓非子將思想與現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分析問題的方法,特別是將國家的治理理念與現實社會的實際情況緊密結合,值得后人深思和反省。“事異則備變,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1]652“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當今爭于力”[1]619的歷史觀,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實際的情況。在“爭于氣力”的時代,只有積極面對現實社會中亟待解決的問題,順歷史之運,“是故力多者則人朝,力寡者則朝于人,故明君務力”[1]680。面對現實問題,反省興衰成敗,歷史經驗應合乎現實需求的基本面向,這是歷史的經驗,也是歷史選擇的必然。
[參考文獻]
[1]張覺.韓非子校注[M].長沙:岳麓書社,2006.
[2]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廖名春,整理.陳明,呂紹綱,審定.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王國維.王國維考古學文輯[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4]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5]何晏,注.邢昺,疏.朱漢民,整理.張豈之,審定.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6]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7]趙岐,注.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錢遜,審定.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8]蔣禮鴻.商君書錐指[M].北京:中華書局,1986.
[9]左丘明.春秋左傳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作者:景云 單位:閩南師范大學
- 上一篇:淺談口腔醫學PBL教學模式的結合范文
- 下一篇:本科院校科研創新發展醫學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