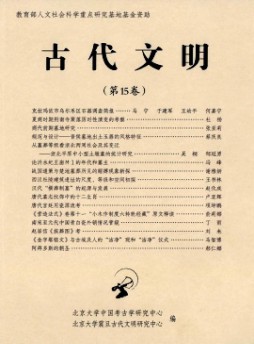古代哲學(xué)的音樂美學(xué)觀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古代哲學(xué)的音樂美學(xué)觀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楊亞麗單位:中央音樂學(xué)院音樂學(xué)系
中國音樂美學(xué)思想發(fā)展的歷史中,魏晉是繼先秦時期后美學(xué)思想發(fā)展歷程中的一個創(chuàng)新的時期。這一時期由于社會的動蕩不安,民眾在亂世中岌岌而生,知識分子之中,有以亂世為機躋身朝堂之上之輩,也有處江湖之遠憂思報國之士,也有消極隱世寄情山水之人,在紛亂的政局中,各種思想交融碰撞,尤其以儒、道、玄學(xué)三家發(fā)展的更為興盛,也爭辯的更為激烈。
一、魏晉時期音樂美學(xué)思想發(fā)展概況
魏晉時期有別于先秦諸子論戰(zhàn)之處是,在這一時期,玄學(xué)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由道家與黃老學(xué)派思想衍生出的玄學(xué),從人性與天理等方向為儒家與道家無法解釋的社會問題打開了新的思想空間。玄學(xué)的興起動搖了儒家思想的政治根基,也為后世的思想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在更迭交替的政局變換中,一大批文人的創(chuàng)新思想開始覺醒,思索、爭辯、論難、著述,涌現(xiàn)出一大批影響后世的著作。無論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和整個意識形態(tài),包括哲學(xué)、宗教、文藝等等,都經(jīng)歷轉(zhuǎn)折。這是繼先秦之后第二次社會形態(tài)的變異所導(dǎo)致的。“社會變遷在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現(xiàn),是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兩漢經(jīng)學(xué)的崩潰。煩瑣、迂腐、荒唐、既無學(xué)術(shù)效用又無理論價值的讖緯和經(jīng)術(shù),在時代動亂和農(nóng)民革命的沖擊下,終于垮臺。代之而興的是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是一種新的觀念體系。”在魏晉玄學(xué)影響下的魏晉整體美學(xué)思想也開始向“意”、“神”、“情”的方向發(fā)展,在這種關(guān)注于藝術(shù)本體自然美的大環(huán)境下,音樂美學(xué)也走向音樂本體論的發(fā)展方向。其中阮籍的《樂論》與嵇康的《聲無哀樂論》、《琴賦》等篇,成為魏晉時期論樂思想中兩種不同方向的和諧統(tǒng)一。
二“、和而不同”的理論基礎(chǔ)
“和而不同”一詞出自《國語•鄭語》:“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diào)口,剛四支以衛(wèi)體,和六律以聰耳……。夫如是,和之至也”,從史伯的這段話中,“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是客觀規(guī)律,只有“以他平他”,異類相雜,才能使萬事萬物統(tǒng)籌在一個整體中,以不同的面貌欣欣向榮,生生不息。“若以同裨同”,相同的事物重復(fù)累積,則違背了普遍性規(guī)律,不利于世間萬物的繁衍生息。
蔡仲德先生在《中國音樂美學(xué)史》中說道:“史伯認(rèn)為音樂和自然萬物、社會人事同構(gòu),也應(yīng)取和而去同,所以‘聲一無聽’,單一的聲音不可能動聽,而要‘和六律以聰耳’,以高低不同的眾多樂音組成悅耳的樂曲,也就是說音樂之美不在于一而在于多,不在于‘同’而在于‘和’,在于寓雜多于統(tǒng)一”。“和而不同”作為世間普適性的客觀規(guī)律,在阮籍、嵇康身上表現(xiàn)的尤為突出:兩人同屬“竹林之名士”,東晉袁宏作《名士傳》將阮籍、嵇康同向秀、山濤、劉伶、阮咸一起歸為竹林名士,這七人作為繼正始名士夏侯玄、何晏、王弼之后探索個人的精神超越與理想人格的塑造的一個群體,在當(dāng)時政治環(huán)境黑暗的氛圍中,高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隱居出世,放任自然,齊聚竹林論難思辯,形成帶有濃重老莊哲學(xué)色彩的在野名士群體。但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而且在政治環(huán)境中為保安身“雖去佐職。恒游府內(nèi),朝宴必與焉”,在官場上得到魏文帝的認(rèn)可,先“拜東平相”,后“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可見阮籍在“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環(huán)境中“欲濟世而無路,求放達而不成”,在司馬政權(quán)下曲意周旋的苦悶的人生狀態(tài)。而嵇康則“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于必濟”,對于無法容忍之事“剛腸疾惡,遇事便發(fā)”,對于司馬政權(quán)始終持反抗態(tài)度,即使臨刑東市,仍神色自若,引《廣陵散》以明其心志。從二人人生遭遇中可以看出兩個人不同的人生觀與人格特征。這種不同涵蓋在探索個人的精神超越與對“自然”的崇尚老莊哲學(xué)及玄學(xué)理論的大的思想統(tǒng)一之下,呈現(xiàn)出和諧爭鳴的景象。
三、阮籍與嵇康樂論中的“和”
作為竹林名士之杰出者,牟宗三先生在其著作《才性與玄理》中說道:“阮籍有奇特的性情,而嵇康善談理,余者皆無足取焉”。阮籍與嵇康論著中都有論樂,阮籍的《樂論》集中涉及四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論音樂的“自然之道”,“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二)論音樂必須平和恬淡,認(rèn)為“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三)論音樂必須整齊劃一,認(rèn)為音樂應(yīng)具有“一天下之意”,使“風(fēng)俗齊一”、“四海同音其歡,九州一其節(jié)”的作用;(四)論“淫聲”與悲樂,認(rèn)為樂以和為主,不以哀為主,哀傷之樂非善樂也。
而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則主要從:(一)“和聲無象”、“音聲無常”;(二)“音聲有自然之和”;(三)“聲音以平和為體”;(四)“躁靜者,聲之功也”;(五)“聲”能使人“歡放而欲愜”等方面論述了“音樂并不包含哀樂,也不能喚起相應(yīng)的哀樂”這一論點,在二人的論樂命題中可以看出,兩人都在論述音樂與自然的關(guān)系,這與兩人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是分不開的。老子在《道德經(jīng)》第四十一章喻道時提出“大音希聲”的音樂美學(xué)命題,用以喻“道”之“大”,“道”之玄妙,從此“大音希聲”成為形而上的音樂審美標(biāo)準(zhǔn)。老子對于“自然”的推崇,將音樂也與自然聯(lián)系起來,認(rèn)為只有“大音”才符合“道”的特征,而“五音使人耳聾”,形而下有具體形態(tài)特征的“五音”則會造成“耳聾”“、目盲”“、口爽”等損害人身的結(jié)果。
老子在第二十五章中對“道”是這樣闡述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由此可見,“大音”是與道相關(guān)聯(lián)的音,而“道”則是“先天地生”、“周行不殆”、“為天下母”的一種無形無質(zhì)的存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效法“自然”而存在的,在老子的“自然觀”中,一直秉持的觀念就是“無為”,然后能本身自在,做到“清靜”、“不爭”、“自在”、“無為”,才能建立起“華胥之國”的理想社會存在方式,在這種“理想國”中,人們能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國與國、社會的存在模式為“小國寡民”、“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應(yīng)是“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自然”之“道”的核心政治觀。也是老子一直秉承的“治世”之“道”。
莊子的“自然”在其理論中占有極大的分量。他崇尚一切天然無人工雕飾的美,不管是《知北游》一篇中“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還是《大宗師》一篇中“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芒然仿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yè)”,都表達了他對于山川宇宙富于浪漫主義色彩的向往。宇宙混沌、樸素、曠遠的形態(tài),符合莊子對于自然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對于這種自然觀,從莊子理想的“自由”意識與“生命”解放的思想中滲透而出,體現(xiàn)在其理論的各個篇章。
在《大宗師》中,莊子說“入于寥天一”,在《應(yīng)帝王》中說“汝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雕琢復(fù)樸”,又說“既雕既琢,復(fù)歸于樸”、“夫虛靜怡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看似形而上的玄妙,但卻深刻的還原了美的根本特征。莊子還特別崇尚“真”,他提出“法天貴真”,以真實的本原為難能可貴的特性。
天然之美在于不受約束不被限制,合乎自然發(fā)展之道,不扭曲不矯飾。這種還原萬物“真”的原貌的美學(xué)準(zhǔn)則,可貴之處在于它順應(yīng)人的自然之情,保持了質(zhì)樸天然的人的天性,那么人就從中獲得了性情的自由和解放,從而以“大自在”獲得美的體驗。在《逍遙游》中,莊子對于大鵬“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也”的向往,對于“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描述,提升了其對于“自然”的升華高度,他極力追求的無限之美和大美,成為對于“自然”的最高理想。
在老莊自然觀的影響下,阮籍與嵇康及其他“竹林名士”都注重人與“自然”的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關(guān)注生命本體的質(zhì)量,提升人的主體精神層面,成為人性真正覺醒的重要標(biāo)志。他們都對于生命形式的自然有自己的領(lǐng)悟。從《晉書》中看到:阮籍“當(dāng)其得意,忽忘形骸”;嵇康“美詞氣,有風(fēng)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zhì)自然”;劉伶“遺形骸”;王戎“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這些注重風(fēng)度、神韻、氣度、俊逸等形態(tài)的審美準(zhǔn)則,對后世審美標(biāo)準(zhǔn)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阮籍與嵇康的樂論中還有“和”的方面,在于兩人對于“平和之樂”的肯定。兩人都認(rèn)為音樂應(yīng)以平和為體,摒棄不平和的音樂,但是仔細(xì)研究會發(fā)現(xiàn),在“平和為體”的范圍之下,兩人的論樂方向卻產(chǎn)生了很大的差異。
四、阮籍與嵇康樂論中的“不同”
竹林七賢都以“反名教”為旗幟,但嵇康對于“名教”的反抗最為激烈也最為徹底。他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換得對于“自然”的向往和對于“名教”以及統(tǒng)治階層的深惡痛絕。
這一方面阮籍的反抗就顯得“軟弱”許多。阮籍在司馬政權(quán)下為官,與掌權(quán)者相處并無矛盾,雖有“濟世志”,但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環(huán)境中,阮籍也只能消極的以酒為盾,逃避其志求而不得的苦悶之情。
其“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與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形成鮮明對比。在阮籍與嵇康的音樂理論中,也同樣表現(xiàn)出兩人人格的差異性。《樂論》在音樂與自然的關(guān)系的論述中認(rèn)為音樂來源于自然,同時又能反作用于自然,使得“五聲和,八風(fēng)平”、“樂從和,和從平”,這是與伶州鳩、季札等人的道家陰陽家的思想相一致的;認(rèn)為音樂能夠“風(fēng)俗移易”、“刑賞不用而民自安”,這一說法卻和儒家的禮樂思想相一致;在音樂的平和恬淡方面,既有“使人無欲,心平氣定”的道家音樂要求,又有必須使音樂能夠維護等級秩序的儒家音樂準(zhǔn)則;《樂論》雖以“自然之道”的基礎(chǔ)出發(fā)進行論樂,但是卻始終強調(diào)音樂必須整齊劃一,“進退有節(jié)”,這是儒家音樂重理性守節(jié)度的音樂規(guī)范要求;最后阮籍否定了“淫聲”,否定了“以悲為美”,在這一方面徹底的偏向了儒家的音樂美學(xué)思想陣營。《樂論》將這儒道兩家思想合二為一,試圖調(diào)和儒道兩家的音樂思想差異,但是在阮籍的音樂理論中,卻清晰的看到了儒家音樂美學(xué)思想的本質(zhì)。
而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卻是從音樂本體論的角度出發(fā),立足于聲音作為自然的產(chǎn)物,不可能“象其體而傳其心”,聲雖有“躁靜”之分,但無“哀樂”之體,但嵇康也承認(rèn)儒家的一些美學(xué)思想,比如音樂具有教化的功能,音樂的雅俗之分,“淫聲”、“正聲”之分等,但我們縱觀嵇康的音樂理論會發(fā)現(xiàn),嵇康的音樂思想則是建立在道家音樂美學(xué)思想“自然”的基礎(chǔ)上的。嵇康強調(diào)“和聲無象”“,他稱音樂之和為‘至和’‘、大和’,既是因為這和諧特性來自天地自然,更是出于對此和諧特性的重視與推崇,所以他認(rèn)為‘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這就將對音樂的形式及其美感作用的重視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五、結(jié)語
“和而不同”是中國古典哲學(xué)的一個核心命題,在以“和”為前提和環(huán)境中的“不同”,才能統(tǒng)籌在統(tǒng)一中“以他平他”,促進世間萬物的繁榮昌盛。在中國古典哲學(xué)體系中,在歷代文人、思想家、哲學(xué)家的上下求索中,嵇康與阮籍是不可忽視的代表人物。
在魏晉時期,阮籍雖有“反名教之心”,但其處世卻消極圓融,所以能在夾縫中求生存,在竹林七賢中,阮籍算不上特立獨行的一個,因為在竹林隱居之后,除嵇康外其余六個都走出竹林,走向仕途。但阮籍的任誕卻是竹林七賢中最突出的一個,《世說新語》中任誕一篇,有8篇都在講述阮籍的故事,對人“青白眼相待”、“居母喪下棋不止嘔血數(shù)升”、“送嫂歸寧”、去不認(rèn)識的“早夭兵家女”家吊喪痛哭一場等等,這些故事在《晉書》中也有記載,作為一個曲意求全的不得意之名士,阮籍內(nèi)心的矛盾與苦悶是十分巨大的,但他求全的本能使他除了“動輒大醉”消極逃避之外,沒有別的方法。
而嵇康之所以在魏晉名士中評價比阮籍高,一則是他一直保持“真”、“自然”、“剛腸疾惡”的秉性之外,也一直旗幟鮮明的貫徹著“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批判性態(tài)度。他不僅僅是反抗封建權(quán)力機構(gòu)的壓迫與束縛的斗士,更是反異化、追求自由的勇士。他用自己的生命捍衛(wèi)了自己一直為之奮斗的信仰,至死不改其對于自我本真自然之道的執(zhí)著追求。這種精神在中國文人士大夫群體中,一直是“崇而敬之”、“心向往之”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