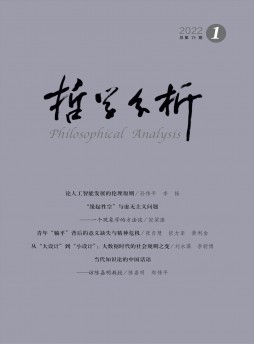哲學(xué)詮釋學(xué)中的翻譯誤讀綜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哲學(xué)詮釋學(xué)中的翻譯誤讀綜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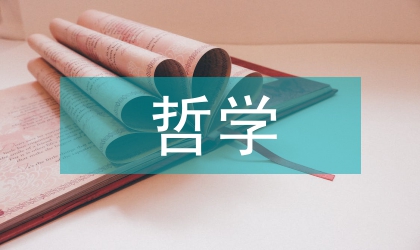
一、解構(gòu)主義和比較文學(xué)視域中的誤讀
解構(gòu)主義是對(duì)結(jié)構(gòu)主義的反叛,其代表人物德里達(dá)認(rèn)為文本沒有固定的意義,作品的終極不變的意義是不存在的,語(yǔ)言的意義一直處于延異之中,誤讀是語(yǔ)言修辭性的結(jié)果,“修辭導(dǎo)致文學(xué)語(yǔ)言具有自我解構(gòu)的性質(zhì),在表達(dá)一種意思的同時(shí)又否定它,任何一種閱讀方式都是相對(duì)的正讀和絕對(duì)的誤讀,從而使文學(xué)解讀得不到終極意義,在意義的層層延伸中推向前進(jìn)”。德里達(dá)認(rèn)為:“翻譯最好被看做是這樣一個(gè)例子,即語(yǔ)言永遠(yuǎn)處于不斷地修飾原文、推延和替換任何理解原作意欲言說的事情的可能性的過程中”。因此,譯作永遠(yuǎn)不可能和原作一模一樣,誤讀和誤譯才是翻譯的名號(hào)。受德里達(dá)影響,美國(guó)詩(shī)歌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1930-)認(rèn)為“閱讀,如我在標(biāo)題里所暗示的,是一種延遲的、幾乎不可能的行為,如果要強(qiáng)調(diào)一下的話,那么,閱讀總是一種誤讀”。宣判作者已死,否定一切確定性,這是激進(jìn)的解構(gòu)主義的勇武表現(xiàn),但也正是它的軟肋所在。當(dāng)文本不得不靠誤讀茍延,原作不得不靠誤譯殘喘,誤讀和誤譯已經(jīng)身處浮冰之上!因?yàn)椴剪斈返睦碚摫臼蔷驮?shī)歌理解而論的,鑒于詩(shī)歌的含蓄特點(diǎn),他的理論在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有著反傳統(tǒng)、打破禁錮的價(jià)值,但是“把西方的這種新詮釋學(xué)觀點(diǎn)延伸到文學(xué)文本以外的領(lǐng)域,其后果是不堪設(shè)想的”。誠(chéng)如張中載所言,將解構(gòu)主義及其誤讀理論引入到翻譯研究中來并不十分合適。解構(gòu)主義對(duì)于語(yǔ)義確定性的否定,會(huì)直接顛覆翻譯———這門以語(yǔ)義傳遞為己任的學(xué)科。解構(gòu)主義對(duì)于翻譯研究的積極意義在于它使研究者突破了“結(jié)構(gòu)主義語(yǔ)言學(xué)翻譯觀以文本為中心的范式”,“開始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考察翻譯活動(dòng)”,但是也要看到解構(gòu)主義誤讀理論被濫用的可能,它可能成為任何誤讀誤譯的借口。比較文學(xué)和翻譯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它又是如何定義誤讀呢?比較文學(xué)是跨越不同國(guó)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學(xué)科的文學(xué)比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種跨越中文學(xué)的同源性、類同性、異質(zhì)性與變異性”。鑒于比較文學(xué)的上述性質(zhì),它和翻譯的關(guān)系密切,并逐漸衍生出譯介學(xué)———從比較文學(xué)媒介學(xué)和比較文化角度“對(duì)翻譯(尤其是文學(xué)翻譯)和翻譯文學(xué)進(jìn)行的研究”。謝天振認(rèn)為當(dāng)代比較文學(xué)文化轉(zhuǎn)向之后,翻譯已成為它的三大研究領(lǐng)域之一。但是比較文學(xué)所說的翻譯研究不是翻譯界所說的文字之間的轉(zhuǎn)換,不是那些技術(shù)層面的“怎么譯”的問題,“而是只從文化層面上展開的對(duì)翻譯動(dòng)因、翻譯行為、翻譯結(jié)果、翻譯傳播、翻譯接受、翻譯影響以及其他一系列與翻譯有關(guān)的問題的研究”。在翻譯研究文化轉(zhuǎn)向之后,譯介學(xué)的這些研究范圍也被包含在翻譯的研究范圍之內(nèi),相對(duì)于對(duì)傳統(tǒng)的語(yǔ)言轉(zhuǎn)換研究,這些可以說是翻譯研究的新領(lǐng)域。由上可知,比較文學(xué)雖然和翻譯關(guān)系密切,但是它關(guān)心的并不是理解是否正確、翻譯是否準(zhǔn)確完整等翻譯界最為關(guān)心的問題。比較文學(xué)更多的是關(guān)心譯作及其所昭示的不同文化間的文化和文學(xué)關(guān)系,其本質(zhì)是文學(xué)研究。隨著文化間不斷的交流,不同文化間的文學(xué)相互影響、不斷變異,因而誤讀及其在翻譯中造成的誤譯在比較文學(xué)的視域中就有了特殊的意義,它們“特別鮮明、生動(dòng)地反映了不同文化間的碰撞、扭曲與變形,反映了對(duì)外國(guó)文化的接受傳播中的誤解和誤釋”。在比較文學(xué)研究中,文化誤讀被不加正誤評(píng)判地作為一種事實(shí)加以描述和接受,它展現(xiàn)的是不同文化間的關(guān)系,它在文化交流中的積極作用受到重視,比較文學(xué)學(xué)者認(rèn)為“誤讀在文化發(fā)展中起很好的推動(dòng)作用”。總之,比較文學(xué)和翻譯都關(guān)注誤讀誤譯問題,但它們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和目的是不一樣的:比較文學(xué)主要看到的是誤讀所帶來的文化間的影響與變異,對(duì)推動(dòng)文化發(fā)展的積極作用,至于它如何背離原作則不予過多考慮;在翻譯研究視域中,一切誤讀都意味著信息的增刪變形,因而為了完整準(zhǔn)確地傳遞原文信息,譯者要探究誤讀的成因并盡量避免誤讀。
二、解構(gòu)主義與比較文學(xué)誤讀理論對(duì)翻譯研究的負(fù)面影響
雖然解構(gòu)主義和比較文學(xué)的誤讀理論對(duì)提高讀者、譯者和譯作的地位以及重新審視它們的價(jià)值或作用有積極意義,但就目前翻譯誤讀研究來講,其負(fù)面影響較為突出。受其影響,現(xiàn)階段的翻譯誤讀研究有兩種常見錯(cuò)誤傾向:(1)不加審視的理論引入;(2)過分強(qiáng)調(diào)并夸大誤讀的積極作用。以《誤讀誤譯再創(chuàng)造》一文為例,作者先引用了樂黛云對(duì)誤讀的定義,然后直接認(rèn)定翻譯中的誤讀誤譯具有與文化交流中的誤讀一樣的功能,“同樣既能豐富主體文化,又能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續(xù),譯者的再創(chuàng)造成為可能”。這一論斷將翻譯研究中的誤讀研究不加審視地等同于比較文學(xué)中的誤讀研究,又解構(gòu)性地認(rèn)為誤譯能延續(xù)原作生命。在這樣的理論推演中,唯獨(dú)沒有對(duì)翻譯之作為翻譯而存在的本質(zhì)屬性和要求加以考慮,其結(jié)果就是草草得出結(jié)論:“古今中外的翻譯史證明,唯有‘誤譯’才能使原作再生”。在此,誤讀誤譯的積極作用被極度夸大,儼然成了永遠(yuǎn)不犯錯(cuò)的君王!在《譯者主體性:闡釋學(xué)的闡釋》一文中,作者認(rèn)為“誤讀概念是指對(duì)文學(xué)作品另有所解,是指對(duì)文學(xué)作品和文學(xué)現(xiàn)象在一定時(shí)期內(nèi)不能窮盡其文本內(nèi)涵和審美價(jià)值的解讀現(xiàn)象”,這種觀點(diǎn)一方面是對(duì)詮釋學(xué)理解理論的誤解,另一方面顯然雜合了解構(gòu)主義的元素,認(rèn)為對(duì)文本新意的發(fā)掘與創(chuàng)造就是誤讀。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誤讀在另一篇論文中同樣受到了贊譽(yù),作者稱這樣的誤讀就是斯坦納所說的“幸運(yùn)的誤讀”,“往往是新生命的源泉”。這種對(duì)理解的錯(cuò)誤認(rèn)識(shí)就在于忽視常態(tài)、傾心偶然、夸大誤讀的作用和價(jià)值。同樣,在《名著復(fù)譯“誤讀進(jìn)化論”》(章國(guó)軍2013)、《林紓與龐德誤讀和誤譯的解構(gòu)主義理?yè)?jù)》(朱伊革2007)、《嚴(yán)復(fù)翻譯中的誤讀》(韓江洪2008)等文章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生搬解構(gòu)主義或比較文學(xué)的誤讀概念,夸大誤讀積極作用的嫌疑。此類研究通常引用布魯姆的誤讀理論或樂黛云的誤讀概念作為理論基礎(chǔ),鮮有人仔細(xì)辨別它們與翻譯誤讀的區(qū)別,這樣做的結(jié)果就是過度夸大誤讀對(duì)翻譯的積極作用,違背翻譯的本質(zhì)和任務(wù)。雖然說有的“翻譯研究和批評(píng)始終徘徊在譯文對(duì)原文‘忠實(shí)與否’的微觀層面,不能以寬容的態(tài)度分析‘叛逆’背后的文化因素”,應(yīng)該受到批評(píng),但是這種批評(píng)不能成為隨意解構(gòu)原作意義的借口。從結(jié)構(gòu)主義文本意義的確定唯一到解構(gòu)主義的文本意義的無(wú)限延異,誤讀究竟該如何定義?所幸的是,哲學(xué)詮釋學(xué)提供了一個(gè)較為合理的視角。
三、翻譯誤讀概念厘定:哲學(xué)詮釋學(xué)視角
在方法論詮釋學(xué)中,“施萊爾馬赫就把詮釋學(xué)稱為‘避免誤解的藝術(shù)’”,“在施萊爾馬赫的一般詮釋學(xué)中,‘誤解’乃是對(duì)作者原初意圖和文本含義的背離,是與理解的客觀性與正確性無(wú)緣的”。因此,按照施萊爾馬赫的作者中心論的標(biāo)準(zhǔn),凡是不符合作者本意的理解都是誤讀。但實(shí)際操作中因?yàn)楹茈y見到作者,詢問他的本意是什么,另外有時(shí)作者本人也似乎很難說清楚自己究竟需要說什么,因而讀者不得已開始求之于文本,因?yàn)槲谋舅坪踉谀撤N程度上可以顯出作者的意圖,即便沒有,文本自己也是一個(gè)獨(dú)立體,能表達(dá)出相對(duì)完整的文本意圖。因而今天人們對(duì)誤讀的判定主要是從文本出發(fā),看所做的理解是否符合或扭曲文本的可能含義。在這種誤讀的定義中讀者完全是被動(dòng)的,等待原作及其作者的尺子來衡量,忽視了讀者的主體性,因而是不盡合理的。顯然理解活動(dòng)并非讀者單向靠近原作者的活動(dòng),讀者作為理解者具有能動(dòng)性,因?yàn)樵诶斫庵跛呀?jīng)擁有了先入之見,他積極地參與了文本意義的構(gòu)建,哲學(xué)詮釋學(xué)充分肯定了讀者的這種作用,較客觀地反映理解活動(dòng),也讓我們看到追求理解和詮釋的絕對(duì)客觀性或絕對(duì)主觀性都是偏頗的,因而哲學(xué)詮釋學(xué)的理解觀更具科學(xué)性和解釋力。需要指出的是,哲學(xué)詮釋學(xué)在被用來解釋誤讀的過程中,它本身就面臨著被誤讀的窘境。有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根本不存在誤讀。“本體論詮釋學(xué)將理解視為意義的生成,所表明的是理解主體的生存狀態(tài)”,“正因如此,就根本不存在誤解問題,因?yàn)樗^的‘誤解’也都是在主體的意識(shí)中當(dāng)下真實(shí)呈現(xiàn)的東西,就其表明了主體的存在方式而言,它與理解是等值的”。哲學(xué)詮釋學(xué)的“誤解”真的等于“理解”嗎?真的不存在“誤解”嗎?事實(shí)上,伽達(dá)默爾雖然肯定了讀者在意義構(gòu)建中的積極作用,但他并沒有從施萊爾馬赫的文本中心論的極端走向讀者中心論的極端。首先他繼承了海德格爾有關(guān)避免錯(cuò)誤前見的思想,認(rèn)為“首要的經(jīng)常的和最終的任務(wù)始終是不讓向來就有的前有、前見和前把握以偶發(fā)奇想和流俗之見的方式出現(xiàn),而是從事情本身出發(fā)處理這些前有、前見和前把握,從而確保論題的科學(xué)性”。其次,他提出了面向“事情本身”的方法來盡量避免誤讀,要關(guān)注“事情本身”,對(duì)于語(yǔ)文學(xué)家來說它就是充滿意義的文本。再者,關(guān)于如何面向“事情本身”,他主張用傾聽和對(duì)話的方式最終達(dá)到讀者和原文本視域的融合。因此并非像美國(guó)實(shí)用主義哲學(xué)家羅蒂所認(rèn)為的“文本的真正本質(zhì)”并不存在,對(duì)我們有用的是以不同手段得到的形形色色的“表述”本身,伽達(dá)默爾的本體論詮釋學(xué)與它有著根本不同,因?yàn)樗]有否定文本的存在及其在與讀者共同構(gòu)建意義中的作用。既然肯定了文本的作用,那么就等于肯定了誤讀的可能性,不能像有的學(xué)者完全否定誤讀的存在,那樣一切理解都是合理而正確的,翻譯將失去依靠,胡譯亂譯都會(huì)衣冠楚楚、挺直腰板!在《譯者主體性:闡釋學(xué)的闡釋》一文中,作者將人們結(jié)合時(shí)代需要對(duì)文本意義的發(fā)掘與創(chuàng)新理解都視為誤讀。其實(shí),按照哲學(xué)詮釋學(xué),這樣的解讀正符合伽達(dá)默爾關(guān)于理解是文本視域和讀者視域的融合的思想,二者相互傾聽,不斷擴(kuò)大自己的視域,最終靠近真理,達(dá)成真正的理解。伽達(dá)默爾認(rèn)為真正的理解是文本和讀者的共同參與,是溝通了過去和現(xiàn)在的創(chuàng)造,是人們存在的反映,因?yàn)槲谋菊鎸?shí)的意義“總是同時(shí)由解釋者的處境所規(guī)定的,因而也是由整個(gè)客觀歷史進(jìn)程所規(guī)定的”。既然理解總會(huì)在不同的歷史語(yǔ)境中呈現(xiàn)出不同面貌,那為什么這樣的理解會(huì)被一些學(xué)者無(wú)辜地扣上誤讀的帽子呢?根據(jù)伽達(dá)默爾,讀者視域和文本視域無(wú)法很好的融合、不能達(dá)成一致時(shí)做出的理解才是誤讀。這里既肯定了文本的客觀存在,也肯定了讀者的能動(dòng)作用,二者是平等的、平衡的、像朋友一樣的關(guān)系。當(dāng)然這是伽達(dá)默爾理想的理解狀態(tài),事實(shí)上,要達(dá)致這種狀態(tài)很不容易,一個(gè)很重要的原因是文本總是沉默的對(duì)話者,讀者在這場(chǎng)與文本的對(duì)話中無(wú)疑占據(jù)主導(dǎo)優(yōu)勢(shì),因此談話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讀者,取決于他的視域能否與原作的視域很好地融合。對(duì)于翻譯來講,譯者作為原文本的讀者,他的視域是否合適關(guān)系到是否會(huì)誤讀文本。下文主要分三部分探討譯者視域的形成和局限、譯者視域的修正、譯者視域的擴(kuò)大及最終形成合理的理解。
四、理解的歷史性與譯者視域的形成與局限
施萊爾馬赫認(rèn)為理解就是重構(gòu)作者心理的過程,是關(guān)于作者意圖和動(dòng)機(jī)的理解,為此就要消除解釋者自身的成見和主觀性,讓他們從自身的歷史性和偏見中脫身。相反,伽達(dá)默爾認(rèn)為,社會(huì)歷史構(gòu)成了人賴以生存的背景,人是歷史性的存在,歷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都會(huì)通過人展現(xiàn)出來。他說:不管是認(rèn)識(shí)者還是被認(rèn)識(shí)物都“是‘歷史性的’,即它們都具有歷史性的存在方式”。論及人和歷史的關(guān)系,他后來又總結(jié)道:“其實(shí)歷史并不隸屬于我們,而是我們隸屬于歷史”。因此作為歷史性存在的人,在理解中必定會(huì)受到其歷史性的規(guī)約,這種歷史性有助于形成解釋者的前見。這種前見不是要清空和消除,而是要發(fā)揮它的積極作用,限制它的消極作用。伽達(dá)默爾認(rèn)為,前見使最初的理解得以可能。海德格爾也認(rèn)為理解在本質(zhì)上是通過先有、先見和先把握起作用的,解釋從來都不是對(duì)某個(gè)給定的東西所做的無(wú)前提的把握。“前理解或前見是歷史賦予理解者或解釋者的生產(chǎn)性的積極因素,它為理解者或解釋者提供了特殊的‘視域’”。視域就是看視的區(qū)域,它包括了從某個(gè)立足點(diǎn)出發(fā)所能看到的一切。因此,譯者的視域就主要是建立在這些前見的基礎(chǔ)之上的。但是前見在使最初的理解成為可能后,就應(yīng)該不斷地受到審視,因?yàn)榍耙娪姓婕僦郑罢紦?jù)解釋者意識(shí)的前見和前見解,并不是解釋者自身可以自由支配的。解釋者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產(chǎn)性的前見與那些阻礙理解并導(dǎo)致誤解的前見區(qū)分開”。綜上所述,人的歷史性存在規(guī)定了人的理解的歷史性,這種理解的歷史性有助于形成了解釋者的前見,并進(jìn)而形成解釋者的視域。這樣翻譯中譯者的視域要想和文本視域達(dá)到融合,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正確的前見,另一方面要規(guī)避或調(diào)整不正確的前見,從而修正自己的視域,對(duì)此,譯者需要面向“事情本身”。
五、面向“事情本身”與譯者視域的修正
假的前見只能導(dǎo)致誤解、誤讀,必須加以識(shí)別和避免,只有這樣才能建立正確的前見。海德格爾對(duì)此十分清楚,他說:“首要的經(jīng)常的和最終的任務(wù)始終是不讓向來就有的前有、前見和前把握以偶發(fā)奇想和流俗之見的方式出現(xiàn),而是從事情本身出發(fā)處理這些前有、前見和前把握,從而確保論題的科學(xué)性”。之所以要這樣原因還在于前見往往是以隱蔽的方式統(tǒng)治我們,使我們不理會(huì)傳承物里所說的事物。因此,海德格爾認(rèn)為受方法論意識(shí)指導(dǎo)的理解所力求的應(yīng)該不只是形成對(duì)事物的某種預(yù)期,而且還要對(duì)這種預(yù)期有意識(shí)地加以控制,以便從事物本身獲得正確的理解。可見要避免隨心所欲的偶發(fā)奇想和受某種前見所支配的難以覺察的思想習(xí)慣的局限,要想獲得正確的解釋,解釋者就必須凝目直視“事情本身”。這里的“事情本身”對(duì)于語(yǔ)文學(xué)家來說就是充滿意義的文本,而文本本身又會(huì)指涉事情。關(guān)注“事情本身”,要求解釋者在解釋過程中不斷克服來自于自身的精神渙散,自始至終注目于事情本身。并且要理解一個(gè)文本總是意味著要進(jìn)行一種籌劃。一種預(yù)先的籌劃,在不斷關(guān)注事情本身的過程中,會(huì)遇到一些不斷出現(xiàn)的新東西,這些東西不斷地修改這種預(yù)期,在意義的統(tǒng)一體被明確地確定之前,各種籌劃相互競(jìng)爭(zhēng),一種前把握被另一種更好地前把握取代,這種不斷進(jìn)行的新籌劃過程就構(gòu)成了理解和解釋的意義生成運(yùn)動(dòng)。在這個(gè)意義生成的過程中,不是來自于事情本身的前見在一直起著干擾的作用。所以“理解的經(jīng)常任務(wù)就是做出正確的符合于事物的籌劃,這種籌劃作為籌劃就是預(yù)期,而預(yù)期應(yīng)當(dāng)是‘由事情本身’才得到證明”。在翻譯活動(dòng)中,譯者在理解中的各種籌劃活動(dòng)也會(huì)受到那些不是來自于事情本身的前見的干擾,形成不當(dāng)?shù)念A(yù)期,進(jìn)而產(chǎn)生不合理的視域。所以譯者要通過文本不斷地凝視注目事情本身,不斷做出更趨合理的籌劃和預(yù)期,才能形成合理的視域,有利于達(dá)到正確的理解。但是要想能夠做到面向事情本身,解釋者就必須以開放的態(tài)度去傾聽文本、和它對(duì)話、交談,向新經(jīng)驗(yàn)開放。
六、向新經(jīng)驗(yàn)開放與譯者視域的擴(kuò)大
在解釋者和文本的關(guān)系中,文本雖然是理解產(chǎn)生的一個(gè)重要源泉,但它似乎總是以一種沉默的態(tài)度出現(xiàn),雖然伽達(dá)默爾主張解釋者和文本之間要建立一種對(duì)話關(guān)系,但是因?yàn)槲谋镜某聊@場(chǎng)對(duì)話很容易流變?yōu)榻忉屨咦约旱莫?dú)白———將解釋者的意圖與解釋強(qiáng)加在文本的頭上,所以任何解釋者都必須十分謹(jǐn)慎,只有當(dāng)他們不再頤指氣使,不再一意孤行,他們才能傾聽文本的聲音。哲學(xué)詮釋學(xué)認(rèn)為人類行為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你”作為“你”來經(jīng)驗(yàn),對(duì)他者保持開放,聽取他們所說的東西,誰(shuí)想聽取什么,誰(shuí)就是徹底開放的,沒有這種開放性,人類就不能真正地連接起來。所以,對(duì)他人和文本的見解保持一種開放的態(tài)度,是開闊解釋者原有視域,避免誤讀誤解的應(yīng)有態(tài)度。伽達(dá)默爾說:“誰(shuí)想理解一個(gè)文本,誰(shuí)就準(zhǔn)備讓文本告訴他什么”。只有解釋者愿意傾聽他人和文本實(shí)際所說的東西,他才能把他所誤解的東西放入他自己對(duì)意義的眾多期待中,他才能認(rèn)識(shí)到自己的先入之見,才能看到文本可能會(huì)有的另一種存在,并因而有可能肯定它的實(shí)際真理以反對(duì)或校正解釋者已有的前見解,開闊他的視域。所以,“誰(shuí)想理解,誰(shuí)就從一開始便不能因?yàn)橄氡M可能徹底地和頑固地不聽文本的見解而囿于他自己的偶然的前見解中———直到文本的見解成為可聽見的并且取消了錯(cuò)誤的理解為止”。對(duì)于哲學(xué)詮釋學(xué)來說,只有解釋者能真正傾聽文本的聲音,解釋者和文本之間的交談和對(duì)話才能開始。對(duì)話、談話是談話者超出自己的成見,取得一致意見的基本模式。在哲學(xué)詮釋學(xué)中沒有比對(duì)話更高的原則了,因?yàn)椤爸挥性跁?huì)話中,只有與另一個(gè)人的思想(這種思想也能進(jìn)入我們的內(nèi)心)相遇,我們才能希望超越我們當(dāng)下視域的限度”。在解釋者與文本的對(duì)話中,解釋者以開放的態(tài)度,傾聽文本的解釋,尊重文本中與自己不同的異質(zhì)成分,不斷修正自己的前見,面向新的經(jīng)驗(yàn),使自己的視域不斷開闊,這樣才能逐漸與文本的視域融合,達(dá)到正確的理解。
七、結(jié)束語(yǔ)
總之,翻譯誤讀現(xiàn)象是翻譯研究中的一個(gè)重要現(xiàn)象,深入研究這一現(xiàn)象有助于深化對(duì)翻譯誤讀的認(rèn)識(shí),提高翻譯質(zhì)量。本文分析了解構(gòu)主義和比較文學(xué)賦予誤讀的不同內(nèi)涵和價(jià)值,分析了它們誤讀研究的側(cè)重點(diǎn)和目的,明確指出因?yàn)槭鼙容^文學(xué)和解構(gòu)主義的“誤讀”概念影響,以及因?yàn)閷?duì)哲學(xué)詮釋學(xué)“理解”概念的錯(cuò)誤理解,當(dāng)今的翻譯研究中有不加審慎地生搬硬套這些領(lǐng)域“誤讀”概念和過度夸大翻譯誤讀積極作用的趨勢(shì)。哲學(xué)詮釋學(xué)批判了神學(xué)詮釋學(xué)和方法論詮釋學(xué)對(duì)讀者主體性的忽視,同時(shí)又不像解構(gòu)主義那樣認(rèn)為意義不可確定,一切閱讀都是誤讀,從而避免了理解的兩個(gè)極端:唯文本的意義絕對(duì)客觀化和唯讀者的意義絕對(duì)主觀化。哲學(xué)詮釋學(xué)兼顧了文本和讀者,認(rèn)為理解是文本和讀者二者視域的融合,好的融合就產(chǎn)生合理的理解,不好的融合或不能融合則會(huì)產(chǎn)生偏狹的或錯(cuò)誤的理解。對(duì)于翻譯研究來說,哲學(xué)詮釋學(xué)的“誤讀”概念有助于譯者在翻譯活動(dòng)中既發(fā)揮自己的主體能動(dòng)性,又限制自己的主觀隨意性,從而和文本形成平等的對(duì)話關(guān)系,向文本開放。通過傾聽文本的聲音,和文本對(duì)話,譯者得以跨越時(shí)間距離“面向事情本身”,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內(nèi)涵,糾正自己錯(cuò)誤的前見,向新經(jīng)驗(yàn)開放,只有這樣才能不斷開闊自己的視域,最終和文本視域融合,形成合理的理解,從而盡量避免誤讀誤譯,更好地實(shí)現(xiàn)翻譯的文化傳通作用。
作者:吳冰甘露單位:湖南師范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湖北民族學(xué)院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