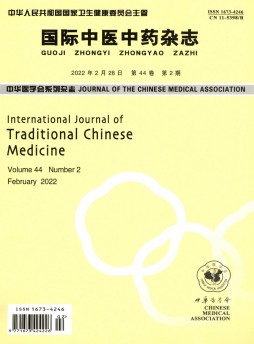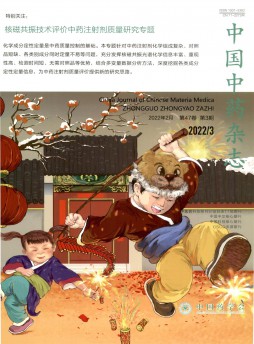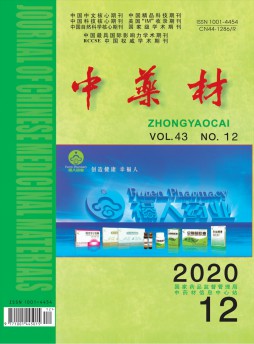中藥制劑利用度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藥制劑利用度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生物利用度是指藥物活性成分從制劑釋放吸收進入全身循環的程度和速度,是客觀評價藥劑內在質量的一項重要指標,一般分為絕對生物利用度和相對生物利用度。化學藥物制劑的口服生物利用度研究較多且充分,而傳統中藥的多成分、多靶點特性,使其生物利用度評價方法存在的問題成為制約中藥制劑國際化的瓶頸之一;近年來研究發現,同化學藥物制劑一樣,許多中藥制劑中的活性成分口服吸收較差、生物利用度低,也影響了中藥制劑臨床藥效的發揮。本文介紹了改善中藥制劑口服生物利用度研究的現狀,從藥劑學、藥動學、中藥復方配伍等角度概述中藥制劑口服生物利用度研究存在的問題和對策,并提出改善中藥制劑口服生物利用度的方法,以期為解決中藥制劑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問題提供思路。
1中藥制劑的分類
根據中藥制劑原料性質的不同,筆者將其分為3類:中藥單體成分制劑、中藥有效部位制劑、中藥復方提取物制劑。
1.1中藥單體成分制劑
該類制劑的原料與化學藥物制劑的原料類似,是將藥材經過提取、純化、分離等步驟后得到的具有明確化學結構的單一成分,純度較高,如:水飛薊素、燈盞花素、葛根素、紫杉醇等,其制劑口服生物利用度問題可完全參照改善化學藥物生物利用度的方法進行。
1.2中藥有效部位制劑
該類制劑的原料來源于某一種藥材的一類或幾類有效組分,其中有效成分有明確的含量范圍規定,臨床或研究應用多年并證實其確有療效的一類混合物,如銀杏葉提取物、黃芩提取物、丹參酮提取物等。這類原料與化學藥物的原料性質相比差異較大,雖有已知并定量的有效成分,但還含有許多未知成分,無法完全借鑒化學藥物通常采用的改善生物利用度的方法來解決這類藥物的吸收問題。
1.3中藥復方提取物制劑
該類制劑是將我國傳統中醫藥的配伍理論與現代制劑技術相結合發展起來的中藥新制劑,既保持了中醫藥多種成分共同作用治療病癥的特色,又解決了中藥復方以湯劑、散劑為主帶來的一系列質量問題,如:復方丹參滴丸、地奧心血康膠囊、銀翹解毒片等。雖然中藥復方在劑型改革上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中藥復方制劑生物利用度的問題往往被研究人員忽視,中藥復方制劑生物利用度的研究與評價方法也處于探索階段。因此,如何界定并考查這類制劑的生物利用度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2改善中藥制劑口服生物利用度研究的現狀
目前改善中藥制劑口服生物利用度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手段,即改變劑型、制劑新技術、應用吸收促進劑、基于藥物生物藥劑學特征進行給藥系統設計、基于配伍規律的中藥復方制劑處方設計等。
2.1改變劑型
藥物的不同劑型可能會導致其生物利用度的差異,一般認為80%~125%為生物等效,超出此范圍即為生物不等效,或生物利用度降低或提高。隨著藥劑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合理的劑型改變也是提高藥物生物利用度的一種有效手段。胃腸道生物黏附片是藥物借助于某些高分子材料與吸收部位細胞膜間的特殊結合力,可延長藥物在胃腸道中的停留時間或特定部位的作用時間,從而促進藥物的吸收,提高藥物的生物利用度[1]。該劑型既可治療局部疾病,提高藥效,又可通過延長藥物在體內的滯留時間而提高藥效。如向大雄等[2-3]研制的葛根總黃酮生物黏附性緩釋片與普通片相比,生物利用度得到顯著提高。靶向制劑是另一種可提高口服中藥制劑生物利用度的新劑型。該類制劑適于具有特定吸收部位,如在十二指腸[4]、結腸[5-6]等部位吸收的藥物,通過避免藥物在胃腸道其他部位的釋放而靶向于特定部位釋放從而提高藥物的生物利用度,也可用于特定部位局部疾病的治療。可見,選擇合適的藥物劑型對于藥物生物利用度的提高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若在制劑處方設計前進行充分的處方前研究,可避免因劑型設計不合理而導致口服生物利用度低,從而避免中藥活性成分不能充分發揮藥效的問題發生。
2.2制劑新技術
根據藥物生物系統分類原則[7],藥物分為4類:第Ⅰ類,高滲透性、高溶解性藥物;第Ⅱ類,高滲透性、低溶解性藥物;第Ⅲ類,低滲透性、高溶解性藥物;第Ⅳ類,低滲透性、低溶解性藥物。一般來講,第Ⅰ類藥物易于從制劑中溶解釋放后被機體吸收,而其他3類藥物均在其制劑的生物利用度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因此,目前發展起來的制劑技術基本都是通過解決藥物的溶解性或膜滲透性來使藥物的生物利用度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隨著回歸自然熱潮的掀起,這些制劑新技術也推動著中藥新制劑的發展,已有許多將制劑技術應用于傳統中藥來改善其吸收的大膽嘗試,主要有較為成熟的環糊精包合技術[8-10]、固體分散技術[11-14]、磷脂復合技術[15-21]、自乳化技術[22-25]以及近年來新興的納米技術[26-27]等。環糊精包合技術是通過一定方法(飽和水溶液法、超聲法、研磨法等)使難溶性藥物分子的空間結構全部或部分包入具有中空結構的環糊精輔料中,形成易溶于水的包合物,從而增加藥物表觀溶解度的制劑技術。環糊精包合技術主要是通過增加藥物的溶解度而提高難溶性藥物的生物利用度,如蛇床子素環糊精包合物[8]在家兔體內相對生物利用度為158.9%。此外,揮發油成分是一種中藥活性成分,在提取及制劑成型過程中易損失而影響揮發油藥效的發揮,在中藥復方新藥制劑的研究開發中,常常把揮發油成分提取收集后制成環糊精包合物,再進行復方的制劑成型研究,如和胃理腸丸中白術揮發油的包合[9]、細辛揮發油的包合[10]等,使揮發油成分固化后有利于揮發油成分的保存和復方整體藥效的發揮。固體分散技術是指藥物以分子、膠體或超細粒子狀態高度分散于惰性載體中形成的一種以固體形式存在的分散系統,即固體分散體。Sekiguchi等[11]最早在1961年提出固體分散體的概念,藥物以某種制劑方式給予機體后,其分子能否很好的透過生物膜屏障并及時分布到體內作用部位發揮預期療效,與藥物的釋放-溶解-吸收密切相關。隨著中藥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固體分散技術在中藥制劑領域中的應用越來越多,例如:銀杏葉提取物[12]、葛根素[13]、黃芩素[14]等。其中,葛根素固體分散體大鼠口服生物利用度較純葛根素提高了2.53倍,黃芩素固體分散體大鼠口服相對生物利用度為164%。固體分散技術不僅能增加難溶性藥物的體外溶出,還能改善其體內吸收,且制備工藝簡單。該制劑技術對原料的純度要求不高,可將有效成分及伴生物質高度分散于適宜載體中而達到改善生物利用度的目的,適于在中藥提取物制劑、中藥復方制劑的研發中推廣應用。磷脂復合技術是將藥物與磷脂分子通過電荷遷移作用而形成較為穩定的化合物或絡合物,從而改變母體藥物的理化性質,提高生物利用度的一種制劑技術。磷脂復合物是以磷脂為載體的一種藥物固體分散體。由于磷脂與生物膜的結構接近,因此磷脂復合物具有較好的生物相容性,藥物的磷脂復合物主要是通過增加藥物的溶出和改變藥物的生物相容性而增加吸收。已有將苦參素[15]、水飛薊賓[16]、葛根素[17]、銀杏葉提取物[18]、三七皂苷[19]、山楂葉總黃酮[20]等制備成磷脂復合物后提高其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報道。如水飛薊賓-卵磷脂復合物相對于水飛薊素膠囊在健康人受試者的相對生物利用度為(270.4±139.6)%,具有更高的生物利用度[21]。磷脂復合技術在中藥單體和中藥提取物制劑方面的應用研究較為廣泛,在改善中藥活性成分胃腸道吸收方面具有一定潛力,值得進行深入的研究探討。但磷脂復合物的性質大多與磷脂的性質類似,黏性強、穩定性差,使其在制劑成型方面具有一定困難。因此,如何克服磷脂本身的理化性質對制劑工藝造成的不便,從而改善中藥活性成分的口服吸收是給藥系統設計過程中需考慮的問題。
自乳化藥物傳遞系統(self-emulsifyingdrugdeliverysystems,SEDDS)[22]是由表面活性劑、油相、助表面活性劑,有時還含有促過飽和物質等形成的固體或液體釋藥系統。該系統可以在胃腸道內或輕微攪拌(37℃)下自發形成水包油型微乳。目前,將中藥單體及化學結構性質相似的同類化合物制成SEDDS的研究比較成功,如冬凌草素自乳化給藥系統[23]、水飛薊素自乳化給藥系統[24]、連香方自乳化制劑[25]等。其中水飛薊素自微乳在比格犬體內的相對生物利用度為227.2%,較市售水飛薊素膠囊(利肝隆)有顯著的提高[24]。自乳化技術可通過改善給藥系統的粒徑并增加與胃腸道內生物膜的相容性來提高藥物的生物利用度,也可能與該藥物傳遞系統中所用輔料具有一定的促吸收作用有關。納米技術是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一門在0.1~100nm尺度空間內研究電子、原子和分子運動規律和特性的嶄新技術。近年來,納米技術迅速發展,已成為日用化工、食品和制藥等領域的研究前沿,并逐漸向中草藥研究領域滲透。納米技術的應用使藥物的物理空間發生了變化,由此引發了藥物的理化性質、生物學特性發生令人驚訝的變化。納米技術賦予傳統中藥新的生機,其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夠提高生物利用度,增強藥效。目前納米技術應用于口服中藥主要是通過載藥系統來實現,已有的口服納米載藥系統主要有:固體脂質納米粒[26]、納米乳[27]、納米混懸劑、脂質體、納米膠束、納米囊等。納米技術能夠顯著改善中藥活性成分的水溶性及生物利用度,但目前僅有少量中藥單體的研究探索,并且該系統較低的載藥量也給在中藥提取物乃至中藥復方的應用帶來巨大困難。
2.3應用吸收促進劑
對于口服吸收不理想的藥物,常常可在制劑處方中加入能夠促進該藥物胃腸道黏膜吸收的
惰性物質,即吸收促進劑(absorptionenhancer)。常用的腸道黏膜吸收促進劑有以下幾類[28]:生物黏附性高分子聚合物(如殼聚糖、卡波姆)、氨基酸衍生物、膽酸鹽、分泌和轉運抑制劑、酰基肉堿類、中鏈甘油酯、類固醇類物質、脂肪酸及其鹽、表面活性劑等。主要是通過離體腸段法、Caco-2細胞模型法、在體腸灌流法、整體動物實驗模型法進行吸收促進劑對藥物的腸道吸收促進作用的研究[29]。與利用制劑技術提高生物利用度的方法相比,篩選合適的吸收促進劑來提高中藥有效成分的口服吸收更為可行,不僅可應用于中藥單體,也可應用于中藥提取物乃至中藥復方,在改善中藥口服生物利用度的研究方面極具發展潛力。已有學者在中藥活性成分吸收促進劑的研究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Xiong等[30]的研究結果表明,腎上腺素能夠有效地促進人參皂苷Rg1的腸道吸收,人參皂苷Rg1與1mmol/L腎上腺素合用后,人參皂苷Rg1在大鼠體內的AUC增加28.19倍。李亞梅等[31]發現明膠可以加快小鼠對黃連總生物堿的吸收,可使黃連總生物堿在小鼠體內的AUC由(17.6±0.18)(mg·h)/L增加至(31.1±0.53)(mg·h)/L。Ho等[32]發現D-α-生育酚聚乙二醇400琥珀酸能夠顯著提高紫杉醇的口服生物利用度,與市售制劑相比,生物利用度提高了3.1倍。同時,隨著對天然藥物研究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新的吸收促進劑被發現。有研究[33]表明植酸(phyticacid)能夠促進花青素在大鼠和人體的口服吸收;胡慧玲等[34]認為冰片在一定劑量范圍內可促進鹽酸小檗堿在大鼠小腸吸收。
但是,大量研究顯示[29],吸收促進劑在改善細胞通透性的同時可能產生毒性作用。殼聚糖、卡波姆等本身就是藥用輔料,沒有毒性;膽酸鹽及酰基肉堿能夠可逆性調節緊密連接,毒性較低;而表面活性劑類對黏膜的損傷較大。因此,吸收促進劑目前在基礎研究中應用較多,而在產品中應用較少,這也提示我們在運用吸收促進劑改善藥物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同時,應進行吸收促進劑的毒性實驗,為吸收促進劑能夠推廣應用于新藥產品奠定基礎。
2.4基于藥物生物藥劑學特征的給藥系統設計
在中藥給藥系統研究過程中,處方前研究往往較多地考慮中藥活性成分的理化性質,而中藥活性成分的生物藥劑學特征常常被忽視。隨著中藥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制劑工作者深刻體會到充分了解中藥活性成分生物藥劑學特征的重要性。除中藥單體以外的中藥制劑中間體(中藥提取物、中藥復方提取物)成分復雜,雖然目前已能對中間體進行充分的理化性質研究之后再進行制劑成型性研究,或者體外評價也表明能達到預期目的,但由于不清楚中間體的生物藥劑學特征,仍會在體內實驗后發現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
因此,加強中藥多成分生物藥劑學特征研究,是中藥現代化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只有結合中藥活性成分的理化性質和生物藥劑學特征才能合理設計給藥系統,達到提高生物利用度的目的。黃芩苷為黃芩的有效成分之一,但口服黃芩苷吸收較差,生物利用度較低。有研究比較了黃芩素與黃芩苷大鼠體內藥代動力學,結果顯示在等摩爾劑量下,黃芩素比黃芩苷的達峰濃度高、生物利用度高[35]。可能是由于黃芩苷需經微生物水解轉化成黃芩素才能被機體吸收的緣故,因此可考慮使用黃芩素替代黃芩苷以解決黃芩苷吸收難的問題。本課題組長期致力于中藥復方的藥代動力學研究,研究過程中發現某些中藥復方中各類成分在藥代動力學方面具有一定拮抗作用,影響中藥復方整體藥效的發揮[36-38]。在此基礎上,我們設計將各類成分分別提取并制劑成型后,組成新的中藥復方釋藥系統,避免有效成分之間吸收過程的相互干擾,從而提高整體中藥復方的生物利用度。
2.5基于配伍規律的中藥復方制劑處方設計
我國的傳統中藥尤其是中藥復方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逐漸發展起來的。中藥復方講究藥味之間的合理配伍,古人在臨床用藥時積累下來的復方配伍,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當時科技發展水平有限,這些復方配伍規律也有諸多不合理的因素。
因此,需充分了解中藥的復方配伍規律并合理利用這些規律,避免藥味間的拮抗作用,加大協同作用,才能夠研制出更有效的中藥復方制劑,推動傳統中藥走向現代化、國際化。楊祖貽等[39]研究了溫里藥配伍對活血藥赤芍效應成分芍藥苷小鼠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影響。結果顯示,溫里藥胡椒、肉桂、小茴香、吳茱萸、花椒分別與活血藥赤芍配伍,能提高赤芍主要有效成分芍藥苷的生物利用度。提示在中藥復方制劑的研究中可考慮將上述5種溫里藥與赤芍配伍以求達到赤芍活血效應最大化。
此外,有研究表明,將肉桂與當歸配伍[40]后復方中阿魏酸的生物利用度較配伍前提高了2倍以上。這從復方有效成分生物利用度的角度揭示了活血溫里復方配伍的科學內涵,同時也為中藥復方制劑研究提供了生物藥劑學基礎。由于中藥復方成分極其復雜,各成分間總會存在或多或少的相互作用,探索中藥復方的配伍規律只能由簡入繁、循序漸進地進行,同時還需遵循中藥復方配伍規律對中藥復方制劑進行合理處方設計,才能提高中藥復方的生物利用度,充分發揮復方效應成分的藥效。
3展望
綜上,目前改善中藥活性成分生物利用度的方法大多受到載藥量的限制,需依賴加入大量輔料來改善中藥活性成分的理化性質,只適于活性很強的單體成分,不適于中藥提取物及中藥復方,而傳統中藥的發展絕大多數依賴于中藥提取物及中藥復方的發展,因此需在中藥單體生物利用度研究的基礎上,嘗試并加強中藥提取物及中藥復方生物利用度的研究。筆者認為要達到以上目的,目前亟需解決以下幾個關鍵問題。
3.1制劑前中間體
(中藥提取物或中藥復方物質)生物藥劑學分類研究化學藥物有生物藥劑學分類(Ⅳ類),其中有兩類不利于吸收,即生物利用度差。在藥物的生物藥劑學分類研究(主要是溶解性和膜滲透性)基礎上進行口服給藥系統的處方設計,改善其生物利用度,主要是通過改善溶解性和黏膜通透性而達到目的。中藥與化藥有許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即為中藥的研究對象常常為較復雜的混合物而不是純度很高的單體。目前大多數混合物只能以少數指標成分進行定量,還未能將混合物的化學結構、物質基礎完全分析清楚。因此,不能將該理論生搬硬套于提高中藥口服生物利用度的研究中。但是否也能對中藥制劑前中間體進行表觀的生物藥劑學分類研究,對其溶解性和滲透性進行測定和表征,從而根據這種分類快速準確地進行改善中藥活性成分生物利用度的研究?
首先需對中藥提取物、中間體半成品標準化,保證不同廠家、不同批次產品的一致性,如主成分的含量、溶解性等;其次則應選取多個模型藥物進行規律探索,挖掘制劑前中間體的理化性質與體內吸收之間的相關性,尋找解決中藥吸收問題的普遍適應性。我們課題組針對中藥提取物溶解性能的表征方法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分別采用沉淀法、指標成分法和粒徑測定法等不同方法對駱駝蓬總生物堿提取物的溶解性進行了研究[41],為其劑型設計提供了依據。但中藥中間體的生物藥劑學性質和分類研究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工程,需要科研工作者前赴后繼地努力才能得以實現。
3.2中藥制劑生物利用度的評價方法探索
中藥復方制劑中效應成分復雜且有些成分含量甚微,如何通過測定體內有效血藥濃度進行生物利用度評價是亟待解決的一大難題。目前,大多以中藥中的活性成分為指標來代表制劑的生物利用度,但這是否能夠反映中藥制劑整體的生物利用度,或者這是否能被稱作是中藥制劑的生物利用度,均存在疑問。因此,需要進行能夠較為準確的測定中藥制劑生物利用度的研究方法探索,應在化學藥物生物利用度研究現狀的基礎上進行延伸。中藥單體成分可借鑒化藥研究方法,而中藥提取物或復方制劑則需在此基礎上開拓新的道路。其中如何體現中醫理論指導下的中藥制劑的特點,即各個成分綜合作用的整體性特征,是中藥制劑生物利用度方法研究中需解決的關鍵問題。
3.3中藥物質胃腸吸收相互作用機制的探討
化學藥物腸吸收研究認為藥物必須溶解后才能透過生物膜進入機體,中藥物質的腸吸收理論是否類同?眾所周知,中藥成分十分復雜,中藥提取物或中藥復方往往是幾類活性成分同時存在,而每一類中還有許多種成分,除此之外,還存在大量伴生物質,在腸吸收過程中,各種物質的相互作用交錯復雜,不僅存在活性成分之間的相互作用,還有活性成分與伴生物質的相互作用。
因此,在不能夠完全弄清楚效應物質組成的前提下,研究中藥物質腸吸收必須與中藥物質的藥理效應結合起來,盡可能多地同時運用化學指標、生物效應指標等綜合評價吸收過程,從而逐步探索并闡明中藥物質可能不同于化學藥物的腸吸收理論。傳統中藥若在腸吸收理論方面有所突破,必將推動中藥制劑乃至中藥產業的進程。
綜上所述,目前廣大學者在改善中藥制劑口服生物利用度方面進行了探索,并取得一定進展,但還有許多關鍵問題需要突破。相信隨著各學科交叉融合,必定能在解決中藥制劑口服生物利用度問題上獲得突破,推動我國創新中藥的研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