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生物醫學研究環境風險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淺談生物醫學研究環境風險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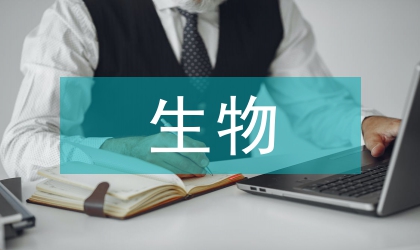
摘要:生物醫學研究的環境風險,因研究與人體密切相關,由醫療器械設備和研究實施過程以及病毒性傳播等導致的環境破壞引起。傳統醫學是以人類為中心的,醫學模式是“生物-心理-社會”模式,醫學研究對象主要是從人的肉體、精神到社會,缺少生態視角。規避相關的環境風險,應秉承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思路,借鑒“生物-心理-社會-生態”模式。具體操作可加入環境風險評估內容;實行環境影響的空間排序機制及時間積累的環境風險評估機制;增強應急環境風險管控;對一定范圍內的環境進行賦價。
關鍵詞:生物醫學研究,環境風險,生態倫理,倫理審查
環境風險一直是生物醫學研究所忽視的一個領域。關于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風險審查,2007年版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中的表述是“對受試者的安全、健康和權益的考慮必須高于對科學和社會利益的考慮,力求使受試者最大程度受益和盡可能避免傷害”。經過幾年的討論之后,2016年進行了重新修訂,對風險的提示已上升到原則范疇,表述為“控制風險原則。首先將受試者人身安全、健康權益放在優先地位,其次才是科學和社會利益,研究風險與受益比例應當合理,力求使受試者盡可能避免傷害;”[1]兩個表述都沒有提及倫理審查中的環境風險。環境風險審查屬于生態倫理范疇。隨著醫學研究與治療深入到分子及基因水平,其所帶來的環境風險日益明顯。醫學研究風險控制的倫理審查有必要增加環境風險控制的生態倫理審查內容。
1生物醫學研究中的環境風險
生物醫學研究中的環境風險,與科學實驗引起的環境風險是異曲同工的。科學研究階段,由于認識的局限,可能帶來環境風險,例如,藥物實驗首先在動物身上進行,實驗進行過程中,病菌可能隨之流散,病毒也可能擴散到自然界中。在科學實驗中,由于涉及的范圍小,實驗環境相對封閉,實驗過程有嚴格的環境風險控制。相對來說,它所帶來的環境風險較小。但即使如此,也可能帶來環境風險。首先是認知上的缺陷,其次是制度缺陷及執行規章制度缺陷等。2004年北京、安徽先后發生非典疫情是由實驗室操作規章制度執行不嚴造成的。具體事由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腹瀉病毒室跨專業從事非典病毒研究,采用未經論證和效果驗證的非典病毒滅活方法,在不符合防護要求的普通實驗室內操作非典感染材料,導致感染源外傳[2]。除此之外,規章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是導致疫情傳播的原因。規章制度原因,首要的是面對科技發展,原有的規章制度不能適應新的實驗要求。即使在嚴格監管條件下,依然存在病源外泄的可能。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中,帶來的環境風險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醫療器械設備所帶來的環境風險,例如,醫療垃圾;另一部分是研究實施過程中,醫療微生物滋生外泄帶來的環境風險。前者是醫療器械設備被拋棄到環境中,當它突破環境承載力時,造成環境污染,由此帶來環境風險。這在一般的環境污染中常見,例如,日本九洲水俁灣工業廢水毒害居民引發水俁病,水俁病即甲基汞中毒,排入海洋中的汞可在海水中引起甲基化,甲基汞在魚體內呈高脂溶性蓄積,人食用此魚可引發甲基汞中毒。醫學實驗中常用的苯類化合物可造成苯的污染,如制作人體組織和病理切片用的二甲苯,若直接倒入下水道中,會污染地下水。還譬如放射性污染,生化實驗、核醫學實驗、法醫親子鑒定等常用同位素進行實驗,同位素具有放射性;醫學實驗用的重金屬也會造成環境的污染[3]。
近代以前,人與環境形成了某種良性互動,環境對人的行為有包容作用,人類小范圍內活動對環境的破壞,不會造成大的問題,環境有自我凈化和恢復功能。當人類對大自然的工具提煉以及返還,超出了自然界的自凈和恢復能力之后,就會形成環境風險。一是人們不能再根據原有的方式從自然界得到生活所需的東西,二是環境會形成報復,有害物質在自然界中循環,最終侵入人體,造成傷害。隨著醫療工具深入到基因、分子水平,在生物醫學研究中,會形成另一種環境風險,即一種活性污染,如醫療微生物污染。這種污染與傳統醫療廢棄物污染不同,一是它產生于藥物與人體接觸過程中。傳統實驗工具與人體只是一種剛性接觸,它對自然界的污染來自它本身。正因為如此,防范它的環境風險相對來說,要容易得多。因為對于工具的性質及特征早已有足夠的了解。二是它在自然界以一種病毒性方式傳播。病毒性傳播與醫療工具所產生的累積性傳播不同,它借助于別的人體進行傳播,并且是一種擴散性傳播,在傳播過程中不斷造成傷害,擴散性傳播危害以指數方式增加。隨著生物治療的深入,病毒性污染對環境造成的風險不斷加大。例如,現在越來越廣泛地利用生物活性治療腫瘤的研究[4],一旦試驗或治療過程把關不嚴,這些病毒性治療物質可能擴散到環境中,造成環境危害。從環境自身角度,生物醫學研究的環境風險的不可預知性在逐步增加。隨著人類醫學研究走向微觀化、分子化,環境內在的組織作用機理越來越復雜。當人類只是出于自身利益,不斷加深對自然的開發利用,它所帶來的后果愈加不可預知。環境風險的產生機制有三種,一是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由于開發新工具,破壞了自然固有的平衡機制,導致自然界產生報復,或者說一種新的不利于人類活動的作用方式。二是對人工環境的破壞。人類逐步加深對自然的利用,就人類活動范圍而言,人工自然所占比重越來越高。生物醫學研究所涉及的環境破壞,包括破壞人工自然,這種破壞往往產生連鎖反應,人工自然構建是一環緊扣一環。三是對人的機理的破壞。人的機理構成人生活環境的另一部分,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出發點是醫治疾病,但在醫治過程中,可能產生一種破壞人的機理的病毒傳播,形成人與人之間交往環境的破壞。
2生態倫理視角的環境風險
環境污染以及環境風險的本質源于人對環境的工具式利用。近代以來,隨著工業社會的來臨,人類對自然和環境的利用方式發生了根本改變。不再是小打小鬧式的利用環境,而是利用現代科學不斷征服自然。對自然的利用已遠遠超出了自然自身修復范圍。環境不斷遭到破壞,各種污染接踵而至,對人的危害也越來越大。人們逐漸認識到,環境自身存在一定的價值。在沒有認識到環境價值之前,人類每向前邁進一步,都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對大自然的利用,只能在它允許的范圍內進行。反過來,生態環境保護具有重要的生命倫理向度[5]。在生物醫學研究中對環境風險的忽視,與傳統忽視環境保護是一以貫之的。因為是對人的醫學研究,它的工具性愈加突出。只要是有利于治療人的疾病的,都可以被拿來利用。只要是有利于解除人的痛苦的,利用起來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環境的危害卻是與日俱增,環境風險是確實存在的。不同的生態倫理視野中,對環境的保護要求不同。總體而言,生態倫理有兩種,一種是人類中心主義,另一種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瑪什和平肖則持有人類中心主義生態觀,他們認為,自然資源、生態環境需要保護,但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人的利益,自然界的權利是因為人而存在的,沒有脫離人的自然權利一說。后來的諾頓和默迪發展了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觀,諾頓將人類中心主義分為兩種,強人類中心主義和弱人類中心主義。前者從感性角度對待自然,后者從理性角度對待自然,前者將自然看作人類的伙伴,后者將自然看作人類工具。諾頓主張弱人類中心主義。默迪認為,自然界不但具有工具價值,而且具有內在價值。某種程度上,這是向非人類中心主義過渡。然而,他強調自然界的內在價值也需要通過人的價值來衡量[6]。辛格認為,動物和人一樣,也有感受快樂和痛苦的能力,整個自然界也一樣,它們有內在價值,可以用來衡量人類的所作所為。當人類的作為違反了它們的內在價值時,就會受到自然的報復。泰勒認為,任何生物都有保持自身的趨向,這是它們內在價值的體現。當人類在利用自然時,不但只關心自己的需要,還要關心自然的需要。羅爾斯頓發展了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他認為自然界既具有工具價值,又具有內在價值,但歸根結底,自然的價值需要依靠內在價值來衡量[7]。從不同的環境倫理視角,對于生物醫學研究的環境風險有不同的度量,從而導致不同的風險來源。人類中心主義環境風險審查主要從環境變化對醫療工具的影響出發,有兩種度量,一種是強人類中心主義。在生物醫學研究中,環境域值考量看它對現有使用工具的影響程度,這些工具不僅包括醫療工具,還包括與此相關的其他工具,所有這些工具都影響到人類活動。強人類中心主義只從影響人類活動角度看生物醫學研究有沒有對環境造成影響。由此導致的環境風險主要是醫療工具設計及實施過程中完全屏蔽掉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環境負面影響總是難以避免的。另一種是弱人類中心主義。強調環境的內在價值,但這種內在價值以是否影響人類活動來衡量并需要通過理性思考獲得。與強人類中心主義不同,弱人類中心主義認為,環境自身沒有內在價值,環境是否遭到破壞,以有沒有破壞現有的工具活動能力來衡量。現有的工具活動能力具有科學評價標準,環境是否破壞也要以這個標準衡量。弱人類中心主義試圖找出現有工具活動之外的環境評價標準,它既以人類為中心,也不同于現有的工具活動評價標準。從生物醫學研究看,弱人類中心主義環境風險來源是在工具設計及實施過程中,只考察一定范圍內的環境影響,而不是從環境內在價值角度,從更大范圍內考察工具對環境的影響。生物醫學研究弱人類中心主義,在工具設計及實施中,并不從漸進角度去評估研究工具的環境風險。弱人類中心主義只關注特定領域的環境風險,這些領域歸根到底涉及到人的現有活動。非人類中心主義有另一套對環境風險的評價,它確定環境有其內在價值,并且,它的內在價值來源于環境本身,而不是人類活動。既然環境的內在價值來源于本身,首先就要確定環境內在穩定范圍,在此基礎上評價人類活動。環境內在穩定范圍是在現有的環境保護基礎上形成的,將人類活動影響限制在一定的環境可承受范圍內,是防范環境風險的有效舉措。從這個角度看,對于生物醫學研究的環境風險評價,就不是以人類活動為評價標準,而是從環境自身標準來評價人類活動。無論是醫學研究工具,還是醫學研究活動,都是如此。
3生物醫學研究的環境風險審查
人類對環境的傷害,并不與它是否觸及到人的利益有關,它只與是否超出自然內在承受力有關。生物醫學研究從更細的尺度去尋找治愈疾病的方法,必然更深層地改變自然,它所帶來的對環境的破壞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將它限定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才可避免由此帶來的環境風險。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風險視角存在巨大的缺陷。一是會引發由時間積累帶來的風險。人類中心主義視角看到的是環境風險中的人工環境的改變所帶來的,這種改變并不能反映環境改變的內在機理。在人工環境沒有發生改變的情況下,自然環境可能正發生深刻改變。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改變逐漸不可逆,它所帶來的危害將是巨大的。二是引發環境風險治理困境。環境風險以人工環境的改變來度量,它并不反映環境風險真正成因。當環境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時,風險治理變得急迫,但并不能找出真正風險的成因,導致環境風險治理困境。或者重新尋找風險成因,或者以人類中心主義視角尋找成因,不管哪一種,都會使風險積累越來越大,風險所造成的危害也越來越大。非人類中心主義環境保護,并不是要改變現有的生物醫學研究行為,回到原始狀態,也不是暫停對環境的利用,只在現有的條件下加深對生物醫學的研究。非人類中心主義環境保護視角只是對生物醫療的范圍、步驟及進度有更嚴格的要求。相比于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保護,它首先要確定環境的內在價值,以環境的內在穩定作為環境風險的衡量標準。對生物醫學研究而言,環境風險評估要以對環境改變的限度為條件,而不是控制的嚴不嚴格,或者它對現有的環境破壞程度為條件。現有的生態醫學模式反映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風險觀。傳統醫學是以人類為中心的,醫學模式是“生物-心理-社會”模式,醫學研究對象主要是從人的肉體、精神到社會,缺少生態視角,而人又是生活在整個生態環境之中的。隨著像非典等疾病的流行,傳統醫學模式面臨挑戰,生態醫學模式應運而生,醫學研究對象不僅包括人的肉體、精神和社會,還包括生態環境,它的模式是“生物-心理-社會-生態”模式[8]。2003年,隨著非典的全面爆發,劉典恩等[9]提出了生態醫學模式是后非典時代的必然選擇的觀點。
規避生物醫學研究過程中的技術和設計帶來的環境風險,需要嚴格的環境及人體變化評估,并做出生態倫理審查[10]。首先,在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的風險評估中,要加入環境風險評估內容。相應地,程序上要有環境保護專家介入環境保護評估,由他們組成生態倫理委員會。盡管當前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整體上倫理審查不令人滿意,但在認識上以及相關文件上,要有涉及環境風險的內容。只有認識到位,制度跟進,具體操作上才可能有保障。其次,對環境風險審查,要有環境影響的空間排序機制。在生物醫學研究中,有兩種空間排序,一種是以實驗室為中心,逐漸向外圍擴展的空間排序。生物醫學研究的環境風險,往往首先來自實驗室,由此不斷向外圍擴散。二是以人為中心,隨著人的活動不斷向外圍擴散。在防范環境風險時,需要嚴格根據空間排序進行審查。以實驗室為中心,逐漸向外進行環境風險排查。排查過程中,需要進行嚴格的風險評估。與此同時,對由人的活動引起的環境風險進行排查。第三,要有時間積累的環境風險評估機制。在生物醫學研究中,環境風險不僅由空間風險引發,也可由時間積累形成的風險引發。時間積累風險,需要通過一定時間段的檢測清除。這要求相關實驗有一定的時間封存測試,這種封存測試并不隨著實驗效果的有效性而改變,也不隨著人的需要的緊迫性而改變。很多時候,對環境風險的封存測試,緊迫性強于人在生物醫學研究中需要的緊迫性。第四,要有應急環境風險管控。我國的環境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和環境保護單行法中,對于突發性污染事件的應急措施制度分別有相應的規定。但在具體部門、具體領域則缺乏相應的操作規范。在生物醫學研究中,要完備相關法律體系,設立統一應急處理緊急事務的機關。突發環境風險事件發生時,由相關機構統一指導突發性事件的應急處理。在處理突發環境風險事務時,需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共同應對環境風險。第五,要對一定范圍內的環境進行賦價,引入相關的經濟學研究,以價格杠桿評估生物研究對環境的影響。有人會覺得,對環境賦價意味著從人的視角出發去保護環境。實際上,是先有一定環境保護,然后才有環境賦價。賦價進一步促進環境保護。在賦價之前,環境是不值錢的。賦價之后,它的內在價值得以凸顯出來,價格只是其內在價值的外在表征。環境賦價并不影響生態倫理專家參與生物醫學研究環境風險評估,科學的賦價可以使生態倫理評估更可靠,也更有可操作性。
參考文獻
[1]海南醫學院.規范生物醫學研究維護人的權益尊嚴:《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學習培訓班在海口舉辦[J].醫學與法學,2016,8(6):86.
[2]曲萍,劉利兵,陳健康,等.關于高等醫學院校實驗室生物安全的思考[J].山西醫科大學學報,2009(1):84-86.
[3]王濤.醫學實驗廢棄物污染環境引發的思考[J].遼寧經濟,2004(5):109.
[4]趙哲夫,吳小濤,王運濤.病毒載體介導的椎間盤退變生物治療的最新進展[J].東南大學學報,2013(1):340-343.
[5]滕永直.生態與環境保護:生命倫理的重要研究向度[J].醫學與哲學,2014,35(9A):36-38.
[7]徐雅芬.西方生態倫理學研究的回溯與展望[J].國外社會科學,2009(3):4-11.
[8]陳俊.醫學倫理的生態化趨勢與生態醫學倫理的建立[J].經濟研究導刊,2012,27:246-247.
[9]劉典恩,楊瑞貞.生態醫學模式:后SARS時代的選擇[J].醫學與哲學,2003,24(11):27-29.
[10]商自申,封展旗,王忠謀.試論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中的風險與收益評估[J].中國醫學倫理學,2007,20(3):47-48.
作者:肖健 鄧線平 單位:南方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擴展閱讀
- 1淺談藝術與營銷
- 2淺談生態文明
- 3淺談李忠的忠厚
- 4淺談醫院文化內涵提升
- 5淺談草原鼠蟲害防治
- 6淺談體育旅游
- 7淺談文化的生態功能
- 8淺談反腐倡廉思想
- 9淺談民俗文化復興
- 10多芬為例淺談廣告營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