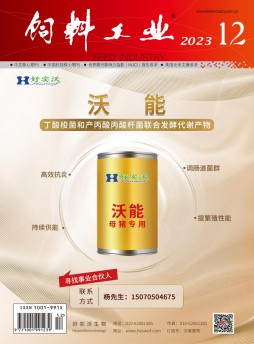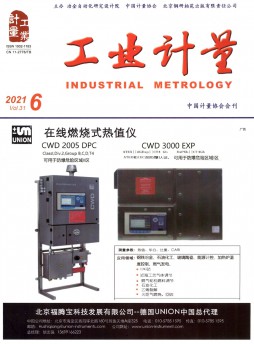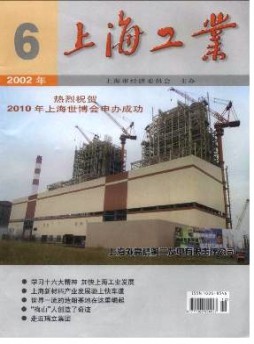工業發展的勞動力要素分析及建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工業發展的勞動力要素分析及建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低成本就業優勢的中國傳統勞動力紅利優勢并未枯竭
另一方面,人口紅利階段,尤其是農村存在大量富余勞動力的情況下,勞動力供應充足,勞動市場的競爭使得工資的上升幅度較慢。人口紅利見頂回落,農村富余勞動力大幅減少之后,勞動力供應趨緊,工資增長速度相對于其他價格加快。從我國實際情況看,勞動力成本的發展態勢也大致符合這一規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長期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制造業雇員工資水平大約是英國的1/27,日本的1/22,美國的1/21。與新興國家相比,大約是韓國的1/13,新加坡的1/12。與發展中國家相比,大約是馬來西亞的1/4,墨西哥的1/3。步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平均工資不斷上升。過去幾年工資漲幅明顯,年薪從2006年的20856元人民幣升至2011年的41799元人民幣。但即使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具有低成本就業優勢的中國傳統勞動力紅利優勢并未枯竭。雖然過去五六年平均工資水平迅速攀升,但仍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1年中國的平均工資僅為41799人民幣或6568美元;而美國平均工資為52607美元,是中國的八倍多。同時,研究產業競爭力,除勞動力成本之外,還要考慮勞動生產率。從勞動生產率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從1980年的0.30萬元/人提升至2011年的14.64萬元/人。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處于平緩發展時期,相當于美國當年勞動生產率的6%左右,1990年后,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表現大幅度增長趨勢,并且與歐美發達國家的差距在不斷縮小。此外,通過計算單位勞動成本(ULC)可以反映一個產業或國家的成本優勢,我們有必要將工業的人年均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結合起來,從單位勞動成本(人年均勞動報酬/勞動生產率)角度來反映我國工業的成本比較優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單位勞動成本大致在0.2—0.3的范圍區間內上下波動,1980年為0.26,曾向上到1986、1987年的相對高點0.30,又逐步回落到1998年的相對低點0.20,再不斷攀升至2009年、2010年、2011年的相對高位,分別為0.29、0.28和0.29。但總體而言,基于我國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升,工資水平的提高并不會成為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內妨礙我國工業競爭比較優勢的重要原因。在剔除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勞動力工資水平的影響后,我國勞動力工資水平相對于發達貿易伙伴國而言處于一個更低的水平。因此,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工業客觀上還存在著逐步提高工人勞動報酬的可能空間。
二、困境分析:面臨“招工難”與“就業難”的兩難局面
(一)面臨“招工難”、“用工荒”的困境一方面,通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的變化趨勢,我們認為,未來幾年,我國的勞動供求關系將發生根本性變化。盡管目前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仍在增長,但每年的增加量正在減少,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速正在逐步下降。預計到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停止增長并隨后轉為負增長,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就此消失。這個人口轉變是伴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必然發生的,是不可以逆轉的,甚至不能指望以生育政策的調整來改變它。可以說,2004年以來,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時常出現的“招工難”“、用工荒”的現象正是這一變化趨勢的初步體現。許多嚴肅的證據都表明,在大規模進行部門轉移和區域流動之后,農業中剩余勞動力的數量和比例,已經迥然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2004年以來“民工荒”現象反復在全國范圍出現,普通勞動者工資的持續上漲,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證據愈益充分。而“劉易斯轉折點”只是意味著工資不變而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結束了,但不意味著資源重新配置過程的結束。畢竟,與相同發展階段國家相比,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至少還高出10個百分點。并且,隨著戶籍制度改革深入、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在農業和非農產業之間重新配置勞動力的效率仍有潛力。
(二)面臨“就業難”的困境另一方面,在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際,本應意味著勞動力市場供求的總量趨于平衡,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卻越來越困難。智聯招聘的“2013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形勢報告”稱,上海平均每101人競爭一個崗位,而去年為69人;這一數字在北京為96人,廣州為115人,深圳為109人,蘇州為102人。這種趨勢會在未來幾年內持續甚至有所加劇,從而導致中國城鎮失業率的上升。同時,2013年,據調查顯示,1/3的企業稱很難找到高技能員工,61%的企業將此歸因于應屆畢業生缺乏基本的職場技能。而根據麥肯錫的最新研究結果,2020年,中國將需要2400萬受過高等教育和先進技術教育的高技能勞動力。應該說“,招工難”與“就業難”的“兩難”局面,表明我國勞動力人口的需求和供給出現了嚴重錯位的局面。具體體現為產業結構與人才結構出現整體性錯位,大學生就業市場,供需雙方出現意愿性錯位,互聯網環境下成長的90后夢想與現實之間的錯位,經濟疲軟帶來更多急功近利、企業更愿意使用有經驗人士等層面。我們認為,造成這一“兩難”局面的核心關鍵可能在于,“第一次人口紅利”的逐步消逝以及“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有待發掘。我們最應該避免的,是不顧所有人的警告,仍然生活在“中國人口太多”的心態里,錯過了為“人口負利”時代到來做好準備的最后機會。
三、政策建議:提高勞動力教育水平和加強職業培訓等措施以提高單位勞動力的生產率
因人口年輕構成的“第一人口紅利”正在快速枯竭的同時,未來我們可能需要大力挖掘第二人口紅利的潛能,即“質”的紅利,主要是指教育和健康等賦予勞動力的價值。理論和經驗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體改善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某種程度上,第二人口紅利的潛力可以說是無限的。從受教育程度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顯上升,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96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近9。而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與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為38788人;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為26779人。文盲率(15歲及以上不識字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個百分點。我們可以利用新的人口結構特征,在老齡化條件下,創造新的制度環境,挖掘經濟增長長期可持續源泉。包括建立有利于資金積累的養老保障制度,以彌補儲蓄率的降低;加強培訓和教育,提高人力資本以適應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發育和完善勞動力市場,消除勞動力供給制度障礙。鑒于勞動人口占比的下降以及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生產要素如果不能持續升級和專業化,它對競爭優勢的價值就會越來越低這一原理;對我國工業部門而言,通過提高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和加強職業培訓等措施以提高單位勞動力的生產率更為緊迫。就我國工業領域的勞動生產率而言,當前以“農民工”為主的工人隊伍由于缺乏必要的職業技術教育,勞動生產率不高。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字,中國高素質的勞動力僅有4%。只有36%的工人具備初中學歷,其余60%缺乏或不掌握任何技能。
四、結語
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目前在世界上仍處于落后地位,增長空間較大,勞動生產率對于抵償勞動力成本增長的負面效應起到了關鍵作用。根據有關資料,1970—1985年,韓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速度高達8.5%,1986—1988年,韓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分別達到12.7%、11%和7.1%。工人勞動報酬的提高,在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不僅不會削弱我國制造業現有的國際競爭力優勢,甚至會強化這種既有優勢,即通過降低單位勞動力成本來提高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國際競爭優勢。因此,提升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也意味著勞動力對工業產出的影響從成本、數量優勢向素質優勢的轉變。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預測未來所需技能,努力使對技能的供給與需求匹配,幫助勞動者適應變化。(本文來自于《中國經貿導刊》雜志。《中國經貿導刊》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張嵎喆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所
- 上一篇:環境綜合管理工作實施意見范文
- 下一篇:村鎮土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