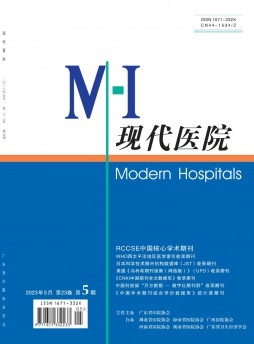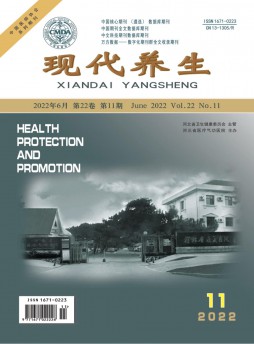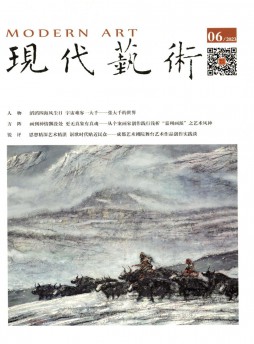現代國家形成理論的演進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現代國家形成理論的演進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教學與研究雜志》2015年第八期
作為政治現代化的一個方面,現代國家(modernstate)是人類的政治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形成的組織形式。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前出現或者與之同時并存的政治組織形式還包括部落、城邦、城市聯盟、帝國、封建主義和神權政體等。馬克斯•韋伯(MaxWeber)最早揭示了現代國家與其他政治組織形式相比的獨特性。在韋伯看來,“正如自中世紀以來所謂的邁向資本主義的進步是經濟現代化唯一的尺度一樣,邁向科層制的官員制度的進步同樣是國家現代化明白無誤的尺度。”因此,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也就是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隨著國家主義在20世紀70—80年代后的興起,社會科學家已經系統地考察了現代國家的形成問題并且發展了一系列解釋模型。從現代國家形成理論的演進軌跡上看,盡管早期的模型大多依賴于歐洲的經驗,但后期的模型越來越多地將歐洲之外地區的經驗納入進來。本文旨在回顧和評析這些理論模型,重點在于揭示這些模型的因果邏輯并比較這些模型的經驗對應性。
一、現代國家形成的理論模型:基于歐洲的經驗
韋伯指出:“國家是在一定區域的人類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在本區域之內要求(卓有成效的)自己壟斷合法的有形的暴力。”作為理性化權威的載體,現代國家正是“那種借助科層制的行政管理班子進行的統治。”由于韋伯對現代國家的這一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8—19世紀的歐洲國家為藍本的,也由于在歐洲之外的其他地區的國家建設也大多是以歐洲的國家建設為藍本的,社會科學家對現代國家形成的理論探討主要依賴于歐洲的歷史經驗。正是基于歐洲國家形成的歷史經驗,社會科學家已經發展了以下的理論模型來解釋現代國家形成的因果機制。
(一)功能主義模型在現代社會科學中最早系統考察現代國家起源的學者是美國歷史學家約瑟夫•斯特雷耶(JosephR.Stray-er)。斯特雷耶認為,歐洲人所締造的現代國家被證明比其他的政治組織形式更為成功。古代世界的兩種主要政治組織形式———帝國和城邦都是不完美的。帝國在軍事上是強大的,但由于多數居民對國家缺乏忠誠,帝國往往走向分裂和瓦解。城邦的優勢在于市民對國家的忠誠,但由于無法解決吸收新領土或新居民的問題,城邦在軍事上的弱小使其要么成為一個帝國的附庸,要么遲早成為征服者的犧牲品。而1100年之后形成的歐洲國家結合了帝國和城邦的力量。“它們足夠大并足夠有力量,以獲得生存的巨大機會。而且它們成功地使很大一部分居民參與到或至少是關注政治活動過程,并成功地在地方團體里建立了共同身份的理念。”這樣,斯特雷耶從現代國家比其他政治組織形式更能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視角來解釋國家的起源,其理論視角主要是功能主義的。由于第一批現代國家是在英國和法國形成的,斯特雷耶主要討論了司法制度、財政制度以及行政管理等現代國家制度在英國和法國的成長。在1100年左右,英國和法國的國王仍然是相當弱小的統治者。面對著內部和外部的和平擾亂者,兩個國家的統治者努力建立提高內部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可以為抵抗外部侵略者襲擊提供必要資金的財政制度。隨著皇家法庭和財政部的建立,英國和法國在12—13世紀已經出現了構成現代國家的基本元素。盡管14—15世紀的瘟疫與戰爭阻礙了國家建設的進程,1450年以后隨著壓力的緩解,西歐各國的君主把時間、金錢和精力投入到現代國家建設中。“到1700年,西歐國家已經發展形成了它自己獨特的政治模式,這種模式決定了今天普遍實行的國家結構。”這樣,歐洲出現了第一批現代國家。
(二)經濟交易模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為現代國家的形成提供了一種經濟學解釋。基于對傳統經濟史研究的不滿,諾思與托馬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試圖運用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保持一致的分析框架來考察和解釋西方世界的興起。在他們看來,在經濟上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西歐的發展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這樣,現代民族國家作為一項制度創新進入到了諾斯和托馬斯的視野中。與斯特雷耶不同的是,諾思和托馬斯認為現代國家形成的關鍵時期是14—15世紀。在這一時期的瘟疫、饑荒與戰爭引起了歐洲人口大幅度和長時間的下降,從而導致了要素的相對價格的變化。由于地租相對于勞動價值的下降,嚴重依賴地租的封建收入也相對下降;由于勞動價值相對地租的上升,軍隊費用大幅度上升,政府支出的最低必需水平也相對提高。正如他們指出的:“對民族國家的發展最有影響的參數變化是因地租下降而引起的封建稅收減少和政府存在所必須的支出水平的相對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國王和大領主不得不采取各種途徑來增加歲入。一種途徑是通過對外征服、設立常備軍和基于聯姻的吞并來擴大其影響和控制的地理范圍,另一種途徑是通過新稅收、借債和特權所得來尋找新的歲入來源。隨著這兩個方面的發展,現代國家在英國、法國、西班牙和尼德蘭逐漸形成了。在后來出版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諾思更明確地提出了一個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國家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國家為獲得收入,以一組服務———保護與公正作為交換。國家試圖像一個帶有歧視性的壟斷者那樣活動,為使國家收入最大化,它將被統治者分為各個集團,并為每一個集團設計產權。由于總是存在著能提供同樣服務的潛在競爭對手,國家受制于被統治者的機會成本。統治者壟斷權力的程度是各個不同被統治者集團替代度的函數。簡而言之,政治組織在諾思的視角下被看作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契約。由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對談判力量的變化,兩者之間的契約形式并非固定不變。隨著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提供公共物品的政治單位的數量減少而規模提高,從而導致了現代國家在歐洲對封建主義的替代。
(三)戰爭驅動模型作為對組織化暴力的大規模運用,戰爭與現代國家之間的聯系顯而易見,但對這種聯系的社會科學探索還是在20世紀70—80年代以后才展開的。比如,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McNeil)在《競逐富強》中詳盡探討了公元1000年以來武器和軍事技術的發展。火藥、火槍、火炮以及其他技術的創新不僅對戰爭的組織模式,而且對國家財政和公共生活都產生了顯著的影響。12世紀,隨著步兵部隊的興起,騎士的優勢開始衰退。14世紀,城市民兵讓位于雇傭的職業軍人。15世紀上半期,對常備軍進行政治管理的模式迅速發展起來。到17世紀中葉,在法國、英國等國一方面建立了稅金收入與陸海軍費用之間的穩定聯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從君主到最低級軍士的一系列明確的命令。18和19世紀以后,歐洲君主們更卓有成效地使有組織的暴力官僚主義化,從而最終形成了現代國家。正如麥克尼爾所指出的:“歐洲開始進行不斷自我強化的循環,在循環過程中,其軍事組織支持了經濟和政治的擴張,它本身也受到了經濟和政治擴張的支持,而這一切都是靠犧牲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利益得來的。”作為一名歷史學家,麥克尼爾敏銳地抓住了戰爭對歐洲國家形成的意義,但他的研究在理論抽象上顯得不足。作為歷史社會學的主要奠基人,查爾斯•蒂利(CharlesTilly)則兼具對歷史的敏感性和對理論邏輯的把握能力,從而最為系統地發展了國家形成的戰爭驅動模型。在《回歸國家》中,蒂利明確提出了“戰爭締造國家、國家發動戰爭”的命題。在《強制、資本與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一書中,蒂利對這一命題進行了更為系統的理論闡釋和史實證明。蒂利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為什么歐洲國家經歷了如此多樣的道路,卻殊途同歸到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上?為回答這個問題,蒂利提供了一個抽象的理論模型。首先,控制著集中的強制資源的人試圖使用這些資源來擴大對其運用權力的人口和資源的范圍。當他們沒有遇到相當的也掌握強制的對手時,他們就對領土上的人群成功地實施了穩定的控制,并且有權常規利用在這領土上產出的部分商品和服務,從而成了統治者。當他們遇到真正的對手,他們就不得不進行戰爭。戰爭和準備戰爭使統治者從那些擁有必要資源的其他人或者那些如沒有強大的壓力或補償就不愿投降的人處榨取戰爭的資源。在其他國家的要求和回報所確定的范圍內,對戰爭資源的榨取和爭奪就產生了國家的中央組織機構。990年到1992年這一千年間歐洲歷史充分表明,“戰爭編織起歐洲民族國家之網,而準備戰爭則在國家內部締造出國家的內部結構。”這樣,戰爭推動了現代國家的形成。蒂利所考察的歐洲歷史上的戰爭主要是在歐洲國家之間發生的。作為蒂利的學生,維克多•李•伯克(Vic-torLeeBurke)也認同戰爭對歐洲國家形成的影響,但他卻強調了歐洲之外的其他文明在歐洲的國家形成中所發揮的作用。在伯克看來:“僅僅局限于一種特定的政治體系中,是無法對一個社會做出解釋的。在一個各種文明相互競爭、對抗的境況中,其他的世界體系可能會阻斷某個社會的發展。”伯克由此提出了一個“文明斗爭模型”,其核心觀念在于歐洲國家的起源是諸多偉大文明之間沖突碰撞的產物。各種文明間的沖突,涵蓋了歐洲與拜占庭、阿拉伯、維京、蒙古、奧斯曼乃至印第安等諸種文明之間所發生的各類戰爭。由于各種暴力手段向內部的轉化,這些戰爭開創了歐洲從封建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可以說,這種文明斗爭模型是戰爭驅動模型的一個變體。正如伯克坦言的:“本人的研究,為蒂利—吉登斯的戰爭事務與國家建設有著密切關聯的原理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
二、現代國家形成的理論模型:來自歐洲之外地區的經驗
在歷史學家、經濟史學家、歷史社會學家以及政治學家的共同努力下,現代社會科學中已經發展了各種關于國家形成的理論模型。不同于社會契約論等政治哲學中的國家起源理論,這些聚焦于現代國家形成的社會科學理論具有明確具體的經驗基礎。盡管這些理論強調了國家形成中的不同因素,但它們的經驗基礎都是一樣的,即現代國家在歐洲形成的歷史經驗。隨著比較政治研究的進一步發展,一些學者開始將歐洲以外地區的歷史經驗納入到國家形成的理論探討中。
(一)精英沖突模型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Lachmann)對國家形成的經濟交易模型和戰爭驅動模型都感到不滿,認為這些模型并不能展現權力擁有者之間的真實權力關系,以及他們是如何統治大眾的,也無法分辨國家形成的多岐過程以及或然性。拉克曼主張從精英關系的結構來分析國家形成問題。某一類精英攫取利益的能力取決于精英關系的結構,因此精英的力量隨著精英關系結構的改變而改變。精英制度往往集中了經濟、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權力,用來對抗敵對的精英和被剝削的非精英。長期以來,國家都是不同精英爭奪資源和權力的場域。拉克曼認為:“任何國家的形成都不是加強統治者權力的單一過程,而是諸多精英進入國家,企圖在和其他精英和農民的斗爭中取得優勢從而產生的計劃外副產品。”因此,國家是精英斗爭的產物。為了驗證上述觀點,拉克曼不僅分析了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的形成,而且分析了處于歐洲邊緣地帶的俄國和歐洲之外的日本國家形成。比如,日本國家形成的關鍵時期是豐臣秀吉統治的16世紀后半期。在這一時期,武士被幕府將軍和大名所馴服,而幕府和大名在朝廷內部展開了對職位和收入的爭奪,精英斗爭由此轉移到了國家內部。這種斗爭在明治維新時期達到了高潮,將軍和許多大名失去了權力,由于此時可能挑戰或反對改革的武士等精英都已經進入國家,明治政府在幾乎不受阻礙的情況下廢除封建領地和建立國家軍隊。這樣,拉克曼運用精英斗爭理論解釋了日本現代國家的形成。同樣基于精英沖突的視角,戴維•瓦爾德納(DavidWaldner)探討了歐洲以外地區國家建設的路徑分歧問題。瓦爾德納注意到,非歐洲地區的國家建設具有兩種不同的路徑,一種是吸納平民發生在國家由間接統治向直接統治轉型后,另一種是吸納平民與這一轉型大致同時發生。前者以韓國為代表,而后者存在于大多數后殖民地區,比如敘利亞和土耳其。瓦爾德納提出的假說是:精英沖突的強度決定了國家轉型的發生是否同時或先于吸納平民。在韓國,精英相對具有凝聚力,因而能夠達成互相的妥協,從而排除了動員平民的激勵因素。因此,韓國的國家建設更多的是圍繞著經濟發展的長期需求而非政治鞏固的緊迫需要展開的。在敘利亞和土耳其,緊張的沖突使精英階層陷入分裂,并無法相互妥協。這樣,只有國家的精英把平民動員起來作為消滅政治對手和鞏固自身統治的社會基礎時,精英間的沖突才得以解決。這樣,瓦爾德納通過在微觀層次上政治精英的選擇解釋了國家建設不同模式這一宏觀的結構性結果。
(二)世界政治的動態模型許田波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視角重新審視了國家形成的動力問題。霸權和均勢是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一對核心范疇。霸權反映了國際政治中的支配邏輯,而均勢則反映了國際政治中的制衡邏輯。許田波提出國際政治中的支配邏輯和制衡邏輯同樣可以分析國內政治和國家形成。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支配邏輯反映在國家強制性機構的發展及其對社會行為體強制能力的提高,而國家形成過程中的制衡邏輯則反映為統治者由于社會反抗和行政成本上升而與社會行為體的權力共享。作為蒂利的學生,許田波在其理論中強調了戰爭的作用。但是戰爭既可以導致支配邏輯的出現,也會導致制衡邏輯的出現。許田波提出,兩種邏輯中的哪一種占據上風將主要取決于國家能否進行成功的自強型改革。自強型改革包括三個關鍵要素:通過征兵建立國民常備軍;征收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及提高生產力;以賢能政治代替貴族政治。這三個要素通過以下方式強化了國內政治中的支配邏輯。首先,常備軍有助于國內鎮壓,暴力手段的壟斷使徒手反抗歸于無效;其次,更多的資源可用于國內壓制,更廣泛的稅基提高了統治者在制定政策時的自由度;再次,行政機構的科層化有助于監視社會和預防反抗。如果統治者無法在爭霸斗爭中通過自強型改革來增強國家實力,他們就不得不采取自弱型權宜措施來制衡其他爭霸國。自弱型權宜措施包括以下三個關鍵要素:通過軍事企業家和雇傭軍建立國民常備軍;通過包稅人來征收正稅并通過貸款和信用來獲得額外收入;向私人資本持有者出售公職。這些自弱型權宜措施使中央權威遭到了中間權力持有者的侵蝕,限制了國家實力的增長。通過這個“世界政治的動態理論”,許田波比較了中國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的戰爭對國家形成的不同影響。由于春秋戰國時期也有制衡邏輯,近代早期歐洲也有國家試圖爭霸,因此支配邏輯的相對強弱是理解近代早期歐洲未能走向統一而春秋戰國卻完成了這一任務的關鍵。歐洲體系的運作結果當然可歸因于制衡邏輯,但制衡邏輯能生效只是因為支配邏輯的效用更弱。這樣,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爭霸國采取的“自強型改革”與近代早期歐洲爭霸國采取的“自弱型權宜措施”就成為兩種不同發展軌跡的主要原因。
(三)政治發展的時間序列模型現代國家只是政治制度的一個要素。如果從政治發展的更宏大視野看,法治、民主等政治制度也在政治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以比較歷史分析的視角考察了從史前時期到法國大革命時期三種政治制度,即國家、法治與負責制政府的起源與演化。福山強調,這三種制度中已存在一種,并不意味著另外兩種也會出現。比如印度具備了法治和選舉民主,但一直缺乏強大的國家。福山在多學科的視野下分辨了不同政治制度的起源。國家往往是戰爭締造的產物,而法治的神圣不可侵犯在歷史上來自法律的宗教起源,而民主往往與貴族、士紳和第三等級等封建勢力的強弱有關。那么,為什么某些政治制度(或者政治制度的組合)出現在某地,而不在其他地區呢?在福山看來,導致這些政治制度發展差異的原因,在于這些外生因素在該地區出現的先后順序。比如在歐洲,植根于基督教的法治在現代國家出現前就已經存在了千年,而負責制政府的興起則可歸因于新生的現代國家無法完全擊敗議會、三級會議等舊的封建機構。印度在歷史上沒有像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或者近代早期的歐洲經歷過漫長的激烈的戰爭,因此無法開發出現代非人格化的國家,但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就已成熟的婆羅門教卻創造了限制國家權力的法治。正如《摩奴法典》所反映的,法律在印度的傳統中并非來自統治者的政治權力,而是來自宗教。在福山關于政治發展的時間序列模型中,現代國家在中國的形成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時間上,中國的國家形成比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略晚,但是,“依馬克斯•韋伯的標準,中國出現的國家比其他任何一個更為現代”。在春秋戰國時期漫長而激烈的戰爭中,諸侯國開始設立常備軍、配備科層化機構來征稅執法并興建大規模的公共工程,特別是秦國的商鞅變法在這些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功。正是在爭霸戰爭的推動下,現代國家的元素在中國逐漸生長起來。自秦朝以后,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由于中國的國家鞏固發生在社會中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組織起來以前,世襲貴族、教會或僧侶群體、組織起來的農民、商人團體和軍隊等社會中的其他力量都無法抵消和約束這個早熟的現代國家。
三、比較與評價:現代國家形成的再思考
韋伯意義上的現代國家主要是以歐洲國家為藍本的,盡管中國很可能比歐洲更早發明了這一政治制度。因此,關于現代國家形成的理論主要建立在歐洲的歷史經驗基礎上。我們可以把基于歐洲經驗的功能主義模型、經濟交易模型和戰爭驅動模型稱為國家形成的原生模型。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斯特雷耶對現代國家起源的解釋是以歐洲中世紀的史實為依據的,但他的主要理論視角卻是功能主義的。因此,功能主義的目的論傾向使斯特雷耶忽視了現代國家形成的各種內生動力。一方面,斯特雷耶的結構功能主義模型并不重視作為政治組織形式與經濟交易網絡之間的關系,也低估了遠程貿易和商業活動發展在中世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斯特雷耶主要集中于分析政治單位的內部事務,低估了戰爭對國家建設的意義。正如蒂利所批評的:“在斯特雷耶的敘述中,戰爭主要是作為他所描寫的政治談判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導致國家結構變化的動因。這也意味著他對入侵的蒙古人將火藥帶進歐洲這一影響至大的事件視而不見。”正是在兩個不足的方面,經濟交易模型和戰爭驅動模型為現代國家形成的動力提供了更為系統的理論解釋。在諾思的經濟交易模型中,“國家是一種為克服封建經濟中的交易和信息障礙而產生的制度解決方案。”盡管諾思也認為理解國家的關鍵在于為實現對資源的控制而盡可能地利用暴力,但受限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諾思仍將國家在本質上看作經濟交易的產物。這樣,諾思的國家理論并沒有真正將國家在合法壟斷暴力上的強制屬性納入進來,因而錯過了韋伯關于現代國家的定義的精髓。與經濟交易模型不同,戰爭驅動模型更直接地在韋伯的國家定義上來探討國家的形成問題。戰爭驅動模型清晰地說明了戰爭的威脅與統治者加強對政治機構控制的邏輯關系。正如亨德里克•斯普路特(HendrikSpruyt)在《牛津比較政治手冊》中所評論的:“蒂利認為早期的國家將其大部分的歲入用于戰爭經費,這無疑是正確的。此外,他的論述為更大的宏觀層次的結構性現象提供了一個基于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微觀層次上的解釋”。
由于戰爭驅動模型更好地抓住了現代國家概念的精髓,戰爭驅動模型比其他兩種模型更適合討論現代國家的起源問題。當然,另外兩種模型也會使我們對現代國家的形成產生更全面的認識。比如,斯特雷耶的研究告訴我們,現代國家的發展經歷了多個世紀的演化,特別是在軍事技術革命發生前英國和法國就已經發展出了現代國家的一些元素。由此提出了一個問題,軍事變革是現代國家形成的唯一動力嗎?又如,蒂利在強調戰爭締造國家的同時,也沒有忽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蒂利承認:“在國家領土上的主要社會階級的組織及它們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極大地影響了統治者用來榨取資源的策略、他們所遇到的抵抗、由此引發的斗爭,榨取和斗爭確定了持久組織的類型,因而影響資源榨取的效率。”實際上,正是基于不同榨取策略的相對成功率,蒂利將國家在歐洲的組織形式分為強制密集型國家、資本密集型國家和強制資本化國家。因此,蒂利對現代國家形成的解釋綜合了軍事和經濟的視角。賈恩弗朗哥•波齊(GianfrancoPoggi)在評述各種國家形成理論時甚至認為:“每一種視角都有其合理性,我們必須采用一種綜合性的視角。”因此,即使在戰爭驅動模型基礎上來分析國家形成的動力,也不會妨礙我們以適當的方式吸收斯特雷耶和諾思在現代國家起源上所闡發的洞見。隨著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政治學家越來越多地探究了歐洲之外地區現代國家建設的歷史經驗。通過對中國、印度、中東、非洲乃至拉美國家形成的探討,這些學者也發展了一系列理論模型,包括精英沖突模型、世界政治的動態模型以及政治發展的時間序列模型。由于這些模型大都建立在對原生模型進行批評或改造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把這些模型稱為國家形成的次生模型。這些次生模型極大地拓展了國家形成理論的情境適應性,展現了不同國家的時空背景和環境條件對國家建設的影響,從而使國家形成理論在比較的視野下超越了歐洲歷史經驗的局限性。精英沖突模型和世界政治的動態模型更平行地將歐洲的經驗和歐洲之外的經驗納入到國家形成的理論解釋中,并通過兩者的比較來檢驗新概念和新命題的有效性。與這兩種模型相比,福山的政治發展的時間序列模型具有更大的理論雄心。經典的現代化理論傾向于將歐洲的發展當作標準來探討其他文明為何偏離西方的道路,而福山更愿意把中國當作現代國家形成的范本來探尋其他文明為何不會復制中國的道路。作為對歐洲中心論的一種反動,福山甚至提出了“中國第一”的國家研究綱領。
比較政治學者的上述貢獻無疑突破了國家形成的原生模型,但他們仍需要參照歐洲國家形成的歷史經驗。正如斯普路特所指出的:“對于研究國家形成的嚴肅學者來說,無論他們的地區研究興趣在哪里,他們的研究都應當以歐洲的國家形成作為參照點。正是現代國家在歐洲成功取代了與其競爭的政治組織形式并擴散到全球。歐洲之外的國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壓力的影響,具有非常不同的國際環境和更為緊湊的時間表。突出歐洲國家形成的關鍵性因果機制有助于展示國家發展的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如何在歐洲以外的地區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作為對現代國家形成因果機制的最清晰展示,戰爭驅動模型顯著地影響了各種次生模型的構建。在許田波和福山關于中國國家形成的探討中,他們都重申了蒂利“戰爭締造國家”的命題并通過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歷史來說明戰爭在中國國家形成中的關鍵作用。在蒂利所闡述的因果機制下,許田波視春秋戰國為“任何合理理論必須能夠圓滿解釋的重要案例”,而非一個偏離了歐洲范圍的“反常案例”。福山雖然批評了西方政治發展史對中國在現代國家創新上的忽視,但認為蒂利的理論邏輯可以用于對中國歷史的解釋。“中國國家形成的主要動力,不是為了建立壯觀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宗教領袖,而是無情的戰爭。……就像蒂利在評論后期歐洲時所說的,戰爭締造國家,國家發動戰爭。這就是中國。”之所以中國與西方走上了不同的政治發展路徑,并不在于國家形成的不同因果機制,而是國家形成的不同時間序列。無論是在對歐洲之外地區國家建設的特殊性經驗的探索上,還是在對國家形成因果機制的一般適用性的檢驗上,中國顯然都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案例。和蒂利的理論邏輯相一致的是,經過20世紀上半期的革命戰爭洗禮后中國最終建立了一個強國家。但此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建設仍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在新的形勢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因此,現代國家形成對中國的政治發展而言仍是一個歷久而彌新的主題,國家形成理論對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涵義仍需要中國的政治學者予以更多的審視與挖掘。
作者:張孝芳 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
- 上一篇: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問題研究范文
- 下一篇:事業單位黨建工作思考范文
擴展閱讀
- 1現代德育
- 2市場營銷現代到后現代
- 3將現代因素融入戲曲現代戲
- 4現代文化
- 5傳統與現代抉擇
- 6劇院現代轉換
- 7中國現代幽默喜劇
- 8現代后殖民文化
- 9現代廣告招貼設計
- 10現代家具實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