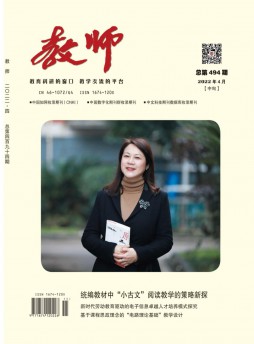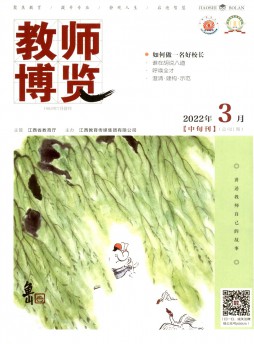教師微笑意蘊的現象學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教師微笑意蘊的現象學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教育發展研究雜志》2015年第十二期
每個學生都喜歡微笑的教師,因為教師的微笑意味著溫暖、寬容、鼓勵、接納、諒解、關心、理解和寬松的氛圍,當然,在某些境域中的教師微笑還有著一些可意會而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意蘊。“在那一刻,教師微笑了……,學生體會到了教師微笑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沒有語言、沒有解釋、也沒有暗示,只有微笑,但學生卻體會到教師微笑的意義,這個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么?這是發生在具體生活“境域”中的“事件”,對它的描寫與解釋唯有借助于現象學的方法才能完成,因此,本文將運用現象學的方法分析這些問題。
一、發生在具體生活“境域”中的微笑
作為學生,每天都會遇到面帶微笑的教師,教師的微笑是什么樣子的?我們可以這樣描述:微微翹起的嘴角像是湖面上的一道漣漪,靈動的眼睛充滿著愛意與真誠,在不經意間微笑像一抹陽光,迅速的劃過臉面。但是,如果我們僅僅這樣描述教師的微笑,那么這種微笑固然能帶給我們“溫暖”“、友好”的感覺,但我們卻不能說,這樣的微笑也能產生寬容、理解、鼓勵、信任、接納的意義。現象學的理論告訴我們:這是因為這些看似“真實”“、準確”的對教師微笑的描述,其實只是對教師微笑的“孤立描寫”,而“孤立”的微笑并不能單獨的產生意義,只有在具體生活“境域”中且出自生活“境域”的微笑才能被體驗到意義。
比如,只有“當教師與犯錯的學生談話時,當學生希望獲得教師的理解時,當學生膽怯的回答問題時”,這時候教師的微笑才能產生寬容、諒解、理解、信任、鼓勵的意義。因此,現象學的理論告訴我們:一個看似“孤立”的微笑能夠“被看到”,能夠產生意義,其實源自于一種沒有被看到的特定“境域”;或者說,教師的微笑能夠產生意義并不是由“微笑”本身決定的,也不是由“學生”這個微笑的觀察者決定的,而是由微笑所置身于其中的那個“境域”來決定的,只有在特定的“境域”中微笑才有其特定的意蘊。那么,什么是境域?在現象學中,境域(Horizont,或譯為“視域”“、地平線”)意指任何一個經驗對象或行為得以產生的整體和背景。[2]在胡塞爾看來,每一個被意指的對象和行為都不是孤立的被經驗到的,都是作為某個具體“境域”中且來自于“境域”的事物而被經驗到的,這就是講每一個當下的經驗都有其發生的“境域”,每一個經驗對象都是在一定的“境域”中與我們遭遇的。
克勞斯?黑爾德(KlausHeld)對此解釋說,認為對象總是在境域之中,即是說對象總是在某個意義指引的網絡中,而諸多意義指引的網絡通過它們之間的相互指引就構成一個“境域”總體,也就是“世界”。因此,對教師微笑的描述就不能僅僅是對教師面部表情的描述,而應當是對教師微笑發生的“境域”的描述,因為微笑的意蘊只有在“境域”中、在“教師”與“學生”打交道的活動中才能呈現出來。比如,我們可以這樣描述教師的微笑“:(這個)教師的這一次的微笑不同于任何其他教師的微笑,也不同于自己以往的任何一次微笑,而是發生在當下的一次微笑,這個微笑可能發生在一個學生正在疑惑是否應該站起來回答問題時,也可能發生在與一個犯了錯誤的學生談話時,亦或者發生在一個學生因為擔心遲到而沖進教室時,正是在這一刻,學生看到了教師的微笑。在當下、在這一刻學生看到的教師的微笑,不是作為教師的面部表情存在的微笑,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作為社會禮儀存在的教師的微笑,而是發生在當下‘事件’中的這一刻的微笑,這個當下的微笑是與學生們正在做的‘某事’相關聯的,也是因為學生做‘某事’而出現的微笑。在這一刻,教師為什么會微笑呢?因為他‘看’到了學生當下的‘遭遇’‘,看”到了學生需要被理解、需要被寬容、需要被鼓勵、需要被關心的所處‘境域’。因此,在這一刻,教師微笑了,微笑中蘊含著意義。”
對教師微笑的現象學描述,不同于對教師面部表情的描述,這樣一種描述告訴我們:微笑只有在一個個實際性的生活“境域”中才有其特定的意蘊,教師的微笑只有在學生與教師的當下“遭遇”中才有意義。如果不是在這些生活“境域”中,教師的微笑只能是抽象的面部表情或者社會性的禮節,這樣的微笑固然能帶來社會性的“友好”和“親和力”,但這樣的微笑卻不能產生鼓勵、寬容、諒解、理解的意蘊。因此,教師的微笑只有在生活“境域”中才能產生意蘊,而不同生活“境域”中的微笑也都有其不同的意蘊,這同樣意味著,只有在這個特定“境域”中的學生才能體會到微笑的特定意蘊。也許從表面來看,教師的微笑只是發生在一個個具體生活“境域”中的微小“生活事件”,但是,依據現象學的理論分析,教師微笑背后反映的卻是整個的教育生活世界。比如,教師微笑發生在當學生需要鼓勵時,發生在學生沉默時,發生在學生取得成績時,發生在學生面對困難時,發生在學生猶豫不決時,諸如此類,這些正是“真實”的教育生活,教師的微笑正是基于這些真實的“教育生活”才產生意義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教師微笑反映的正是教育的生活世界,同時教師微笑也“開啟”了教育生活世界的意義。
二、學生對教師微笑意蘊的“領會”
在那一刻,在這樣一個“境域”中,作為學生的“你”“看”到了教師的微笑,“你”理解了教師微笑的意義,那么,“你”是如何理解教師微笑的意義的呢?依據海德格爾的理論,學生之所以能夠理解教師當下微笑的意蘊,原因就在于學生有一種直接獲得當下微笑意義的能力,海德格爾稱之為“領會”。什么是領會?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指出領會的一個基本意思:你“在世界之中”,就總已經對“世界”有所領會,領會是“此在”理解世界的方式。海德格爾認為,在生活世界中,“此在”與世界都不是“現成”存在的,而是在交互之中相互構成的“。此在”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并不是把世界當作被研究、被觀察、被對象化的客體,而是首先就是“在世界之中”,就是與世界的相互纏繞、相互構成。“領會”就是在“此在”與世界的相互纏繞中發生的。海德格爾認為“,領會”能夠發生,還需要一個根本性的前提,那就是“此在”在對當下生活世界的理解之前還需要一種對世界的“前了解”“,前了解”就是“此在”對需要理解的生活世界已經有所“了解”。而領會就是“此在”順著已有的“前了解”不斷描述、不斷重復、不斷審視、不斷打量當前的生活世界,這樣,“此在”的“前了解”與“生活世界”就有了某種逐漸的融合,領會就發生了。
因此,領會就是“此在”對世界的不斷描述、不斷重復、不斷審視、不斷打量。同時,這也意味著“,領會”本身就有解釋的意蘊,領會中就包含著表達與解釋。那么,學生對教師微笑意義領會的過程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做出如下現象學的描述:在當下境域中,學生看到了教師的微笑,學生看到的絕對不是孤立的微笑的面孔,而是顯現出微笑的整個生活“境域”。這說明,在學生看到教師的微笑時,學生就已經被卷入到當下微笑的世界中,在那一刻,學生是沉浸在微笑中的,微笑呈現在學生的意識中,仿佛在向學生訴說著什么,一切都存在著意義。教師的微笑在向學生訴說什么呢?這個地方不能用對象化的方式來分析,或者說,外在的解釋和論爭是沒有辦法解決的,而只能需要學生自己的領會。當然,學生對教師微笑意義的理解,并不是當下明白的,而是一個正在“實現的經歷”,是在對教師微笑不斷的揣摩、體會、理解中實現的。學生能夠領會教師微笑的意義,需要兩個基本條件:首先,教師微笑的意義是與當下的“境域”有關的。如果這是一個學生需要被鼓勵的境域,那么教師的微笑就意味著鼓勵;如果這是一個需要被理解的境域,那么教師的微笑就意味著理解;如果這是一個需要被寬容的境域,那么教師的微笑就意味著寬容。這就是說,教師微笑的意義是與當下的“境域”有關的,同樣意味著只有處于當下“境域”中的學生才能夠理解當下微笑的意義。其次,正如前文所講,學生能夠理解教師微笑的意義,還需要一個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學生對老師的“前了解”。如果學生不是事先“了解”了教師是一個什么樣的教師,學生是不能領會教師微笑的意義的。如果學生認為教師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個和善、關愛學生、尊重學生的人,那么學生就能夠領會教師微笑的意義;如果學生認為教師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個專制、冷淡、欺騙學生的人,那么學生就很難領會到教師微笑的意義。因此,總體來看,學生對教師微笑領會的過程,就是學生對當下“境域”不斷描述、不斷解釋、不斷反復的過程,是學生自己的“前了解”與當下“境域”不斷融合的過程,雖然領會的過程非常短暫,但對于學生來講卻是一個完整的“體驗”意義的過程。那么學生在教師的微笑中能“領會”到什么?可以確定的是,在不同的生活境域中,教師的微笑會有不同的意義。雖然在不同的生活境域中,學生會領會到教師微笑的不同意蘊,但有“兩點領會”卻是在所有的教師微笑中都能領會到的:一是領會到教師體驗到了“我”(學生)當下的體驗,二是領會到教師相信“我”(學生)能……。學生“領會”到教師能體驗到自己當下的體驗,是關心、理解、寬容、鼓勵等意義產生的前提;學生領會到教師相信自己能……,則是學生做出下一步決定和行動的動力,這正是學生在“看”到教師的微笑后,總能做出“正確”行動的原因。
下面,具體描述學生在所有的微笑中都領會到的這兩點共同領會:第一,學生領會到教師體驗到了自己當下的體驗。在教師的微笑中,學生領會到教師體驗到了自己當下的“遭遇”,不管是高興的、窘迫的、怯懦的、擔心的,還是希望的,學生領會到這些體驗被教師體驗到了。學生為什么能體驗到這些呢?這種體驗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而是學生的“實際生活經驗”告訴他的:因為曾經在自己遇到困難時得到過教師熱情的幫助,在自己獲得成功時得到教師對自己的鼓勵和贊揚,在煩惱時教師和自己屈膝長談。正是這些共同的“實際生活經驗”,正是這些曾經發生的有“意義”的事情,讓學生相信教師體驗到自己當下的體驗,也正是這些共同的“實際生活經驗”和有“意義”的事情推動著學生相信教師體驗到了自己當下的體驗。因此“,共同的生活經驗”是學生能夠領會到教師體驗到自己當下體驗的基礎。而相反,如果沒有這些“共同的生活經驗”,沒有師生之間的親切交談,沒有教師對學生的熱情幫助,沒有教師對學生的鼓勵和關心,沒有生活中這些有意義事情的發生,學生也就不會領會到教師能夠體驗到自己當下的體驗。因此,在表面上,看似只是學生自己的領會,其背后卻是教師與學生雙方都投入到對方生命中的結果。第二,學生領會到了教師相信“我”(學生)能……教師的微笑不僅意味著教師體驗到了“我”(學生)當下的體驗,同時,也是對“我”(學生)能……的相信。對學生能……的相信,就是對學生進一步決定和行為的認可。比如,當“我”(學生)在考慮是否要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學生)看到了教師的微笑,這個時候教師的微笑中包含著相信“我”(學生)能回答好這個問題;當“我”(學生)因為做錯了事,拘束地站在教師面前時“,我”(學生)看到了教師的微笑,這個時候教師的微笑中包含著的就是相信“我”(學生)能改正錯誤;在“我”(學生)因為遲到而惶恐時“,我”(學生)看到了教師的微笑,這時教師的微笑中就包含著對“我”(學生)下次不會遲到的相信。因此,教師微笑中包含著的相信,不是語言表達出來的相信,而是當下境域“建構”起來的相信,是懸置在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正在“生成中”的相信,因而,這種相信也只有在這個境域中的學生才能領會到。教師的微笑并不是相信本身,而是“激發”學生去相信,也許學生原本有所懷疑(懷疑自己能不能做好這個事情),有所焦慮(懷疑自己是否會受到批評),但是,當他們看到教師的微笑時,一切懷疑都消失了,因為,他們在教師的微笑中“領會”到了“相信”。學生對教師微笑意義的領會是一個“正在實現”的過程,那么,學生“何時”才能領會到微笑的意義呢?依據現象學的理論,這個何時,并不是一個客觀的、確定的時間,而是一個在等待中、期待中的時間,即是講只有在學生投入到對微笑的關注中、在對當下生活境域的理解中,教師微笑的意義才會到來。因此,學生何時才能領會到微笑的意義,并不是現成的時間上的領會,它需要教師的愛心、投入、關注,也需要學生的投入、關注、理解,正是在雙方投入的姿態中,在真誠的等待中,教師微笑的意義才能來臨。
三、處于“投入”狀態的教師和學生
“在這一刻,教師微笑了……,學生看到了教師的微笑……,學生領會到了教師微笑的意義”,在教師微笑的“這一刻”,在學生看到教師微笑的“這一刻”,教師和學生處于怎樣的狀態?在教師微笑的這一刻,教師處于怎樣的狀態?我們可以借助于一個“事件”來描述:假如現在一個學生正焦急地向你(教師)解釋他不小心犯的錯誤,這個時候,你(教師)看著他,你(教師)看到了他的窘迫,看到他在努力向你(教師)做著解釋,可能因為著急眼角還溢出了淚水,在這一刻,你(教師)向他發出了微笑。在這個境域中,教師所處的狀態就是“投向學生的看”和“這一刻的微笑”。“看”意味著關注,意味著對學生當下境況的體驗,微笑則是告訴學生你(教師)理解他當下的處境,你(教師)相信他能處理好當下的事情。因此,教師從“看”到學生當下的處境到這一刻發出微笑的過程中,始終都不是把當下的“事件”看作是一個與己無關的“外在事件”,也不是把學生看作是一個客觀的對象,而是從一開始,教師就已經卷入到當下的事件中,就已經沉浸在當下的境域中,就已經與當下的境域渾然一體。現象學把這種一開始就沉浸于當下境域中的狀態稱之為“投入”。
因此,在教師微笑的這一刻,教師處于“投入”的狀態。那么,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在看到教師微笑的“這一刻”,學生處于怎樣的狀態?我們同樣可以借助這個“事件”來描述:假如現在你是一個不小心犯了錯誤的學生,你焦急地向教師解釋著你無意中犯的錯誤,這個時候,你看到教師正在靜靜地看著你,傾聽著你的訴說,在教師的“看”和“聽”中,你體會到教師體驗到了你當下的體驗,也正在“經歷著”你不小心犯錯的經歷。這個時候,你還可能因為著急眼角溢出了淚水,在你不知所措時,在這一刻,你“看”到了教師的微笑。在看到教師微笑的那一刻,你停止了訴說,你沉浸在教師的微笑中……,你領會到了教師微笑的意義。因此,在學生看到教師微笑的這一刻,學生是沉浸在微笑中的,或者說,在看到教師微笑的這一刻,學生就被卷入到微笑之中,就已經與微笑融為一體。因此,在學生看到教師微笑的這一刻,學生也處于“投入”的狀態。因此,在教師微笑的這一刻,在學生看到教師微笑的這一刻,教師和學生都處于“投入”的狀態。那么,投入是一種怎樣的狀態呢?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有關于投入的經驗,比如,我們專注于一幅繪畫作品時,專注于科學研究時,聆聽音樂時,或者看電影時,都會有投入的狀態。在投入時,人會完全喪失于正在投入的體驗中,而不會把正在看的作品、做的研究、聆聽的音樂當作一個被體驗的對象,甚至我們也意識不到自己正在看或者聽。在投入狀態中,沒有對投入對象的分析,也沒有對自己當下體驗的分析,而只有當下“對某物”的體驗,只有“向著某物的經歷”。
因此,當教師在微笑的這一刻,教師并沒有思考應該不應該微笑、應該怎樣微笑,也沒有一個諸如“自我”之類的主體控制和決定著自己的微笑,甚至教師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微笑了,只是在那一刻,教師在“投入”到這個境域中時,微笑自然發生了。同樣,學生在看到教師微笑的這一刻,學生是“沉浸”于微笑中的,在“沉浸”中學生領會到了教師微笑的意義。與投入的微笑相對應,在教育中還存在著另外一種教師的微笑,本文稱之為“形式的微笑”。“形式的微笑”是指教師的微笑并不是在當下境域中自然出現的,而是由教師先于“與學生的相遇”帶入到當下境域中的。在教育中,我們總是告訴教師要保持微笑,通常指的就是“形式的微笑”。固然,“形式的微笑”也能帶來寬松的環境、友好的氛圍,但“形式的微笑”卻很難產生鼓勵、諒解、理解、寬容的教師價值。這是為什么呢?我們同樣可以借助于這樣一個“事件”來描述:假如現在你是一個不小心犯了錯誤的學生,當你焦急地向教師解釋你無意中犯的錯誤時,你“看到了教師的微笑”,當你希望教師能夠理解你時,你“看到了教師的微笑”,當你因為著急眼角溢出了淚水時,你“看到的還是教師的微笑”。這個時候,作為學生的你一定會想“:為什么教師一直在微笑?教師有沒有聽到‘我’的解釋?教師有沒有原諒‘我’犯的錯誤?教師有沒有看到‘我’改正錯誤的決心?”因此,在“形式的微笑”中,學生體會到的不是理解、諒解和寬容,而是“疑惑”。因此“,形式的微笑”不是教師“投入”其中的微笑,而是教師“帶入”到當下“事件”中的微笑,這種微笑脫離了當下的生活境域,成為教師可以控制的對象。在這樣的微笑中,教師和學生都沒有“投入”其中,因此也不能產生教育意義。并且相反“,形式的微笑”不但不能對學生產生當下的鼓勵、理解、寬容、關心、接納的教育意義,反而有可能會給學生帶來“虛情假意”的印象,這是我們教師在微笑時應該注意的。
在教育中,我們總是要求老師要保持微笑,事實上,我們需要的是出現在當下境域中教師“投入”的微笑,而不是“形式的微笑”,因為只有發生在當下境域中的教師“投入”的微笑,才會產生溫暖、寬容、鼓勵、接納、諒解、關心、理解的意蘊。在已有關于教師微笑的研究中,大多關注的只是教師微笑的意義與作用,幾乎沒有探討教師微笑意義發生的過程、學生對教師微笑的領會等問題,原因就在于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這些問題是難以描述和解釋的。本文在對教師微笑意蘊的現象學闡釋中,并沒有“理論的“”對象化的”分析教師微笑,而是運用現象學的方法把教師微笑放置在“實際生活境域”中,從教師和學生體驗的角度來描述和解釋教師微笑意義發生的過程,雖然這樣一種研究方式并不能完全透徹地解釋清楚教師微笑的意蘊,但卻給我們進一步研究教師的微笑提供了一種不同的研究方式。
作者:張魯寧 單位:魯東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
- 上一篇:云課程的實施困境及其突破范文
- 下一篇:商文化與城墻有關的祭祀遺存分析范文
擴展閱讀
- 1教師威信
- 2教師檢討書|教師檢討書范文|教師違紀檢討書范文|教師檢討書
- 3教師黨性
- 4教師頂崗實習
- 5教師黨性
- 6美術教師計劃
- 7教師總結
- 8教師黨性
- 9教師計劃范文
- 10教師教育中教師的培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