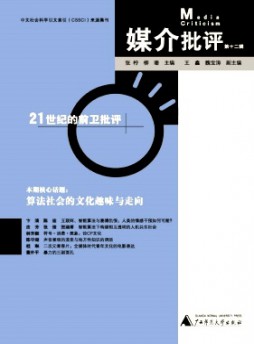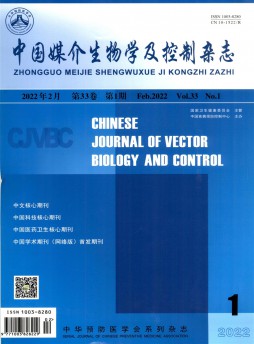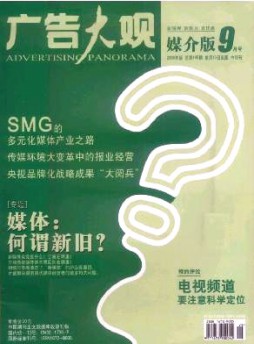媒介與文體視域下的敘事塑形思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媒介與文體視域下的敘事塑形思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上海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
摘要:
敘事形式的產生與發展并非自律性的,而是受到媒介與文體雙重因素的交互影響。圖像逐步內化為敘事不可或缺的塑形工具。各種文體實驗在窮盡了紙質媒介敘事可能性的同時,也使得敘述與故事決裂,塑形本身成為比故事更重要的存在。今天,影像雖已成為敘事的主體卻并未引起敘事形式產生實質性變化,但虛擬和互動技術的發展則為敘事提供了某種新的契機,預示著故事將回歸史詩式的未來。
關鍵詞:
敘事塑形;圖像化;敘事線條;文體;媒介
黑格爾在《美學》中提出:“史詩領域有最廣闊天地的要算長短程度不同的小說。對于這些藝術品種我們在這里不能敘述它們從起源到現在的發展史,就連描繪粗線輪廓也不可能。”[1]這可能是因為18世紀時小說才剛剛嶄露頭角,黑格爾還無法把握小說敘事的發展。時至今日,關于小說的論著已汗牛充棟,但敘事的“主要動力則可能已從文學轉向其他媒介”。在不斷變化的敘事媒介中,圖像塑形是把握敘事最直觀的工具。從某種意義上說,故事就是被圖像化的情節。20世紀末,希利斯·米勒在《解讀敘事》中分析了敘事文本中的線條意象,對開頭、中部、結尾逐一進行了解構,因為把“敘事想象為某種理想的線條……(會產生)一種敘述的難題”。[2]47但米勒在論著中并沒有梳理敘事的圖式化(線條)思維究竟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變化發展的,但這恰恰是解讀敘事發展的關鍵,也是解決“敘述的難題”的根源。追蹤敘事塑形的產生與變化,我們不僅能夠了解敘事的過去,或許也可以把握敘事的未來。
一、賦予生命的線條
亞里士多德對敘事有一種清晰的理性認識,敘事(史詩和戲劇)藝術“著意于一個完整劃一、有起始、中段和結尾的行動。這樣,它就能像一個完整的動物個體一樣,給人一種應該由它引發的快感”。[3]163因此,亞氏認為,穿插式是敘事之“最次”,歷史敘事甚至算不上“一個行動(敘事)”,而這兩者或許恰是柏拉圖的喜好。柏拉圖說:“詩的摹仿對象是行動中的人,這行動或是由于強迫,或是由于自愿,人看到這些行動的結果是好還是壞,因而感到歡喜或悲哀。……詩的摹仿盡于此了……在整個過程之中,一個人是否始終和他自己一致呢?是否……對于同一事物同時有相反的見解,而在行為上也自相矛盾。”[4]81-82詩都是摹仿,而摹仿的本質在于敘事者對故事本身和敘事話語的控制,在這種理性制約下的敘事中,柏拉圖卻看到了敘事中的非理性因素。在文體形式上,柏拉圖反感的“摹仿敘述”大多出現在戲劇中,史詩和歷史記述則基本由他所倡導的“單純敘述”組成。但亞里士多德則批評多數詩人不用戲劇化的“摹仿敘述”做史詩,所以史詩中只有荷馬的摹仿是卓爾不群的。可以說,西方敘事從源頭上就存在兩種敘事的可能性,只不過亞氏的《詩學》用邏各斯中心化的“戲劇性”結構將柏拉圖的敘事理想遮蔽了。從兩位先哲所論述的語境來看,柏氏偏重史詩,而亞氏主要講戲劇。口傳史詩和戲劇化的線性情節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兼容的,因為“古希臘口頭史詩真正的思想或內容保存在記憶中的傳統套語和詩節模式中,而不是存在于是以有意識地組織或謀劃的敘事里”。[5]而亞氏卻懸置史詩和戲劇的實質性矛盾將它們一視同仁,認為史詩詩人“也應該編制戲劇化的情節”。一方面,情節只要清晰明朗,敘事就“越長越好”,“因為長才能顯得美”。另一方面又須注意“體積”,敘事“如果太大了(或太小)都不美”。他也認識到實際上“若要符合這種要求,作品的結構就應比早先的史詩短”。[3]168亞氏雖有意將兩種敘事調和,卻以戲劇同化史詩而告終,其戲劇原則也在文藝復興之后演化為布瓦洛的“三一律”。語言敘事一直處在被輕視和壓抑的狀態。盧卡奇認為:“同史詩規則的稚氣相比,小說是十分成熟的藝術形式。……這意味著,小說世界的完整,如果從客觀上看,是一種不完美,如果從主觀上體驗,它就相當于屈從。”[6]71而這種不完美與屈從自史詩的戲劇化發端,小說就是戲劇化史詩的后裔。史詩敘述的龐雜難于以圖式化方式表現出來,而戲劇式敘事則意味著一種圖像化。“故事被描述為一根線條,它可以被投射、標示或者圖解為連續不斷的一根空間曲線或者鋸齒形線條———總之是某種形狀的可視圖形。”[2]62因為“傳統時間就是一種空間化的時間。這樣的時間與空間一樣,是純一的、同質的東西。……時間在經由空間測量時已被歸結為空間”。[7]理想狀態下,時間被表現為一條均質的、無始無終的直線,故事時間就是這直線上的線段(見圖1)。敘事實際并非如此,它既然被限定在一定長度內,“突轉與發現”的“復雜行動”就成了理想敘事中最重要的部件,是“最完美的悲劇”的核心。但直到1863年,德國戲劇家弗雷塔格在《戲劇技巧》中才第一次將這種理念直接圖形化,即著名的弗雷塔格金字塔“行動的兩部分在一個點(C)上結合起來,如果用線條將這種安排圖式化,那么戲劇就具有一種金字塔結構。……這個中點是戲劇的高潮,是這個結構中最重要的部分。”[8]這與亞氏的表述如出一轍。折線替代僵硬直線的重要原因是它的有機性,線條是“有生命”的,而生命體與無機物的本質區別就在于生命自身內在的發展變化。柏拉圖認為“每篇文章的結構都應該像一個有生命的東西,有它所特有的那種身體,有頭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整體,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調和”。[4]150亞氏雖也提到敘事應像一個“完整的動物個體”,卻使用了“起始、中段和結尾”這樣更徹底的邏輯語言。兩人雖都使用動物做類比,但亞氏卻削去了故事的“四肢”,只留下頭、身和尾,它更像是一條蛇,也更符合理想線條的圖形投射。柏拉圖還在史詩和戲劇間猶豫不決,而亞氏則促使史詩進入戲劇化時代。亞氏的觀念是邏輯連貫性逐漸獨霸敘事意義的濫觴。“敘述的主要特征或許在于它的內在連貫性:敘述由一系列獨立的事件、意識和關于人類的一切事物組成……這些構成部分自身沒有生命和意義,只有當它們在作為整體并在出現的一系列事物中處在一定的位置時才具有意義。……語言之外的現實對故事本身而言意義不大,這突出表明敘述有其內在的結構,換句話說,是語句的連貫性而不是它們的正誤對自身的總體構建或組織起著決定作用。這樣的連貫性與故事的意義密不可分,與人們借以把握它的精神組織模式也是密不可分的。”[9]而多數史詩恐怕并非如此,因為口頭“講述故事的一半技巧在于講述時避免解釋。……不把事件心理上的邏輯聯系強加于讀者”。[10]邏輯連貫性對語言敘述來說是一種后起的概念,使得小說長期處在一種適應和不定型中。在古典時代,“正統文學中的所有體裁在一定程度都是和諧地相互補充,所以整個文學作為多種體裁的總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高度和諧的整體。……小說從來都不進入這個整體,不參加到多種體裁的和諧生活中去。在這些時代小說處于正統文學之外,過著非正式合法的生活”。[11]506-507文學主流對小說的漠視使小說的戲劇性結構也顯得并不正統,似乎小說總披著一件借來的外衣。在此期間,文字敘事以各種形式呈現,如詩體敘事、羅曼司等等,這反映出小說體裁的不定型。而“通常認為小說的不定型性大概就源于此:小說的形式常規的缺乏似乎是為其現實主義必付的代價”。[12]13文字敘事的獨立首先從內容開始,它反映現狀,而非傳統敘事那樣對現實缺乏興趣。小說的最初“現實性”是以文體為手段的,當時幾乎每一種紀實文體都產生了一種對應的小說翻版,作品類型更是不勝枚舉,書信體小說、日記體小說、游記小說、傳記小說等等。“絕大多數十七八世紀的作者都或明或暗地否認他們在寫長篇小說或羅曼司。他們為自己的作品加上‘歷史’‘傳記’‘回憶錄’等等名稱,以便將自己從長篇小說或羅曼司的無聊的、空想的、未必然的,甚至不道德的那些方面開脫出來。”[13]43小說借助內容的“勝利”,使自身的結構及整體性與其他體裁平起平坐。紀實文體外形的“現實主義”并不能掩蓋其結構形式的虛構性。巴特就稱之為不可能的真實:“在寄給友人的書信中,維特敘述自己生活中發生的事情以及他的情欲所產生的結果……戀愛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是如此瑣碎,以致人們只有通過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變其為寫作……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能靠它引起的巨大反應而存在,而那是記錄我的反應的日記;有誰能理解這些東西?”[14]也就是說,現實文體與現實其實無關。18世紀對小說虛構性認識最深入、最具跨時代意義的莫過于斯特恩的自傳體小說《項狄傳》,“憑著某種早熟的藝術手法,斯特恩將他諷刺的鋒芒指向這種新形式直到很晚才發展起來的種種敘述方式”。[12]291《項狄傳》第六卷中敘事者以戲謔的方式探討敘事線條,如果不以正式的理論話語來評判,斯特恩比弗雷塔格更早地將敘事線條具象化出來。小說第一卷至第五卷的敘事的“進展線路”是一些曲線,而第六卷則可以達到“完美境界”,即一條直線(見圖3):這條直線是“最好的線”,但敘事“根本不是用尺子畫出來的一根直線。倘若是那樣的話,就不會引起讀者的任何興趣。敘事之趣味在于其插曲或節外生枝。這些插曲可以圖示為圓環、結扣、線條的中斷或曲線”。[2]68斯特恩線條中的曲線代表著離題,而弗雷塔格的折線則意味著一以貫之的戲劇化情節。①參閱:FrédéricCALAS,LeRomanEpistolaire,Paris:ArmandColin,2007,Index.小說借用紀實文體更容易以直接引語和心理獨白等方式來表現人物,因為它比“第三人稱敘事的敘事者更‘天經地義地’有權以自己的名義講話”。[16]雖然在結構功能層面,不少敘事學家注意到第三人稱敘述和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的相似,但是從小說發展的歷時來看,由紀實文體帶來的第一人稱敘事為小說的確立奠定了新的基礎。施萊格爾明確地說:“一部小說作為一部作品的整體性,并非源于其故事的戲劇性語境,而是源于一種高于字面的統一性。小說一般輕視也應該輕視這種字面上的統一性,但它圍繞一個精神上的中心點建立起概念上的聯系,借此形成一部作品。”[17]小說以敘事性文字反映精神或思想的方式確立了自身獨特的藝術價值。至19世紀,小說已初步完成從“形式現實主義”到“心理現實主義”的過渡。紀實文體小說的春天十分短暫,如書信體小說在18世紀大量涌現,到19世紀初數量已屈指可數。①因為小說“從‘我’的觀點出發總是危險的。讀者會禁不住認為作者自夸……‘我’也可能假裝謙虛……講故事時最好把人稱代詞隱藏起來”。[18]小說已從紀實文體中獨立,找到自身特定的表達形式和內容,它“諷刺地模擬其他體裁,揭露形式和語言的假定性質,排除一些體裁,把另一些體裁納入自己的結構,賦予它們新的含義和新的語調”。[11]507這種訴求的最終結果是19世紀末亨利·詹姆斯所總結的“圖畫法”和“戲劇法”。戲劇法通過外在行動展現事件,圖畫法則通過心理意識反映事件,是自然主義小說和意識流小說的濫觴。表面上,亨利.詹姆斯在追求戲劇的直接性與真實性,但事實上卻是對戲劇化情節的反叛,其后逐步形成了現代敘事的重要特征———情節淡化,小說在“戲劇”的名號下逐步“反叛式地”實現了自身的獨特性。盧卡奇稱小說是“罪惡時代的史詩”,這是柏拉圖式史詩敘事的某種復興,意味著情節整一的邏輯理性被瓦解,而關于小說的有機性論述卻方興未艾,“只有在小說中,時間與形式被置于一起……時間是有機體———這種有機體具有純粹的與生命相似的外觀,它對抗著意義”。[6]122古典有機論更重視情節的因果邏輯,而現代小說則直接與生命體驗關聯。原本理想的線性情節被轉變為非線性或者無時性的情節,“20世紀之初,大部分批評家都承認,亞里士多德及其追隨者所提倡的整齊的情節結構無法被強加于那個叫做長篇小說的松弛臃腫的怪物”。[13]82現代敘事的產生伴隨著另一種刻意性的自律過程,它“表現為效法主觀思維而構造的存在結構的無形式性,實際上是奴役主體的東西,是純粹、為他性的”。[19]意識流等現代小說形式自律,內容自我,實際上卻展現了人的無力和對外部世界的無奈。如果情節拒斥理性與形式,最終“沒有絲毫的連貫性,混沌無序將會盛行,會成為一種永遠不變的本質。……如果為了保護一個不變的形式概念而忽略了這一點,就會導致這樣一種處境,它與人們使用傳統‘盡善盡美的形式’等等粗暴術語的境況沒有多大區別”。
二、數學規則的視覺化入侵
現代敘事畫地為牢地陷入個體意識的漩渦之中,本雅明斥之為“經驗的貧乏”。情節淡化的同時意味著邏輯性和目的性的減退,空間在時間維度延綿,小說呈現出弗蘭克(Frank)所稱的“空間形式”或卡爾維諾的“時間零”。這里,“空間”是時間極致化的表現,就像對運動的研究是從“飛矢不動”開始一樣,生活和世界不再是一個整體,徹底斷裂為個體記憶片段的集合,敘事線條也隨之隱去。作家或主人公感性的、游牧式的思緒實際上是無法圖式化的,與其說這些內容被賦予了某種形式,不如說它就是鮮活的思維本身。自尼采之后,活力論(vitalism)強調形式與生命之間的對立,“形式駁斥那種認為藝術作品具有直接存在特性的信念……藝術品的存在歸功于形式,因為形式是它們的中介體,是它們在自身中得以反思的客觀條件……某些藝術作品備受推崇的樸素性,到頭來反會敵視和妨礙藝術”。[20]144失去傳統形式的現代小說難以把握,它們建構了意義的黑洞,“普魯斯特、里爾克或喬伊斯這樣的現代主義作家似乎有解釋不完的意義,他們的淵源似乎探索不盡,對他們的評論和注釋也沒完沒了”。[21]288外在形式的隱退帶來內容的爆炸,它具有開放性,思維可以無限附加。總體變成了無序,自律變成了自娛。超現實主義文學家布勒東等甚至提出“純心理自動寫作”實驗。他把一些作家集合起來,在半催眠的狀態下,寫下自己的真實思想,然后合在一起拼成一篇夢中囈語般的小說。“對世界無法掌握的感覺已經導致一些領域的小說有意不以時間方式結構自身,而是通過一種炫耀,甚至更加另類的模式去結構。”[22]此時,最先出現的是數學化的形式,“它們幫助被解放了的主體同混亂無序、沒有條理的素材進行首次較量,為主體提供了某些可隨意使用的預先形式手段”。[20]143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法國文學組織“Ouli-po”,其宗旨是“尋找能被作家使用的任何合 適的新的形式和結構”。[23]他們認為“意識流、自動寫作等理念向人們展現作家混亂不堪的思維,連同浪漫主義鼓吹靈感的創作理念,實則是對作家表現現實的扭曲,顯得武斷而粗陋”。[24]盲目屈從于所謂靈感,實際上是一種不自由。與其如此,不如潛心參照數學,以理性的思維推演事物存在的可能性。通過制定規則和方法,使文字獲得一種結構魅力。喬治·佩雷克(GeorgesPerec)是“Ouli-po”的干將之一,其1978年創作的《人生拼圖版》(Life:AUser'sManual)便是小說的數學實踐名作之一。作品圍繞著一棟十層樓房展開,此樓的平面圖如同棋盤被橫縱劃分為100個方格,對每個空間的敘述即為一章。佩雷克按國際象棋規則在方格間跳馬步,每個方格只能進入一次,進入哪個房間就敘述關于哪個房間的故事,最后會跳盡所有方格,數學上稱之“馬踏棋盤”問題(Knight'sTour)。如圖4所示,敘事在整棟大樓中按棋子的移動順序進行。①這種規則是外在于故事的,如果沒有小說末尾的那幅大樓平面圖和他本人在別處的提示,再細心的讀者也不可能猜測到這種規則的存在。雖然小說手稿“展示了佩雷克在寫作這部小說時所做的限定……揭示了決定小說建構的嚴格形式結構,并闡明游戲在很大程度上激發和決定了小說結構”。[25]但這部小說里“沒有一個中心的人物,甚至幾個為主的人物也沒有,在這部小說里,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故事線索,甚至幾個互相有關的主要線索也沒有”。[26]很吊詭的是這種散亂卻是由數學規則帶來的。因為佩雷克設置的圖4“跳馬”線條只是作者某種特定寫作規則的圖形化,而非情節線條那樣是故事邏輯的視覺演繹。這里,線條以限定空間描寫次序的方式來決定故事,這意味著圖像不再是過去情節邏輯的圖形化說明,而成為敘述行為的外在控制裝置,圖像開始作為敘事手法這一現象也表明敘述行為本身的復雜性。圖像把自身嵌入到敘事結構中去,以至于沒有這種數學化的圖形,敘事就無法展開。敘事結構的有機性轉化為敘事進程的數理化和規則化,這種圖形化的、可直觀把握的結構,開創了敘事形式與科學結構交叉的先河。但“數學化作為一種以某種內在方式將形式對象化的方法是一種妄想。無濟于事的原因在于:每當傳統的形式確定性感覺分化瓦解、致使藝術家失去客觀標準之時,才有人乞靈于它。正是在這樣的關頭,藝術家求助于數學。數學似乎能把藝術家所取得的客觀性幻象結合在一起。這些東西之所以是虛幻的,其原因在于組織結構構成了形式,但并非源于特定作品的形狀外觀,因此在個別細節面前顯得無能為力。這便是數學化為何在貶斥傳統形式為非理性的同時又偏愛傳統形式的原因”。[20]143佩雷克的故事雖和意識流小說一樣沒有邏輯性,但對線性時間的懷舊使其在小說附錄中加入了一份70頁的索引,詳注了關于樓中人物的事件紀年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客觀的歷史性時間。佩雷克的規則并不體現在故事中,而卡爾維諾則把規則的運用方法寫進小說,《命運交叉的城堡》《命運交叉的飯館》中通過塔羅牌的排列組合規則將結構層面的元敘事直觀地用圖像展現出來。規則不再是小說背后與一般讀者無關的隱秘,而是變成理解小說的一種角度。不僅“講什么”是一種虛構,連“怎么講”(結構)同樣也是虛構的,小說不過是一場語言或符號游戲。利奧塔“把‘后現代’歸結為‘元敘事的終結’,而現代則以元敘事規則為特征,始終崇奉某一中心理念……并集中到一個目標上”。[27]故事匯集的原因是一場虛構的游戲,而游戲本身就是一種無目的性的娛樂。在這個意義上,卡爾維諾更具有后現代性。總之,無論這些借助數學或幾何形態的敘事線條多么復雜,暗示了多少種敘事的可能性,它的文字仍然是線性排列的。這類小說的敘事構型并非故事內容本身的結構,而是敘事者進行講述的順序,這與意識流小說敘事發展受主體思緒的掌控是相似的,只不過把它換成了一種客觀的、數學化的規則。這種毫不介入的、不動心的零度寫作“成為作家面對其新情境的方式,它是一種以沉默來存在的方式。……如果寫作當真是中性的……它在面對著人的空白存在時僅只具有一種代數式的內涵,于是文學就被征服了……不幸的是,沒有什么比這種白色的寫作更不真實的了”。[28]這是因為“把形式等同于數理關系的觀點是絕對站不住腳的……無論怎樣,它們只是方法,只是形式的載體———不是形式本身”。[20]249數學化寫作正是對個體的、浪漫主義的、情緒化的多樣寫作的反抗,它是現代性寫作最后的絢爛。當作品結構從生物式的有機性演變成數學式的“自然客體”,敘事便無法再用具有“生命”的有機體來形容,取而代之的是佩雷克的“棋盤”,卡爾維諾的“晶體”或博爾赫斯的“迷宮”等等,敘事從思想的線條變成客觀的網格,展現出另一種“非人化”景觀。如阿多諾所言:“在藝術史上……當藝術與數學的關系如此密切之時,我們可以說藝術早已意識到其演繹推理的層面。……藝術將自己安置在經驗目的的領域之外。藝術越是不受邏輯的制約,它就越會直接地趨向于制造虛假的邏輯性印象的那些預先設立的風格,也就是說,有個性的作品在這里將輕易地跳過邏輯派生這一過程。”[20]239-240數學或物理的推演代替了文本的自律性結構,“在不能推想有機體本身有自覺的、有目標的活動的時候,人們就想出另一種飄浮于有機體之上的、追求一定目標的實體來指導有機體的活動”。[29]雖然如此,這些文本讀起來仍是小說,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非文學文體的借用,迫使小說以非傳統的方式現身。
三、跨文體的敘事
狂歡數學式的結構有種生硬的隔離感,古希臘就將數學視為形而上學的實體,是一種外在于人的東西。作家在尋找更具人性的敘事規則時,注釋體與辭典體等小說文體應運而生。與日記體、書信體不同,這類文體并不直接影響敘事內容從而更具客觀性。而與數學規則相比,它又需要讀者參與才能完成文本,敘事塑形本身不再是一種自在或既定的東西,而具有了某種動態的交互性。納博科夫于1962年出版的《微暗的火》在對一首999行的長詩所做的繁瑣注釋中呈現出小說內容。閱讀時需要讀者通過反復對照,自行在頭腦中構成故事。作者建議:“盡管注釋按常規全部給放在詩文后面,不過我奉勸讀者不妨翻閱它們,然后再靠它們相助翻回頭來讀詩,當然在通讀詩文全過程中再把它們瀏覽一遍,并且也許在讀完詩之后第三遍查閱這些注釋,以便在腦海中完成完整圖景。”[30]而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則采用辭典的形式,用67個詞條講述了哈扎爾王國興衰的歷史。辭典的閱讀方式自然與眾不同,“讀者可以按自己認為便利的方式來查閱。一些讀者可像查閱任何辭典那樣查閱他們在彼時彼地感興趣的名字和辭匯,另一些讀者可把這本辭典看做一本書,從頭至尾一口氣看完,從而獲得關于哈扎爾問題以及相關的人物、事件的完整概念。……純按讀者意愿,你可任意翻開一頁,便從那里讀起……每個讀者可以像玩骨牌或紙牌那樣自己動手來編輯一本屬于他自己的完整的書”。[31]此外,胡利奧·科塔薩爾的《跳房子》和約翰·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等小說也具有情節上的多向選擇性,書中也給讀者做了相似的推介。作者們建議的諸種閱讀方法仍是作者傳統權威的顯現,但這種“余威”很快在20世紀60年代末解構主義的漩渦中消弭,取而代之的是巴特的“作者之死”或福柯視作者為“一套話語系統”,闡釋權從作者完全轉移到讀者。無論是巴特對《薩拉辛》的闡釋,還是希利斯·米勒對《俄狄浦斯王》的解讀,都忽略了作者的設定,示范“可寫的文本”是如何由讀者生成的。盡管如此,“可寫的文本”與“理想文本”仍差距甚遠,“理想之文本內,網絡系統觸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統,均無等級;……諸意義系統可接收此類絕對復數的文本,然其數目,永無結算之時,這是因為它所依據的群體語言無窮盡的緣故”。[32]事實上,這種理想已然在文體交互中,某種程度上由敘事文本自身實現了,它進一步從有限的既定選擇進化為無盡的網狀結構。法國作家馬克·薩波塔的《第一號創作———隱身人和三個女人》被稱為“撲克牌小說”,因為小說為單面印刷且沒有裝訂和標注頁碼,閱讀之前讀者可以將未裝訂的151張書頁任意“洗牌”,這種排列組合可達驚人的10236。無獨有偶,英國作家B·S·約翰遜的《不幸者》是第二部被稱為“撲克牌小說”的作品。全書173頁共27章,小說除了開頭和結尾兩個章節固定以外,其他25章的順序可隨機排列,讀者任意進行閱讀。兩本小說看起來也和撲克牌很像(見圖5),它們可謂后世超文本小說的鼻祖。與《第一號創作》不同的是,《不幸者》的書頁并不是每一頁完全獨立,這在很大程度上使情節的連貫性加強了。《不幸者》并不能完全打破故事序列,小說非常易讀,而且有一個很強的故事線條,這幾乎無視了作者自己的原則。因此,讀者對情節的理解并不會產生太大的差異。“《不幸者》中很強的敘事線條與約翰遜最重要的理論聲明形成對照,建立時序并賦予事件以意義的需求遍及小說。這是書寫故事和否定約翰遜聲稱的現實范式的關鍵。”[33]可以把《不幸者》看作一種向古典敘事的回歸,而《第一號創作》則與線性敘事斷裂得更加徹底。相對于故事,我們更關注它們的形式。這種隨機性所生成的故事可能無法進行交流,因為每個讀者讀到的順序不同,領會到的故事也就不同。每一次閱讀都有可能生成一種結局,只不過讀者同時認識到這種結局不過是無數可能性中的一種,判定某一個結局的合法性是毫無意義的,這種文本的虛無主義是由相對主義造成的。純粹的撲克牌小說放棄了作者對文本的掌控,讀者失去了既有參照,不知故事該從何處開始又該在哪里結束。這是“置于迷失之境的文,令人不適的文(或許已至某種厭煩的地步),動搖了讀者之歷史、文化、心理的定勢,鑿松了他的趣味、價值觀、記憶的堅牢,它與語言的關系處于危機點上”。[34]23“悅的文”具有“社會性”,閱讀起來是快適的,而“醉的文”則是一種脫離主體的“中性之物”,它并不在乎讀者,“在讀者在場的情況下,作者不可能進行廣義上的寫作,尤其是當作者是為了寫作而寫作,當寫作本身就是目的的時候,作者只能在讀者不在場的情況下寫作”。[35]同時“醉之文”也不再受作者控制,因為“作者已死”。失去了所有主體,文本就拒絕闡釋,所以“醉不可說,受禁、處于言說之間”,[34]27而鮑德里亞則提醒,“消除了主體,會滋生麻木不仁的意識而不是參與意識”。[36]的確,沒有人愿意花費一輩子的時光讀那本永遠也讀不完的撲克牌小說。文本主體的缺席意味著傳統闡釋的無效性,而傳統的“闡釋也并不總是奏效。今天眾多的藝術實際被認為是受了逃避闡釋的鼓動。為逃避闡釋,藝術可變成仿擬”。[37]8撲克牌小說恰是仿擬極佳的例證。這類后現代意義上的小說“一般拒絕任何解釋,它提供給人們的只是在時間上分離的閱讀經驗,無法在解釋的意義上進行分析,只能不斷地重復”,[21]288重復就是形式的某種增殖。博爾赫斯曾經在小說中想象過一種“沙之書,因為那本書像沙一樣,無始無終。……這本書的頁碼是無窮盡的。沒有首頁,也沒有末頁。我不明白為什么要用這種荒誕的編碼辦法。也許是想說明一個無窮大的系列允許任何數項的出現”,[38]這與巴特“醉之文”的設想十分近似。撲克牌小說的出現為實現這種設想提供了機遇,它“拓展了小說(fiction)一詞的范圍,使它不再囿于文字意義上的小說(no-vel),而是直接在普通世界里找到自己的立足點。(使某種理念)‘物質性’和‘具體化’”。[39]①隨意移動撲克牌小說的頁碼,在內容上沒有太大變動,應被關注的是文本自身的形式變化。如果把古典敘事結構看作一種為內容而存在的形式,那么撲克牌小說中的情節則成了為形式而存在的內容。①情節內容與結構塑形的關系逐步反轉,形式不再依附情節,具有了獨立的審美價值。桑塔格強調:“需要更多地關注藝術中的形式。如果對內容的過度強調引起了闡釋的自大,那么對形式的更廣泛、更透徹的描述將消除這種自大。……最好的批評,而且是不落俗套的批評,便是這一類把對內容的關注轉化為對形式的關注的批評。”[37]9-10因為只有形式本身才具有更突出的美學價值,內容不過是形式的累贅和附庸。這些源于游戲的敘事形式并不是傳統意義上對敘事情節的圖形化映射,而是讀者閱讀的可能蹤跡。形式獲得獨立和最大自由的同時,敘事塑形也就達到了印刷文本所能承載的極限。而這種“高級的藝術形式”同樣是有問題的:“低級的是自律性藝術。中等類別的藝術作品將一種顯而易見的形式虛飾置于其不完全的整體之上……最高級的藝術超越總體而趨向于片段狀態。形式的困境在結尾時所遇到的困難中大量顯現出來。……形式的整一性在現代已經是很成問題的了。騙人的無限性,實則是難以了結的無能性,被如此這般地轉變成一種自由選擇的方法和表現原理。”[20]147自由選擇伴隨著事件間時間性與因果性的退場,傳統意義上的情節和故事也就淡化了。如利科所說:“拒絕連貫話語始終是可能的。……運用于敘事領域,這種拒絕意味著一切敘述范例的消亡,敘事的消亡。”
四、新媒介的敘事契機
對敘事邏輯性的反抗必會導致一種發散性的、無中心的、網絡性的、無終結的傾向,其邏輯顯現為對連貫性的否定。這個意義上,現代與后現代敘事是一致的。不同之處是,現代敘事是刻意對形式進行反叛性地加工,而后現代則以隨意的方式來展示它對形式的不以為然。“后現代主義小說中的情節,經常要么少得可憐,要么多到瘋狂”,[41]以此使事件產生各種可能性和不確定性。然而情節的淡化并不意味著敘事完全消失,利科的預言為時過早,拒絕連貫話語只是跨入了冥界之門的垂死,材料與形式的決裂才讓敘事真正陷入死亡的地獄。利奧塔論及“后現代之后的藝術”提到:“材料是某種非目的性的東西,它沒有被命定,它完全不是以填充某個形式和使之現實化為其功能的材料。應該說,被這樣設想的材料本質是未出面的、未面對精神的東西。……藝術對精神無所求……物是一種不能呈現于精神的呈現,它總在擺脫精神的控制,它不向對話和辯證法開放。……(這種)藝術思維,它不是無交流的思想,而是無概念交流的思想。……這種交流性是作為一個愿望而不是作為一個事實,正是因為它被假設為原初的、本體的、脫離交流活動的。它不是一種可接受性,而是某種自控自成的東西”。[42]109-142藝術理念脫離了藝術實踐,這揭示了米勒認為“理論的興起與狂歡恰恰證明了文學與藝術的衰落與死亡”的深刻原因,[43]也成了黑格爾藝術哲學終結論的又一個新注腳。我們不得不追問“一種不以既定思維,而是以自發的、自由的、隨心所欲的形式實現的藝術會是什么呢?當它與呈現相關時,當呈現本身顯現為不可能時,藝術與精神還有什么聯系呢?”[42]137就敘事來說,那就會存在一種不可呈現之“事”,完全沒有思維限定的敘事是根本不存在的,那種敘事只能以被“他者”言說的方式“在場”。如果說,現代敘事的特征是困難的形式,那么利奧塔所論的后現代之后則是形式的困難。利科也注意到敘事“完全跳出一切范例期待之外是不可能的。……拋棄時間順序是一碼事,拒絕任何塑形的替代原則是另一碼事。敘事不要任何塑形是不可設想的”。[40]37那么利奧塔式的敘事終結不過是一種假死,因為那種情況根本不可能發生。利科樂觀地認為:“情節變形在某處遇到一個界標,超過這個界標,就再也認不出把講述的故事變成一個統一和完整故事的時間塑形的形式原則。然而,不論怎樣,或許必須相信協調需求如今仍然在建構讀者的需要,相信我們尚不知如何定名的敘述形式正在誕生。這些新形式將證明敘事功能可以改變但不會消失。”[40]45這恰符合黑格爾的論證邏輯,“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利科的這種期許仍然是以敘事形式的再塑形為鋪墊的,敘事形式與讀者需要之間的協調使敘事的功能得以保證。然而“藝術代表了人文價值在人類文明中最后一片飄搖的立足之地———藝術本身對文明已經嗤之以鼻。而這只體現在藝術作品的形式上。由于藝術內容不可避免地反映著周遭的物化世界,它無法提供持久的救贖資源”。[44]如今圖像文明的文化工業中,敘事形式的發展已讓位于構筑敘事幻象的需要。“在得到了技術支持的敘事中進行的各種各樣的實驗,美妙而大有前途,但卻沒有給經久不變的敘事結構帶來一場革命,甚至微小的變化……超媒體敘事和數碼敘事……將在未來成型和發展……不會發生變化的是我們永遠參與的事情:因果鏈。……大約90%的CD和網絡敘事都是復制書和電影產業,愛情和復仇的線性故事仍然有增無減。不妨贅言,敘事的未來似乎就是敘事的過去。”[45]531-532這個未來我們似曾相識。從本質看,“在今天大眾傳播的層面上,語言信息幾乎存在于所有圖像之中……侈談‘圖像文明’并非十分恰當,我們仍然并且前所未有地處于文字文明之中,因為文字和言語依然是信息結構不可或缺的要素”。[46]也就是說,語言敘事的幽靈正在新媒體上游蕩,建立凌駕于其他媒介之上的權威。例如,語言敘事與繪畫較早地建立了聯系,這恰恰制約了繪畫本身的發展,在西方直到印象派繪畫在題材上才逐漸擺脫對語言敘事的深度依賴。新媒介與現實世界間相似性的提高并沒有使敘事形式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反而使人更容易被故事情境吸引,甚至無法區分現實與虛構而被“仿像”世界包圍,這是敘事語言最終的“完美的罪行”,它以非刻意的方式影響著我們的世界。因為“在每一幅影像的背后,上帝早已消失。他沒有死,他只是消失了。也就是說這個問題沒必要再提。它已通過虛擬解決”。[47]語言就是那位已經“隱蔽的上帝”。另一種新媒介敘事的傾向是超文本敘事。敘事利用電腦鏈接進行,使前文提到的撲克牌式的敘事狂歡日常化,鏈接就是超文本的常態。它終于實現了理論家們“可寫的文本”“文本網絡”的理想,但那“是否意味著任何兩個事件,只要按順序排列就能組成故事?從理論上講,答案應該是肯定的……時間順序本身是個很不嚴密的環節。不過它卻意味著所涉及的事件應該發生在同一個被描述的世界……時間連接就要求我們想象出一個能讓這兩個時間同時并存的世界”。[40]34-35事實上,利科已經放棄了敘事時間而試圖從純空間角度定義敘事。超文本在本質上是詩歌性的,而非是敘事性的。“鏈接即超文本附加給寫作的那個因素,彌合了文本中的縫隙———文本的位面(lexias)———因此產生了類似于我們用來定義詩歌和詩意維度的類比、隱喻和其他思維形式、其他比喻的效果。”[48]如果追問“什么時候敘事不再是敘事而是別的東西?……當線性敘事讓位于抒情敘述時,也就是說,當話語的吸引力———審美的或抒情的吸引力———犧牲故事而引起人們注意的時候。……像喬伊斯的《下午》這樣的被動的互動式超文本虛構中……伴隨著故事的消失,伴隨著向詩歌狀態的運動”。[45]534-537我們已無需再對敘事與否進行精確的二元劃分,而“將所有敘事視為模糊的集合,將敘事性視為一種分級屬性,而不把心理表征分成故事與非故事的僵化二元特征。……贊許基于認知而非基于言語的敘事界定”。[49]敘事的定義并不像看上去那樣重要,“問一個對象是否‘是’敘事既是十分明了的,也是毫無用處的,就像一個形象‘是’視覺的這樣一個概念并不一定要求對那個對象進行視覺的分析一樣”。[50]超文本挑戰的并不是敘事,而是對敘事的界定,它就是那種難以履行的約伯式的神諭。雖然如此,學者們仍對技術抱有信心。“新敘事媒介最富于野心之處是整個系統都具有潛在的敘事可能。對數字環境特征最充分利用的形式并不是超文本或電子游戲,而是模擬技術:充滿著的相互聯系實質的虛擬世界,是一個我們在體驗過程中能夠進入,操控和觀看的世界。”[51]這種技術是要將虛擬影像、超文本技術以及游戲互動結合在一起,并且具有一種“主動的互動性”。而傳統意義上,“互動敘事(interactivenarrative)這一名詞存在固有的內部沖突。敘述從根本上說是線性的,而且不是交互式的;互動故事體現了不同于故事敘述的特征。……互動敘事的關鍵挑戰是用戶主體與作者對故事的控制之間的沖突。……在基于計算機的故事和游戲中,‘互動敘事’概念的流行頗令人驚異……這又是所謂‘互動性神話’在作祟”。[52]在游戲中,其實“故事敘述在玩家眼中可有可無,游戲中的故事和色情電影中的故事一樣,不能沒有,但完全不是重點”。[53]105互動性和敘事性沖突抵牾,只有通過“主動的互動性”來打破這種僵局。傳統故事中的故事元素都是在為戲劇性轉化做鋪墊和準備,而真正的互動敘事中,“為戲劇性發展做出鋪墊的不是故事的作者而是讀者本身……要通過一系列的‘動詞’驅動讀者對故事的發展,為令人滿意的結局逐步建立起所需要的上下文”。[53]46那么提供給讀者的就不會是那幾個屈指可數的關鍵性選擇,而是許許多多微小的選擇,故事內容本身也會根據讀者的選擇“主動”發生變化。互動敘事最終回到了讀者自身,“完全由玩家驅動的故事(fullyplayer-drivenstories)其實不能算作故事,游戲并不包含任何傳統意義上的故事情節”。[54]換句話說,讀者或玩家并沒有意識到故事,他只是在“經歷生活”。“真正用媒介思維的作品并不思考媒介,因為它激發讀者本身去思考。”[45]516我們將回到一個活在故事中的史詩時代。“史詩中,意義的生活內在性如此強大,以至于取消了時間:生活進入了生活的永恒……小說中,意義和生活隔離,因此恒常的本質與幻變的時序才彼此分離。”[6]122互動敘事乃是對史詩的某種回歸,史詩本質上只是一種記憶的方法,而非某種“敘事性的”主觀刻意,敘事的限制就是人自身的本性。如果將生活以互動敘事的方式進行言說,那么就“沒人能使用所有這些語言,這些語言沒有共同的元語言。……大多數人已經沒有了對失去元敘事的懷戀。這并不意味著將退回野蠻。之所以避免了這種現象,是因為人們認識到合法化只源于自身的語言實踐和交流才能”。[55]史詩必須一次次地面對面傳唱,互動敘事也只有在交流實踐中才能實現。總之,我們回到了生活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仍然可以說“故事的過去就是故事的未來”。這是一種“活”的敘事,其有機性在于話語的涌現或生成,而不是傳統敘事僵死的結構。新的敘事正在技術發展中生成,這可能是柏拉圖式史詩敘事復興的契機。敘事塑形或許會再次模糊或隱身,但敘事的邏輯性并不會完全消失,因為“雖然邏輯性強調形式原則,但藝術作品正是通過其自律性的形式律與邏輯性相抗衡。假如藝術與邏輯及因果關系絲毫無涉的話,那它將會是一種與他者毫無關聯的無聊運動;假如藝術對邏輯及因果關系過于刻板的話,它就會屈從于邏輯的魔力。能使藝術擺脫這種魔力的不是別的什么東西,而是藝術本身導致的永久的雙重性沖突”,[20]143敘事在自律與他律間發展。海德格爾和鮑德里亞的提醒言猶在耳,互動技術形成的新敘事究竟是技術支配人類所使用的更加完美的罪行,還是未來敘事的應許之福地,我們還需探究。
作者:李森 單位:南京藝術學院人文學院
- 上一篇:對天下與中國模式的反思范文
- 下一篇:財務風險論文(4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