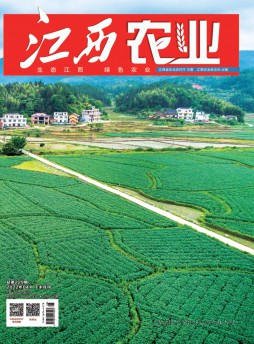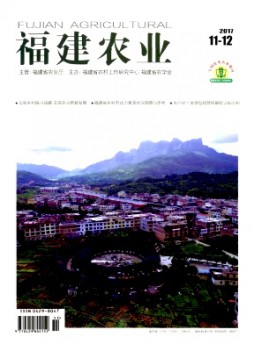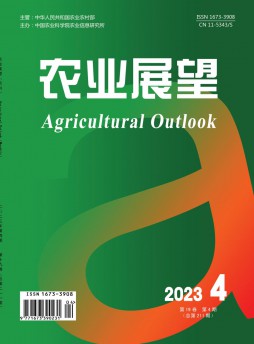農業經營模式的優化路徑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農業經營模式的優化路徑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農村經濟雜志》2014年第五期
一、邏輯主線:農業機械化———雇傭關系———土地流轉
農業生產既是農作物利用陽光、降水等條件的自然生長過程,也是勞動者運用生產資料作用于土地的社會生產過程。生產資料(如種子、化肥、農藥、機械等)、勞動力、土地是農業生產的主要投入要素。現有家庭經營模式下,種子、化肥、農藥、機械等生產資料從市場上用貨幣購買,可以統一表示為資本;勞動力由作為產品索取主體的家庭成員提供;土地由集體所有,通過承包,家庭獲取了土地的自主經營權。因此,從生產要素角度出發,我國傳統農業可以向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土地密集型方向演進,推廣農業機械化、發展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是其演進的可行性路徑。
1.農業機械化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國二、三產業對勞動力需求急劇增加,種子、化肥、農藥、機械等生產資料的供給能力大大增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相對價格變化引起了農業生產要素結構的調整,如勞動力流出,資本流入。農業生產要素的密集度也發生變化,如勞動密集度下降,資本密集度上升。農業機械化實質上是用資本代替勞動力,將農業的勞動力密集型屬性改造成資本密集型屬性。然而,我國尚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工業對能源和機械需求量大,煤炭、石油、鐵礦石等長期處于供不應求狀態,價格偏高;制造機械、使用機械和維修機械的工用勞動本身也處于一種短缺狀態。農用勞動與工用勞動的價格差是勞動力流出的內在動力,而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則隨著可流動性下降而遞減,農村中不可流動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幾乎為零。農業機械化帶來的資本排擠勞動力,必然導致農村中不可流動的勞動力失業,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時,農業各個生產環節依次繼起而非并列,具有明顯的季節性。生產周期長且各環節使用不同的生產資料,將導致農用機械投資總量大、使用頻率低,生產成本難以得到有效分攤。我國的農產品市場已接近飽和狀態,大規模投資帶來的產量增量將打破市場原有的均衡,進一步拉低農產品價格。現有資源稟賦下,我國農業機械化實質上是以稀缺的資本要素代替豐裕的勞動力要素來生產已經相對過剩的農產品,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同時必然進一步降低其經濟效益。可見,現階段我國農業機械化難以大面積推廣,傳統家庭生產模式仍將是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
2.勞動力市場:雇傭關系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農民擁有勞動力供給主體和產品索取主體雙重身份,承擔著生產和監督雙重職能。農業生產所得減去生產資料購置成本后的凈收益,是對農民雙重身份的統一回報。作為勞動力供給主體,農民承擔勞動力供給的全部成本,作為剩余索取主體,農民獲得勞動供給的全部收益。因此,家庭生產模式為勞動力供給提供了自動激勵機制。然而,在農村勞動力市場的雇傭關系中,產品索取權歸雇傭者所有,被雇傭者僅僅作為勞動力供給主體而存在。沒有產品索取權的激勵,被雇傭者往往滋生機會主義傾向,勞動力供給扭曲性地減少。盡管勞動力供給扭曲性減少會受到雇傭者監督努力的制約,但是雇傭者的監督努力并不是無成本行為,而是在其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處達到均衡。被雇傭者的“偷懶行為”在監督努力的作用范圍之外依然存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生產決策必須在現場做出,否則信息不足。然而,農業活動的勞動空間范圍廣、勞動強度大,被雇傭者偷懶的動機十分強烈;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也難以程序化,監督十分困難。同時,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對勞動力需求往往集中于某一時段,需求的時際波動大;生產環節之間的時間間隔長,各個環節對農用勞動力的需求呈現離散狀態。農村現有勞動力的可流動性差,難以跨區域流動。因此,農村勞動力市場具有明顯的區域性,雇傭關系也只能以零工、散工方式出現。監督困難、偷懶行為和勞動力的時際離散需求大大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市場效率。3.土地市場:土地流轉土地流轉,即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是指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以一定的條件將土地經營權轉讓給其他
農戶或經濟組織。流轉后的土地,仍然只能用于農業生產,不能用作房地產開發等其他用途;農民依法享有土地流轉權益,如租金、股份分紅等。土地流轉后,相當于實行“三權分離”,經營權歸受讓方,承包權還是歸承包農戶,所有權也還是屬于集體。我國人多地少,耕地面積有限,流轉后的土地仍然用于農業生產,有助于保證農用耕地的數量和質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家庭是基本的生產和生活單位。土地的流轉,進一步強化了家庭作為基本生產單位的天然優勢:農業生產的產品索取權對家庭所有成員提供充分激勵,可以有效抑制機會主義和偷懶行為。土地流轉代替勞動力雇傭,一方面,通過保留索取權的自動激勵機制,避免了雇傭關系帶來的監督成本和勞動力供給的扭曲性減少;另一方面,土地由弱生產能力家庭向強生產能力家庭的轉移,重新實現了土地和勞動力之間的合理匹配。土地流轉有效激活了農村生產要素市場,農民可以在轉讓土地要素和出售農產品之間做出選擇,農用勞動力不足的家庭,從自給自足的角度出發,通過轉出土地,實現橫向生產規模的收縮和縱向銷售環節的退出,變傳統的出售產品為轉出土地,從而有效防止“農產品賣難”問題;轉入土地的家庭則以市場為導向,通過橫向生產規模的擴張和縱向銷售環節的延伸,實現農業經營的規模經濟。細碎化土地的有效集中,一方面,可以實現更大范圍內生產活動的協調,避免農活之間的“負外部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行為個體對公共資源(如水資源)的“攫租行為”,實現公共資源的合理利用。土地流轉,有助于充分發揮土地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雙重功能,實現轉出方和轉入方的互利共贏,因而是一種典型的帕累托改進。
二、基本結論
本文通過把農業生產要素細分為資本、勞動力、土地,闡釋推廣農業機械化、發展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是農業經營模式演進的可行性路徑,從而形成了“農業機械化———雇傭關系———土地流轉”的邏輯主線。在分析我國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資源稟賦現狀的基礎上,指出農業機械化實質上是以稀缺的資本代替豐裕的勞動力來生產相對過剩的農產品,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同時必然降低其經濟效益;通過分析農業生產必須現場決策的行業屬性和勞動力市場需求的時際和區際屬性,進一步揭示:突破農業經營家庭模式,監督困難、偷懶行為將不可避免,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績效將被大大侵蝕。然而,土地流轉則既維持了家庭模式提供的農產品索取權的自動激勵機制,又重新實現了土地和勞動力的有效匹配,因而是家庭經營模式的優化路徑。
作者:高鵬傅新紅單位:四川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 上一篇:農村空心化形成機理范文
- 下一篇:創業教育發展教育論文5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