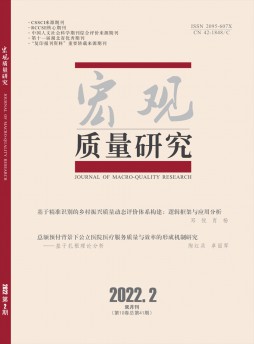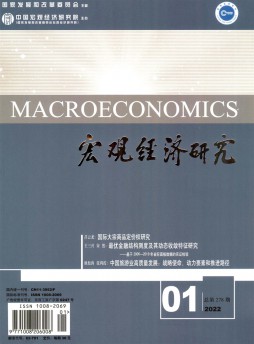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相關文獻述評
Gaggl和Steindl(2007)、Steindl和Tichy(2009)、Priesmeier和Sthler(2011),以及盧二坡(2008)對宏觀波動影響經濟增長的文獻進行了綜述,曹永福(2007)則綜述了美國經濟“大緩和”及其成因的相關文獻,以下結合其他學者的研究分別進行概述。
(一)國外有關宏觀波動影響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通過將“技術創新”和“干中學”等內生經濟增長因素納入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及其拓展模型,可從理論上解釋經濟增長與宏觀波動的關系,但既有研究并無定論。主要包括:(1)標準封閉式經濟增長模型認為,資本積累推動經濟增長,但宏觀波動對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兩面性:波動及不確定性一方面會加大家庭預防性儲蓄和投資,且更高的風險規避度和跨期替代彈性予以強化(Jones等,2005a、2005b;Wang和Wen,2011);另一方面,不確定性也會導致經風險調整的預期回報率下降并減少投資(Kebs,2003)[10]。(2)考慮“創造性破壞”機制的模型認為,企業在衰退期會因機會成本更低而加大研發投資,且優勝劣汰提升生產率,宏觀波動和經濟增長正相關。該結論要求金融市場完備,但融資約束使企業在衰退期面臨更大流動性風險,會削減投資,經濟增長與波動可能負相關(Aghion等,2010)[11]。該理論認為創新投資有逆周期性也受到質疑(Barlevy,2007)[12]。(3)考慮“干中學”機制的模型強調人力資本和知識積累在生產率提升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在衰退期,雇傭率下降,宏觀波動和經濟增長負相關(Martin和Rogers,1997)[13]。但考慮知識積累函數呈邊際收益遞增時,經濟增長與波動可能正相關(Canton,2002)[14]。(4)其他更復雜的研究認為,理論模型選擇、參數設定、沖擊的不同類型等均影響經濟增長與波動的相關性(如,Annicchiarico等,2011;Annicchiarico和Pelloni,2014)。
(二)國外有關宏觀波動影響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少數宏觀波動影響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利用行業或地區面板數據(如,Imbs,2007),大量研究則基于跨國宏觀面板數據和國別宏觀時間序列數據進行,但同樣沒有一致性結論:(1)基于跨國面板數據的多數研究認為,宏觀波動對應的不確定性導致資源錯配,并阻礙經濟增長(Ramey和Ramey,1995;Norrbin和PinarYigit,2005)。也有研究認為,宏觀波動與經濟增長表現為與“風險-收益”類似的正相關(Grier和Tullock,1989)[20]。(2)基于國別時間序列數據的實證研究一般采用各種GARCH-M模型進行,有研究認為,在美國、英國、日本等G7國家,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Fountas和Karanasos,2007)[21];但Bredin等(2009)、Bredin和Founta(2009)卻發現,在部分亞洲和歐盟國家,宏觀波動和經濟增長負相關;還有研究認為,在美國、日本及其他OECD國家,產出波動和經濟增長無顯著相關性(Grier和Perry,2000;Wil-son,2006)[。(3)部分研究認為,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階段性,非對稱性和非線性特征:少數研究關注經濟發展階段對“宏觀波動-經濟增長”關系的影響,如Kose等(2006)認為貿易和金融一體化顯著弱化了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負效應[26];Koren和Tenreyro(2007,2013)認為[27]-[28],隨著一國經濟發展,經濟結構將轉向波動更小產業,且投入趨于多元化,運用熟練技能和技術的廣度趨于深化,沖擊引致的波動更低,經濟增長與波動因此負相關。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還有非對稱性,如:Neanidis等(2013)發現G7國家的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主要存在于低增長狀態,但Henry和Olekalns(2002)、Kim和Kim(2010)卻發現美國宏觀波動在繁榮和衰退期分別對經濟增長有正、負效應[30]-[31]。研究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還需考慮二者的非線性特征,如:Fang和Miller(2008、2009)采用帶結構突變點的GARCH-M模型[32]-[33],證實了在日本和美國,經濟增長與其波動無顯著相關性。但這一結論并不穩健,如:采用類似方法,Fang和Miller(2014)發現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在美國、日本等國家顯著[34]728;Fang等(2008)選取美國、日本等6國為研究對象,卻發現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顯著影響僅在日本存在,且為負相關。
(三)中國宏觀波動影響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利用各種GARCH-M模型和宏觀數據的研究:基于月度數據,劉金全、張鶴(2003)證實了產出波動與經濟增長正相關[36]32,Laurenceson和Rodgers(2010)也認為二者正相關或不相關,但不存在負相關。基于年度數據,劉金全等(2005)認為產出波動與經濟增長正相關[38]5,徐偉(2013)、李永友(2006)則分別認為二者有顯著或不顯著的負相關性[39]54,[40]8;盧二坡、呂介民(2012)還證實了產出波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衰退期為負、繁榮期為正。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研究:杜兩省等(2011)認為產出波動與經濟增長顯著負相關[42];盧二坡、王澤填(2007)證實了二者在改革開放前負相關,而后在多數省份表現為正相關。盧二坡、曾五一(2008),陳昆亭等(2012)則分別將改革開放前后產出波動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差異歸因于市場化進程加快,以及教育投入和人力資本積累增加。此外,邵軍、徐康寧(2011)發現,經濟向下波動反而促進技術進步,支持“創造性破壞”的觀點。
(四)國內外宏觀波動“大緩和”的相關研究美國及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宏觀經濟波動于20世紀80年代后相繼進入“大緩和”時期,究其成因,大致包括外部沖擊減弱、信息技術與庫存管理改善、經濟結構轉向波動更小的產業、貨幣政策的成功運用、金融創新與金融市場完善、技術進步與全要素生產率波動下降等多個方面(曹永福,2007)。此外,次貸危機盡管導致工業化國家宏觀波動快速而短暫攀升,但仍于2010年初回落,“大緩和”仍將持續(Clark,2009;Charles等,2014)[47]-[48]。就中國而言,劉樹成(2000)較早認為經濟波動將從大起大落轉向微波化[49],并認為從21世紀開始,經濟波動將表現為適度高位平滑化特征(劉樹成等,2005)[50]。劉金全、劉志剛(2005)發現,產出波動于1997年前后表現為“凸型”特征,并伴隨投資、政府支出和凈出口波動降低[51]。張成思(2010)發現,經濟增長、通脹、貨幣供給、有效匯率等宏觀經濟變量波動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均發生顯著結構性轉變[52]。林建浩、王美今(2013)證實了“大緩和”在次貸危機前中斷,且于2010年初重返“低波動、高增長”狀態。大量研究還認為,結構性沖擊減弱、貨幣政策更為完善、國際貿易發展,以及市場化進程等因素均有助于解釋中國宏觀波動“大緩和”(如:雎國余、藍一,2005;殷劍鋒,2010;萬曉莉,2011;洪占卿、郭峰,2012;He等,2013;He,2014)。
(五)文獻簡評綜上所述,融合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盡管認同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其相互關系受到諸多因素制約,理論研究并無定論。由此,從客觀數據出發,探究宏觀波動影響經濟增長的經驗證據尤為重要。然而,實證研究同樣無法給出一致性答案,特別的,與本文研究對應,既有基于國別宏觀數據的研究在以下方面有待完善:(1)國內研究在經濟增長指標和數據頻率的選取方面并不恰當。Statsny和Zagler(2007)指出[59]2,利用時間序列數據考察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影響時,廣為采用的GARCH-M模型需注意:其一,與其在金融市場運用一致,應采用高頻數據“捕捉”波動集聚性;其二,樣本區間應足夠長,以避免待估參數較多導致的結論不穩健。從國內研究來看,少數學者采用年度和季度GDP數據度量經濟增長,數據頻率相對較低,樣本區間也相對較短;還有研究將季度GDP增長率分解為月度數據,盡管滿足“高頻”需求,但并沒有增加有效信息量。(2)Statsny和Zagler(2007)認為[59]3,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應考慮序列結構突變,但國內研究并未加以關注,由此導致波動平穩性和持續性的誤判。如:劉金全、張鶴(2003)選取GARCH(1,1)模型描述經濟增長條件方差[36]34,α1和α2分別為0.8150和0.4489,波動持續性參數(α1+α2)>1;劉金全等(2005)采用ARMA(1,2)-ARCH(1)-M模型描述經濟增長與宏觀波動關系[38]7,α1=1.6380>1,條件波動均不平穩。又如:李永友(2006)用GARCH(1,1)模型刻畫經濟增長波動[40]12,(α1+α2)高達0.99和0.97(分別以GDP和人均GDP度量經濟增長),選用TGARCH(1,1)模型時(α1+α2)則為0.92和0.95;徐偉(2013)選取ARMA(1,2)-GARCH(1,1)和ARMA(1,2)-GARCH(1,1)-M模型刻畫宏觀波動與經濟增長關系[39]56,(α1+α2)的估計值也分別高達0.99和0.95,即宏觀波動均表現為高持續性。(3)既有國內外研究均未關注到“宏觀波動-經濟增長”關系的階段性特征,以及次貸危機對此的影響,因而無助于后危機時代重新審視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少數國內外研究關注到經濟發展階段、高低增長狀態,以及改革開放、全球化、市場化進程等對“宏觀波動-經濟增長”關系的影響,但均未界定經濟周期并分階段予以考察。Fang和Miller等學者在結構突變點分析基礎上考察了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結論并不穩健甚至前后矛盾,可能的原因是:盡管區分了經濟增長與宏觀波動各自的階段性特征,但并未考慮到二者關系也會呈現出階段性差異,即二者不存在全樣本區間內、一致性的正相關或負相關。(4)如何結合高頻數據判定經濟增長及其波動的結構突變與階段性特征,國內學者也未予以關注。既有國內外研究均認同宏觀波動“大緩和”的存在,且次貸危機僅造成短暫沖擊而未改變波動平穩化趨勢。就檢驗數據來看,相關研究多基于季度GDP增長率進行,但國內數據樣本量相對偏少,選取月度增長率指標不但能極大拓展樣本容量,且能對比檢驗既有研究結論的穩健性,也能為考察“宏觀波動-經濟增長”階段性關系提供有力支撐。針對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選取1993年以來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月度同比增長率高頻數據,結合結構突變分析考察經濟增長、宏觀波動,以及二者關系的階段性特征。論文創新性如下:(1)內生結構突變點判別發現,經濟增長及其波動分別有2個和3個突變點,經濟增長呈現“降-升-降”的分段趨勢,宏觀波動可分為“高-低-高-低”4個時段,這一結論和既有基于季度數據的研究有別,且與直觀圖示和經濟趨勢更為相符。(2)在AR(p)-GARCH(1,1)模型中納入上述均值和條件波動突變啞變量,可“捕捉”經濟增長序列的高自相關、非正態性,與國內研究不同,宏觀波動的高持續性不復存在。(3)與國內外研究不同,含均值、條件波動雙突變的AR(p)-GARCH(1,1)-M模型檢驗表明,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存在階段性影響,在經濟增長趨緩時二者正相關、經濟增長向好時負相關,具體為:宏觀波動整體上對經濟增長有不顯著的負效應;結合經濟增長的分段趨勢,宏觀波動在經濟增長的第一、二階段分別對其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和負效應,在第三階段有不顯著的正效應;考慮次貸危機影響后,宏觀波動在經濟增長的第三階段對其有較顯著的正效應。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設計
本文將基于中國經濟增長的時間序列數據,采用含結構突變的AR(p)-GARCH(1,1)-M模型研究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階段性影響,數據來源與研究設計如下:
(一)數據來源與預處理既有研究認為,改革開放和市場化進程是影響中國宏觀波動“大緩和”及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重要因素,鑒于1992年底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選取1993年1月至2014年12月為實證樣本區間。同時考慮到滯后項影響,在數據預處理時還納入了1992年7月-12月數據,所用數據源于Wind咨詢。選取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月度同比增長率(IPt)作為經濟增長變量,原因如下:有部分研究采用了這一做法;滿足高頻數據要求;有相對較長的樣本區間;符合樣本區間內我國處于工業化階段的事實;通過圖示發現樣本區間內該指標與GDP增長率表現為相同趨勢。數據預處理:(1)因春節影響,工業增加值增長率序列{IPt}的部分1、2月數據值缺失,在此采用三次樣條函數插值予以補全。(2)由于異常點會影響研究結論穩健性,借鑒Fang和Miller(2014)的方法[34]733,對{IPt}序列,利用|IPt-mean|>k.SD來識別異常值(其中mean和SD分別為均值和標準差),一般取k=3,這也符合一般的3σ原則,能基本保證識別出的異常值數量適度。(3)異常點的修正:估計AR(p)-GARCH(1,1)模型,其滯后項階數p由“t-sig”準則確定(選擇最大滯后期為6,顯著性水平為5%,從最大滯后階數開始檢驗,直到滿足顯著性水平終止,以確定對應滯后項階數),再用模型所得預測值替代異常值。后繼研究均基于經異常值修正后的{IPt}序列進行,且主要采用SAS9.1軟件進行數據處理。
(二)研究設計1.經濟增長及其波動序列的結構突變點判別選取Bai和Perron(1998,2003,2000)等提出的方法[60]49-52,[62],并借鑒其提供的GAUSS程序檢驗經濟增長變量及其波動的內生結構突變點。該方法由Bai和Perron(1998)提出[60]49-52,通過全局最小化殘差平方和得到可能的多個突變點,然后據以下統計量加以檢驗:F統計量的上確界檢驗(SupF)、雙極大值檢驗(UDmax和WDmax)、序貫檢驗(SupF(l+1|l))等。Bai和Perron(1998,2003)還考察了這一方法的實際運用問題[60]56-65,[61],并認為:當樣本容量不大時,截斷參數(trimmingparameter)選取較小會導致規模扭曲(sizedistortion);序貫統計量SupF(l+1|l)的檢驗勢最高,但存在多個突變點時,對SupF(1|0)的檢驗往往難以拒絕原假設。因此,在實際應用時,可考慮如下策略:先用UDmax或WDmax檢驗是否至少存在1個突變點,若是,再用SupF(l+1|l)依次檢驗是否存在2個以上突變點。
三、實證檢驗
(一)經濟增長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平穩性分析數據預處理:首先對{IPt}序列進行插值,1992年7月至2014年12月共涉及27個樣本;然后結合3σ原則和AR(p)-GARCH(1,1)模型,判別并修正了5個異常值點。表1列示了經上述修正后的{IPt}序列的初步考察結果(1993年1月~2014年12月)。據表1數據,對{IPt}序列而言:JB統計量表明,1%顯著性水平下拒絕正態性假設;無論是檢驗自相關的廣義DW統計量,還是檢驗異方差的LM和LBQ2統計量,均表明序列具有非常強而顯著的自相關和ARCH效應;采用ADF檢驗平穩性,基于AIC準則判別滯后階數(最大滯后階數設定為6),發現序列基本滿足平穩性條件。以上分析表明,{IPt}序列存在明顯的自相關、異方差和非正態特征,且滿足平穩性要求。可考慮納入序列的結構突變點,運用AR-GARCH類模型進行后繼研究。
(二)經濟增長變量及其波動的結構突變點檢驗主要依據序貫檢驗判別{IPt}序列突變點個數與位置:鑒于樣本觀測數為264,且檢驗式中含有自回歸項,選取截斷參數為0.15并設置最大突變點數為5。判別{IPt}波動序列的突變點時,鑒于檢驗式中無自回歸項,選取截斷參數為0.2,最大突變點數為3。按照t-sig準則,可判別{IPt}序列的最大自相關滯后階數為3(見表1);據此結合前述Step2方法檢驗序列的內生結構突變點,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見:5%的顯著性水平下,純結構突變模型、部分結構突變模型均可檢測出{IPt}序列存在2個突變點。這兩種模型檢測到的第一個突變點較為一致,但第二個突變點存在較大差異。由于純結構突變模型的設置更為靈活,以其所得突變點為準,進行后繼研究。對純結構突變模型而言,所得2個突變點將樣本區間劃分為3個時期,即:1993年初至1998年中,經濟在過熱之后趨于下行(軟著陸);1998年7月至2009年中,經濟增長在筑底反彈之后趨于上升,且因次貸危機沖擊而出現短暫的深度下調與快速的回升;2009年7月至2014年底,經濟增長在后危機時代回落并進入“新常態”。據前述Step3的方法得到{IPt}序列的條件波動,并依據Step4的方法對其進行結構突變點判別,5%的顯著性水平下,得到3個突變點,如表3所示。據表3,盡管SupF(3|2)未通過檢驗,但按照信息準則,BIC和LWZ檢驗均判別為3個突變點,對應統計量值分別為1.10和1.25,均通過5%顯著性檢驗,且序貫檢驗總體上判斷{IPt}序列的條件波動有3個突變點,分別為1997年底4月、2006年4月和2010年8月。這3個突變點將條件波動分為4個時段,期間條件方差均值分別為4.87、1.12、2.90和0.81。結合突變點位置,由圖1可知:伴隨市場化改革進程,經濟增長呈現三階段特征。此外,宏觀波動也呈現階段性“大緩和”特征:從1993年初到1997年中期,伴隨經濟過熱及其治理,宏觀波動處于高位;隨后經濟軟著陸,宏觀波動處于較低水平;受經濟過熱及次貸危機影響,宏觀波動于2006年中之后再次攀升至高位,并于2010下半年開始重新回歸平穩化。由此可見,經濟過熱、外在沖擊等因素增加不確定性,宏觀波動趨高,反之則趨于緩和。從宏觀波動“高”或“低”的4個時段來看:第一、三階段,即波動維持高位的時間不到4.5年;對波動平穩化時期,第二階段為9年,第四階段截止2014年底將近4.5年且預期仍可持續。
(三)宏觀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的階段性影響檢驗首先檢驗考慮{IPt}序列及其條件波動結構突變的AR(p)-GARCH(1,1)模型,并結合殘差分析表明其有效性;在此基礎上估計均值、波動雙突變的AR(p)-GARCH(1,1)-M模型,驗證宏觀波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具有階段性特征;最后基于次貸危機視角,再次考察宏觀波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以證明次貸危機前后“宏觀波動-經濟增長”關系發生了改變。1.宏觀波動與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特征:含結構突點的AR(p)-GARCH(1,1)模型估計結合前述檢驗所得{IPt}序列及其條件波動的結構突變點,估計含均值、條件波動雙突變啞變量的AR(p)-GARCH(1,1)模型。同時選取2組AR(p)-GARCH(1,1)模型進行對照:未考慮均值或條件波動結構突變的一般形式的AR(p)-GARCH(1,1)模型,以及僅考慮均值結構突變的AR(p)-GARCH(1,1)模型。所得結果如表4所示,其中Model3為主要的檢驗模型,Model1和Model2為對照模型,Model4在Model3基礎上剔除了部分不顯著變量。由表4中的參數估計結果,可得如下結論:(1)由Model2~Model4可知,與{IPt}序列結構突變點對應的趨勢參數b、b1和b2均很顯著,且分別為“負-正-負”,很好刻畫了經濟增長“降-升-降”的三階段特征。(2)由Model3~Model4可知,刻畫條件波動結構突變的參數λ1、λ2和λ3較顯著,特別是在Model4中,λ2和λ3在10%水平下顯著。λ1~λ3的符號分別為“負-正-負”,也與{IPt}序列條件波動的四階段特征對應,即:條件波動分別在第一個突變點之后下降;在第二個突變點之后上升;在第三個突變點之后重新趨于下降。此外,b2和λ3的符號表明,后危機時代經濟增長與宏觀波動“雙降”,二者可能因此正相關。(3)JB統計量表明,Model1即一般AR(p)-GARCH(1,1)模型不能保證殘差的正態性,Model2~Model4表明,在均值方程或同時在波動方程中納入結構突變啞變量,可保證殘差正態性。(4)對比Model1~Model4,考察納入條件波動突變啞變量的必要性:對GARCH(1,1)的波動方程σ2t=α0+α1ε2t-1+α2σ2t-1而言,參數(α1+α2)→1表明波動持續性高,一般選用IGARCH模型。但也有研究表明,持續性參數(α1+α2)很多時候被高估。特別的,忽略時間序列及其波動的結構突變,也將導致其波動的高持續性,由此誤用IGARCH模型是不可取的(Mikosch和Stric,2004;Hillebrand,2005;Krmer和Azamo,2007)。由表4數據可知,Model1和Model2的持續性參數分別為0.99和0.98,說明在一般的AR(p)-GARCH(1,1)模型中,即便在均值方程中考慮結構突變,也無法改變波動高持續性現象(IGARCH效應)。一旦在波動方程中納入結構突變參數,Model3和Model4的持續性參數下降為0.65和0.68,說明條件波動的結構突變是導致其高持續性的主因。2.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階段性影響:含結構突變點的AR(p)-GARCH(1,1)-M模型估計接下來考慮{IPt}序列及其條件波動雙突變,估計以下AR(p)-GARCH(1,1)-M模型,以檢驗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表5的部分結果與表4類似:經濟增長及其條件波動的階段性特征明顯,考慮均值與波動雙突變可消除波動高持續性。此外,λ1~λ3的系數之絕對值有所提升,顯著性均有所加強。令人遺憾的是,對于我們所關注的系數δ而言,盡管在4個模型中均為負值(在Model5中絕對值很小),但在10%的水平下無一顯著。說明即便考慮均值和條件波動雙突變(Model7和Model8),也無法檢測到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顯著影響。結合圖1中{IPt}序列及其條件波動的階段性趨勢,導致表5中系數δ不顯著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具有階段性特征。相對于表5中的Model8,表6中的參數估計效果有明顯改進:一方面,δ、δ1和δ2的符號分別為“正-負-正”,且δ和δ1非常顯著,說明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在第一、二階段有顯著的正效應和負效應;在第三階段即2009年7月以后,宏觀波動與經濟增長正相關但不顯著。另一方面,其他均值方程的變量系數仍在5%水平下顯著,b、b1和b2的符號同樣符合預期;值得注意的是,與Model4、Model8相比,波動方程參數的系數也全部顯著;此外,持續性參數λ1~λ3的估計效果良好且符合預期,表征擬合效果的R2也略有改善。3.宏觀波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再檢驗:考慮次貸危機的影響結合圖1可知,源于次貸危機的影響,從2008年6月開始,我國經濟增長急轉直下,與此同時,財政與貨幣政策也迅速轉向,并于2008年底相繼推出四萬億計劃等宏觀舉措,經濟增長也從2009年底開始逐步回歸正常軌道。為考慮上述次貸危機對宏觀波動及經濟增長的影響,當t在2008年6月至2009年12月之間時,定義啞變量Crisis=1(否則為0)。由表7中數據可見:在考慮均值、條件波動雙突變的AR(p)-GARCH(1,1)模型(Model9)中加入Crisis啞變量后,發現次貸危機導致經濟增長顯著下降(φ),均值方程中的其他參數仍顯著,且b、b1和b2的符號符合預期;就波動方程而言,次貸危機對宏觀波動有微弱且很不顯著的正效應(φ),但除GARCH參數外,其他變量系數(包括λ1~λ3)均不顯著,這一結果與表4中的Model4存在很大差別。Crisis啞變量對含雙突變點的AR(p)-GARCH(1,1)-M模型(Model11)的影響:波動方程、均值方程的檢驗結果與Model9基本一致,但參數φ的顯著性趨于下降,條件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δ)仍表現為不顯著的負相關(與表5中的Model8)一致。Model9和Model11中,Crisis啞變量的加入導致波動方程參數估計效果顯著變差,可能的原因是Crisis啞變量與VDk(k=1~3)不相容,為此在波動方程中僅保留Crisis啞變量,并重新估計Model9與Model11,所得結果見表7的Model10和Model12。結果發現:相對Model9而言,Model10中對應參數估計的顯著性有明顯上升,特別的,α0~α2的顯著性大為上升,參數的估計值也由0.08上升到0.51,但仍不顯著(P值由0.90下降到0.26)。Model12相對Model11的比較也存在類似規律,且δ仍為不顯著的負值。進一步結合表6的檢驗模型,基于Model12,考察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階段性影響是否會因Crisis啞變量的加入而有所不同,由此估計如下AR(p)-GARCH(1,1)-M模型。由表8中數據可知:與表6類似,在考慮“宏觀波動-經濟增長”階段性關系之后,主要參數的估計效果大為改善。φ和的估計值及顯著性表明,次貸危機直接導致經濟下滑(期間工業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長率平均約降低1.58%),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漲了宏觀波動上升。與表6相比:δ、δ1和δ2符號并未改變,δ和δ1仍顯著;特別的,δ2的數值與顯著性大幅改善(估計值由0.15升至7.93,P值由0.76降為0.12),表明后危機時代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的正效應。此外,其他波動方程變量、絕大部分均值方程變量的系數仍顯著。
四、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以1993-2014年間工業增加值月度增長率作為經濟增長變量,實證檢驗了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宏觀波動影響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特征,以及次貸危機的沖擊效應,主要結論如下:(1)經濟增長與宏觀波動具有明顯且不同步的階段性特征。運用內生結構突變點判別方法,驗證了經濟增長序列有2個結構突變點(1998年7月和2009年7月),由此劃分的3個時段分別表現為“降-升-降”的階段性趨勢;在此基礎上也驗證了宏觀波動具有3個突變點(1997年4月、2006年4月和2010年8月),對應于波動的“高-低-高-低”4個時段。特別的,宏觀波動于第1個突變點之后趨于“大緩和”,但因經濟過熱和次貸危機引致不確定性增加,于第2個突變點之后再次上升,并于第3個突變點之后重返平穩化階段。從宏觀波動首次步入平穩化、次貸危機短暫沖擊并回復平穩的時點來看,與既有研究有別。(2)納入上述兩類結構突變點影響的AR(p)-GARCH(1,1)及其拓展模型可有效刻畫經濟增長與宏觀波動的階段性特征,同時也很好避免了均值殘差的高自相關性、非正態性。與既有研究不同,模型還能確保條件波動的平穩并克服了條件波動高持續性的誤判。(3)與既有研究不同,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同樣具有階段性特征。考慮均值、條件波動序列同時發生結構突變,采用改進的AR(p)-GARCH(1,1)-M模型,驗證了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僅具有不顯著的負效應;考察宏觀波動在經濟增長不同階段對其有何影響,結果發現,二者在第一、二、三階段分別為顯著正相關、顯著負相關和不顯著正相關。(4)有別于既有國內外研究,通過在傳統AR(p)-GARCH(1,1)-M模型的均值方程和波動方程中分別引入次貸危機啞變量,并考慮經濟增長的突變與階段性特征,結果發現:次貸危機對經濟增長有顯著負效應,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宏觀波動;與此同時,考慮次貸危機的影響之后,后危機時代宏觀波動與經濟增長的正相關性和顯著性也大為提升。鑒于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波動“大緩和”的趨勢仍將繼續,且宏觀波動對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正效應,因此,為維持“新常態”形勢下一定水平的經濟增長速度,“穩增長”的政策取向不能一味以平抑宏觀波動為出發點。相反,以創新驅動、轉型發展,加大市場化資源配置力度等為目標,對應的結構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引致的良性波動更應得到鼓勵和提倡。未來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首先,宏觀波動在經濟下滑和上升時期對經濟增長分別具有正效應和負效應,其內在機理如何?特別的,經濟結構、技術進步與創新、宏觀財政與貨幣政策等因素對此有何影響?相關研究對后危機時代深化經濟結構轉型和宏觀政策調控具有重要意義。其次,宏觀波動與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特征是否表現為全球性趨勢,能否調和既有研究結論的不一致?最后,所有結論均基于樣本內數據所得,能否基于樣本外預測進行檢驗,以便提前識別經濟增長及其波動的結構性變化,并制定相應的政策,也需進行探索。
作者:黃波 孫力軍 單位:上海立信會計學院 金融學院
- 上一篇: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關系研究范文
- 下一篇:債務重組的經濟后果范文
擴展閱讀
- 1新聞宏觀失實
- 2國際服務貿易宏觀因素
- 3宏觀經濟
- 4國際服務貿易宏觀因素
- 5宏觀角度反傾銷
- 6宏觀價值
- 7國際服務貿易宏觀
- 8貨幣政策宏觀經濟
- 9宏觀財務經濟監測
- 10宏觀調控行為可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