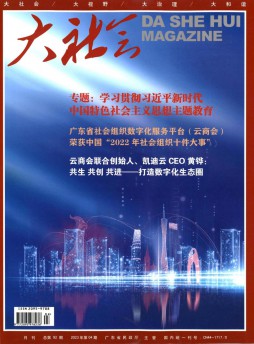社會經濟發展及其原因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會經濟發展及其原因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秦漢時期郴州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是郴州歷史發展的第一個高峰。社會經濟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秦漢王朝對郴州治理開發的加強以及中原人口的遷入,促進了漢、越民族的往來與融合,推動了郴州封建化進程。
關鍵詞:漢代;郴州;發展;原因
郴州地處五嶺北麓,耒水上游山林河谷地帶,山巒重迭,溪河眾多。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社會文明。1964年桂陽縣樟木鄉小泉村上龍泉出土的刻紋骨椎,表明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郴州境內就有人類繁衍生息。戰國中晚期楚國、秦代在此設立郴縣,西漢設置桂陽郡(桂陽郡的范圍比今郴州要大)以來,經過秦漢王朝的治理開發,到東漢郴州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郴州共發掘漢墓360余座,出土了陶瓷器、銅器、鐵器、玉石器、金銀器、玻璃器等各類文物4000余件。為研究漢代郴州及南嶺地區考古學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同時也對研究中原與嶺南的聯系、漢文化與越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漢代郴州社會經濟發展的具體體現
(一)農業生產力提高
1.鐵農具及牛耕的推廣。漢初,牲畜比較缺乏,一般農民只能用人力耕作。西漢政府下令禁止宰殺耕牛,規定殺牛、盜牛者受重刑。到漢武帝時,耕牛數量增加,牛耕方式已經從黃河、長江流域一帶,傳播到東北、西北、嶺南。與此同時,由于漢武帝實行國家壟斷冶鐵業的政策,鐵制農具逐步推廣到西域和珠江流域,且鐵制農具的種類增多,鐵制掘土工具的大量出現,使人工溝渠的開挖變得容易。在郴州360座漢墓中,有94座墓出土了鐵器,共出土鐵器120件,出土鍤、䦆、斧、刀、刮刀、環首刀、夯錘、釘等鐵工具,表明鐵農具在當時郴州得到了普遍運用,提高了農業生產力。
2.糧食產量顯著提高。湘南地區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區。道縣玉蟾巖遺址出土了距今1萬多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桂陽縣千家坪遺址出土文物標本表明,早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郴州原始稻作農業有了初步發展。秦漢時期,水稻的種植更為普遍,水稻在人們的糧食構成中日漸重要。2013年,郴州市桂門嶺1號墓女墓主所穿的服飾中出土了兩粒稻谷殼,湖南省文物專家認定此墓葬年代為秦漢之際。到了東漢,農業生產有了明顯的發展。耕作技術方面,開始注意“精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在郴州市高山背、飛機坪等地出土了帶廁所的陶豬圈,說明當時重視施肥。由于耕作技術的改進,東漢糧食產量顯著提高,也促進了糧倉建筑的發展。郴州出土了圓形平底陶倉、圓形三足陶倉、圓形四足陶倉等多種結構的糧倉建筑模型和陶臼、杵、碓房等糧食加工設施。1995年,郴州市飛機坪原北湖區政府出土了一組五件陶制房屋建筑,其中一件為糧食加工作坊,塑有三俑,其中兩俑持杵于臼中作舂米狀,一人雙手持箕作簸米狀。這是漢代郴州糧食儲備增多和糧食加工工具進步的反映。郴州的糧食生產不僅可以自給,而且還有節余,出現了南糧北運。東漢安帝“永初七年(113)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1]220,這是桂陽郡租米北調的明確記載。這充分說明東漢時期郴州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
3.畜牧業發展。漢代,郴州養殖業有了較大的發展,當時人們的肉食來源主要是“六畜”,即牛、羊、豬、狗、雞、鴨。郴州東漢墓出土了雞、鴨、狗、豬、豬圈、雞塒等隨葬明器。如1995年郴州市飛機坪原北湖區政府出土的一件陶豬圈,有兩頭仔豬和一頭正在哺乳的母豬。1987年,郴州市萬花沖農機公司1號漢墓出土陶豬狗圈和負鞍陶馬,盤形豬狗圈內有一長方形食槽和二豬、二狗。1993年郴州市上自建里鐵路家屬區4號墓出土一件東漢禽獸云紋銅杯,杯身刻劃云紋三周,外口沿下刻劃水波紋間以雞、鴨、鵝、牛、羊、豬、狗等禽畜圖案。說明家禽家畜已很興旺,也從一方面反映了漢代郴州農業生產的發展。
(二)手工業發展迅速
1.冶鐵業發達。冶鐵業是各項手工業的先導部門,也是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主要手工業部門。隨著農業對鐵制生產工具需求的日益增加,必然促使冶鐵業優先發展起來。鐵農具的廣泛使用,提高了人們對耕地的加工整理能力,“鐵使更大面積的農田耕作,開墾廣闊的森林地區成為可能,它給手工業工人提供了一種其堅固銳利非石頭或當時所知道的其它金屬所能抵擋的工具。”[2]159鐵器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生產、軍事和生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鹽鐵論•復古篇》大夫曰:“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冶鐵業的發達是經濟發展的標志之一,大大促進了農業生產、手工業發展和其它行業的進步。郴州漢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鍤、䦆、斧、刀、刮刀、夯錘、釘等鐵工具,劍、矛、箭鏃等兵器,帶三腳支架釜、盉、燈、帶鉤等生活用具,說明當時郴州人們在生產生活中普遍運用鐵制工具。
2.冶銀業歷史悠久。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桂陽郡,有金官”[3]566,主管白銀的冶煉。《述異志》記載,漢時“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1985年,郴州地區文物工作者在郴縣安和鄉新田嶺五馬垅(今北湖區保和鎮)發現冶煉遺址,遺存長約200米,寬80米,兩橫排的冶煉爐數十個,爐身皆以石塊砌框,內壁抹泥漿,穹窿爐頂,爐體下方有一圓孔,孔徑約25厘米。據《文獻通考》載,此爐冶始于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本為煉鉛銀之處,后因歷代官府屢行為礦禁,時采時停。2004年,郴州市蘇仙橋10號古井出土編號C2-181西晉簡牘:“故進山鄉銀屯署廢無居人”記載表明,經過東漢末年及三國戰亂,到了西晉初期,雖許多采銀礦井被廢,但仍有“口一千七百卌八采銀夫”(C2-146西晉簡牘),可見漢代郴州白銀冶煉的規模。郴州漢墓中還出土了不少指環、鐲、珠、簪等金銀飾物,如2003年郴州市駱仙嶺出土的一件東漢鏤空金珠,構思精巧,造型別致,工藝精湛,堪稱金飾中的精品。
3.冶銅業進步。郴州作為楚南重鎮,自戰國中晚期楚國設置郴縣后,官府加強了礦藏資源開發,出土了大量銅兵器和生產生活用器。1995年,郴州市山川塘出土一面戰國六山紋銅鏡,其紋飾圖案在山字紋銅鏡中絕無僅有,卻與1959年郴州市馬家坪2號墓所出的戰國幾何紋銅鏡相似。湖南省博物館專家研究后認為,很有可能是郴州本地所鑄。郴州出土的漢代銅器有釜、洗、壺、樽、盉、簋、碗、缽、杯、耳杯、燈、銅鏡等,主要是生活用具。紋飾有雙魚、弦紋等圖案,或祝福吉祥、富貴話語。郴州360座漢墓中有114座墓出土了銅鏡,共處銅鏡130面,最多的一墓出土三面。其中有一部分銅鏡應為郴州制造。2010年,郴州市南塔嶺69號墓出土一件漆奩,蓋飾一周、奩身兩周約2厘米寬的動物云紋金邊,奩內盛有一把環首銅刀,刀身飾龍虎鳳云紋,采用滲錫工藝鑄造。工藝精湛,紋飾精美。
4.釀酒業初具規模。隨著糧食生產發展,漢代郴州釀酒業也發展起來了。酒具是酒文化的物質積淀。郴州漢墓中出土了瓿、樽、壺、瓶、罐、筩、高足杯、耳杯、卮等陶、瓷、銅制酒器。2010年,郴州市南塔嶺43號墓出土了一套滑石器,其中鼎3件,盒2件,鈁4件,壺2件,盤4件,杯2件,耳杯5件,案1件。2013年,郴州市桂門嶺四號墓出土云紋漆耳杯。1994年,郴州市磨心塘出土寬弦紋銅樽,內有漆勺。東漢郴縣程鄉(今資興市)產一種名為“程鄉若下”名酒,東漢鄒陽《酒賦》記載古代名酒有:“沙洛綠酃,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縈停。”[4]27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耒水篇》:“郴縣有淥水,出縣東俠公山,西北流,而南曲匯于耒,謂之程鄉溪,郡之酒官,釀于山下名程酒,獻同酃也。”[5]2004年,郴州市蘇仙橋10號古井中出土的編號為(C1-22)西晉簡牘就有“郴縣呈(程)鄉獻酒官”的記載,應證了史籍中的記載。編號C2-118西晉簡牘還有“口二十三酒工”記錄,說明當時郴州釀酒業達到了一定的規模。
(三)商業逐步發展
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推動了漢代郴州商業的發展,商品交換進一步脫離以物易物的原始階段,而代之以幣易物交換。郴州境內出土了楚蟻鼻錢,“半兩”“五銖”“大泉五十”“貨泉”“大布黃千”等貨幣,尤以漢“五銖”銅錢為多。說明郴州境內至少在漢代已使用銅錢進行商品交換。在郴州市文物處清理發掘的360座漢墓中,出土銅錢的墓達119座之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漢代郴州的商業活動已達一定規模。湘粵古道貫穿郴縣(當時桂陽郡郡治)、便縣、臨武縣全境,這些郡治、縣治所在地已有人設鋪開店。每逢圩期,商販匯集,有的抱布而市,有的提籃挑擔沿街擺賣。郴州漢墓“五銖”等銅錢的大量出土,說明當時郴州地區錢幣流通的頻繁與商品貿易的發展。
(四)人口快速增長
在漢武帝之前,郴州地區的開發是較緩慢的。主要表現在:一是地廣人稀。據考,桂陽郡人口密度為2至3人左右每平方公里,人口分布密度較為稀疏。由于缺乏足夠的勞力,大部分土地尚未得到開發利用。桂陽郡越族人口在數量上占多數。人民“率依阻山澤”,以漁獵山伐為業,耕種方式或采用“火耕水褥”,民無積蓄而多貧。氣候暑濕,疫疾多作。加之文化風俗滯后,“信巫鬼,重謠祀”,人口增長緩慢。西漢末的元始二年(2),桂陽郡領十一縣,總戶數為28119戶,總人口156488人,人口密度為3人每平方公里,在西漢98個郡中位列77位,比較偏后。到了東漢,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促進了人口的增長。東漢永和五年(140),桂陽郡有戶135029,人口501403,較西漢分別增長380%和220%,其人口密度也從3人每平方公里增加至9.8人每平方公里,在105郡國中位列57位,為中等發展地區。在古代,人口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標志之一。在當時經濟總體發展水平還很低的農業社會里,人口的增減與農業的豐歉息息相關。漢代桂陽郡人口的大幅度增加,表明當時桂陽郡的農業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
(五)城市不斷發展
城市是人類文明里程的標識,是工商業匯集的中心地,也是先進技術與科學文化的匯聚地。漢王朝在郴州設置桂陽郡,郡治設在郴縣(東漢建武年間曾移置耒陽縣,不久還郴),加強城市建設。《漢書•地理志》:“桂陽郡郴,項羽所立義帝都此。”《水經注》:“郴縣城,項羽遷義帝所筑”。初為夯土城,漢高祖六年,太守楊繆始筑城垣。從此,郴州不僅作為南方的軍事重鎮和交通要道,而且成為湘南粵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1993年,在郴州地區行署發現南護城河,護城河呈直線形,河壁、河底經修整,光滑平整,幾乎與現人民路平行,殘長26.8米,河口寬3.5~4.2米,底寬2.3~3.08米,距原房屋地面深3.5米,橫截面呈梯形。2003年,在郴州市蘇仙橋原郴州市美術印刷總廠內發現古井11口,其中10號古井出土西晉簡牘900余枚,10號古井出土三國吳簡100余枚。由此進一步證實此為桂陽郡郡治所在地。桂陽郡城東抵郴江邊,南至今人民路,西臨北湖公園,北至郴州市氣象局、郴州市一中,面積約12萬平方米。瓦的發明是古代建筑史上的一大進步。護城河填土中發現有漢代板瓦、筒瓦、瓦當。臨武渡頭漢城遺址也出土了繩紋筒瓦。郴州漢代出土的房屋模型屋頂大都飾有瓦壟。1995年,郴州市飛機坪原北湖區政府出土一組陶屋,屋頂全部有瓦壟,屋檐有圈點紋瓦當,其中一件兩層陶屋后部敞開無墻體,由兩個圓形立柱支撐屋頂,一根立柱下安有圓形石柱礎。尤其是出土的干欄式吊腳樓,屋檐下設有走廊,圍以欄桿,房屋下有立柱6根,分前后兩排。干欄式建筑適應了郴州以丘陵山地為主,潮濕多雨,常有水患獸害的居住環境需要。這些發現,證實漢代桂陽郡一帶已能生產和使用粘土瓦,人們的居住條件得到了改進,城市建筑達到了一定規模。(六)漢文化傳播影響日漸廣泛到了東漢,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漢文化的傳播日益廣泛,人才輩出。如造紙術發明家蔡倫,長沙太守、尚書胡騰,焚身祈雨、舍身為民的汝南郡平輿縣令(今河南駐馬店市平輿縣)張熹(臨武縣人),長沙郎令、龍川長、湞陽丞等官宦及“當時名儒”劉常[1]1184、孝廉劉尚等。2004年,郴州蘇仙嶠十號古井出土的千余枚西晉簡牘中,編號為C2—228的簡牘:“漢故長沙太守胡滕(騰)墓,石虎石柱石碑。”郴州蘇仙橋西晉簡牘C2—242:記載“漢故平輿令張喜(熹)墓,石虎。”C—264:“漢故郡察孝廉劉尚墓石碑。”表明郴州文化教育事業得到了發展,漢文化的影響日深。漢王朝在郴州設置郡縣,任官治理,加強了對郴州的行政管理和開發,歷任桂陽郡太守“奉職循理”,推行有利于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措施,加上郴州具有豐富的礦藏資源,中原漢人的南遷,帶來了先進的文化等,漢代郴州社會經濟發生了顯著變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二、漢代郴州社會經濟發展原因
(一)秦漢王朝對郴州治理開發的加強
郴州社會的發展進步,對于秦漢王朝在南方統治的鞏固和疆域的擴大,對于密切內地人民與嶺南人民的經濟文化往來,促進漢族與南方少數民族的交流與融合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1.秦漢時期國家大一統的需要。郴州縱貫五領,為長江水系湘江干流耒水、珠江水系北江、贛江之源。“北瞻衡岳之秀,南直五領之沖”,襟帶湖湘,對接粵海,是內陸通往嶺南的門戶。戰國中晚期、秦代在郴州設立郴縣,是五領地區最早設立縣的地區之一。公元前206年,項羽以“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為名,徙義帝于長沙郴縣(今郴州)。高帝五年(前202年),設置桂陽郡,內附長沙國,郴縣為郡治治所。桂陽郡南接南越國,地處長沙國與南越國爭斗的前沿地帶,像個楔子插在長沙國與南越國之間,政治軍事地位十分重要。在兩漢時期,郴州一直作為漢王朝對南方統治的軍事重鎮而發揮作用,漢王朝加強了對桂陽郡的治理與開發。南越國丞相呂嘉發動叛亂,漢武帝任令衛尉路博德帶領軍隊駐扎在郴州,做好軍事斗爭準備。當叛亂發生時,封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一舉消滅南越國。為了更好地控制嶺南粵北,漢元鼎六年(前111),漢武帝滅南越國后,將鄰近桂陽郡的南越故地,設置曲江(今廣東韶關)、湞陽(廣東英德)、含洭(今英德境內)三縣內屬桂陽郡。東漢時期,交趾郡征側、征貳姐妹起兵對抗漢朝官吏蘇定的貪虐統治。光武帝劉秀拜戰國名將趙奢后代馬援為伏波將軍。伏波將軍馬援也是從桂陽郡出發的。秦漢國家大一統局面的需要,為郴州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
2.休養生息政策的實施。漢初,統治者總結了秦王朝滅亡的教訓,在全國實行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重視生產的政策,促進了封建租佃關系的發展和部分奴婢的解放,人口大大增加,從為而漢代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隨著中央王朝對郴州管理的加強,漢武帝以后,到了東漢,郴州社會經濟發展步入了快車道。
3.桂陽郡太守“奉職循理”。東漢桂陽郡是循吏輩出的時代。《后漢書•循吏傳》所載的十三循吏中,桂陽郡占了三個,且首篇是《衛颯傳》。東漢時期,通過桂陽郡太守的勵精圖治,郴州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是郴州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之一。桂陽郡內住有大量越人,其中曲江、湞陽、含洭三縣,為越故地,漢武帝平南越時,內屬桂陽。東漢初期,桂陽郡南部越人,“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1]2459除重視糧食生產外,經濟作物亦得到種植和發展。東漢初,茨充任桂陽郡太守時,“教民種植桑麻苧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1]2460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已逐漸形成。漢光武帝時,衛颯“修癢序之教,設婚姻之禮”[1]2459。漢和帝時,許荊“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荊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1]2472漢順帝時,欒巴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1]1842。(學校的建立,習俗道德觀念的變化,說明漢文化已為越來越多的越人、桂陽蠻人所接受,當地人們的文化素質不斷提高,加快了嶺南嶺北平地、河谷地區越人的漢化進程。輸租賦之法加速了越人、桂陽蠻的封建化進程。這些漢族移民和接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越人、桂陽蠻人,被編入國家戶籍管理,“流民稍還,漸成聚居,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從而推動了郴州社會經濟發展。
(二)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地理環境
郴州屬中亞熱帶季風性氣候區,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境內河流密布,水系發達,地下水資源豐富,適合人類居住和農業生產。西漢惠帝元年(前194),長沙王吳淺倡導,在郴縣與便縣(今永興縣)引溫泉灌溉田,一年三收。《后漢書•郡國志四》注引《荊州記》記載:桂陽郡郴縣“城南六里縣西北有溫泉,其下流有數千畝田,常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新谷便登,一年三熟。”因特殊的地質構造而孕育著地下豐富的礦產資源,盛產銀、銅、錫、鉛等,享有“有色金屬之鄉”、“世界有色金屬博物館”之美譽,有著悠久礦冶歷史,為漢代冶鐵、鑄銅、冶銀等工商業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為與郴州發達的冶鑄業相匹配,西漢王朝在郴州設置金官、鐵官。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桂陽郡,有金官”,主管白銀的冶煉,桂陽郡是全國獨置金官的郡。西漢初年,漢王朝實行允許郡國和私人經營冶鐵業的政策,使得全國的冶鐵業獲得了迅速發展,鐵器在軍事、生產、生活中得到了推廣。為了加強對冶鐵業的管理,漢武帝在全國設鐵官49處,江南唯桂陽郡一處,由此冶鐵業迅速發展成為漢代桂陽郡的支柱產業,并推動了農業、手工業、商業、交通建設等其他行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郴州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鐵器不但本土用,還供應長沙國,銷往南越國等地。廣州地區西漢前期墓中所見的銅、鐵兵器和鐵刮刀等,形制大小與郴州西漢出土的大抵相同。《史記•南越列傳》記載:“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趙佗說:“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6]2969于是,趙佗自尊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國邊邑。
(三)湘粵古道的建設和拓展
商業交換關系的發展,促進了交通的發達。五嶺橫亙東西,為長江水系、珠江水系的分水嶺,“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3]2781,自古就是南北交通的瓶頸。秦始皇略取五領,負阻于五領。秦占領嶺南后,為保障戍軍后勤供給和加強中原與嶺南的聯系,利用五領山谷鑿筑通往嶺南的道路“新道”。漢武帝平南越國后,在南越國北地置曲江(今韶關)、湞陽(今英德)、含洭(今英德境內)三縣內屬于桂陽郡。因這三縣地處嶺南,“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1]2459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東漢建武十六年至二十五年(39~49),桂陽郡太守衛颯上奏朝廷批準,號令郡民鑿山開險,修通了郴縣至曲江(今韶關市)、含洭、湞陽等縣的山道五百里,沿途設亭傳郵驛。東漢章帝建初八年(83),大司農鄭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于是夷通,至今遂成常路。”[1]1156嶠道通往嶺南,遠達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道長一千余里。嶠道沿途,多筑有亭障、郵驛,以保衛商旅,安頓食宿,便利交通。東漢延熹年間(158~167),桂陽郡太守周憬在曲江北段盧溪與溱水(今武水)交匯的瀧口河道(今樂昌市境內)裁彎取直,疏浚河床,提高了溱水上游的通航能力,便利了曲江、郴縣之間的商貿運輸,桂陽郡內的交通條件得到進一步改善。南海貨運逐漸放棄通行困難的衛颯開通的嶠道(曲江路段),轉而取水路到達郴縣南境,再沿郴宜九十里大道到郴縣。從此,郴州成為溝通中原與嶺南地區的交通要沖和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刺激和帶動了漢代郴州社會經濟發展和工商業的興盛。
(四)中原漢人的南遷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派50萬大軍略取嶺南。為了鞏固對嶺南越人的統治,還分兵“戍五嶺”,郴州是中原通往南海郡郡治番禺(今廣州)秦新道的必經要沖,郴州成為秦軍戍守五嶺的后方基地。中原人大規模遷移至郴州,或經郴逾嶺,使漢人與南方土著越人雜居,漢人先進的生產技術先后傳入嶺南,推動了南方的開發,促進了漢族和越族的融合。兩漢之交,中原戰亂,大量漢人南遷桂陽郡,加快了居住于平地、河谷越人的漢化,加速了郴州社區的封建化進程。
參考文獻:
[1]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班固.漢書[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4]葛洪.西京雜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酈道元.水經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73.
作者:胡仁亮 單位:郴州市博物館
- 上一篇:水資源與社會經濟發展研究范文
- 下一篇:人口性別比失衡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