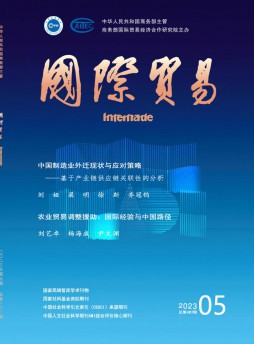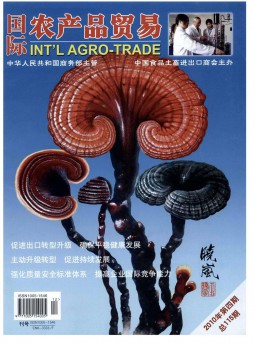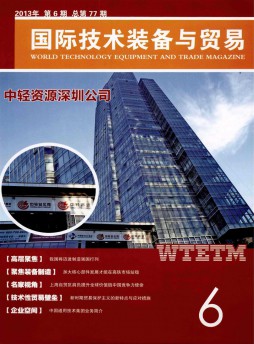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Gawande等(2005)最早從國內外利益集團游說競爭的角度對該問題進行了探討,他們的分析結果表明,國外利益集團對美國政府的游說活動顯著降低了其所在行業的保護水平。進一步來說,Gawande和Krishna(2005)考察上下游生產者之間的游說競爭對貿易保護結構的影響,他們發現,上下游企業游說競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上述難題。此后,Chang和Willmann(2006)通過將廠商異質性引入標準的PFS模型,分析了國內企業和出口廠商的利益沖突對關稅形成的影響,也得到類似結論。另外,Freund和Ozden(2008)把“損失規避”心理納入行為人的效用函數,按照其模型推導出的a值也有所降低。但是,上述研究只能在一定程度減輕a值過大的問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該“悖論”,必須更深入地考察貿易政策的制定過程。雖然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企圖從政策制定的政治過程出發尋找貿易保護主義的根源,但是原始的PFS模型之所以會出現上述“悖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對政治過程的描述過于簡化。正如Gawande和Hoekman(2006)所指出的,在PFS模型中,政府被簡化為單一的政治實體,而在現實中,利益集團通常向多個人開展游說活動,顯然,這一“稻草人”是不合理的。據此,Gawande和Hoekman(2006)認為,貿易政策制定過程的復雜性決定了利益集團政治活動的結果具有事前的不可預測性。于是,他們在PFS模型基礎上引入了游說成功的概率,但是,由于參數的取值現實中根本無法獲得,因此,我們也就無法通過該理論對貿易保護的水平和結構進行預測。本文在Grossman和Helpman(1994)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多個政治人,其中,利益集團向多個政治人捐資,而均衡的貿易政策則由這些人按照多數制投票決定。為了正文表述方便,我們以美國政體為例說明貿易政策是如何制定的。貿易政策的制定過程包括3個階段:第一階段,給定其他利益集團的捐獻計劃和政策的預期決策規則,每個利益集團決定向哪個議員捐資并確定捐資額度,以最大化集團成員的聯合福利;第二階段,貿易政策制定機構對于貿易政策提出議案(下文簡稱為政府),并提交國會投票表決;第三階段,根據利益集團的捐獻額,國會議員進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獻額和社會福利的加權值,投票結果按多數制確定。
一、基本假定
(一)產品市場1.供給假定本國是一小國開放經濟,本國有m+1個生產部門,生產m+1種可貿易產品,以第1種產品X0為計價單位,產品X0僅使用勞動要素以規模收益不變技術進行生產,投入產出系數是1。勞動供給足夠保證產品X0的供給,勞動力在本國可以自由流動但是不能跨國界流動。
(二)政治市場貿易政策的制定過程包括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給定其他利益集團的捐獻計劃和政策的預期決策規則,每個利益集團決定對每個投票人的捐資額度,以最大化集團成員的聯合福利;第二階段,根據利益集團的捐獻額,投票人按多數制進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獻額和社會福利的加權值。接下來,我們將通過逆向歸納法求解均衡貿易政策。
二、結論
通過在Grossman和Helpman(1994)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多個政治人,本文考察了貿易政策制定機構規模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本文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現有文獻沒有考察貿易政策決策部門規模與貿易保護水平的關系,而本文分析結果則表明,貿易政策制定機構規模越大,貿易保護水平越低。第二,原始的PFS模型假設只有一個政治人,這不僅有悖于現實,而且無法回答現有文獻提出的質疑,即政府賦予社會福利的相對權重a估計值過高的問題,而本文模型可以解決該問題。
當然,本文研究還存在諸多不足。首先,為了集中分析a值估計過高的問題,本文仍然以美國政治體制為基礎,今后可以進一步探討不同政治體制下貿易政策的差異性,尤其是將模型擴展到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有望得到有益的啟示。其次,本文限于篇幅只分析了理論模型及其結論,可以考慮通過利用跨國數據,檢驗不同國家政治制度差異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
作者:王永進單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副教授
- 上一篇:經濟模式的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
- 下一篇:絲綢之路的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
擴展閱讀
- 1中哈貿易中俄貿易
- 2服務貿易技術性貿易
- 3區域貿易合作服務貿易
- 4貿易轉型下服務貿易探析
- 5貿易增長
- 6石油貿易
- 7服務貿易
- 8國際貿易鏈貿易便利化實現策略
- 9貿易增長
- 10貿易自由化農產品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