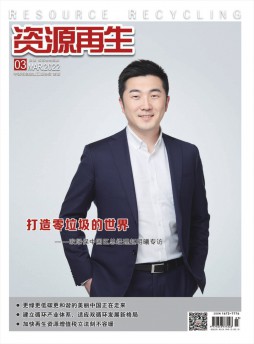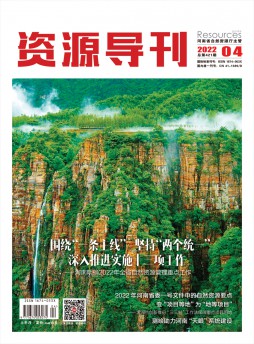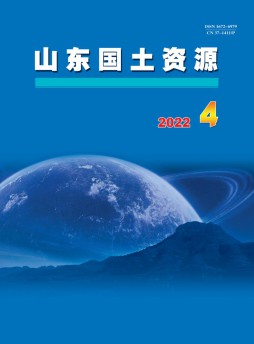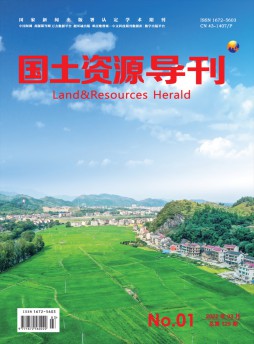資源開發與社會發展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資源開發與社會發展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南京工業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
摘要:
本文以晉南一個村莊的煤礦開發為例,通過分析煤礦開發對村民和國家的不同意義,探討資源開發中國家與村民的關系及其對資源開發和環境問題的影響。研究發現,對村民而言,煤礦開發具有解決溫飽和改善村民生活狀況的意義,這使人們進一步寄予它奔向“小康”的美好愿望。對國家而言,煤礦開發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國家治理目標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開發的深入和持續伴隨著區域發展差異拉大、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矛盾加劇以及生產安全等問題,給國家治理帶來了困難。研究認為,國家和村民的共生關系使資源得以開發實施,并使環境問題被忽視;競爭關系使資源開發受到影響,并使環境問題凸顯。研究提出,從國家層面整合和規范資源開發,以緩和資源開發中出現的人口、資源、環境矛盾,解決區域發展失衡等問題;處理好相關社會群體在資源的占有、開發中的關系,解決好資源分配與環境負擔之間存在的矛盾。
關鍵詞:
資源開發;國家治理;社會發展;環境問題;環境與社會
引言
日常生活中,山西省的煤礦資源開發常為人們津津樂道,但由此引發的環境問題為何延續數十年,卻并未得到相應的研究。2006年,筆者曾在晉南市西莊鄉劉村、王村開展相關調研。劉村是山西省“省級文明村”,曾獲得晉南市“文明和諧村標兵”“先進基層黨組織”等榮譽稱號。村內有一座煤礦,一排排整齊的歐式別墅,漂亮的學校,高大的村舞臺。村民一提起煤礦,就夸獎村里的老書記,并對本村煤礦開發充滿自豪感———盡管煤礦開發使許多房屋成為危房,還使許多農田廢棄……與劉村相比,王村并沒有煤礦,2006年,村內幾塊洼地被新任黨支部書記出租給附近某個煤礦企業投放煤矸石,租金為10萬元/年,受運送煤矸石的載重卡車擠壓,村內的道路已被破壞,晴天浮塵漫天、雨天泥濘。但是許多村民認為:村內洼地太多,并不平坦;廢礦石填平了低洼地,又讓村集體獲得了資金;此外,還有不少含有煤炭的煤矸石可以在市場上出售,能增加農民收入。
從這兩個村的情況我們發現:第一,受煤礦開發的影響,水位下降(包括地表水完全消失,地下水位下降)、地質沉降(許多地處煤炭開采區的住房因此成為危房)、粉塵污染(晴天浮塵漫天,雨天泥濘不堪)、道路交通隱患等問題突出,但許多村民似乎寧愿接受生活環境被污染的代價。第二,煤礦開發拉大了村與村之間的發展差距和村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但開發活動依然持續了很長時間,且以煤炭開發為主導產業的村集體還獲得了“省級文明村”“文明和諧村標兵”“先進基層黨組織”等榮譽稱號。對于這一現象,筆者不禁要問:環境惡化的原因究竟在于資源占有者的開發行為,還是因為國家對資源開采行為缺乏有效監管?筆者認為,這一問題需要從資源開發的作用入手,通過分析資源利用過程中不同群體的關系,才能全面回答。
目前,國外環境社會學如美國環境社會學的相關理論雖然產生了生態學解釋和政治經濟學解釋,但前者側重功能分析,后者偏于宏觀視角,導致其解釋力受到相當的限制。日本環境社會學的研究中致害論、受害論的視角,尤其是受害圈與受益圈的理論[1],雖然在相當程度上闡釋了環境危害中的受益方和受害方,有助于我們辨明資源開發中的不同社會群體,但微觀的視角和它所遭遇的水土不服問題,限制了它在本文案例中的運用。國內環境社會學的現有研究顯示,因為“政經一體化開發機制”的影響[2],或者因為政績的原因[3],或者因為制度變遷的原因,國家與農民之間存在著利益分化。這種情況下,農民的環境抗爭不僅難以取得成效,而且抗爭者常常落入受害枷鎖之中。即便有個別成功的例子,也只是表明了權力的界限,而且它往往預示著污染被轉移到農村[4]。也有研究從經濟政治制度變遷的角度來尋找國家與農民利益分化的原因[5],還有研究關注了村莊工廠中利益主體復雜化的現象[6]以及農民環境抗爭運動中熟人關系網絡和新聞媒體、環保組織等關鍵性支持資源的運動[7]。總體來看,國內對資源開發過程中國家與農民關系的研究并不多,特別是對山西煤礦開發中國家與農民的利益關系情況,我們依然知之甚少。
基于以上原因,筆者以2006年在山西省晉南市所搜集的材料為基礎,從煤礦開發對村民和國家所發揮的功能入手,通過分析煤礦開發過程中村民與國家由共生向競爭的關系轉變,探討資源開發下的環境問題發生的機制及其解決辦法。本文中的“共生”概念與“合作”概念有所差別:前者指出了所有個體、群體和社會組織在環境中的區位狀態和對特定資源的共同依賴,其目標不盡一致,資源獲取方式也不完全相同;后者僅僅表明了它們之間的共同的行為和共同的目標。因為這種差別,本文傾向于使用“共生”這一概念。本文首先論述村辦煤礦開發對村民的意義,闡述煤礦開發解決溫飽的功能和村民對煤礦奔向“小康”的寄望;其次論述村辦煤礦開發對國家的意義,闡述煤礦開發在實現國家治理目標和偏離國家治理目標上的轉變;最后總結資源開發中村民與國家關系由共生狀態向競爭狀態的轉變,并開展相關討論。
一、煤礦開發對村民的意義:從解決溫飽到奔向“小康”
劉村隸屬于西莊鄉,坐落在晉南市北郊,緊鄰晉南市最大的國有煤礦企業礦井礦①。由于距離接近,在改革開放前,劉村村民就與煤礦發生了聯系:從筆者所掌握的材料來看,村民雖然一再提及過去缺衣少食的情況,卻唯獨沒有提到缺少取暖、炊飲燃料,這反過來說明村民能夠得到礦井提供煤炭的關照。與此同時,因為地處城郊和煤礦企業周邊,劉村相對更容易受到城市發展和煤礦企業建設占用耕地的影響。這首先可以從晉南市耕地面積減少的大環境中體現出來。1984年晉南市總耕地面積比1949年減少近2萬畝,比1956年減少近10萬畝。與此同時,1984年晉南市年末農業總人口比1949年增加近22萬人。受這兩種因素的影響,1984年晉南市人均耕地面積比1949年人均耕地面積減少近1.5畝(見表1)。而劉村人均耕地面積一直維持在1畝左右,遠低于晉南市的人均耕地面積(約1.42畝)。在人均耕地面積較少的情況下,以糧食作物為主的種植模式依然沒有改變。這種情況使地處城郊和緊鄰國有大型煤礦企業周邊的劉村,特別需要通過勞動力轉移或村莊經濟轉型的方式來改善村民生活和實現村莊的持續發展①。而在煤炭工業、冶金工業掛帥的區域經濟結構下,劉村選擇相對容易進入的煤礦資源開發行業,就成為了最簡易可行的選擇。
村辦煤礦給劉村村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直接的影響。在生產方面,村辦煤礦影響了村莊經濟布局。村辦煤礦開發運營后,劉村村集體把村內過去以種植糧食作物為主的小塊土地集中起來,一部分土地改造為玫瑰園、果樹園,以向旅游農業轉型;另一部分改造為蔬菜種植園,用于發展大棚蔬菜供給城區蔬菜市場和滿足本村村民需求;還有一部分用于生產糧食作物,供給村民生活。通過這種方式,劉村逐步推動村莊經濟結構轉型。
村辦煤礦還帶動了家庭勞動力分工。在村辦煤礦較為興旺的時期,劉村每個家庭幾乎都有勞動力參與其中。以筆者調研期間借宿的一家為例,在村莊煤礦開發前,其家庭男女主人一直從事農業生產。村辦煤礦興起之初,家中的男主人就到礦上從事安全檢查工作。2006年時,他每月工資兩千余元。女主人起初從事農業生產,待兩個孩子念中學后,就到村辦煤礦做炊事員,負責礦工伙食。鄰居一家男主人同樣在村辦煤礦工作;女主人因為孩子尚小,早晚照顧孩子,待孩子上學后就送蔬菜供給城郊居民。調研期間,筆者看到她騎著自行車馱著滿滿兩框西紅柿到城里出售,有時候一天往返菜地和城區幾趟。少部分老年村民———通常是女性還撿拾煤矸石,堆積在院子里以待出售。與劉村不同,王村撿拾煤矸石的人員多為中年婦女,她們人數較多,許多時候還未等運送廢礦石的車輛卸貨完畢,就一哄而上搶拾煤矸石,置自身安全與漫天的灰塵于不顧。
村辦煤礦對村民的生活影響首先反映在生活水平方面。據《晉南縣志》記載和筆者搜集的相關材料,改革開放前晉南縣城鄉村民生活極為困難。村民飲食主要以面食、糊飯為主,只有在“過大年”及接待貴客時才食用餃子,在農忙或重體力活時才吃小米干飯或撈飯等。吃飯時,因為飲食簡單,人們都端著碗在門外聚餐,或蹲或坐,邊吃邊聊[8]570。在劉村,人們記憶中三頓飯里“兩頓糊糊漿水菜(指腌制酸菜)”。日常衣著服飾、居住條件都非常簡樸,被戲稱為“衣裳缺栓(紐扣)、房屋缺梁”。此外,劉村地處太行山麓,出行難和缺少交通工具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村民。從改革開放村辦煤礦興建到20世紀90年代,劉村村民的生活狀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許多村民蓋起了二層樓房。調研期間筆者借住的二層樓房的主人已搬遷到村集體修建的別墅,他家已經有了小汽車,家中除了四大家電外,還有一臺十余萬元的鋼琴。已經搬遷進入別墅的村民中,半數以上的家庭中有小汽車,幾乎每家都有其他車輛如農用車等。與此同時,收入增加使村民的生活狀況得到改善。在劉村舉辦的第二屆農民演唱會上,一首農民自編歌曲形象地反映了煤礦開發前后的生活變化。
《四個大娘話今昔》
[合]太陽出來暖洋洋,四個大娘坐街上,不說短來不說長,說說劉村變了樣。
[合]劉村現在變了樣,千萬不把過去忘,想來過去那個樣,不由心里就發慌。
[甲]俺家過去沒有房,住了三間土圪廊,天一下雨里邊漏,還有一根拆大梁。
[乙]過去種地真正傷,俺家土地在江江,趕車路過跌驢溝,不見小鬼見閻王。
[丙]過去一天三頓飯,每人端個大缸碗,十字路口你去看,不是糊糊是菜飯。
[丁]那時我才二十三,有襟衣裳盤著轉,遇見生人不知情,還說俺有五十三。
[甲]如今咱住啥新房,洋式結構前后窗,瓷板腳地光又光,一不小心叉了襠。
[乙]現在種地去江江,大路修的平蕩蕩,小地田地變大塊,跌驢溝不知道啥地方。
[丙]如今一日三頓飯,人人端是小瓷碗,中午炒上四個菜,如同老外吃西餐。
[丁]如今咱已六十三,胭脂口紅眉毛彎,再有生人不知情,還說咱有三十三。
[合]劉村如今變了樣,村民各個喜洋洋,三個代表指航向,內心感謝共產黨。
[合]太陽出來喜洋洋,四個大娘坐街上,夸咱劉村變了樣,團結一心奔小康。
村辦煤礦對村民的生活影響也反映在其擇偶交往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劉村年輕村民在擇偶方面較其父輩更加容易。據年長村民回憶,過去的劉村年輕人經常“愁眉不展,好閨女不肯嫁來”,婚姻圈局限于本鄉周邊村莊。村辦煤礦開發后,村民收入增加和村集體經濟繁榮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許多劉村和周邊村村民都說:這里(指劉村)的年輕人好找媳婦,許多閨女都愿意嫁來。
除了生產、生活方面的影響,長期與煤礦接觸還使人們改變了對煤炭和煤礦的看法。劉村和王村常有村民說:我們這里的煤是“香煤”,你們那里的煤是“臭煤”。筆者了解到,王村農民但凡有親戚在煤礦工作,因得到親戚的照顧,就會儲存不少好炭和冬季取暖用煤。而劉村每家每戶都有村集體供應優質燃煤。而所謂“香煤”是指煤炭中不含硫等雜質,而碳含量很高,燃燒中生成無色無味的二氧化碳,沒有嗆人的味道。從這一簡單分類,可以看到煤礦對村民觀念的影響。這種觀念在劉村更為直觀。該村某村委委員在筆者進入該村的第一天,就與其子開車接送筆者和同學到礦的職工劇院觀看職工演出。他與演出管理人員都非常熟悉,簡單地打過招呼后,就帶領我們進入了演唱廳聆聽紅歌合唱。據該村委委員之子介紹,礦出土的煤炭中有一種名叫“蘭花”的煤炭,它可以用火柴直接點燃;燃燒時不僅沒有煙塵,而且有蘭花的香味;燃盡后只有細細的白灰,沒有煤渣。“蘭花”常用紙張包裹,由海路運往英國,專供皇室壁櫥、餐廳使用。筆者雖未有幸目睹“蘭花”,但相關資料印證了這種煤炭確實存在。然而如此優雅的名稱和出路,表達了和煤礦長期接觸的村民的崇敬、榮譽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總之,村民對煤礦開發所寄予的期望已經遠遠超出生產、生活的物質層面:在村辦煤礦開發改善了村民生產、生活等狀況后,他們進一步期望村辦煤礦能夠帶給他們“小康”生活。盡管學界對“小康”的研究成果豐碩、指標體系完整規范,但村民對什么是“小康”并沒有準確的概念。在他們的心目中,“小康”生活一定會比今天的生活更加美好。也就是說,煤礦開發改善生活狀況、解決溫飽的功能催生了人們的依賴,使人們認為它是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必要條件。
二、煤礦開發對國家的意義:治理目標的實現與偏離
對于國家而言,煤礦開發的意義表現在對國家治理的作用變化上,具體而言,煤礦開發首先發揮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發展地方經濟的優勢,繼而因為人口與資源環境失衡、區域發展失衡以及國家治理困境而成為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阻礙。盡管20世紀90年代政治學中的治理概念興起后,“治道”說與“善治”說使治理的概念復雜化,但在社會學中,治理的定義相對穩定和統一。1942年吳文藻提出的邊政學中提及了治理這一概念,它探索采用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方法來研究邊疆政治,包括邊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實、制度及行政等內容[9]。雖然吳文藻并未明確指出其內涵,但卻隱含了作為目標的治理和作為手段的治理兩個方面。這表明,治理是指國家通過各種措施實現良好秩序的過程,是與“亂”相對應的社會狀態,是和平的狀態、穩定的狀態、有序的狀態。作為手段時,治理指與傳統專制、集權、人治和無限政府所不同的、屬于現代模式的措施。作為目標時,治理是與“亂”相對應的狀態。
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煤礦開發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變地區經濟落后狀況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煤礦開發改善了當地人民生活狀況,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這已在前文中有所論述。不僅如此,煤礦開發具有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作用。以晉南市為例,其煤炭資源儲量為47億噸,雖然僅占山西省煤炭儲量的1%①,但因煤層厚、煤炭優等特點,使其在很長時間保持著山西省經濟強市的地位。其次,煤礦開發具有示范性作用,對于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可以反映在晉南市改革開放初期村辦煤礦如雨后春筍般的發展壯大上。1956年,晉南市有煤礦17座,到1984年增加270座,其中鄉村辦煤礦就猛增到265座[8]256。這些擁有村辦煤礦的村莊往往同劉村一樣獲得了“文明村”等榮譽稱號。再次,煤礦開發具有實現國家治理目標,維持良好秩序的意義,這可以從以各種形式表達對黨和國家、地方政府的感激之情等內容的演唱會中反映出來。演唱會中的感激雖不同于人類學意義上能夠呈現社會地位、社會榮耀的物,但同樣具有“總體性呈現”的意義[10]。如同寶力格所述,方物或者特定的地區物品在中國的世界觀中具有經濟和政治雙重性質。朝貢的方物不僅具有象征性,還代表了主權運氣。也就是說,朝貢者貢獻主權運氣,主權者饋贈以物質[11]。在社會交換中,物質、金錢、尊敬、依從所具有的價值逐漸增高。這表明,最高價值的禮物被奉獻給了國家,可見煤礦開發作為一種治理手段,在改革開放后起到了實現國家治理目標的作用。
然而,持續的煤礦開發也帶來了人口、資源、環境矛盾及區域發展失衡的問題,給國家治理帶來了極大的困境。一方面,煤礦開發原本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狀況、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意義發生了偏離,拉大了村與村之間的發展差距。在村辦煤礦開發持續20余年時,那些經營煤礦的村莊在集體經濟狀況、村民收入水平方面已經遠遠超出那些沒有煤礦的村莊;那些資源條件好、開采早的村莊經濟狀況也遠遠好于資源條件差、開采晚的村莊。這種情況下,村集體以大型農民演唱會的形式表達對黨和國家的感激之情,其意義是尋求繼續開發煤礦的機會,以此維持整村搬遷、村莊經濟轉型、提高村民收入等目的。從一首《老兩口話今昔》的話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訴求。
《老兩口話今昔》
……
老頭:……看咱們村地覆天翻,村容新環境美道路平坦……路兩旁花草樹爭奇斗艷,教學樓新舞臺設施齊全,這一切還全靠集體企業。村領導一班人想方設法,將咱村帶進幸福樂園。……
老頭:……比起好的地方,咱還差著遠了。比人家1村、2村①,咱算啥?咱不但要富而思源,還要富而思進。在村領導的帶領下,咱還要再努一把力,再鼓一把勁,使咱們村再過三年五載,全村實現了園藝化,過進了富裕型小康村,那時候才要讓你生活得更幸福呢。
老伴:還是老頭想得遠。
老頭:(唱)想過去看現在眼光放遠,好前景美如畫就在眼前,到那時咱們村還要大變,實現了園林化幸福無邊,山是山水是水還有農田,路是路、河是河如同花園,村民們定能夠福壽雙全,咱老倆也歡度晚年,前段美好光景要想實現,咱還得聽黨話致富思源,團結一致發奮圖強大干幾年,定能夠變成一個山花爛漫、幸福美滿的嶄新農村。
另一方面,煤礦開發這一治理手段日益偏離治理目標,使國家治理陷入困境。以劉村的煤礦開發為例,地方政府得到了村集體的贊譽、肯定等高價值的“禮物”,獲得了形式上的治理意義和地方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隨后,地方政府授予村莊繼續實施煤礦開發的權利和各種榮譽稱號,實際上延續和加劇了村莊之間的發展不平衡,使地區內部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持續加大,整體上不利于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不僅如此,煤礦開發過程中生產安全事故頻繁發生,既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巨大損失,又加大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使國家治理難度變大,如頻繁發生的礦難事件,曾一度導致地區領導和山西省領導頻繁更替。基于這一原因,國家不得不考慮煤礦資源整合的問題。可以說,煤礦開發由發展手段轉變為地方層面單純的發展目標,偏離了國家治理的長期目標和總體目標,導致國家治理困境。這一雙重偏離和功能轉變是影響國家治理路徑的重要原因。
三、結論與討論
從本文的材料和分析來看,煤礦開發對村民和國家具有不同的意義。對劉村村民而言,煤礦開發首先滿足了其燃料需求,其次因為造成人均耕地面積減少而成為滿足人們生存需求的最簡易可行的生計方式。而村辦煤礦改變了村民的生產分工和家庭勞動力分工,并且帶給村民巨大的影響:它不僅解決了村民的溫飽問題,而且逐漸使村民對煤礦開發寄予奔向“小康”美好生活的意愿。這使村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開發所帶來的環境問題。對國家而言,煤礦開發只是實現國家治理的手段。在改革開放初期,煤礦開發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地區經濟發展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了國家治理的目標。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煤礦開發不斷加大村莊之間發展差距并使區域發展失衡;加之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加劇,資源開發過程中的生產安全等問題突出,使國家陷入治理困境。
對比煤礦開發對村民和國家的意義可以發現,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煤礦開發在改革開放初期滿足了村民解決溫飽、改善生活狀況的需求,推動了地區經濟發展,因而也滿足了國家治理需求。由于煤礦資源開發的實施過程中國家與村民處于不同的位置、采取了不同的行為、具有不完全相同的目標,我們稱國家與村民的這種關系為共生關系。煤礦開發的持續使村民產生了依賴,使其成為村民心目中奔向“小康”、實現美好生活的重要手段。不僅如此,煤礦開發也成為滿足地方經濟發展需求的主要手段。這種情況下,作為治理手段的煤礦資源開發日益偏離國家治理目標,它所帶來的相關問題給國家治理帶來了困境。由于煤礦資源開發對國家與村民所具有的意義有差異,而且國家與村民所寄予的期望也不盡相同,因而我們稱國家與村民的這種關系為競爭關系。從現實的情況來看,在國家與村民處于共生關系時,煤礦資源開發中客觀存在的環境問題處于被忽視的狀態。在國家與村民處于競爭關系時,煤礦資源開發中的環境問題則處于凸顯的狀態。
共生與競爭關系也存在于劉村和周邊村落之間。就共生關系而言,我們可以從煤礦開發帶來的資源分配與勞動力的就業等情況來發現。作為資源中心,劉村的煤礦開發推動了村莊勞動分工,影響著村莊產業結構與發展轉型,劉村的村民被安排在就業層次的上層,獲得了較多報酬;作為資源邊陲,王村通過提供廢棄礦石場地獲得資源,抑制了農業發展及其轉型,王村的村民處于就業層次的下層,以撿拾煤矸石等廢棄礦石維持較少的報酬。可以看到,不同的群體和社會組織共同依賴于資源,但受制于資源環境中的區位等關系,他們在資源的利用方式、分配和收益、依賴程度上互不相同。就競爭關系而言,它表現在資源邊陲內部的發展道路選擇上。對于王村而言,它選擇出租低洼地,獲取了煤矸石和廢棄礦石帶來的收入,實際上使其淪為廢棄物掩埋地。它獲得的部分報酬無法彌補其承受的巨大損失,使其在近年遭遇整村拆遷的命運。然而,在王村村民和與筆者同行的山西籍同學看來,出租低洼地可謂“一舉三得”,主導該事件的新任黨支部書記是“有頭腦”的人。如果我們將這一事件與前任黨支部書記不出租洼地的情況對比,就會發現客觀存在著是否出租低洼地以及向誰出租的抉擇。筆者無法獲知與王村一類村莊的數量,但我們可以推測,在一個對煤礦產生依賴的區域,與王村類似的村莊可能產生的“資源”競爭也將令人驚訝。這表明,村落之間的共生關系使村民乃至社會默認和接受了其中的環境問題,而競爭關系則使環境問題惡化。由此可見,環境問題日益凸顯的過程,也是共生關系向競爭關系的轉變過程。
從短期的發展過程來看,煤炭資源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資源中心的財富,即資源開發可以在短時間內改善局部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從長期的發展過程看,資源中心和周邊區域的收入差距與發展差距逐漸拉大,不僅帶來了區域間發展失衡的代價,而且因為共生關系造成發展依賴,由此導致惡性競爭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從短期和局部的角度看,資源對于周邊人群是一種福祉;從長期和整體的角度來看,資源對于周邊人群是一種禍患。由此我們可以理解身處資源周邊的人們的無奈以及有識之士對無序資源開發的痛心。因而,如何處理好相關群體在資源的占有、開發中的關系,解決好資源分配與環境負擔之間存在的矛盾,將是維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關鍵,也是考驗國家治理能力的重大問題。這也提示我們,只有從國家層面上整合和規范煤礦資源開發,才可能緩和人口、資源、環境矛盾,解決區域發展失衡等問題。
參考文獻:
[1]包智明.環境問題的社會學理論:日本學者的研究[J].學海,2010(2):85-90.
[2]張玉林.政經一體化開發機制與中國農村的環境沖突[J].探索與爭鳴,2006(5):26-28.
[3]羅亞娟.鄉村工業污染中的環境抗爭:東井村個案研究[J].學海,2010(2):91-97.
[4]張玉林.環境抗爭的中國經驗[J].學海,2010(2):66-68.
[5]陳占江,包智明.制度變遷、利益分化與農民環境抗爭[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50-61.
[6]陳阿江.水域污染的社會學解釋:東村個案研究[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1):62-69.
[7]童志鋒.變動的環境組織模式與發展的環境運動網絡:對福建省P縣一起環境抗爭運動的分析[J].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86-93.
[8]晉南縣志編纂委員會.晉南縣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9]吳文藻.邊政學發凡[J].邊政公論,1941(5/6):1-11.
[10]牟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M].汪珍宜,何翠萍,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87-108.
[11]寶力格.一個世界性的友鄰共同體正在形成[M]∥包智明.社會學名家講壇:第四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1-15.
作者:曾祥明 單位: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
- 上一篇:高校財務工作研究(4篇)范文
- 下一篇:小波臨界值光學頻譜降噪分析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