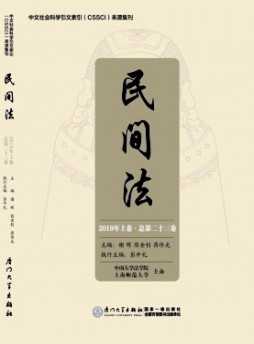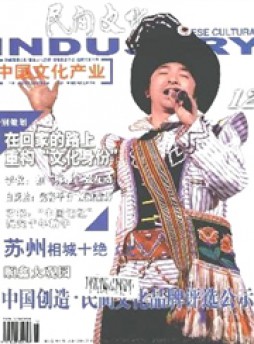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發展差異性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發展差異性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城鎮化是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不容忽視,本文主要從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兩大主體來分析其對城鎮化的影響。政府投資的規模性和壟斷性帶動了我國城鎮化水平的大幅增加,而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發展更具直接影響,但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間的相互作用對城鎮化的影響并不協同,從分地區的實證結果看出我國整體上是政府主導型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同時,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市場化改革的深化,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更為重要。因此,大力激發民間投資活力,以政府投資作為引導,規范政府投資范圍,優化投資結構,完善投資環境,是保障我國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
關鍵詞:
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城鎮化;廣義矩估計;門檻回歸
一、引言
城鎮化發展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主題,城鎮化的發展伴隨工業化發展,是非農產業的城鎮聚集、農村人口的城鎮流動的過程,是國家現代化發展的標志。《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明確指出,城鎮化的發展需要堅持“市場為主導,政府為引導”的戰略原則,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與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相一致,城鎮化的發展也受到了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推動力,但與西方城市化演進不同,我國的城鎮化發展主要是政府主導。所以,西方國家更多關注的是城市化進程中市場的作用,我國則更多關注政府的作用,而政府行為確實對城鎮化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比如對城鎮化發展進行宏觀調控、制定市場規則、提供公共服務領域,都離不開政府的角色(周加來等,2008)[1]。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必然對城鎮化的發展具有影響。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建設,應讓市場在城鎮化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這關鍵就在于大力鼓勵民間投資,發揮民間資本的活力,推動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辜勝阻等,2014)[2][3]。同時,民間資本推動城鎮化發展的融資難題以及準入難題,加之公共投資對民間投資具有一定“擠出”效應,這些都會使得民間資本參與城鎮化發展的積極性不高。另一方面,就全國平均水平來看,從公共基礎投資與城鎮化的貢獻彈性角度,中部地區的公共基礎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大于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謝長青等,2008)[4]。或者說這是由于地方政府投資對城鎮化的促進作用,地方競爭及“唯GDP”的晉升機制導致地方政府加大投資從而刺激了城鎮化的發展(谷秀娟,2013)[5]。當然,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之間也具有相互影響,大量的研究學者在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關系研究中,一方面認為政府投資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如楚爾鳴等(2008)通過SVAR模型得出政府投資在第三期對民間投資產生了明顯的反向沖擊,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作用較為明顯[6];另一方面又認為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并沒有顯著的“擠出”作用,或出現較弱的“擠入”作用,如陳時興(2012)通過IS-LM理論模型分析了政府對私人的“擠出效應”,又通過VAR模型實證分析了政府對民間投資存在部分擠出效應和部分擠入效應,但整體上累積擠出效應并不存在[7]。由于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數據,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關系并無統一結論,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政府投資還是民間投資,亦或是其相互作用都會對經濟發展、城鎮化發展產生影響。從投資的總量來看,鄭子龍(2013)認為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呈現倒“U”型結構,即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達到最大值后會呈現逐步減少的趨勢[8]。同時,從不同主體來看,張秀利等(2014)通過ADF檢驗和單位根檢驗發現民間投資和城鎮化之間無長期均衡關系,隨后通過格蘭因檢驗發現城鎮化并沒有對政府投資產生影響,而相反政府通過大規模的財政資金進行固定資產投資,從而推動了城鎮化的發展。同時也認為這種推動作用存在明顯滯后性,政府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存在績效損失[9]。林勇等(2014)通過PVAR模型分析了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和城鎮化三者的關系,認為相比于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貢獻度更大[10]。投資通過資本積累推動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也推動了城鎮化的發展,無論是投資總量來看,還是分主體的投資來看,對城鎮化的發展均具有一定影響。顯然,不同的投資主體對城鎮化的影響作用是不同的。同時,雖然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之間的相互影響并無定論,但是這種相互作用對于城鎮化發展也會產生一定影響。然而,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數學者在研究投資和城鎮化的關系時,多從某一主體來分析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或者是從投資的總量(投資整體)來分析其對城鎮化影響,亦或者忽略了投資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城鎮化的影響,而方法上則多采用協整分析、格蘭因因果檢驗、VAR模型,而較少用到工具變量的廣義矩估計方法。考慮到不同主體對城鎮化的影響不同,以及各個行為主體間的投資具有相互作用,再加之投資和城鎮化的相互影響,因此本文從兩大投資主體出發,研究其對城鎮化的影響效應,并同時分析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相互作用對城鎮化影響,在方法上則采用工具變量法解決因變量和自變量間的相互影響問題。
二、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
(一)我國城鎮化、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現狀分析
我國城鎮化水平從1996年的30.48%上升為2012年的52.52%。整體上各個省份的城鎮化水平處于穩步上升的態勢,但橫向來看,各個省份的城鎮化水平發展并不均衡,2012年北京、上海的城鎮化率接近90%,而貴州、云南的城鎮化率僅為40%,差距達到一倍。同時,從東、中、西部分地區來看,各個地區的平均城鎮化水平差距也較大,具體見圖1。從圖1可以看到,東中西部地區的平均城鎮化水平仍然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地區平均城鎮化水平較高,中部次之,而西部地區的平均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整體來看,2000年以前東、中、西部地區的平均城鎮化水平差距不大,但都相對較低,均沒有達到50%的水平,西部地區的平均化水平不到30%。隨著我國城鎮化發展,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但差距也逐漸拉開,以2012年為例,東部地區的平均城鎮化率達到66.2%,而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僅為49.6%和44.9%.擴大固定資產投資是城鎮化空間發展的前提,固定資產投資是資本投入的重要方式,擴大投資能擴大生產并完善城市基礎設施,表現在空間上就是城市建成區面積的擴大。同時投資可以通過就業促進城鎮化,使得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直接拉動人口的城鎮化聚集。我國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012年達到374694.7億元,其中國有經濟投資為104775.5億元,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27.96%,所占比例有逐年遞減趨勢;私營個體經濟的投資為103011.02億元,占全社會固定資產的27.49%,所占比例逐年遞增。從圖2可以看出,整體上我國的國有經濟投資水平是不斷上升的,特別是2008年后,國有投資水平上升速度加快,直到2010年略有回溫,繼而又穩步上升。這主要是因為2008年受到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影響,我國政府提出了4萬億救市計劃,這使得2008年后的投資水平出現急劇上升的趨勢。直到2010年,世界經濟逐漸走向正規,政府的投資水平也逐步回落到穩步上升的水平。國有經濟投資占比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在2008年,國有經濟投資占比也呈現了較為明顯的波動,同上分析,這同樣是受到我國的投資救市計劃影響,使得國有經濟投資的占比出現小幅度上升,到2010年又回落至平各個地區的民間實際投資水平在2004年以前,并沒有明顯差距,均處于一個較低水平,雖然我國市場化發展以來,越來越強調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但在轉型早期,由于激進式的改革并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政府仍然對市場有著較為明顯的主導作用,而我國的投資也主要是政府拉動型的投資模式。但隨著我國加入WTO,市場經濟不斷深化,可以看到,民間投資的活力不斷釋放,東、中、西部的民間投資額也逐步拉開了差距,東、中部地區的民間投資遠遠超過了西部地區的民間投資總量。東部地區的民間投資比例的變化速率最大,2005年之前,東部地區的民間投資比例基本在10.2%左右徘徊,處于中、西部地區投資比例之下(中部地區基本在17%左右,西部地區在15%左右)。之后東部地區的民間投資比例迅速增加,逐步大幅超過西部地區的民間投資占比,基本與中部地區的民間投資比例持平并略有反超。
(二)投資對城鎮化影響機理分析
大規模的投資資金進入,必然會帶動城區的產業發展,固定資產投資能夠促進城鎮化的發展,不同的固定資產投資主體對城鎮化的發展模式也有所不同。景春梅(2010)指出,國家投資的主體是建設新城或擴建舊城,從而引發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和城市的外圍擴張,這是一種“自上而下”型的城鎮化發展11。政府投資通過大規模的財政資金進行固定資產投資,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公益性項目設施具有重要作用,特別是一些大型的、跨區域的建設項目,必須依托政府投資完成。民間投資則能增加鄉鎮企業的活力,使得大量農村人口從事二、三產業,形成一種“自下而上”型的城鎮化發展。民間資本較為零散,特別是針對短期回報率不明顯,或者回報率較低的公益性項目,民間資本的投資熱情并不充足,同時由于一些項目的政府壟斷色彩,也使得民間投資的準入較難。因此,我國的民間投資仍處于起步階段,而政府投資仍占據主導。當然,值得指出的是,正如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之間也會有相互影響。政府投資增加,市場競爭激烈,導致私人投資減少,即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會產生“擠出”效應。我國的投資項目分為公益性投資項目、基礎性投資項目以及競爭性投資項目,公益性投資項目收益群體是整個社會,因此必然應由政府擔當,而基礎性投資和競爭性投資則多由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分擔,當政府資金大規模進入競爭性項目進行生產建設時,則會對民間投資的進入產生不利的影響。當然,如果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能夠合理分工,當政府通過大規模的政府資金作為依托,為民間資本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合理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投資項目,而不是在競爭性的項目中和民間資本惡性競爭,或者是通過政府權力壟斷投資有利的項目,提高民間資本的投資壁壘,那么政府投資同時也能對民間投資產生有利的影響。基于上述分析,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兩大主體通過不同渠道對城鎮化產生影響,同時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之間有相互作用,其對城鎮化也會產生影響。因此,本文構建如下的作用機制:通過圖6的作用機制可以看到,本文試從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不同效用出發,試圖對下述問題進行分析:1.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是否具有差異?2.當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存在相互作用的前提下,這種相互作用又是如何影響城鎮化的發展?3.經濟水平不同的地域,政府投資、民間投資以及相互作用對城鎮化的影響是否存在差別?4.從整體水平來看,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是如何隨著經濟水平的變化而變化的。本文最終將從投資的角度,對我國不同時段、不同地域城鎮化的發展模式為政府主導型還是市場主導型作出判斷,同時通過門檻分析找到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對城鎮化影響的閾值,提出城鎮化發展的投資模式的調整與改進。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及指標選取實證分析
主要選擇城鎮化率為被解釋變量,政府投資為主要解釋變量。城鎮化率以城市常住人口為基數,以城鎮人口除以常住人口表示,記為Urate。為探討在控制了外生變量前提下,考察政府投資對于城鎮化的影響,構建如下模型:Urateit=uit+α1Ginvestit+β1Minvestit+δ1Xit+εit(1)其中it表示第i個省份的第t年的數據,εit為誤差項。樣本包括1996-2012年度27個省份(除西藏、重慶、四川和海南①)的省級面板數據。同時考慮到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之間會產生相互作用,構建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交乘項,以分析其對城鎮化的影響作用,構建模型如下:Urateit=uit+α2Ginvestit+β2Minvestit+γ(G×M)+δ2Xit+εit(2)Ginvest、Minvest和(G×M)———三個核心解釋變量,分別為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并同時構建兩者的交乘項,表示民間投資和政府投資的相互作用對城鎮化的影響。文獻中關于政府投資指標的度量有很多種,由于我國投資項目被劃分為公益性、基礎性和競爭性三個類別,而基礎性和競爭性的投資項目是政府通過國有經濟投資形式和民間資本分擔,因此本文借鑒張秀利(2014)的做法,采用國有經濟投資指標來表示政府投資額,采用個人和私營投資指標表示民間投資額。但不同其處理方式,本文采用國有經濟投資占社會總投資比例來表示政府投資,系數α*衡量了政府投資對于城鎮化的影響作用,其值為正表示政府投資比例增加能夠促進城鎮化進程,其值為負則表示兩者間的反向作用。采用個人和私營投資占社會總投資比例表示民間投資,系數β*衡量了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作用。由于政府對民間投資有一定影響,因此構建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交乘項,表示兩者間的相互作用對城鎮化的影響,系數γ衡量了兩者的相互作用對城鎮化的影響大小及方向。Xit———控制變量,包括人均GDP、城鄉收入差距、貿易開放度和人力資本四個控制變量。人均GDP代表了一個地區的經濟水平狀況,采用一個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與總人口的比重并取對數表示,當一個地區經濟水平較高,則具有一定的經濟集聚性和輻射性,從而帶動人口的流入;城鄉收入差距是導致人口流動的最為直接的原因,采用城鎮可支配收入與農村收入的比重表示,當城鄉收入差距過大時,則必然會產生人口的城鎮化聚集;貿易開放度采用一個地區的進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表示,衡量了一個地區的對外開放程度,對城鎮化具有促進作用;人力資本采用的是各個不同教育階段的勞動人口比例的加權比重表示,作為生產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經濟增長從而城鎮化發展具有促進作用。δ*表示的是一組系數矩陣,分別代表各個控制變量對城鎮化的影響系數。本文選用的數據均來源于1997-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及《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各個變量的計算方法和基本統計量
(二)初步估計結果
由于隨機效應在1%水平下并沒有通過Hausman檢驗,因此拒絕RE模型而選用FE模型對上述沒有加入交乘項的模型(1)和加入交乘項的模型(2)分別進行回歸,均采用固定效應的穩健回歸分析。具體分析結果.通過回歸分析可以看出,加入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交乘項的模型優于沒有加入交乘項的模型,其擬合度R2達到0.8371,各個指標變量均較為顯著,采用模型(2)進行回歸結果分析。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均對城鎮化有促進作用,投資作為拉動經濟“三駕馬車”之一,同樣也是帶動城鎮化發展的快捷方式,投資通過資本積累與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城鎮化得到持續發展的保障。1996年,我國政府投資總額為12056.24億元,約占全社會投資總額的52.48%,而民間投資總額僅為3211.17億元,約占社會投資總額的13.98%。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民間社會資本的活力不斷釋放,政府投資占比從1996年開始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而民間投資占比則呈現了逐年遞增的趨勢。截止2012年,國有經濟投資占比和民間投資占比基本持平,分別為27.96%和27.49%。特別是江浙一帶如“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其私營和個體投資比重較大,帶動了小城鎮的經濟發展和人口聚集。引入交乘項的模型可以看到,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交互作用并不能促進城鎮化發展,反而對城鎮化發展起到反作用,這說明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并不協同,這可能是由于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作用使得投資對城鎮化發展的作用不明顯。相比于民間投資,政府撥付財政資金通過國有經濟進行固定資產投資,在某些投資項目中具有一定壟斷地位,對民間投資主體進入同一投資項目有一定排斥,從而不利于城鎮化的發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如上分析,投資能夠積累資本,加速基礎設施建設,帶動就業水平,推進城鎮化發展;而另一方面,城鎮化的發展同樣能夠對投資產生影響,城區不斷擴大是城鎮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同時也為投資創造了有利條件,新的投資機會使得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規模不斷增大(雖然政府投資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實際的絕對規模逐年增加)。因此,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和城鎮化的雙向因果關系可能會造成模型估計中出現解釋變量產生內生性問題。當模型中的投資變量出現內生情況,就不能滿足解釋變量應嚴格外生的前提假設,這會導致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存在偏差,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采取工具變量法的廣義矩估計進行回歸分析。在大樣本條件下,增加工具變量能夠較大解決內生性問題(Wooldbridge,2002),工具變量作為一種矩估計,一方面要和內生解釋變量相關,一方面要和隨機擾動項無關,本文選擇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滯后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進一步的實證分析[12]。
(三)穩健性實證分析
投資變量的內生性問題表明以上固定效應模型的分析會存有偏差,不能較好反映實際情況,同時考慮個體效應和內生性問題,主要選取工具變量的廣義矩估計IV-GMM方法對模型(1)和模型(2)分別進行回歸分析。首先兩個模型在進行戴維森—麥金農內生性檢驗(Davidson-MacKinnon,1993)時分別在5%和1%水平上拒絕原假設,認為模型均存在內生性問題,這將導致上述基礎回歸的結論不再有效。因此選擇政府投資的滯后一階和民間投資、人均GDP、城鄉收入差距、對外開放程度和人力資本的滯后一階和二階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廣義矩估計回歸。當存在多個工具變量時,用Sargan(1958)提出的過度識別的檢驗方法,得到的Sargan檢驗值說明所有工具變量均與干擾項不相關,工具變量的選擇是合適的。具體分析結果見表3。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回歸分析看到各個變量仍然顯著,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程度差異縮小。增加一單位政府投資占比能帶動城鎮化水平提高約0.33個百分點,增加一單位民間投資占比能帶動城鎮化水平提高約0.39個百分點。民間投資能夠直接提供就業機會,促進人口流動,對城鎮化的發展具有直接影響,而政府投資多為基礎設施投資,其對城鎮化的發展具有間接作用。我國市場化改革以來,民間投資逐步活躍,對經濟發展和城鎮化的發展具有帶動作用,但仍然存在一定局限,特別是我國政府主導型的投資約束下,民間投資的活力不能釋放。同時辜勝阻等人(2014)也指出,基礎設施類大多數項目投資成本高,資金回報慢,再加上民間投資的諸多門檻限制,使得民間投資的拉動作用表現不明顯。回歸結果也可以看到各個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均顯著。隨著經濟水平的增加,城鎮化水平也會逐步增加,經濟實力的增強是支撐城鎮化發展的重要保障,人均GDP增長1%帶動城鎮化率增加約0.07個百分點;本文采用城市可支配收入和農村收入的比例表示其差距,一般國際水平在2倍左右為較高水平,而我國平均水平達到2.86倍,最高達到4.76倍,這也直接導致了我國農村人口的城鎮化流動;貿易開放度是一個地區的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衡量指標,“珠三角”、“長三角”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領先代表,其對外開放是促進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手段,從全國的角度來看,對外開放增加1%,對城鎮化產生約0.1%的帶動作用;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投入要素,和資本要素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能引起城鎮化水平增加約0.05個百分點
(四)分地區影響差異分析
由于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客觀差異,為檢驗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效應是否會因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而受到影響,將地域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分別進行回歸分析③,對上述實證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在上述回歸分析中已對模型做了內生性檢驗,接下來仍采用工具變量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三個地區的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具體分析結果見表4。由表3可以看到,Sargan檢驗結果看出工具變量的選取同樣較為合理,分東、中、西部地區的回歸模型也較為顯著,主要分析政府投資、民間投資以及交乘項對城鎮化的影響。總體上,東部地區的政府投資對城鎮化影響比中、西部地區要大。越是發達地區,投資資金越充足,特別是政府投入較大,對城鎮化的帶動作用越強。東部地區的平均國有經濟投資額達到1350.22億元,平均民間投資額達到1134.17億元,平均城鎮化水平達到51.56%。而中、西部地區的平均國有經濟投資額分別為957.16億元和640.78億元,平均民間投資額為745.94億元和265.05億元,城鎮化水平僅為38.09%和32.80%。整體來看,東部地區的政府投資資金是中部地區的1.41倍,為西部地區的2.11倍,同時也為民間投資金額的1.19倍,沒有較大規模的政府投資資金依托,投資對城鎮化發展的拉動力并不明顯,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我國城鎮化發展是“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而在欠發達地區,投資不足導致其對城鎮化的帶動力較弱,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政府投資資金較為薄弱,而民間資本的資金又較為零散,加之金融融資借貸環境的約束,使得投資方向受到限制,投資資金并不能形成規模效應,從而導致城鎮化水平較為落后。回歸結果也可以看到即使西部地區的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帶動能力較大,每增加一單位民間投資占比,城鎮化水平增加0.88個百分點,但是沒有政府投資的合理引導,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仍然較低,這主要還是由于民間投資的資金較少以及投資熱情不足導致。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增加,其相互作用越強,對城鎮化的反作用越強。具體來看,第五列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交乘項對城鎮化的負面影響隨地域而逐步增強,西部地區的交乘項對城鎮化的負面影響系數為-1.7892,而東部地區則達到了-2.4905。與上述基礎回歸分析結論相同,并進一步說明了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發展的不協同,特別是當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日益增加的情況下,這種不協調作用更為明顯。
(五)面板門檻回歸分析
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政府資金的投入具有規模效應,對我國城鎮化進程起到了主導作用,也促進了我國城鎮化水平的不斷發展。隨著不同的經濟水平,政府投資對城鎮化發展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傳統的按照地域或者人均GDP來主觀劃分經濟水平的不同往往會導致回歸結果的偏差。Hansen(1999)發展的“面板門檻模型”能夠對數據自動識別來劃分門檻值,使得回歸結果更為客觀與準確[13],本文借鑒其方法來研究隨著人均GDP的變化,政府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的變化,構建如下模型:Urateit=uit+θ1Minvestit+θ2(G×M)+θ3Xit+α3GinvestitI(lrjgdpit$q1)+α4GinvestitI(q1<lrjgdpit$q2)+α5GinvestitI(lrjgdpit>q3)+εit(3)其中,I(·)為指標函數,取值為0或1。取人均GDP為門檻變量,q為門檻值。θ1、θ2和θ3分別表示民間投資、交乘項和控制變量的影響系數。而α3、α4和α5則表示當人均GDP取不同區間值時,政府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其值表示了隨著經濟水平的變化,政府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是如何發生變化的。同時,為了研究民間投資對城鎮化影響隨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構建如下形式的門檻模型:Urateit=uit+μ1Ginvestit+μ2(G×M)+μ3Xit+β3MinvestitI(lrjgdpit$q1)+β4MinvestitI(q1<lrjgdpit$q2)+β5MinvestitI(lrjgdpit>q3)+εit(4)同上,I(·)為指標函數,取值為0或1。人均GDP為門檻值q為門檻值。μ1、μ2和μ3分別表示民間投資、交乘項和控制變量的影響系數。而β3、β4和β5則表示當人均GDP取不同區間值時,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的變化。值得指出的是,一般情況下模型(3)和模型(4)應用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分別做門檻回歸來確定客觀確定各自的門檻值,但是為后文保障一致性的對比分析,這里僅用政府投資來做嚴格意義上的門檻回歸,也即模型(3)按照Hansen的面板模型方法回歸分析。而模型(4)的門檻值則同模型(3),按照政府投資作出的人均GDP的變化值來對模型(4)進行回歸分析,具體見后文分析。首先確定門檻個數以確定模型形式,依次在無門檻、單一門檻、雙重門檻和三重門檻下搜索并對數據進行分析,門檻效果自抽樣檢驗得到的F值和P值見表5,門檻估計值和置信區間見表6。通過表5可以看出,單一門檻、雙重門檻和三重門檻均顯著,P值分別為0.000、0.003和0.050,分別通過了1%、1%和5%的檢驗。但從表5可以看到,雖然第三門檻也通過了檢驗,但置信區間較大,與第一門檻和第二門檻的置信區間重疊,因此考慮雙重門檻進行分析.兩個門檻值所對應的似然比函數圖見圖7和圖8。似然比檢驗統計量LR為零所對應的值即為門檻參數的估計值,即圖7對應的最低點9.422和圖8對應的最低點10.229。圖中虛線部分對應的LR值為7.35,虛線以下部分對應的門檻參數區間即為門檻估計值的95%置信區間。第一門檻值為9.422,第二門檻值為10.299,按照這兩個門檻值將樣本根據經濟水平劃分為人均GDP小于9.422的第一部分,人均GDP在9.422和10.299的第二部分,人均GDP大于10.299的第三部分④。根據上述分析的門檻值對模型(3)進行回歸,同時以相同的門檻值對模型(4)作相同回歸分析,具體估計結果見表7。重點研究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影響力如何隨經濟水平變化而變化,可以看到模型(3)估計的結果較為顯著,除城鄉收入差距指標在5%水平下顯著,其他所有變量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模型擬合度R2達到0.8349,各個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與基礎估計基本一致。由于為了同時對比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對城鎮化影響的變化,模型(4)并沒有按照嚴格意義的門檻回歸進行分析,因此回歸結果中部分指變量顯著性不強,但并不影響分析。當人均GDP處于較低水平時,即人均GDP小于9.422時,此時投資水平也較低,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較弱。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當人均GDP達到9.422和10.229之間時,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規模也隨之增加,其對城鎮化的帶動力度逐步加強,政府投資占比每增加一單位拉動城鎮化發展增加約0.39個百分比,此時模型中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系數并不顯著。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我國投資主要是政府投入資金,政府資金占據了社會投資資金的半數之多,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和經濟發展主要是政府主導型,而我國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也說明國有經濟投資的主導地位。在經濟發展起步階段,“政府主導”式的投資方式對拉動中國經濟起飛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這種具有一定壟斷性質的投資方式并不有益于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當人均GDP大于10.229時,即隨著經濟水平進一步發展時,這種投資效應開始減弱,相對來說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作用更大。從樣本數據來看,至2012年為止,僅西部地區個別省份沒有跨過這一門檻(貴州:9.861;云南:10.0076;甘肅:9.998)。這也意味著當經濟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未來城鎮化發展應更為積極的釋放民間資本的活力,以民間投資帶動城鎮化水平提高。
四、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促進作用較強,然而政府投資相比于民間投資更具規模效應,特別是對經濟發展促進作用較大的基礎設施投資方面,仍是政府投資主導。在經濟起飛階段,沒有政府投資的引導,資金零散、薄弱的社會資本(民間資本)對城鎮化的拉動作用仍較小。同時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的相互作用并不協同,對城鎮化的發展起到了一定負面影響,且這種負面影響會隨著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增加而加強。第一,協調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明確政府投資的范圍與政府部門的職責。協調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規范政府投資管理,削弱政府的不正當干預以及部分投資項目的壟斷壁壘,創造良好健康的投資環境,打造服務型政府。發揮政府“相機抉擇”型財政功能,當市場失靈時,逆經濟周期適當干預市場,將投資主力放在公益性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加大基本公共品投入,特別是環境和社會保障建設,提升城鎮化質量。同時,從門檻回歸模型中可以看到投資效應隨著經濟增長水平減弱,因此為了城鎮化發展的可持續性,應優化投資結構,注重政府投資結構轉變,不應把重心放在量的增加,重點關注投資效率,用較小的投資存量撬動更大的投資效應。政府投資主要側重公共設施和公共事業等公益類項目的投資,諸如公共交通、醫療、教育、養老、通信基礎設施、基礎科研、國防、文化藝術、環境保護、文物古跡保護等。退出競爭性行業投資,將更大的投資機會讓利于市場,讓市場主導資源配置的平衡。第二,政府投資的規模大,針對性強,后發展地區應加大政府投資力度,加快城鎮化進程。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民間投資對城鎮化的促進作用較大,但依靠民間投資來促進城鎮化發展在經濟起步階段仍較單薄。民間投資因資金零散,投資環境不完善,并不能在經濟水平較低時拉動城鎮化發展。政府應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投資力度,以一定規模的財政投資資金帶動城鎮化發展,提升經濟實力,以更好發揮市場作用。第三,以政府投資為引導,民間投資為主導,多方位發揮民間資本的活力,構建PPP投資模式。加強市場化作用,隨著民間投資比例的增加,政府投資應逐步引導并讓位于民間投資,以更大市場活力推動城鎮化發展。單純依靠政府投資會加大政府融資壓力,增加地方債務風險,特別是一些地區會為了增加地方收入更加依賴土地的極差租金。為打破政府投資“瓶頸”困境,應多渠道推動社會資本投入到城鎮化建設中,放寬民間資本的投資范圍,改善民間資本的融資環境,發揮政府投資的引導作用,帶動民間資本的投入,完善公共私營合作制(PPP),利用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創新民間資本融資渠道,以推動城鎮化更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周加來,石麗娟.城市化進程中政府行為研究[J].經濟與管理,2008,(8):23-26.
[2]辜勝阻,劉江日,曹譽波.民間資本推進城鎮化建設的問題與對策[J].當代財經,2014,(2):5-11.
[3]辜勝阻,曹譽波,李洪斌.激發民間資本在新型城鎮化中的投資活力[J].經濟縱橫,2014,(9):1-10.
[4]謝長青,錢文榮,翟印禮.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與小城鎮人口非農化關系研究———基于1995~2006年數據的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08,(5):58-65,96.
[5]谷秀娟.中國地方政府投資對城鎮化的影響———基于動態面板模型的經驗分析[J].金融理論與實踐,2013,(10):69-73.
[6]楚爾鳴,魯旭.基于SVAR模型的政府投資擠出效應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08,(8):41-46.
[7]陳時興.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擠入與擠出效應的實證研究———基于1980-2010年的中國數據[J].中國軟科學,2012,(10):170-175.
[8]鄭子龍.我國信息化對城鎮化的非線性動態影響機制研究———基于面板數據門限回歸模型的經驗分析[J].財政研究,2013,(8):48-51.
[9]張秀利,祝志勇.城鎮化對政府投資于民間投資的差異性影響[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2):54-58.[
10]林勇,郭慶.政府投資、民間投資于城鎮化發展———基于PVAR模型的實證分析[J].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14,(5):19-23.
[11]景春梅.城市化、動力機制及其制度創新———基于政府行為的視角[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作者:吳俊培 艾瑩瑩 張帆 單位:武漢大學 浙江財經大學
- 上一篇:集體土地征收糾紛的特點范文
- 下一篇:無公害蠶豆栽培技術分析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