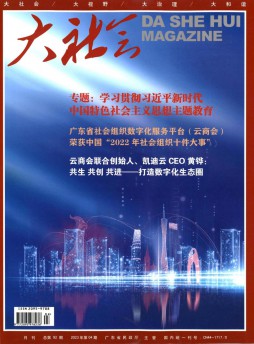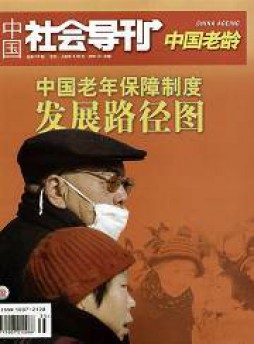社會音樂生態環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會音樂生態環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破舊立新的歷史環境
20世紀是一個動蕩的年代,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危機、獨裁統治等世界局勢的巨大變化,使緊張、憂慮不安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戰爭撕碎的不僅僅是歐洲和整個世界的格局,也不僅僅是人們對于一個美好世界的渴望,并且切斷了未來與過去的聯系。戰后的世界以一種加速度向著現代社會而去,這種變化必然會在藝術和音樂中有所體現。反映在音樂中,就出現了許多帶有強烈刺激性、夸張,甚至怪誕的作品。繪畫藝術中出現的達達和超現實主義,反人工控制、自動寫作的思想和實踐打開了藝術創作的一扇門,通向結構的反面,即解構,從而造成傳統言路的斷裂。這種斷裂的普遍化是二戰后出現的。具體音樂、偶然音樂尤其是后者,率先將傳統以來一直到現代主義的音樂所具有的“主體發展邏輯”或“對比統一”的有序性打破了。按貝爾的話說,偶然音樂、概念音樂、環境音樂等無序化、行為化的作品“溢出了藝術的容器”。20世紀音樂,顯然是經過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過渡之后,作為一個極其獨特的風格樣式成型,并且,與其之前的所有音樂風格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強烈反差。它全面變換音響結構方式,并極度關注音響本身。如果用極端方式對20世紀音樂做一個定位的話,一端是走向更高度的組織化,比如序列音樂,其結果是產生了一種極其復雜并且極端理性的音樂;另一端則是走向更大的自由,比如偶然音樂,在這里藝術已不再反映生活,反而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像生活一樣的不確定。進一步看,兩者的內在走向,就是有序和無序,以及美和非美的樣式。[1]
20世紀的社會和文藝思潮變換復雜,哲學出現了存在主義,心理學誕生了弗洛伊德學說,繪畫發展出表現主義,文學詩歌涌現出象征主義、未來主義等。藝術是相通互連的,同一時代音樂家的創作往往會與這些人文思潮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在20世紀音樂作品里,無論是在內容的選擇還是技法的運用上,都可以發現作曲家們在努力地發掘、探索、調動一切可能的因素推陳出新。向由來已久的傳統挑戰,追求藝術表現手法的不斷更新,歷來是音樂家們的共同追求。為此,音樂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多年來形成的審美標準不僅失去了光環,甚至遭到排斥和反叛。這種從古典到現代的歷史性轉型并不是孤立的,“世紀末”轉折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被稱作西方音樂“現代性”的萌發期。此時,歐洲處于“世紀末”的焦灼和混亂之中,傳統的觀念和標準風雨飄搖,文藝思潮空前活躍。音樂在經歷了19世紀末的浪漫主義沖刷后,正在發生深刻的裂變。統治西方音樂近300年的傳統建構開始土崩瓦解,德奧音樂的支配地位趨于喪失。新潮的音響和技法已在形成,各種音樂流派和音樂思潮層出不窮,相互重疊。作曲家們依據各自對傳統和未來的理解,在創作中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策略和技法。[2]20世紀音樂之所以與其之前所有音樂風格樣式形成如此截然不同的強烈反差,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嶄新的。
20世紀西方“現代性”文化邏輯深埋在它的歷史中。從理性崛起到理性獨白,再到反對理性中心主義,形成了一條比較清晰的軌跡。人們逐漸地發現,“音樂”這個詞慢慢地被“聲音”所代替,它傳達了一種新的欣賞態度,“新的聲音,要有新的聽法。不要力求聽懂,而是要注意音響的活動。”在大多數情況下,現代音樂并不是以一種形態出現的,但是無論怎樣,各種可以被稱作是現代音樂的音樂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說對和聲功能的破壞,比如說不穩定的節奏或者根本毫無節奏可言,比如說對于普遍意義上的噪音的運用,比如說對發聲樂器的功能的再定義。從90年代中期電子音樂大爆發開始,幾乎所有的音樂都帶上了電子的味道,甚至世界音樂也成為了電子音樂中的一種素材而被經常地使用。但是這也帶來了一些問題,當音樂家面對的可能性更多的時候,音樂就更多的是在于選擇而不是創造,而這樣的選擇總是會伴隨著某種泛濫的趨勢。
二、科技催生的創作環境
現代音樂的始端就是基于一種和古典主義決裂的概念,而在這個概念之上隨著科技,或者說材料的發展而跟進,并且整個音樂的未來都將必然和科技的變革和發展有著極大的關系。由發端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科學革命所引發的現代技術革命,始于20世紀40至60年代,人類科學在原子能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半導體技術、空間技術、激光技術等方面都得到了突破性進展。特別是進入70年代以后,由于微電子技術的產生和迅速發展、電子計算機技術的不斷更新換代及其在各個技術領域的廣泛應用,使現代技術革命更加明顯地展現出以信息革命為核心的特征。現代技術革命給人類的生產生活所帶來的巨大變化是無法抗拒的,科學技術日益滲透到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個領域,人們的音樂生活也隨之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48年,法國作曲家皮埃爾·舍費爾創作的《地鐵練習曲》,不用樂器,不用人聲,直接使用“具體的聲音”來制作音樂,把車輪滾動、噴汽、汽笛等聲音進行拼接、錄制而成。通過電子技術手段,作曲家皮埃爾·舍費爾第一次擺脫了“組織音符”的常規,實現了直接“組織聲音”和創作、制作、演出的一體化,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技術的發展,引發了20世紀現代音樂的一場觀念上的革命,拉開了電子音樂的帷幕。從50年代的具體音樂(MusiqueConcrete),到60至70年代的磁帶音樂(TapeMusic)和80至90年代的計算機音樂(ComputerMusic),電子音樂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橫跨了“模擬技術”和“數字技術”兩個技術時代,包容了多年來人類在電聲學、音響學、錄音技術、計算機技術及電子信息技術等眾多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為音樂藝術與科學技術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以高科技為依托成為這個時代的音樂標志。[3]
音樂創作利用計算機技術,可以進行音樂的數字合成,既能合成已有的各種音色,也可以合成自然界中以及現有世界上還未有過的聲音。當電子樂器開創了用電子技術模仿樂器音色和探尋新鮮音色的先例之后,真正成熟的自動化電鳴演奏是通過電腦(計算機)控制電子合成器進行音樂表演,既而進行音樂創作的實驗。這對于不斷追求音樂創新的音樂家們而言,無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創作空間。電子樂器與電子音樂、計算機作曲、微電腦制作音樂以及“彩色音樂”等的興起,給音樂帶來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尤其是計算機應用于音樂,使科技與音樂的聯系更為緊密,甚至使“彩色音樂”得以真正實現,這是一種通過聲與光,通過電子計算機控制、相互結合而成的藝術新品種,它使20世紀的藝術生活更加五彩繽紛。20世紀音樂幾乎貫穿整個世紀,可以說,是一種極端專業化了的現代音樂:通過新的觀念、新的技法、新的音響結構方式,以及某些新的聲音材料創作出來的那部分音樂。因此,從20世紀整個音樂發展來說,20世紀音樂是極其前衛和先鋒的;另外,和整個西方史相比,無論在創作還是表演上,也已經在工藝技術上及至頂端。[4]人們窮盡想象進行創新,藝術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技術的大比拼把音樂的表現疆域推進到所能想象的極限。縱觀歷史發展進程,科技的發展帶動了音樂的發展,充分體現了音樂與科技的同步性。
現代派音樂創作由于受到科學主義的影響,從20世紀中期以來就有意無意地將自身等同于某種科學技術,正是技術本位的觀念意識,成為造成西方現代專業創作脫離聽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技術話語的侵蝕,在現代社會里,文化已成為少數精英的特權,而日益失去與大眾的聯系,現代藝術變得非常難以理解。我們還應該看到技術本位觀念所引導的另一種分裂(商品與消費的分裂),體現在傳媒領域正在進行的另一類型的文化技術(產業)化當中。在資本利益的驅動下,這種技術化一方面把藝術降低為一種純粹的感性刺激物,一方面把大眾當作純粹的感官動物,這種潮流也是世界性的。[5]從表面上看,傳媒的商業炒作,那種絕對迎合大眾的媚俗來滿足人的感官享受,和某些“嚴肅”的現代音樂的極端理性化到背離音樂藝術最基本的聽覺性原則的強烈反差,似乎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但實際上它們恰恰都是社會技術化不可避免的產物,都是社會生態不可避免的結果。
三、自由分流的受(聽)眾環境
音樂聽眾分流是描繪現實音樂畫面的邏輯起點,新與舊的鴻溝隨著這個世紀的進展變得越來越寬。毫無疑問,聽眾在20世紀以前也曾經遇到過所謂的困難音樂。但是在這個世紀的前幾十年里,當作曲家創作沒有調中心的音樂時,卻受到了挑戰。大多數聽眾難以接受,許多人公然表示抵制。阿諾得·勛伯格和他在維也納的追隨者們對他們的音樂會屢遭擾亂而感到不耐煩,成立了他們自己的私人音樂演出協會,使他們完全脫離公眾的查看。
從20世紀初以來西方專業音樂在創作領域發生的“新音樂革命”不難發現,專業創作音樂生態與大眾音樂生態分離所帶來的一系列后果。以現代嚴肅音樂及其聽眾為一方和以傳統音樂及其追隨者為另一方的前所未有的分歧,并非偶然,它是半個世紀以來音樂思想革命的結果,人們不可能生活在一個統一的、有著共同習俗的音樂世界里。作為人類分工的一個結果,專門化是一個必然的傾向,而專門化的一個特征,即是在任何一個獨特的領域里,少數人的深入探索總是不可能簡單地為大多數人所知曉,音樂也不會例外。任何專門話語的系統發展,都是為獨特追求所驅使的,獨特追求的合理性,則保證了獨特話語的合理性。其實,對于現代主義的音樂創作而言,只要明確其所具有的“打破一切傳統創作規范限制,探索一切可能的創新性的音響”的獨特感性追求,就可以為獨特的成果找到充足的理由。作為尊重這些音樂創作的成果是一回事,而要求所有人都喜歡這些音樂作品則又是另一回事。人類音樂愛好的差異性,正是在這種不同的感性追求中出現。現代作曲家與公眾音樂審美興趣的差異也因其在音樂中的不同感性追求而迥然異趣。[6]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聽眾變得不那么對抗,早期那樣的激怒最終冷卻了下來,因為新的聲音開始得到接受。這是因為音樂藝術追求個性,是從“共性創作”完全轉向“個性創作”發展的必然邏輯結果,只是在20世紀以更加極端和劇烈的方式表現罷了。也正是由此產生了專家文化與大眾文化的裂變,或者說作曲家與聽眾的分離。各種風格和流派的代表作曲家,以完全不同的寫作手法和技術語言表達對世界對人生的態度和看法,音樂在20世紀以后所經歷的觀念創新和語言更迭,其程度之烈超過了以往所有時代的總和。每種音樂流派都有自己的追隨者和聽眾群。作為吉尼斯戶外音樂會觀眾紀錄保持者:1998年9月6日,為紀念莫斯科建城850周年舉辦的讓雅爾專場音樂會,觀眾人數達350萬。在這次音樂會上,讓雅爾除了運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舞臺視頻和激光設備外,還邀請到“聯盟”號宇宙空間站的兩名宇航員通過衛星與現場視頻對接,一時間震動全球,在世界音樂會史上開辟首創。
隨著傳播媒介的飛速發展,各種傳媒科學技術對音樂領域進行了全方位的滲透和影響,特別是互聯網技術日新月異的急速發展,使人們接受、欣賞音樂渠道呈多元化,方式更加層出不窮,音樂呈現出多種藝術、多種媒體信息綜合化的情形,“聽眾”作為人類音樂生活中極為重要,同時也是音樂生活中占據數量最多的一個群體,其“聽眾”稱謂的單一概念進而轉換為“受眾”的全方位接受音樂信息概念,“音樂受眾”的音樂審美過程,是一個全方位、多層面、多種感官共同參與的接收信息的過程,是一個主體被動接受同時又體現主體能動性的辯證過程。從被動接受音樂信息轉向了主動參與和自由選擇音樂信息,甚而可以左右音樂潮流的趨向,各種音樂傳播媒體也因爭取聽眾而競爭激烈,五花八門的音樂載體輪番角逐登場,搶占音樂市場。通過各種音樂傳播媒體,聽眾聽到了向他們撲來的音樂,歷史上還從未有過一個時期像在20世紀結束的時候那樣擁有如此眾多的聽眾,或者說擁有如此大量的音樂風格可以選擇。
四、結語
20世紀作為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其跨文化互動的深度和強度是史無前例的,20世紀已經落幕,這股潮流卻還在繼續加速。還有一個更具影響力的因素在塑造著未來幾代人的音樂生活,那就是圍繞著計算機發展建立起來的、日新月異的技術系統。新的計算機技術將會帶來新一輪音樂變革,變革會帶來多種可能的結果,預測音樂的未來是非常困難的,但理解世界歷史上最近的一個階段音樂發生了什么,現在正在發生什么,卻是理解未來音樂將發生什么的最好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