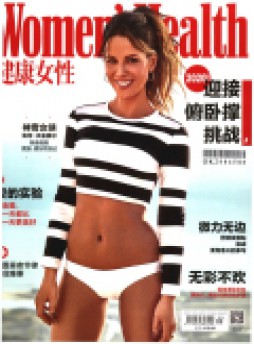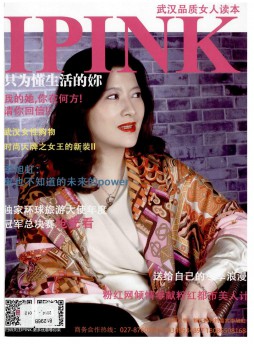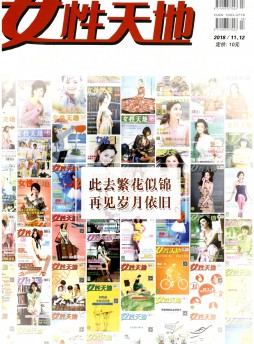女性婚姻與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的法律比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女性婚姻與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的法律比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唐代社會開放,禮法寬松,女性在律法和禮俗上享有較大的婚姻自主權(quán)及財(cái)產(chǎn)權(quán);宋朝受商品經(jīng)濟(jì)繁榮的推動,禮法文化雖然趨于保守,但婦女的法律權(quán)益較之于唐代并未減少,且增添了濃重的時代色彩,人們更加注重婚姻的經(jīng)濟(jì)因素。本文從法制史的角度,比較唐宋女性權(quán)益的法律規(guī)定,認(rèn)為宋朝沿襲唐朝律令的法律以及社會禮俗,依然在較大程度上保障了女性的婚姻與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在這一方面唐宋一脈相承,并沒有太大的改變。
關(guān)鍵詞:唐宋社會;女性;法律權(quán)益
一、唐宋婦女婚姻自主權(quán)的法律比較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婚姻禮俗。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子女不能違背父母之命去自由選擇婚姻,否則會受到禮與法的雙重懲罰。正如孟子所言:“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1]2711但是,在社會開放和經(jīng)濟(jì)繁盛的唐宋時期,婚姻禮俗和法制呈現(xiàn)出空前寬松的局面,傳統(tǒng)禮法對女性的束縛明顯減少,女性貞節(jié)觀念也趨淡薄,婦女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權(quán)。概括起來,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擇偶自主權(quán)《唐律疏議·戶婚》規(guī)定:“諸卑幼在外,尊長后為定婚,而卑幼自娶婚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從尊長,違者杖一百。”[2]747唐律這條規(guī)定無疑給成年子女自主婚姻提供了法律保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婚姻自主權(quán)。事實(shí)上也如此,唐代社會各階層女性自主決定婚事的事例屢見不鮮。有詩文為證,詩人白居易《議婚》詩寫到:“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詩中生動描繪了富家女子向往愛情自由的神態(tài),可做唐代女性追求自主婚姻的注腳。《太平廣記》曾敘述多起女子自主婚姻的事例。如崔韜游安徽滁州時,有女子主動以身相許,該女子自述家貧,但想嫁與一良人。崔韜為女子的誠意所動,最終與其結(jié)為夫妻。牛僧孺的筆記小說《玄怪錄》記載名門韋氏之女,“及笄二年”,全然不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最后選擇嫁給了自己中意的張楚金。類似的自主擇偶的愛情歡歌在唐代各類文學(xué)作品中被不斷演繹著,于是有了后人耳熟能詳?shù)拇搡L鶯與張生的千古佳話。唐記小說的創(chuàng)作源于現(xiàn)實(shí),反映了當(dāng)時的社會生活,具有較高的歷史真實(shí)性。由于社會空前開放,唐朝出現(xiàn)了較多與胡族通婚的現(xiàn)象。如《新唐書》記載裴光庭母庫狄氏為鮮卑女,陳楚母張氏為契丹女。[3]1532《舊唐書》載楊收母長孫氏為鮮卑女,薛昌朝妻王氏為契丹女,李邕妻扶余氏為靺鞨族。[4]可見唐朝不同民族之間通婚現(xiàn)象比較常見,間接反映了唐代女子擇偶觀的開放性。宋朝法律對于婚姻自主權(quán)的規(guī)定基本沿襲了《唐律疏議》,為子女自主擇偶開了綠燈。《宋刑統(tǒng)》曰:“卑幼謂子孫弟侄等,在外謂公私行李之處,因自娶妻,其尊長后為定婚,而卑幼自娶婚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從尊長所定,違者杖一百。”[5]從相關(guān)史載來看,這里所謂的“卑幼”絕不僅限于指男性青年,也包括成年女性。依照宋律的規(guī)定,凡成年子女在外自行嫁娶的行為,如果是家中家長訂婚在后的,則從子女之意。這實(shí)際上承認(rèn)了成年子女在家庭之外享有一定的自主擇偶權(quán)。《宋刑統(tǒng)》曰“為婚之法,必有行媒”。[5]宋代“媒人”這一新興職業(yè)發(fā)展迅速,甚至出現(xiàn)了官媒,這是前朝從未出現(xiàn)過的現(xiàn)象。依照宋代禮法,女方如有中意的對象,也可找媒人說媒,一定程度上落實(shí)了子女自主擇偶的法律規(guī)定。婚約成立后男女雙方均不能毀約,否則將受到法律的懲罰。宋律規(guī)定“諸許嫁女已報(bào)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杖六十。男家自悔者不坐,不追聘財(cái)。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財(cái),亦是。若更許他人,杖一百,已成,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減一等,女追歸前夫。前夫不取還聘財(cái),后夫如法。”[6]顯然,宋律對于男女悔婚的懲罰沿襲了傳統(tǒng)的禮法。男方悔婚主要損失其聘禮,女方悔婚則要承擔(dān)一定的刑罰責(zé)任,這體現(xiàn)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應(yīng)當(dāng)指出的是,宋代高度發(fā)達(dá)的商品經(jīng)濟(jì)也改變著婦女的擇偶觀念,“厚嫁之風(fēng)”盛行。人們普遍注重聘禮、財(cái)產(chǎn)等經(jīng)濟(jì)利益,通常會將錢財(cái)列為能否締結(jié)婚姻的重要因素。為了保證女兒在婆家的地位,女方娘家常贈與貴重“奩產(chǎn)”作為陪嫁。但厚嫁之風(fēng)也給社會帶來了不良影響,給普通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負(fù)擔(dān),不少人因懼怕日后給女兒準(zhǔn)備巨額嫁妝而溺殺女嬰,社會上也出現(xiàn)了很多大齡剩女,她們大多是因?yàn)榧抑袩o法支付巨額嫁妝,以至于到了適婚年齡還待字閨中。隨著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自主意識的加強(qiáng),上層社會女子在擇偶過程中出現(xiàn)了高標(biāo)準(zhǔn)的趨勢,程顥之女就是如此。史書記載她“幼而莊靜,……,風(fēng)格瀟灑,趣向高潔,發(fā)言慮事,遠(yuǎn)出人意,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意。”[7]因?yàn)樗远ǖ膿衽紭?biāo)準(zhǔn)過高,以至于七八年未曾找到中意之人。在上層社會,婚姻還常具有政治色彩。依宋朝制度,娶皇族宗室女子者皆可授予官職,于是許多商人為了獲得官職,爭娶宗室女子,導(dǎo)致許多宗室以女賣婚,用來換取錢財(cái),出現(xiàn)了政治尋租現(xiàn)象,敗壞了政治風(fēng)氣。
(二)離婚自主權(quán)婚姻事關(guān)人生幸福。古代女子即使嫁錯了對象,通常缺少再次選擇的機(jī)會,因?yàn)閶D女缺乏離婚的自主權(quán)。但在商品經(jīng)濟(jì)繁榮發(fā)達(dá)的唐宋時期,由于社會較為開放,婦女的貞潔觀念相對淡薄,婦女享有一定的離婚自主權(quán)。史載顯示,唐朝女子不僅具有一定的擇偶自主權(quán),還有離婚自主權(quán)。女子對婚姻不滿而離婚的事例在史籍中多有所見。如《太平廣記》記載唐侍御史李逢年和妻子(御史中丞之女)感情不和,妻子主動提出了離婚。[8]當(dāng)然,古代中國是典型的男權(quán)社會,即使在婦女地位較高的唐代,離婚的主動權(quán)多數(shù)掌握在男子手中,法律也偏重于維護(hù)男子權(quán)益。例如《唐律疏議》所規(guī)定的“七出”便是男子提出離婚的法律條件。所謂“七出”源自于秦漢,《儀禮》指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妒忌、惡疾,這些原本是禮俗上男子休妻的傳統(tǒng)理由,唐代首次將這些禮俗納入了法律。《唐律疏議》還有所謂“三不去”的法律禁令,如女性處于“經(jīng)持舅姑之喪、娶時賤后貴、有所受無所歸”這三種情形,男方不得提出休妻,若女性犯義絕、淫佚、惡疾,則不拘此令。[9]315依照唐代律法,妻子有“七出”中的任何一種情形,丈夫可解除婚約,不必經(jīng)過官府的許可。這無疑給了男性比較大的離婚權(quán)利。在“三不去”中,有持舅姑喪及糟糠之妻等情形,丈夫是不能提出離婚的,否則要受到法律的處罰,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hù)了已婚婦女的權(quán)利。此外,唐律中有所謂“和離”,即協(xié)議離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2]747這條規(guī)定也給女性提供了自主離婚的空間。依律,如果夫妻婚后生活不協(xié)調(diào)、不和諧,或者沒有感情基礎(chǔ),可協(xié)議離婚,法律保護(hù)這種“和離”。唐律中所謂“義絕”,是指夫妻雙方任何一方做出有違夫婦之義的事情,如夫?qū)ζ逇獨(dú)⑿袨榧捌迣Ψ驓獨(dú)⒌龋写饲樾畏杀銖?qiáng)制離婚,當(dāng)事人不主動離婚,則要追究刑事責(zé)任,從而保護(hù)受害方的權(quán)益。宋朝婦女離婚自主權(quán)分前期和后期兩個階段。據(jù)《宋刑統(tǒng)》記載,宋朝前期承襲唐朝律法,離婚條件也分“七出”“三不去”“義絕”“和離”和違律結(jié)婚。妻子如犯有無子、淫亂、不孝順父母、多言、盜竊、妒忌、惡疾七項(xiàng)中任何一項(xiàng),丈夫可以名正言順地和妻子離婚,“七出”的主動權(quán)實(shí)際上掌握在丈夫的手中。而“三不去”是在妻子處于無家可歸,為公婆守孝及糟糠之妻三種情況下,丈夫不能拋棄妻子,否則要受到法律處罰,這一定程度上保護(hù)了婦女的權(quán)益。顯然,唐宋律法中關(guān)于離婚的相關(guān)規(guī)定沒有太大的變化,體現(xiàn)了唐宋兩朝法律上的承續(xù)性。依據(jù)宋律規(guī)定,如果感情破裂且經(jīng)官府強(qiáng)制離婚,而當(dāng)事人拒不執(zhí)行的,將受到律法的懲罰。[10]此外,宋朝沿襲了唐代有關(guān)“和離”的法律規(guī)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彼此情不相得,兩愿離者,不坐”[11]。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女性提出離婚的自主權(quán)。宋律對違律結(jié)婚行為做出了嚴(yán)格的處罰規(guī)定,凡同姓夫妻、同宗族的異輩婚姻、雙重婚約等違反禮法的情形,均須遵守律法的規(guī)定解除婚約。為了維護(hù)女性權(quán)益,宋朝規(guī)定凡婚前有變故者、丈夫外出多年無歸、丈夫犯罪、丈夫?qū)⑵拮淤u予他人為奴為婢等情況,可以由女方家長要求解除婚約,如果男方不同意,女方則可到官府提起訴訟以維護(hù)權(quán)益。南宋時期,律令規(guī)定夫妻關(guān)系中有男人三年不歸者,女方可以依法解除婚約。顯然,較之于唐代的律法,宋朝加強(qiáng)了對婦女權(quán)益的保護(hù)。北宋后期,尤其是從宋仁宗開始,程朱理學(xué)盛行,理學(xué)家提倡“守節(jié)”、強(qiáng)化封建倫理綱常,要求婦女必須做到“三從四德”,禁錮了社會各階層的思想。南宋法律明顯限制了女性離婚的權(quán)利,如為人妻者若擅自離婚,將會受到法律的懲罰,即所謂“諸妻擅去其夫,徒兩年。”
(三)改嫁自主權(quán)《禮記》曰:“夫婚禮,萬世之始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這種“從一而終”的婚嫁觀念始終貫穿于封建社會,[12]135影響著女子對愛情的追求。開明的唐朝形成了不同以往的婚姻觀念,人們的貞節(jié)意識淡薄,整個社會不歧視婦女再嫁,從上層社會到下層民眾普遍存在婦女再嫁與改嫁的現(xiàn)象,可以說當(dāng)時社會形成了改嫁自主共識。李唐皇室多有改嫁之事,如李建成之妻楊妃改嫁唐太宗李世民,太宗一度欲立其為后。武則天本是太宗的才人,后被其子高宗立為后。唐代公主改嫁的事情更是頻繁發(fā)生,太平公主三度嫁人,先適薛紹,再嫁武承嗣,后嫁武攸暨;安樂公主也有一次改嫁。有學(xué)者統(tǒng)計(jì)了唐代公主再嫁現(xiàn)象:唐高祖時期有四人、太宗時期六女、高宗時期一女、中宗時期三女、唐睿宗時期二女、唐玄宗時期八女、肅宗時期一女。其中中宗時期三嫁者三人、玄宗時期一人、肅宗時期一人。[13]官宦之家也多有女子改嫁現(xiàn)象,如唐憲宗時期,韓愈之女先嫁其父門生,后改嫁樊宗懿。當(dāng)時不僅上層社會婦女改嫁能夠得到普遍認(rèn)同,民間的改嫁現(xiàn)象也很平常。婦女改嫁分為離婚后的改嫁和夫亡后的改嫁。唐太宗時期為了增加戶口曾出臺過鼓勵孤寡者再嫁的政策。《太平廣記》記載某人妻向其夫索取休書,為的是“廢我別嫁”。唐朝雖有婦女頻繁再嫁和改嫁的現(xiàn)象,但也尊重女性“守節(jié)”的自主權(quán),除了家長之外,其他人不能干涉。唐律規(guī)定:“諸夫喪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qiáng)嫁之者,徒一年;期親嫁者,減二等。各離之。女追歸前家,娶者不坐。”[2]747這條規(guī)定表明,非親族強(qiáng)迫喪夫女性改嫁將會受到法律懲罰。在理學(xué)盛行的宋朝,女性改嫁能否得到社會的認(rèn)同?事實(shí)是:理學(xué)在宋代的影響力有限,婦女改嫁和再嫁的現(xiàn)象依然普遍。宋律有很多傾斜于保護(hù)婦女再嫁和改嫁的規(guī)定。宋初曾下詔夫亡而無子者,服除聽還其家。宋神宗年間,“詔宗室袒免以上女,與夫離而再嫁,其后夫己有官者,轉(zhuǎn)一官。”[14]7087宋徽宗規(guī)定再嫁婦女允許再給一次嫁妝,這無疑保證了再嫁婦女的經(jīng)濟(jì)地位。《宋刑統(tǒng)》規(guī)定“諸夫喪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qiáng)嫁之者,徒一年。”[15]217強(qiáng)調(diào)除祖父母、父母之外,任何人不得強(qiáng)迫自愿守節(jié)的女子改嫁。北宋自神宗朝開始,律法規(guī)定如果丈夫長期外出不歸,通過官府的認(rèn)定后允許再嫁,明顯加強(qiáng)了對女性權(quán)益的保護(hù),即所謂“不逞之民娶妻,給取其財(cái)而亡,妻不能自給者,自今即許改適。”[14]1895南宋規(guī)定丈夫外出“三年不歸,亦聽改嫁。”[16]353另外,“女居父母喪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并聽百日外嫁娶之法。”[14]11513可見宋朝律法對女性再嫁改嫁的規(guī)定越來越寬松,也更加人性化。例如丈夫失蹤后妻子無法維持生存時,法律給其出路,準(zhǔn)許改嫁。宋朝出臺了朝廷出資幫助寡婦再嫁的政策,甚至出現(xiàn)了朝廷為再嫁女追加封號的事例。據(jù)《諸軍婚嫁》規(guī)定,有孀婦未再嫁者,可以給與一定資財(cái)以示資助寡婦再嫁。宋朝鼓勵婦女改嫁是比較人性化的,社會各階層普遍贊成婦女再嫁。宋代皇室公主再嫁者不乏其人,如太祖同母妹、秦國大長公主最初嫁給了米德福,后再嫁忠武軍節(jié)度使高懷德。北宋時期,范仲淹在其所著書中表明了支持婦女再嫁的態(tài)度,并予以嫁資,其母謝氏就是再嫁者。范仲淹的兒子早亡,他沒有要求兒媳守節(jié),而是主動將其嫁給了進(jìn)士王陶。在民間,亦有許多家長主動要求子女改嫁的,王一的妻子吳氏,無子寡居,對家中老人能盡孝道,家中老人可憐吳氏孤苦,為她找了再嫁夫家,并認(rèn)了再嫁夫?yàn)榱x子。這種民間婆婆要求媳婦再嫁的事例實(shí)屬難能可貴,體現(xiàn)了宋朝女子改嫁風(fēng)氣的寬松。比較起來,宋朝下層女性再嫁較多,主要原因在于上層女性受傳統(tǒng)禮教思想束縛較重,而下層女性受到的封建禮教約束較輕,且多數(shù)是因?yàn)榻?jīng)濟(jì)困苦、無人依靠的原因而再嫁。方建新、徐占軍著《中國婦女通史·宋史卷》對《名公書判清明集》中婦女再嫁的統(tǒng)計(jì)研究,也證實(shí)南宋仍多有女性再嫁的事例。[17]379可見宋朝婦女守節(jié)之風(fēng)并沒有后人想象的那樣深受程朱理學(xué)束縛,理學(xué)對宋朝的影響是有限的。總體上來說,宋朝女性在改嫁再嫁上有一定的自主權(quán),這體現(xiàn)了宋朝統(tǒng)治政策人性化的一面。
二、唐宋婦女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的法律比較
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社會開放的唐宋時期,女性不僅可以蓄私財(cái),更有一定的財(cái)產(chǎn)繼承和管理權(quán),以下試做比較分析。
(一)閨閣之女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一是奩產(chǎn)所有權(quán)。閨閣之女出嫁時有獲得妝奩的權(quán)利,這是古代社會的傳統(tǒng)禮俗。春秋時期就有“賦封田以嫁妝”①的記載。通常情況下,古代女子的嫁妝有衣物、家具、生產(chǎn)資料、交通工具以及首飾、珠寶等各色物品。史載表明,唐朝在古代歷史上開創(chuàng)了立法保護(hù)女子嫁妝私有權(quán)的先例。依照唐律規(guī)定,嫁妝是屬于女性的私有財(cái)產(chǎn),不參與婚后家庭資產(chǎn)劃分。通常富裕的家庭會在女兒的嫁妝上大做文章,嫁妝的多寡決定了女子在夫家的家庭地位。以唐朝公主婚嫁為例,唐高宗之女太平公主出嫁時,不僅嫁妝十分豐厚,婚禮場面也異常豪華。她的婚禮被安排在長安附近的萬年縣舉行,婚禮之夜照明的火把竟烤焦了沿途的樹木。為了讓寬大的婚車通過,甚至拆了城中的圍墻,其婚嫁場面之盛大可見一斑。《太平廣記》記載富裕的蕭家嫁女時嫁妝“寶鈕犢車五乘,奴婢人馬三十匹”[18],奩產(chǎn)可謂豐厚。宋朝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形成了“婚姻不問閥閱”而“直求資財(cái)”的風(fēng)氣,社會上盛行著厚嫁之風(fēng)。女方接受聘禮及回送禮物十分豐厚,通常包括“綠紫羅雙匹、彩色緞匹、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須掠女工等”。[19]宋律對女子嫁妝給予法律保護(hù),強(qiáng)調(diào)“諸應(yīng)分田宅者,及財(cái)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財(cái),不在分限。”[15]217女子嫁妝的私有權(quán)受到侵犯時,則可以通過法律途徑維權(quán)解決。民間不乏這種事例,對在室女嫁妝的保護(hù)落到了實(shí)處,保護(hù)了女性的私有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二是財(cái)產(chǎn)繼承權(quán)。依照“長幼有序”的傳統(tǒng)倫理,在財(cái)產(chǎn)繼承權(quán)方面歷代都有相應(yīng)的法律規(guī)定,男子通常是家庭財(cái)產(chǎn)的主要繼承人,女子也有財(cái)產(chǎn)繼承權(quán),只是份額少于男子。依照唐律規(guī)定,閨閣之女可以獲得的家庭財(cái)產(chǎn)繼承權(quán)是家中男子的一半,即“依子承父分法給半”[2]547。此外,唐律規(guī)定閨閣之女在“戶絕”(注:家中無男性家長或者家中無子嗣)時,享有完全的家庭財(cái)產(chǎn)繼承權(quán)。《太平廣記》記載唐朝時期鄭紹路過華山,和一個女子攀談后得知,這個女子為“戶絕”女,獨(dú)自擁有家產(chǎn)。[20]《唐令拾遺》載:“身喪戶絕者,所有部曲、奴裨、店宅、資財(cái),并令近親轉(zhuǎn)易貨賣,將營葬事及量營功德之外,余財(cái)并與女。”[9]835依唐律規(guī)定,“戶絕”家庭所有財(cái)產(chǎn)包括房屋、奴婢等均可以出售,除了辦喪葬之事需要的費(fèi)用,其他的全部財(cái)產(chǎn)歸女兒所有。宋朝前期律令規(guī)定女兒繼承財(cái)產(chǎn)的份額沿襲唐朝舊制,“諸身喪戶絕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資財(cái),并令近親轉(zhuǎn)易貨賣,將營葬事及量營功德之外,余財(cái)并與女。”[21]217宋承唐律,在室女是“戶絕”家庭財(cái)產(chǎn)第一繼承人,最高可以獲得全部遺產(chǎn)。
(二)已婚女子的財(cái)產(chǎn)繼承權(quán)一是娘家財(cái)產(chǎn)繼承權(quán)。依據(jù)唐朝禮法,出嫁女可以獲得本家的嫁妝,這份嫁妝是出嫁女的私有財(cái)產(chǎn),夫家是不能參與分割的。所以嫁妝的豐厚程度一定程度上能保證出嫁女在夫家的地位。除此之外,出嫁女也擁有娘家“戶絕”時全部家產(chǎn)的繼承權(quán),“百姓及諸色人死絕,無男空有女,已出嫁者,令文合得資產(chǎn)。[9]835唐朝把出嫁女和在室女“戶絕”時繼承財(cái)產(chǎn)的地位劃了等號,在室女和已嫁女在繼承娘家家產(chǎn)上享有相同的權(quán)利。宋朝沿襲了唐朝的規(guī)定,出嫁女子的嫁妝是其個人的財(cái)產(chǎn),不允許被分割和侵犯,由其自己支配。直到妻死之后,嫁資才遺留于夫家。另外,若女方要求離婚,有權(quán)帶走其嫁妝等私人財(cái)產(chǎn)。宋律規(guī)定,已嫁女有權(quán)參與娘家“戶絕”時的財(cái)產(chǎn)繼承,但份額較之唐朝有所減少。正如有學(xué)者指出的那樣,如果沒有在室女,則出嫁女“得資財(cái)、莊宅、物色,除殯葬營齋外,三分與一分,如無出嫁女,即給與出嫁親姑姊妹侄一分。”[22]317與唐代相較,宋代已婚女子的娘家財(cái)產(chǎn)繼承權(quán)被削弱了。二是夫家財(cái)產(chǎn)繼承權(quán)。唐朝,為人妻者在夫家多有“管鑰”權(quán),家中財(cái)產(chǎn)是共有財(cái)產(chǎn),但是管理權(quán)仍由家長掌管。一般家庭設(shè)有存放貴重物品如地契、銀票、賬本、首飾、古玩等物品的倉庫或箱子,妻子通常有掌管家庭財(cái)產(chǎn)的機(jī)會和權(quán)利。如《舊唐書·李光進(jìn)傳》記載,“光顏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jìn)娶妻,光顏使妻管鑰家藉財(cái)物歸于其擬。”[4]865母親去世之后,由其妻子掌管家中財(cái)物,這是為人妻在夫家的財(cái)產(chǎn)掌管權(quán)的具體體現(xiàn)。社會認(rèn)同這種做法,并形成了習(xí)慣,無論貴族大臣或是平民百姓家,為人妻者大多有這種管理家財(cái)?shù)臋?quán)利。唐律規(guī)定,丈夫死后,如果家中無子嗣的,由妻子繼承丈夫全部家產(chǎn);有子嗣的,寡妻可以和兒子同分財(cái)產(chǎn),這種分配順序只適用于守節(jié)的婦女。如果妻子選擇改嫁,則沒有權(quán)利參與丈夫的財(cái)產(chǎn)分配。男方解除夫妻關(guān)系后,女方可以帶走嫁妝,除此之外男方還給女方一定錢財(cái)以供女方婚后正常生活。女方的嫁妝是男方不能參與分割的財(cái)產(chǎn),是女性婚后的個人生活保障。在宋朝家庭中,一般由丈夫享有財(cái)產(chǎn)的使用權(quán)和支配權(quán),丈夫去世,妻子才有可能獲得家中財(cái)產(chǎn)的支配權(quán)和使用權(quán)。與唐朝一樣,如果妻子守節(jié),則可獲得全部資產(chǎn);如果妻子改嫁,財(cái)產(chǎn)歸子女繼承,沒有子女的家庭,財(cái)產(chǎn)大部則被官府沒收。三是寡母的家庭財(cái)產(chǎn)處置權(quán)。唐宋時期,寡母具有較高的家庭地位和財(cái)產(chǎn)管理權(quán)。唐令中,寡母可以成為授田的對象,當(dāng)時規(guī)定“諸給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頃,老男、篤疾、廢疾以四十畝,寡妻妾以三十畝,若為戶者則減丁之半……”[9]540寡母或寡妻個人財(cái)產(chǎn)包括女性從娘家?guī)淼募迠y及在娘家繼承的財(cái)產(chǎn)。寡母也接受來自兒子的贍養(yǎng),如河南人李素“母夫人固在,食其祿”。[23]73此外,寡母還有家產(chǎn)管理與處置權(quán)。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寡母管理家財(cái)?shù)睦硬粍倜杜e。如《太平廣記》記載東洛福昌人陳彝爽進(jìn)士及第后,異地任官。其母因戀洛陽舊居,于是獨(dú)自留在舊居掌管家業(yè)。[24]
宋朝寡母有家財(cái)管理支配權(quán),有權(quán)處置家庭財(cái)產(chǎn)。如宋人張介然死后,有三子,家中事悉聽其母劉氏。宋律規(guī)定:“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cái)。借使其母一朝盡費(fèi),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25]831可見丈夫家產(chǎn)控制權(quán)實(shí)際上是掌握在寡母手中。宋代寡母的家產(chǎn)管理權(quán)已是司空見慣之事,但宋朝寡母的財(cái)產(chǎn)處置權(quán)仍有許多限制,比較獨(dú)立的家財(cái)處分權(quán)則表現(xiàn)在作為家長的寡母身上。據(jù)《宋刑統(tǒng)》記載,“尊長既在,子孫無所自專。若卑幼不由尊長,私輒用當(dāng)家財(cái)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26]197家長在,子孫不能擅自動用財(cái)務(wù)。此律法確定了寡母的財(cái)產(chǎn)處置權(quán)。如果兒子在沒有得到母親允許的情況下處分家產(chǎn),會受到律法的懲罰。史載“孫某有母在,而私以田業(yè)倚當(dāng),亦合照瞞昧條,從杖一百。”[27]284《宋刑統(tǒng)》也明確“應(yīng)典賣物業(yè)或指名質(zhì)舉,須是家主、尊長對錢主,或錢主親信人當(dāng)面署押契貼,或婦女難于面對者,須隔簾幕親聞商量,方成交易”[15],宋律承認(rèn)母親有訂契約的權(quán)利,這是寡母者財(cái)產(chǎn)處置權(quán)的具體體現(xiàn)。當(dāng)然,歷來權(quán)利與義務(wù)是相互依存的。母親在擁有家庭財(cái)產(chǎn)處置權(quán)的同時,更多承擔(dān)教養(yǎng)子女的義務(wù),母親平日必須教子孫學(xué)習(xí)知識,否則要追究母親的責(zé)任。正如宋人所說的那樣“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愛而不知教也。”[28]綜上所述,比較唐宋女性在婚姻及財(cái)產(chǎn)上的法律權(quán)益,我們無法簡單用進(jìn)步或是倒退來概括此間的歷史演進(jìn)。以往人們多認(rèn)為宋朝受理學(xué)思想影響,禁錮了女性的發(fā)展,這種觀點(diǎn)似與史實(shí)不盡符合。我們看到的事實(shí)是:沿襲唐朝律令的宋朝法律以及社會禮俗,依然在較大程度上保障了女性的婚姻與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在這一方面唐宋一脈相承,并沒有太大的改變。
作者:李福長;易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