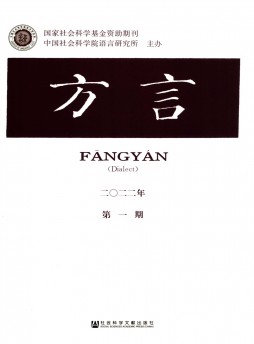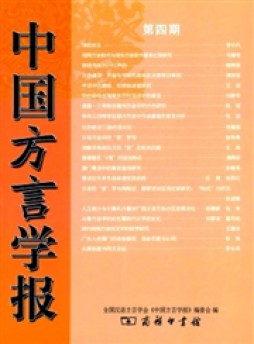方言歸屬之爭及成因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方言歸屬之爭及成因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重慶理工大學學報》2015年第八期
關于永興方言歸屬的不同意見從20世紀30年代一直持續到21世紀,較其他方言而言,永興方言的歸屬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爭議,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語言研究者們各自使用的分區標準與方法存在差異;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則是與永興方言自身的復雜性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分區標準與方法存在差異導致永興方言歸屬存在分歧楊時逢先生的分區方法可以概括為重要特點派,即“把某一處方言特點歸納起來,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點,聲調的類別、音韻特點、開合口及調類等區別來作為分區的條件”。《湖南省漢語方言普查總結報告(初稿)》所使用的分區方法可以概括為印象派,憑借分區者的語言印象將湖南方言分成幾個土語群,并總結出明顯特點來,然后把特點大致相近的土語群合并為一個方言。日本學者辻伸久《湖南方言的分類和分布》的分區法就是比較純粹的單一特征法,以古全濁聲母的演變情況作為唯一標準來進行分區。周振鶴、游汝杰《湖南方言區畫及其歷史背景》的分區法則是數學與人文地理的結合派,首先通過數學方法比較湖南75個縣方言特征的接近程度,然后再結合語言、歷史、人文地理等因素進行分區的調整和補充[6]59。鮑厚星與顏森的《湖南方言的分區》采用的分區標準頗為靈活多變,可以概括為語音詞匯結合派,即不但考慮語音特點,還兼顧到了詞語的異同來進行方言分區。李藍《湖南方言分區述評及再分區》采用的是聲韻調三重投影法,先從選擇出來的幾個代表點的語音系統中抽取出聲母、韻母、聲調系統的區別性特征,然后以區別特征來分析各點的方言相近程度,最后歸并相近方言點。可見,各家在分區時所使用的標準和方法是存在差異的,分區標準與方法的不同難免導致永興方言的歸屬存在分歧。
(二)永興方言自身的復雜情況給方言的歸屬帶來了多種可能
1.永興方言內部存在較大的差異早在《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中,趙元任、董同和在記錄永興縣方言的語音面貌時,就曾指出“永興城鄉方言據發音人說,江右、江左有二種方言”;在《永興縣縣志•方言》中指出“根據地理環境和語音語調的差異,縣內方言以便江為界,分為江左方言和江右方言。江左受郴州話的影響較深,江右又深受贛語的影響”。同時縣志還指出根據當地人的語感,多數人認為便江東西的方言差異非常大。然而,《湖南方言調查報告》調查的具體語音點僅有永興縣東北角的白泥塘鎮(今柏林鎮),也就是便江以東(江右)方言的語音情況,后來不少專家對永興方言的歸類就是以這份報告提供的語音材料作為基礎,如日本學者辻伸久的分區,周振鶴、游汝杰的分區,李藍的分區。后來的有些專家對永興方言進行了重新調查,如李冬香的《湖南贛語的分片》等,但仍然沒有給永興方言的東西內部差異予以足夠的重視。這樣看來,對永興縣便江東西方言差異的忽略必然會影響到對永興方言歸屬的全面客觀認識。永興縣全縣25個鄉鎮,為了解便江東西方言的差異,筆者曾選取永興縣東、中、西3鎮———柏林鎮、城關鎮、馬田鎮作為永興方言的3個代表點開展了深入的田野語音調查。柏林鎮作為永興縣東部的大鎮,白銀治煉業相當發達,故永興縣也因此有“中國銀都”之稱,該鎮的經濟一直較周邊地區發達,是周邊鄉鎮趕場云集之地;城關鎮作為永興縣縣政府駐所之地,是全縣的政治、經濟、教育中心,在地理上居于永興縣的中心地帶,便江正好穿過城關鎮,分永興縣為兩片;馬田鎮素有“湘南第一鎮”的美名,是永興縣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一個鎮,也是周邊鄉鎮(悅來鄉、高亭鄉、油麻鄉、耒陽市小水鋪等地)趕場的重要地點。可見,不論從地理位置上,還是從方言的影響力上,這3個鎮都是能夠代表便江東、中、西的方言實際的。為呈現便江東西的方言差異,以古全濁聲母的演變情況為例,我們將以上3點的語音情況作一個對比。以上所舉例字均是日常生活中常說常用之字,因此更能保留語言中相對底層的語音面貌。
從古調查的三個點的讀音來看,我們發現柏林點的這些字大多讀送氣音;到了城關,送氣音明顯減少;再往西到了馬田,這些字就都不送氣了。湘語與贛語最顯著的區別特征是古全濁聲母的演變規律:湘語古全濁聲母舒聲字今逢塞音、塞擦音時,無論清濁,一般念不送氣音;贛語古全濁聲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時與次清聲母合流,無論平仄多讀送氣清音。可見,在全濁聲母的演變上,柏林點的贛語色彩較明顯,從東往西,贛語的這一特點在明顯減弱直至消失。在地理位置上,柏林鎮與江西省隔縣相望,其受贛語的影響與沖擊較大;越往西部,這一沖擊的影響力也在逐漸的弱化。
2.永興方言深受郴縣西南官話影響永興縣與郴縣關系密切,這不僅體現在地理位置上的永興縣南部與郴縣北部(今郴州市的蘇仙區、北湖區)接壤,還體現在永興縣的歷代建置沿革上。現代方言的分區與歷史上的二級行政區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歷史上各郡(府)的治所所在地,常常是各郡(府)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交通中心,在語言上治所對其所屬的轄區也存在較強的內聚力,轄區對治所的語言也較容易存在認同感。那么,永興縣的建置及歷史沿革情況如何呢?表2是筆者根據《永興縣志》和《郴州市志》的相關資料整理所得。通過上述材料,我們發現永興縣與郴縣在建置沿革上有著密切的關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永興縣歷史上所屬之郡、軍、路、府、州、專區、市的治所長期設在郴縣。由表2可見,從西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便縣至今,二千多年來,永興縣所屬之郡、府等之治所不在郴縣的只有以下兩個時期:新王莽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至東漢建武元年(公元25年),所屬之南平郡治所設在南平亭(今衡陽市耒陽市);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至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治所設在平陽縣(今郴州桂陽縣)。表2中元代治所設在郴陽縣,是因為當時改郴縣名為郴陽縣;明朝1376年以后直至民國元年(1912年)這段時間治所設在郴州,是因為這一時期郴陽縣并入郴州;1958年郴縣城關鎮改為郴縣郴州市,至今治所設在郴州市。不難看出,永興縣所屬之郡、府等之治所設在郴縣有長達兩千年的歷史,自然而然,郴縣的這一歷代郡、府之治所的身份,必定使其自身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交通等方面形成一定的內聚力,對轄區內各縣形成較大的影響力,處在轄區范圍內的永興縣自然也不例外。第二個方面,永興縣與郴縣的特殊關系還體現在永興縣在歷史上曾2次并入郴縣。“第一次是南朝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便縣并入郴縣,陳永定三年(公元559年)復置便縣;第二次是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便縣再次并入郴縣,唐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分郴縣北置安陵縣即今天的永興縣。”歷史上的這兩次永興縣并入郴縣有近三百年的歷史,這也使永興縣與郴縣的關系顯得尤為密切。地理位置的接壤、兩千年的治所所在、幾百年的并入歷史,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郴縣對永興縣的經濟、文化、語言等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郴縣(今郴州市蘇仙區、北湖區)屬北方話的西南官話片,永興境內尤其是便江以西的鄉鎮,因在地理位置上多與郴縣接壤或鄰近,受官話的影響也就更為明顯。
3.永興方言與江西贛方言關系密切永興縣與江西省雖不接壤,但與江西省隔縣相望,地理位置上的接近無疑成為語言之間相互影響的有利條件,然而江西贛方言與永興方言的密切關系還體現在人口大遷移背后的語言影響。“移民運動是語言宏觀演變的最重要的原因”,移民要對新居地的固有方言產生深刻影響,必須具備數量大以及遷徙時間集中兩個條件。據譚其驤研究,自宋開始一直到清代,江西人大批遷入湖南。元代連年戰禍,使得湖南省大部分地區田園荒廢,居民百不存一。隨后,外省人特別是江西人,大批涌進湖南,明初僅寶慶、靖州、湘陰等府州縣就有474族。這種大規模遷徙的結果,使得明代的湖南居民人口中,外來移民(江西移民為主)遠遠多過湖南當地的土著人。那么,從宋代到清代,在江西人大量遷入湖南的大時代背景下,郴州及永興的人口遷入情況又如何呢?(1)郴州人口遷入情況。表3是筆者根據郴州市志的有關資料所得,從表3可見,宋代是江西人口遷入郴州的鼎盛時期,多達69戶;元代,外地遷入總戶數雖然不多,但大多來自江西,共有22戶;明代是本省外地人口遷入的高峰期,但此時江西人口的遷入仍有30戶;清代是廣東人口遷入的高峰期,江西人口的遷入為10戶。宋代至清代,郴州的遷入人口以江西人最多,總計131戶,占外地遷入人口的34%;本省外地遷入人口居第二位,共99戶,占26%。在分析上述資料的過程中,除了江西人口的直接遷入,我們不能忽視江西人口經由湖南省其他地區輾轉遷入郴州的現象。也就是在宋、元時期遷入湖南其他地區的江西人口,到明清時期又由湖南省其他地區再次遷入郴州地區,那么這一部分人口也可以認為是江西人口的遷入。因為缺少相關的數據資料,這種原籍江西經由本省他地輾轉遷入郴州的人口戶數,我們還暫時沒有辦法進行統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現象在當時還是相當普遍的。有一郴州永興縣馬田鎮馬田村劉氏家譜資料,可以作為上述情況的一個佐證,據家譜載:劉氏祖始,一世祖劉式,原名克幾,字叔度,系籍江西臨江府清江縣荻斜村,仕宋太宗朝(公元976年~998年),官工部尚書。三世祖(劉式之孫),孟二郎,名政,字亨父,初舉孝廉不就,游歷于衡山之南遂家焉。七世祖,小三郎,名友榮,字應華,太學明經為士林望,由衡山遷耒陽城關。八世祖,小三郎長子正十一郎,住耒陽城關。十二世祖富遠有五子,第五子為鐘仁,鐘仁三子:文綬、文維、文惠。文綬、文維徙居耒陽小水鋪,文惠于明成化末葉(公元1485年)遷居永興縣馬田,當時年僅三十歲。自此以后其子孫在此繁衍生息。可見家譜中所記載的一世祖劉式原籍江西,三世祖劉政于北宋中葉遷至湖南衡陽,七世祖約在南宋末年遷入湖南耒陽,明代中葉十三世祖劉文惠遷入永興馬田。(2)永興人口遷入情況。宋代中原戰亂,為避戰亂,當時遷入永興定居的有曾、劉、陳3姓人氏,其中曾氏(曾鞏后裔)于紹興年間(1131—1162年)從江西南豐遷入,劉姓(劉式后裔)在宋朝南渡以后從江西吉安遷入,陳姓世居永興。元代,因當時政治動亂遷入永興定居的有鄧、彭、黃3姓人氏,其中鄧姓由江西饒州府遷入,彭姓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由江西南昌遷入,黃姓來歷不明。明代,有李、曹、馬3姓人氏遷入永興定居,其中李氏的一支由江西安福縣遷入,其余兩姓由本省外地遷入(如上文,不排除從江西輾轉遷入的情況)。清代,因經商、出仕、自然災害,外地人陸續遷入永興,其中有江西人,亦有本省外地人。宋以后從外地遷入的姓氏中,宋、元時期三姓之中有兩姓來自江西,明代三姓之中亦有一姓來自江西。總之,從宋代至明代,郴州和永興接納的江西移民比例都是相當大的,時至今日湖南人還常稱江西人為“江西老表(表親)”,可見這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宋至清代的這種時間相對集中式的大規模江西移民所帶來的贛語,給永興方言帶來的巨大影響也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說外來方言贛語融合甚至取代當地永興方言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二、結語
關于湖南永興方言的歸屬問題,近幾十年來不同的研究者形成了不同的意見,這場歸屬的歷史爭論與永興方言自身的內部差異有關,與永興方言深受西南官話的影響有關,同時也與因移民運動帶來的贛方言的影響有關。目前永興方言的歸屬已形成了趨于一致性的意見,即認為永興方言屬于贛方言,與此同時永興方言自身的復雜特點以及其兼有的西南官話及湘語特征的這一混合性也越來越受到研究者們的特別關注。
作者:尹喜艷 單位: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
- 上一篇:高校學風的文化屬性范文
- 下一篇:陳設藝術在餐飲空間中的應用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