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背山下的同性之愛的心理學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斷背山下的同性之愛的心理學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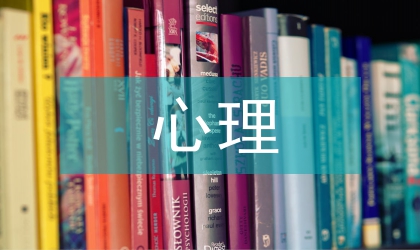
《電影文學雜志》2014年第十四期
一、恩尼斯和杰克成為男人的掙扎
從心理動力學的角度,男人的形成需要具備四個條件:(1)男性的生物結構;(2)男性的生理刺激;(3)與父親的認同;(4)與母親的解離。恩格斯和杰克應該不會缺乏(1)和(2),不僅如此,從外形上來講,他們還頗具魅力,俊朗的外表甚至像一個不老的神話。那么,他們的(3)和(4)發展得如何呢?關于他們的成長,描述的細節不多。恩尼斯,父母早亡,跟著姐姐和哥哥長大,只上過一年高中。9歲那年他曾經目睹農場上同居的兩個老牛仔被人亂棒打死并鞭尸,父親親自帶著他看到了整個場景,他曾看到兩個男人男性生殖器被活活扯下。這樣的童年夢魘一直深深地困擾著他。杰克,一個破爛農場主的兒子,家境似乎并不寬裕,重要的是這個不滿20歲的青年不管怎么努力,卻總是得不到父親的認同。兩個人的成長,有一個共同點,在成為男人的路上沒有被父親見證和祝福過。恩尼斯,父親缺席,讓恩尼斯少了一個可供認同的男性榜樣。早年目睹的創傷性事件內化成了恩尼斯內心巨大的超我,并且是以施虐者的形象出現的。一位缺席和施虐的父親,對于男孩來說,是一種雙重閹割。在一種無客體、無回應的世界當中,每個人只能靠愛自己成為它生存的惟一工具。而施虐性的父親,只能讓一個人自我閹割掉,以避免和男人競爭所帶來的威脅感。所謂的閹割,是一種象征表達,意味著犧牲男性的位置,或者無法成為一個男人。從人際模式中,我們了解到,父母對于孩子俄狄浦斯情感的處理和涵容是非常重要的:母親一方面要能享受兒子對他的愛戀,同時又不能出現誘惑性的行為;父親應該平靜地接受孩子對母親的迷戀,不必感覺被威脅,并隨時準備好做兒子的榜樣,同時接納兒子對他的攻擊渴求和貶抑。即科胡特所說的:“沒有敵意的堅決與沒有誘惑的深情。”恩尼斯父親早亡,印證了恩尼斯早年無意識的幻想:“殺了父親,好取代父親。”這一事實的應驗讓孩子贏得了巨大的俄狄浦斯勝利感的同時,也產生了罪惡“成為男人原來是如此邪惡!”按照梅蘭妮克萊因的說法,作為解決之道的一種可能性是,恩尼斯可以在一個女性的位置,以便修復父親。如此,我們便能夠理解,為何在和杰克的關系中,恩尼斯始終處于被動位置。分離之時,他也更加脆弱無助。心理學認為,青春期與同性的性也將影響性取向的發展。它將對同性戀的個體產生類似“印刻效應”的影響。如果不是杰克的主動,恩尼斯也許永遠會把同性戀的欲望潛藏在無意識的深處,如同他的爸爸一樣。
相比起恩尼斯的理智隱忍,杰克更加率性張揚,在兩人的關系中,也始終處于主動的一方。因為在杰克的成長中,創傷性的事件鮮少發生,杰克率性而為,他更像一個叛逆者。而相反的是,他愛的女人露琳和恩尼斯都很壓抑。從影片中,我們了解到影片中的一個細節。杰克死后,恩尼斯拜訪杰克的家人,杰克的父親對待兒子的男友,態度頗有些生硬冷淡,而杰克的母親見到恩尼斯,卻是由衷地喜歡,像是她另外一個兒子。由此我們可以猜測,杰克的成長中,父親嚴厲,而母親溫和。母親愛兒子可能比愛父親更多。父親在俄狄浦斯的競爭中,備感威脅,所以,一味地打壓兒子。因為不能認可兒子就意味著:我永遠是勝利者,你不可能贏過我!這讓杰克在成長中,會有很多的無助感,他永遠無法贏得一個男人的位置。此外,我們看到,當杰克成為父親后,如何暴怒地反抗他的岳父,爭奪家中男性的位置。杰克一直是個反叛的角色,反叛父親,反叛傳統。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反叛不會徹底,比如,他的岳父和父親一樣,永遠不會認可他;他和恩尼斯的愛情將永遠藏匿于黑暗之中。所以,成為男人的掙扎讓杰克還有另一個選擇,成為男孩。既可以贏得母親的歡心,還可以不威脅到父親。永遠做一個兒子比做一個成熟的男人,掙扎會少一些。此外,杰克和母親的分離不好,成為同性戀,也許還可以表達杰克另一個隱秘的愿望:媽媽,你放心,我將永遠愛你,你看,你不會被任何一個女人取代,我將永遠不會背叛你。這也許就是為什么杰克的媽媽對于兒子成為同性戀比較接納的原因。
二、成為同性戀是杰克和恩尼斯別樣的選擇
心理動力學認為,性別認同發生于俄狄浦斯情結時期,這個時期的發展將決定孩子成為同性戀還是異性戀。按照動力學的假設,每一個人都是從同性戀發展成異性戀的,即從自戀到他戀。所以,也許李安導演是對的,每個人心中都藏有一座斷背山。自戀的極致是同性戀,這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弗洛伊德所言,因為我們都是有性生殖器的族群,所以沒有人比我們更愛自己,自戀的投注永遠比他戀更早出現。隨著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出現,人們才慢慢發展成異性戀,但也依然保留著同性戀的遺跡。社會的文明代價就是犧牲人類的許多快樂和能力換來的,越是苛責的文化越是壓抑人性。比如,基督教文化對同姓戀者的嚴厲制裁是以《圣經》上的訓誡為依據的。舊約上有這樣兩段關于同性戀的語錄,一段是“你不可像和女人交合那樣地同男人交合,那是令人厭惡的”;另一段是“如果某人像同女人交合那樣地同一個男人交合,他們兩人就都是邪惡的,他們應當被處死”。由此可見,在西方的基督教社會中,同性戀行為是難以得到認可的。從恩尼斯童年目睹同性戀慘死,到農場主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審視恩尼斯和杰克,再到騎馬術表演的人拒絕杰克給他買酒。三個場景中的父親的化身,均代表著社會的權利和規則。如此嚴苛的超我會更加激起本我欲望的反抗,所以,有著反叛精神的杰克在同性戀的情感中飛蛾撲火,而有著童年創傷的恩尼斯則注定了更加沖突,以至于杰克的意外事故,恩尼斯堅信杰克是被人亂棍打死的。這是恩尼斯想象中的超我所施加的巨大懲罰。盡管杰克魂飛天外,《斷背山》以悲劇落幕,然而,如伊甸園般的斷背山卻是恩尼斯和杰克靈魂愿望的棲息之所。
恩尼斯和杰克,兩位主角自始至終都年輕英俊,就像古希臘神話中的“Narcissus”,是一個不老的傳奇。作為一個可供認同的,理想化的男性形象,他們是彼此的鏡像。對于恩尼斯來說,杰克溫暖包容,回應了他內心的孤寂,像一位臨在的母親,這是恩尼斯從小喪親內心極度渴求的,重要的是,杰克身上還擁有他非常缺乏的開放和勇氣,這是他內心理想自我的化身。而杰克也從恩尼斯身上感受到了愛和尊重,這是他那個冷淡的父親不曾給予的,而更加重要的是,恩尼斯節制冷靜,是典型的美國式父親,這是杰克由男孩到男人的路上及其缺乏并需要認同的。他們都在彼此身上尋找理想自我。不幸的是,由于恩尼斯對于成為同性戀的懼怕,讓他一次次拒絕杰克的邀約。情感沒有回應的杰克絕望之極,憤怒地罵道:“我們本來可以很美滿地在一起!真正的美滿生活!如果我們有一個屬于我們自己的地方就會大不一樣。但你并不想那樣,恩尼斯!這就是我們現在為什么會在斷背山!這是一切的根源!”杰克的憤怒在于,他有一種幻滅感。他原以為他的反叛最終會勝利,但最終他很無望,他無法最后贏得這位父親。我們完全可以從不同視角去觀賞這部傷感的影片,然而,這部影片悲情的元素孕育的是人類一個永恒的主題,那就是“愛”。人類的禁忌無論如何不能扭曲人性,剝奪情
感。當所謂的法律優先于愛,機械優先愛,試圖根植愛于虛假之中,就從根本上扭曲了人生。所謂美國式的父親若不是要么施虐,要么缺席,男孩在成為男人的路上也不至于困難重重。在這樣一個彌漫著功利、經濟、物質的社會,斷背山似乎也象征著物質的欲望隱退之后的棲息所。每個人的內心都在呼喚真愛,渴望認可。當人類的發展能真正以人為目的的時候,人們將會接納愛情選擇的多樣性,同不會再是禁忌,心靈將不再被捆綁。
作者:王偉單位:武漢職業技術學院計算機技術與軟件工程學院
- 上一篇:紅色影視中英雄人物形象的美學范文
- 下一篇:中國電影音樂的藝術特征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