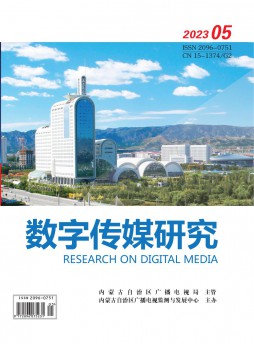數字時代檔案編研形態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數字時代檔案編研形態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湖北檔案雜志》2015年第七期
一、檔案編研選材多元化
素材構成一部編研作品的具體內容。實際中的檔案編研,由于種種原因,其選材并非都是檔案,而經常挾夾一些考古發現、網絡新聞、圖書情報、研究結論、甚至一些“道聽途說”等資料。說明檔案編研是一項可合理使用多種素材的活動。這種編研選材多元化的格式,其原因歸納起來包括:選題的綜合性,素材涉及范圍廣泛,需采用各類文獻;一些時效性較強的選題,因要用到反映事態發展的最新信息,對其它素材的選取成為必需;或由于材料不完整,需從其它文獻中補充;或由于某史實相互考證的需要,需廣泛采納各類其它素材;或為增強編研成果的可讀性,人為增加圖片、背景說明等材料;甚至一些主題因涉及多類型載體的文獻,如實物、紙張、電子等,需用到有關的全部素材等等。實際上,“館藏檔案作為檔案編研工作選材的主要對象,但并不是其唯一的對象。”
數字時代,檔案編研選材的多元化借助新技術手段,不只是偶然,已經成為常態。因為在國家信息化工程推進中,各數字檔案館、數字圖書館、數字博物館、數字文化館建設卓有成效,各相關信息網站紛紛建立,各類政府信息數據庫日益增多,而且網絡觸角遍布社會各個角落。這樣的環境下,同一主題下的檔案編研,可在計算機強大搜索功能基礎上,廣泛收集分散存儲在各地的相關信息,從一地區、一國家,甚至全世界范圍內檢索相關信息進行編研。這樣,數字時代的檔案編研就不再局限為某個館(室)藏,而是整個社會公開的相關信息數據。即:數字時代,檔案編研借助計算機進行廣泛的素材搜索,如通過網絡螞蟻、登錄聯機數據庫等形式,實現編研取材的智能化和泛社會化獲取。而且這種趨勢在社會大力倡導政府信息公開、文獻共享形勢下,變為常態。可以認為,在數字時代,“傳統的檔案編研成果基本上以紙質載體為主,而今,電子信息載體、網絡信息載體已經占據檔案編研成果載體的半壁江山。”[4]數字時代,檔案編研選材的多樣化需引起重視。
二、檔案編研出版網絡化
數字時代的社會是一個網絡社會,各類信息通過網絡快速流動,人們的信息利用行為也更多移向網絡空間。這對檔案編研成果的出版發行提供新機遇。這源于紙質環境下檔案編研的“不合時宜”。因為以紙質發行為主的傳統時代,檔案編研從編輯、照排、制版、裝訂到發行,耗時較長,已延后現今“外餐式”的生活節奏,與人們第一時間,甚至直接獲取時效強的信息需求存在矛盾;從編研成果形成到推送至讀者手中,中間歷經層層傳播驛站,如出版社、發行社、書店、郵局等,額外增加眾多中介環節;特別對一些音頻視頻文獻,以文本形式為主的傳統檔案編研不可能實現。這些矛盾均制約著紙質環境下檔案編研出版發行的進一步開展。數字時代檔案編研的出版發行徹底改變這一格局。它通過在線編研,直接在線發行,有效的壓縮了紙質環境下編研成果的傳播路線和環節,時效性大大提高;它可第一時間收集讀者通過e-mail、QQ、留言版等形式反饋的信息,快速修正編研形式,并及時跟蹤信息需要,繼而有效推送相關的編研成果,甚至可開展個性化的成果推送。
如,為某一學者直接推送某一課題的檔案編研成果;而最大的優勢是,對一些集文、圖、聲、像于一體的檔案信息,數字環境下的檔案編研可實現,它可制作視、聽、讀的三維信息成品。“數字化的出版方式,集文、圖、聲、像于一體,將立體化的編研成果呈現給讀者,具有強烈的感官沖擊、藝術效益和感染力,可更好的吸引讀者。”[5]如近年來國家檔案局網站在線相斷推出的專題片,如《偉大勝利———中國受降檔案》、《浴血奮戰———檔案里的中國抗戰》等,其出版和傳播取得良好效果;而且網絡環境下的檔案編研可有效利用超文本技術,通過鏈接匯集甚至無限多的相關信息。可以認為,數字時代的檔案編研具有時效性好、容量大、反饋及時、視頻沖擊力強等優點,但總的平臺是網絡化。
總之,數字時代的檔案編研,其形態相較紙質環境,已發生許多變化,而且這些變化已經深刻改變了檔案編研領域的生態。“與傳統的檔案編研相比,網絡環境下的檔案編研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點,這些新的特點客觀上也對檔案編研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6]這需要我們對新環境下的檔案編研形態作進一步的研究。
作者:黃艷 單位:南寧市城建檔案館
- 上一篇:古代上行文書發展特點范文
- 下一篇:檔案信息化建設思考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