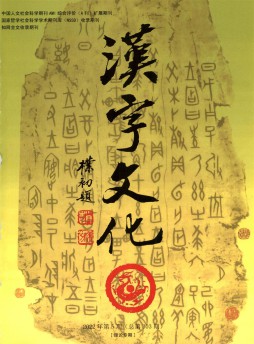漢字結(jié)構(gòu)和傳統(tǒng)漢民族思維方式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漢字結(jié)構(gòu)和傳統(tǒng)漢民族思維方式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漢字作為世界上唯一在使用的自源文字,其產(chǎn)生和發(fā)展深深地受到了漢民族的思維方式的影響。漢字的結(jié)構(gòu)特征體現(xiàn)出了直觀性思維、整體性思維、“天人合一”思維以及意象性思維。它承載著漢民族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特征,是傳統(tǒng)思維的綜合產(chǎn)物。
關(guān)鍵詞:漢字結(jié)構(gòu);直觀性思維;整體性思維;“天人合一”思維;意象性思維
漢字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是當(dāng)今世界上唯一在使用的自源性文字,也是世界上現(xiàn)存最古老的文字。與漢字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莫過于漢語。漢字不僅是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tǒng),更是承載著民族文化的代表。
一、漢字與漢民族
遠古人類已具備了相應(yīng)的思維基礎(chǔ)和發(fā)音器官,且經(jīng)過漫長的發(fā)展,他們可以發(fā)出簡單而有意義的音節(jié)。追溯漢民族漫長的發(fā)展史,我們可了解漢字與漢語的發(fā)展?fàn)顩r。學(xué)界一致認(rèn)為,漢民族起源于華夏民族。何為華夏?范文瀾說:“文化高的地區(qū)即周禮地區(qū)稱之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稱之為華,華夏合起來稱為中國。將文化低即不遵守的人或民族稱之為蠻夷戎狄。”隨著華夏民族的不斷壯大,漢語與漢字也不斷發(fā)展與傳播。據(jù)知,黃帝時代已有倉頡作書,民族共同語的出現(xiàn)與使用促進了漢民族歷史的發(fā)展進程。同樣,漢民族的歷史發(fā)展也鞏固了漢語與漢字地位。且不說漢語與漢字的長盛不衰使它們能夠高高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連幾千年間朝代的數(shù)次政權(quán)變革,也沒有迫使新興的政府完全廢除漢字與漢語,是所謂“亡國而未亡種”也。漢民族的思維方式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漢字的方方面面,如為何漢字起源之初被制定成了表意文字而不是表音文字。反過來說,幾千年經(jīng)久不衰的漢字必然長期影響著漢民族的思維方式,如漢字作為表意文字,使得人們更習(xí)慣于以形求義等等。
二、漢字與傳統(tǒng)思維
(一)漢字與直觀思維所謂直觀性思維,就是人們不需要經(jīng)過逐層分析,而能夠迅速地對問題做出合理的猜測或設(shè)想。漢字是當(dāng)今世界上唯一在使用的自源性文字,也是世界上現(xiàn)存最古老的文字。說起漢字的起源,就不得不說甲骨文。它是漢字的早期形式,也是現(xiàn)存的最古老的一種成熟文字,它上承原始刻繪符號,下啟青銅銘文,是漢字發(fā)展的關(guān)鍵形態(tài),但原始圖畫文字的痕跡還是比較明顯,發(fā)展到后來的銘文、小篆也沿襲了甲骨文直觀性的特點。《說文解字序》:“昔者庖犧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象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許慎在此明確地告訴我們,創(chuàng)造漢字的靈感來源于世間萬物,早期漢字的產(chǎn)生則源于對外界事物的描繪。由于早期人類的思維并不完善,無法自如地運用抽象思維,所以直觀性思維在此時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觀世間萬物,制文字符號。如甲骨文中的“日”字,古人在創(chuàng)制時就畫出了一個圓,其內(nèi)再加一個黑點;“水”字則像一條流淌的河流;“山”字就像山脈的輪廓等等。早期文字較少且大多是由所見之物繪制而成所寫之字,再加之漢字長時間的使用也不斷深化著漢民族的直觀性思維,這也就導(dǎo)致即便后期出現(xiàn)了會意字、指事字及大量的形聲字,漢民族也非常習(xí)慣通過直觀性思維去初步了解字義。漢民族直觀性思維的形成與發(fā)展是一個復(fù)雜的問題。首先,中國作為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大國,早已適應(yīng)了自給自足的生產(chǎn)方式,這種落地生根、安于現(xiàn)狀的民族氛圍使得漢民族不擅長變通,而且更習(xí)慣運用長久固定下來的直觀思維去思考和解決問題;第二,中國并未像西方兩河流域等地一樣過早出現(xiàn)商業(yè)貿(mào)易的現(xiàn)象(即沒有開放的社會環(huán)境和自然條件),因此便很難像西方諸國一樣在經(jīng)過漫長的發(fā)展后,使文字形態(tài)從楔形文字轉(zhuǎn)換到現(xiàn)在通用的拉丁字母。
(二)漢字與整體性思維整體性思維,是指人們在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時候,注重事物本身的統(tǒng)一性。整體性思維對漢民族的方方面面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中醫(yī)的“頭痛醫(yī)腳,腳痛醫(yī)頭”以及漢民族在分析問題時更偏重綜合、少于分析等等。同樣,整體性思維在文字上也有所體現(xiàn)。人類在創(chuàng)制漢字時并不是僅僅局限于某一個事物的部分,恰恰相反,他們更加偏重對整體性的把握。以“鳥”等字為例,我們可以通過其甲骨文形式“”,清晰地了解到關(guān)于鳥的自然特征——尖嘴、爪子及軀體,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另外,從字形而言,漢字屬于結(jié)構(gòu)緊湊的方塊字。狀如豆腐塊的漢字使人們對它的把握首先是從整體的角度來進行的,這和注重局部的拼音字母不一樣。例如英語中的“expensive”意為“昂貴的,貴重的”,但“expansive”則是“易膨脹的”,兩個單詞中只有“a”“e”兩字母不同而已,因此這就需要人們在學(xué)習(xí)英語時要學(xué)會抓住它們的局部特征進行辨認(rèn)。漢語在這方面就表現(xiàn)出了明顯的差異,“貴重”與“易膨脹的”不管是從形體、讀音或是意義上來說,都是迥然不同的,二者沒有局部的變化,只有整體上的差別。還有研究表明,處在閱讀狀態(tài)下的人可以不用仔細看每一個字的形體結(jié)構(gòu)就可以通過其大致輪廓迅速地獲得信息,這是因為在不精確地調(diào)動該漢字形體結(jié)構(gòu)的情況下,儲存在人腦中的漢字也是整體而模糊的。因此我們在書寫漢字時,即便多寫或少寫一畫(雖然是錯別字),我們的大腦依舊可以辨認(rèn)出其所傳達出來的信息。
(三)漢字與“天人合一”思維“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最早是由莊子所闡述,這是中國人觀察和認(rèn)識世界的基本思維方式之一。“天人”指的是自然與人為,或者天道和人道,“天人合一”強調(diào)的是自然與人為、天道與人道的合一。漢字作為民族文化的載體,也必然會受到這一傳統(tǒng)思維的影響。如“大”,《說文解字》曰:“天大地大人亦大。”這里就包含了天地人貫通的思想。此外,由于早期人類沒有科學(xué)思維基礎(chǔ),導(dǎo)致他們無法運用科學(xué)知識來解釋未知現(xiàn)象,因此他們常常從自身角度出發(fā)去揣測事物的發(fā)展,這同樣也影響了漢字的創(chuàng)制。據(jù)考查,在甲骨文中,有關(guān)動物、植物、地理等方面的字所占的比例多的可達17%,最少的僅約占1.4%,但關(guān)于人或人自身的字卻達到20%以上。事實上,語言中所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字或詞匯與其在該文化系統(tǒng)中所處的地位成正比。那么,我們便可清楚地了解到有關(guān)“人”的漢字在該文化系統(tǒng)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兩類:第一,以人示物。所謂以人示物,是指某些漢字看似表示與人體相關(guān)的概念,實則還可以表示某種器物。如“耳”除了表示人耳之外,也有附于物體兩旁便于提舉之意;“首”除了有人頭意義之外,還有兵器把柄的頂端之意等等。第二,以物示人。從《說文解字》所收錄的字來看,以物示人的例子明顯不及以人示物多,但仍舊有一些例證,如“支”,《說文解字》曰:“去竹之枝也。從手持半竹。”由此看來,支最初指的是植物。但隨著新字的產(chǎn)生,出現(xiàn)了“肢”字,換言之,“支”增加了“肉(月)”部,那么該字便由從指物類轉(zhuǎn)變?yōu)橹溉恕?/p>
(四)漢字與意象思維所謂意象思維,是指用某種具體而明確的事物來表示抽象的概念。我國漢民族的意象思維一般可分為三類:第一,符號意象,即通過使用某種符號來代表某種神秘的現(xiàn)象。這一點在《易經(jīng)》中可找到很多例子,比如使用陰爻“--”和陽爻“-”來代表陰陽八卦,表示宇宙最基本的元素。陰爻和陽爻相互組合構(gòu)成不同的卦象以揭示某種神秘的法則。第二,玄想意象,即用選擇出的意象符號來代表某種“形而上”的概念,比如“道”“無”和“太極”等等。第三,審美意象,即通過塑造審美意象來渲染出某種審美氛圍。最初的漢字?jǐn)?shù)量很少并且以象形字為主,所表達的概念也多是具體的事物。但隨著生活以及認(rèn)知水平的發(fā)展,人們迫切需要表達出自己無法言說的抽象概念,因此往往假借他字或引申意義來表達。如“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僅數(shù)字便可說出“高”像樓臺層疊之形,表示崇高義。再如“祭,祭祀也。從示、以手持肉”,根據(jù)甲骨文字形可知,左邊是牲肉,右邊是手,中間是祭祀桌,表示以手持肉祭祀神靈(祭祀儀式)。這些漢字的創(chuàng)制及其隱含的意義也形象地表現(xiàn)出先賢為表達抽象概念而做出的努力。此外,漢字的意象思維還表現(xiàn)在形聲字上。比如“瓊”字乃左形右聲,有比喻美好之意。為何會有美好之意?這是源于“瓊”字從玉旁,玉器文化在漢民族早期便已經(jīng)產(chǎn)生并且發(fā)展成熟,人們認(rèn)為有好玉自然是美好的事情,故而有美好之義。另外,漢字也可以通過塑造審美意象來表現(xiàn)某種審美氛圍。最經(jīng)典的莫過于馬致遠的《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fēng)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全曲共二十八個字,雖無一“秋”字,卻勾勒出秋郊夕陽圖。寥寥數(shù)字,便能使人們從這首詞里讀出清冷、寂寥之感,身臨其境一般。
三、結(jié)語
總而言之,漢字作為一種意象性的符號系統(tǒng),其生成和發(fā)展與漢民族的思維方式息息相關(guān),同時這些思維方式對漢字也給予了一定的制約和影響。雖然漢字并不是漢民族唯一的思維媒介,但它處處體現(xiàn)出了傳統(tǒng)的漢民族思維,二者相互影響,互相印證。雖然傳統(tǒng)思維缺乏懷疑和批判精神,也表現(xiàn)出了非批判性的歷史思維特征,這使得漢字具有一定的保守封閉性,但漢字的綿延不衰更重要的是滿足了漢民族的思維和表達需要。
參考文獻:
[1]何九盈.漢字文化學(xué)[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2]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13.
[3]成中英.中國語言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思維方式[J].理論信息報(京),1988-6-22.
[4]王作新.漢字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與傳統(tǒng)思維方式[M].武漢:武漢出版社,1999.
[5]高晨陽.中國傳統(tǒng)思維研究[M].濟南:山東大學(xué)出版社,1994.
作者:母丹丹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xué)國際漢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