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情感觀念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儒家的情感觀念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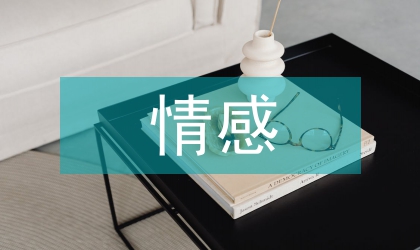
《江西社會科學(xué)雜志》2014年第五期
一、原創(chuàng)時代儒學(xué):情感觀念的本源意義
(一)孔子的情感觀念在《論語》中,沒有關(guān)于孔子直接論及單純情感意義的“情”的記載。但這并不意味著孔子沒有關(guān)于情感的論述,恰恰相反,孔子曾廣泛地談?wù)撨^“仁”、“愛”、“安”、“怨”、“憂”、“懼”等情感問題。其中,最核心的是仁愛情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這里的“仁”,在“愛”的意義上,顯然說的是情感。儒家所說的“仁”,有時指形而下的道德規(guī)范,有時指形而上的心性本體,有時則又指一種原初本真的情感。孔子所講的“愛人”之“愛”即是這種情感。這種“愛”的情感與“安”或“不安”的情感、情緒有密切關(guān)系: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論語•陽貨》)這里,孔子是以對父母之“愛”的情感、居喪期間“安”與“不安”的情緒來論證守喪之“禮”的“合情合理”。這正如郭店楚簡《語叢》所說:“禮生于情”(《語叢二》);“禮因人之情而為之”(《語叢一》)。更值得注意的是,《論語》記載孔子僅有的一次直接用到“情”字,具有重大意義: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孔安國傳:“情,情實也。言民化于上,各以實應(yīng)。”邢疏:“情猶情實也。言民于上,各以實應(yīng)也。”朱熹的解釋似乎略有不同,實則一致:“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yīng)也。”(《論語集注•子路》)其實,孔子這里所說的“情”固然指“情實”(事情的實情),但也包含了“情感”的意義,即民之“用情”與孟子所說的“盡心”是一致的,都有情感的意義。所以,孔穎達(dá)在談到孔子這段話時指出:《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圣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yīng),用此道也。(《尚書正義•禹貢》)這里的“敬”,尤其是“天下皆悅”就是情感。其實,古代漢語“用情”這個短語往往都有情感的含義。例如《詩經(jīng)•檜風(fēng)•素冠》:“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兮。”孔穎達(dá)疏:“已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于哀戚之人,其形貌欒欒然瘦瘠者兮;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而憂之兮。”又如《禮記•檀弓下》孔疏:“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nèi)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這里的“用情”之“情”指“愛”、“好”、“惠”的情感。總之,孔子所說的“情”是兼指情感與事情的,即在孔子看來,仁愛的情感是最真切的情實。
(二)思孟學(xué)派的情感觀念孔子以“情”涵蓋情感(人情)與情實(事情),這種觀念為思孟學(xué)派所稟承。郭店楚簡中的儒家文獻(xiàn)《性自命出》,通常認(rèn)為屬于思孟學(xué)派,其中這樣幾個命題尤為重要:“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這里給出了這樣一個觀念序列:天→命→性→情→道。表面看來,這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沒有區(qū)別,甚至與后儒的“性→情”之論也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但實際上問題并非這么簡單,因為《性自命出》又講:“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好惡,性也”。“喜怒哀悲”、“好惡”顯然是“情”,卻稱之為“性”,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這里只有兩種可能,要么《性自命出》的觀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要么是我們的理解有誤。筆者傾向于后一種可能,即人們以后世的觀念誤讀了《性自命出》。實際上,在人性問題上、情感范疇內(nèi),先秦諸子對“性”與“情”并沒有嚴(yán)格的概念區(qū)分(下文對孟子的分析將進(jìn)一步證明這一點)。但“道始于情,情生于性”顯然嚴(yán)格區(qū)分了“情”與“性”,這就表明,這里的“情”未必是指人性論意義上的情感。聯(lián)系上文關(guān)于“情”兼人情與事情的分析,我們似可得出結(jié)論:《性自命出》的“情生于性”,其“情”并不是說人之情,而是說事之情。但這樣理解似乎也有問題,因為這就意味著“情生于性”是說:事情出自人性。其實,先秦諸子所謂“性”也未必說的是后儒“性-情”對立的人性。當(dāng)時“性”更常見的用法是與“生”同義的,在出土的先秦簡帛中,這兩個字往往沒有區(qū)分。此“生”未必是指人生,倒可能是指《易傳》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辭下傳》)、“生生之謂易”(《系辭上傳》)的存在論觀念。③《易傳》還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彖傳》)這里的“乾道”指天道,“性”、“命”不僅是說人的本質(zhì),而且是說萬物的本質(zhì):人得天命而有人性,物得天命而有物性。這也是“性自命出”這個命題的含義:事情之實情出自天命。因此,《性自命出》所講的“性”、“情”不僅僅是人性論范疇,更是存在論范疇。這里還涉及對《性自命出》中“道”的理解。其所謂“道”指人道,《性自命出》說:“惟人道為可道也。”因此,“道始于情”是說:人道不僅始于人情,而且始于事情的實情。于是,“天→命→性→情→道”不外乎是講:人道出于天道。所謂人道,主要是指義、禮等倫理政治問題。聯(lián)系上文所引《語叢》“禮作于情”之說,以及“情生于性,禮生于情”(《語叢二》)、“仁生于人,義生于道”(《語叢一》之論,我們可以還原出這樣一個觀念序列:性→情→人→道→仁→義→禮。顯然,這里的“性”、“情”是在“人”、“道”之前的事情,是存在論范疇,而非人性論范疇。孟子繼承了這種思想觀念。在他看來,仁愛的情感是最真實的事情。他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孟子•告子上》)孟子以“山之性”譬喻“人之情”,明顯地是“性”、“情”同用:不僅“情”即是“性”,而且兼指情感(人情)和情實(事情)。這就是說,儒家有兩種不同含義的情感觀念:一種是作為主體的人的情感,被后世的儒家理解為“性”之“已發(fā)”;另一種卻是前主體性的本源情感,同時被理解為“實情”、“情實”、“事情”,這是原典儒學(xué)的觀念。孟子即持后面這種觀念: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這里同樣是在講“性”的問題,卻也是說“乃若其情”,此“情”顯然既指人之性,又指人之情,并且也指事情的實情。所以我曾說過,如果將整個儒學(xué)史上的情感觀念綜合起來,那就是“情→性→情”的觀念架構(gòu)。其中“情→性”架構(gòu)是原典儒家的觀念,故先秦時期常見的是“情性”的說法,罕見“性情”之說;而“性→情”則是秦漢以后帝國時代儒學(xué)的情感觀念,而人們誤以為這是儒家情感觀念的正宗。
二、帝國時代儒學(xué):情感觀念的形而下化
中國社會第一次大轉(zhuǎn)型之后,進(jìn)入帝國時代,儒家的情感觀念也發(fā)生了轉(zhuǎn)折,即從“情→性”觀念轉(zhuǎn)變?yōu)椤靶浴椤庇^念。后者有兩大特征:一是“情”不再指“事之情”,而專指“人之情”④;二是“情”與“性”相聯(lián)系,即形而下的“情”只是形而上的“性”之“已發(fā)”狀態(tài)。這種觀念又與“本→末”、“體→用”的觀念聯(lián)系起來:性是形而上的本、體,情是形而下的末、用。上文談到,從《中庸》還看得出這種轉(zhuǎn)變的痕跡:“喜怒哀樂”本來是說的情感;但當(dāng)其被理解為“未發(fā)”之“中”時,它說的就是“性”了。“性”發(fā)為“情”,可善可惡,在于是否“中節(jié)”。所謂“中節(jié)”即是“合禮”———合乎社會規(guī)范。此即毛亨《詩大序》“發(fā)乎情,止乎禮義”之意。此“性”乃是“大本”,即是形而上的“本體”,天地位于此,萬物育于此;而“中節(jié)”或“合禮”之“情”則是“達(dá)道”,即是形而下的“大用”。進(jìn)入帝國時代,性情關(guān)系問題成為儒學(xué)的一個主要話題。性情理論是為帝國的倫理政治服務(wù)的,意在說明以倫理規(guī)范為價值尺度的善惡現(xiàn)象及其來源,由此找到勸善懲惡的路徑。例如董仲舒說:“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其中的貪性也就是情,故而他主張“輟其情以應(yīng)天”。(《春秋繁露•深察名號》)這同樣是某種“性→情”架構(gòu)。整個帝國時代的儒學(xué),其情感觀念的主流基本上都是“性→情”觀念的某種發(fā)揮,而最初的鮮明表達(dá)見于韓愈的《原性》、尤其是李翱的《復(fù)性書》,最成熟的理論形態(tài)則是宋明理學(xué),致使后世誤解了儒家的情感觀念,以為就是“性→情”觀念而已。韓愈認(rèn)為:“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者也。”性、情各有三品:“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dǎo)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原性》)李翱講:人之所以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fù)其性。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也。(《復(fù)性書上》)情者,性之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耶?”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情者,妄也,邪也。(《復(fù)性書中》)李翱對“情”的定性不無矛盾:時而認(rèn)為性善、情有善有不善,主要傾向則認(rèn)為性善、情惡。但無論如何,這都是典型的“性→情”架構(gòu)。這種“性→情”觀念在宋明理學(xué)中得到充分發(fā)揮,程朱理學(xué)最為典型。程朱理學(xué)將“性”、“情”關(guān)系理解為兩種:一是“未發(fā)-已發(fā)”的關(guān)系。“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情之發(fā),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發(fā)之為惻隱、辭遜、是非,乃性之情也。”(《朱子語類》卷五)二是“形上-形下”的關(guān)系。“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二程遺書》卷二十二下)“只是這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朱子語類》卷五)這里的“性”作為“理”即是“天理”,所以叫作“理性”(《二程遺書》卷十八),而“天理”顯然是“形而上者”。因此,“性→情”關(guān)系就是“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關(guān)系。但是,程朱理學(xué)已意識到先驗理性的一個根本困惑:既然性為善,情又是性之所發(fā),那么,情怎么可能惡呢?換句話說,情之惡必有其性上的來源。故程子又提出“氣質(zhì)之性”的說法:“一為理性,一為氣質(zhì)之性。”(《二程遺書》卷十八)朱熹繼承了這個觀念。然而這樣一來,就出現(xiàn)了兩個性,程朱理學(xué)因此陷入了二元論,而且對于“氣質(zhì)之性”究竟是形上的還是形下的這個問題,始終無法自圓其說。相比之下,陽明心學(xué)則以“無善無惡”的心體克服了這種二元論,堅持了徹底的一元論。不過,陽明心學(xué)的性情觀念也同樣是“性→情”的架構(gòu)。在帝國時代的儒學(xué)中,盡管上述“性→情”觀念成為主流,但“情→性”觀念并未絕跡。例如,張載就說過:“飲食男女皆性也。”(《正蒙•乾稱下》)這里的“飲食男女”其實是情欲。王安石則干脆以情說性:“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原性》)值得一提的還有作為宋代儒學(xué)一派的蜀學(xué)。蘇軾說:“儒者之患,患在于論性。”(《韓愈論》)在蘇軾看來:“夫六經(jīng)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于人情”(《中庸論》);“夫六經(jīng)之道,唯其近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詩論》)。
三、現(xiàn)代儒學(xué):本源情感觀念的逐漸復(fù)興
儒學(xué)由“性→情”向“情→性”的范式轉(zhuǎn)換與觀念復(fù)歸,發(fā)生于中國社會第二次大轉(zhuǎn)型即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之中。這至遲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際。
(一)明清之際儒學(xué)的情感轉(zhuǎn)向解構(gòu)“性→情”觀念,其前提是解構(gòu)先驗論的“性”觀念。為此,王夫之通過闡釋《尚書•太甲上》“習(xí)與性成”命題,否定了先驗的人性:“習(xí)與性成”者,習(xí)成而性與成也。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豈一受成?(形),不受損益也哉(《尚書引義•太甲二》)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為進(jìn)一步揭示生活情感的本源意義開辟了道路。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通過“生”與“習(xí)”的闡發(fā),已接近于揭示生活的本源地位。隨后,戴震更進(jìn)一步對“情”、“欲”加以張揚,矛頭直指宋明理學(xué)之“理”,斥之為“以理殺人”。他指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情得其平,是為好惡之節(jié),是為依乎天理。在己與人皆謂之“情”,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天理者,節(jié)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jié)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孟子字義疏證•理》)人倫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quán)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孟子字義疏證•權(quán)》)在戴震看來,所謂“王道”或“人道”,就是滿足情欲而已:圣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孟子字義疏證•理》)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孟子字義疏證•性》)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達(dá)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dá),斯已矣。(《孟子字義疏證•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戴震所謂“情”并不僅指人之情感,更指“事情”: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夫事至而應(yīng)者,心也;心有所蔽,則于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惟以情?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茍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孟子字義疏證•理》)因此,梁啟超稱戴震哲學(xué)為“情感主義”、“情感哲學(xué)”[5],其實是不全面的。戴震所說的“情”,意思是:對于人道來說,自然的情欲就是事情的實情,這不僅是倫理的本源,而且是具有存在論意義的。
(二)20世紀(jì)儒學(xué)的情感觀念20世紀(jì)以來,出現(xiàn)了一種“反智重情”的思潮,最典型的如朱謙之的“唯情論”、袁家驊的“唯情哲學(xué)”。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李澤厚的“情感本體論”。他說:“‘情本體’是以‘情’為人生的最終實在、根本。”“不是‘性’(‘理’),而是情;不是‘性(理)本體’,而是情本體;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學(xué),而是審美形而上學(xué),才是今日改弦更張的方向。”對于李澤厚的“情本論”,可以更全面地審視。第一,出自美學(xué)思考,其思想立足點是20世紀(jì)80年代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的“實踐本體論”,把一切建立“在人類實踐基礎(chǔ)上”,屬于歷史唯物論性質(zhì)的“人類學(xué)歷史本體論”。第二,這種本體論仍然是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的思維模式,所以李澤厚批評海德格爾:“豈能一味斥責(zé)傳統(tǒng)只專注于存在者而遺忘了存在?豈能一味否定價值、排斥倫理和形而上學(xué)?回歸古典,重提本體,此其時矣。”以上幾家均非儒學(xué)。與儒學(xué)有密切關(guān)系的情感主義傾向,有梁啟超的情感觀念。他認(rèn)為“情感是人類一切動作的原動力”,因此主張“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他說:“只要從生活中看出自己的生命,自然會與宇宙融合為一。”“怎么才能看出自己的生命呢?這要引宋儒的話,說是‘體驗’得來。”這種情感體驗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淵源。儒家情感主義的復(fù)興,梁漱溟是一個典型。盡管受到柏格森的影響,但梁漱溟的情感論仍然屬于儒學(xué)。其早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判定:“西洋人是用理智的,中國人要用直覺的———情感的。”中期的《中國文化要義》仍然是這種“中/西—情感/理智”二分的觀念,只不過是用他自己的獨特概念“理性”來表示情感。梁漱溟說,“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為其根本”;“孔子學(xué)派以敦勉孝悌和一切仁厚肫摯之情為其最大特色”;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的,而“倫理關(guān)系,即是情誼關(guān)系,……倫理之‘理’蓋即于此情與義上見之”。
(三)21世紀(jì)的“情感儒學(xué)”儒家情感觀念更為徹底的復(fù)興,見于蒙培元的專著《情感與理性》及一系列著述,他的理論被稱為“情感儒學(xué)”。陳來也認(rèn)為,蒙培元的思想可以概括為“生命-情感儒學(xué)”。在蒙培元看來,儒家哲學(xué)乃是“情感哲學(xué)”。他說:“人的存在亦即心靈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什么呢?不是別的,就是生命情感。”因此,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的導(dǎo)師是馮友蘭。通常以為馮友蘭“新理學(xué)”不重情感,其實不然。蒙培元這樣理解馮友蘭的哲學(xué):“情感與理性各有其地位與作用,并不構(gòu)成矛盾。就其終極理念而言,情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這就是最終實現(xiàn)對萬物有深厚同情、與萬物痛癢相關(guān)的‘萬物一體’亦即‘自同于大全’的境界。”筆者曾在主編的文集《情與理:“情感儒學(xué)”與“新理學(xué)”研究》序言中說:在現(xiàn)當(dāng)代儒學(xué)中,“如果說,熊牟一系或可稱之為‘心性派’(熊多言心、牟多言性),那么,馮蒙一系則可稱之為‘情理派’(馮重理而亦論情、蒙重情而亦論理)”;并援引陳來的觀點,即在馮友蘭看來,中國哲學(xué)乃是“應(yīng)付情感的方法”。蒙培元的情感儒學(xué),極大地推動了學(xué)界對于儒學(xué)與情感之關(guān)系問題的討論。在祝賀蒙培元先生七十壽辰的“儒學(xué)中的情感與理性”研討會上,許多知名學(xué)者充分肯定了馮友蘭-蒙培元一系儒學(xué)的情感特色。例如陳戰(zhàn)國說:“熊牟一系的儒者和馮蒙一系儒者之間區(qū)別的關(guān)鍵所在就是‘情感’,這個我是認(rèn)可的,覺得說得很深刻、很恰當(dāng)。”此次會議之后,學(xué)界討論儒家情感觀念的文章明顯增多。筆者提出的“生活儒學(xué)”及“中國正義論”,其實也是這種“情感轉(zhuǎn)向”的體現(xiàn),在這個意義上,也是一種“情感儒學(xué)”。生活儒學(xué)首先追問作為形而上者的本體何以可能,從而突破兩千年來的“形上-形下”兩級架構(gòu),揭示人類觀念的三個層級。觀念的生成關(guān)系:生活感悟→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觀念的奠基關(guān)系:生活感悟→形而上學(xué)→形而下學(xué)。生活儒學(xué)認(rèn)為,生活或存在是所有一切的大本大源;生活不是存在者,而是給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所謂“生活感悟”指生活情感及生活領(lǐng)悟。生活感悟不是一種認(rèn)識,一切認(rèn)識都淵源于生活感悟。這是先于存在者的、與生活渾然共在的事情。這里首要的就是生活情感。所謂“生活情感”并不是主體性的情感“人之情”,而是“事之情”,既是事情的實情,也是本真的情感。就“情”的原初含義而論,也可以說:情感即生活,生活即情感。在情感中,儒家最重“仁愛”或“愛”的情感:“愛,所以在”。這種“仁”、“愛”不是上帝之愛,⑤而是孔子所講的“愛人”之“愛”,孟子所講的“惻隱之心”、“不忍之心”(《孟子•公孫丑上》)。⑥中國正義論是生活儒學(xué)在倫理學(xué)層級上的展開,意在探索制度倫理學(xué)問題,即社會規(guī)范建構(gòu)及其制度安排的一般原理,其核心的理論結(jié)構(gòu)是:仁→義→禮。社會共同體的一套規(guī)范及其制度,儒家謂之“禮”,包含三層:禮義→禮制→禮儀。禮制就是社會規(guī)范及其制度,禮儀是其外在的表現(xiàn)形式,而禮義則是其背后的價值根據(jù)———正義原則,儒家稱之為“義”。漢語“義”有兩個基本語義:正當(dāng),如孟子說“義,人之正路也”(《離婁上》);適宜,如《中庸》說“義者,宜也”。由此,中國正義論的兩條正義原則是:正當(dāng)性原則,要求社會規(guī)范建構(gòu)及其制度安排超越差等之愛,追求一體之仁;適宜性原則,要求社會規(guī)范及其制度適應(yīng)當(dāng)下生活方式。因此,中國正義論不同于西方正義論,根本是對正義原則的理解不同。在中國正義論中,仁愛情感是為正義原則奠基的。有一種常見的誤解,以為儒家只講“愛有差等”(《孟子•滕文公上》),愛的強度表現(xiàn)為遞減序列“親親→仁民→愛物”(《孟子•盡心上》)。其實,儒家盡管尊重“差等之愛”的生活情感的實情,但并不認(rèn)為這是建構(gòu)制度規(guī)范的正義原則;恰恰相反,儒家的正當(dāng)性原則主張“一體之仁”、“推擴”、“推己及人”,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論語•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總之,在本源層級上,儒家的情感觀念不是一個倫理概念,而是一個存在觀念。
作者:黃玉順單位:山東大學(xué)儒學(xué)高等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