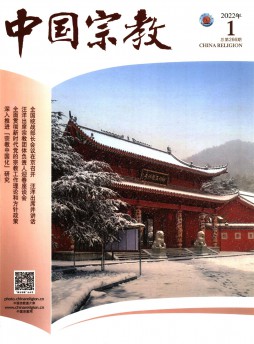宗教教育與民族教育的現(xiàn)代化探尋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宗教教育與民族教育的現(xiàn)代化探尋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汶川地震已歷十年,在逐漸恢復(fù)和自我調(diào)適的過(guò)程中,羌族面臨的族群搬遷和家園重建等問(wèn)題,使得其由宗教文化所蘊(yùn)生的民族教育內(nèi)容與民族的當(dāng)代生存現(xiàn)狀以及現(xiàn)代教育模式之間,產(chǎn)生了更多復(fù)雜的矛盾。在生活環(huán)境、教育需求皆發(fā)生了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如何以保存、延續(xù)族群文化為核心,重建新時(shí)代的民族教育價(jià)值內(nèi)核和教育框架,需要從文化認(rèn)同和文化融合的角度,進(jìn)行文化還原、道德重塑、信仰引導(dǎo)以及尋根教育,進(jìn)而探尋當(dāng)代羌民族教育重構(gòu)和文化傳承之路。
關(guān)鍵詞:羌族;宗教教育;民族教育;教育重構(gòu)
羌民族的宗教文化,素有中國(guó)原始宗教活化石之稱(chēng)。在幾千年的歷史長(zhǎng)河中,羌族仍然保留的原始宗教內(nèi)核,是族群誕生和延續(xù)過(guò)程中影響最為深遠(yuǎn)的文化內(nèi)因,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指歸,是民族心理認(rèn)同和民族教育傳承的原生動(dòng)力。它所代表的民族生存經(jīng)驗(yàn)以及核心的精神信仰等等,成為一直以來(lái)傳統(tǒng)民族教育的主要內(nèi)容。在宗教的神秘玄幻性和教育的世俗理性沖突過(guò)程中,雖然由于特有的文化生態(tài),羌族原始宗教并沒(méi)有像其他宗教一樣將宗教教育與世俗教育進(jìn)行嚴(yán)格的分離,但隨著媒體時(shí)代和消費(fèi)時(shí)代的來(lái)臨,羌族宗教文化在文化商品化和“他者敘述”等文化開(kāi)發(fā)活動(dòng)中,其精神內(nèi)核及其蘊(yùn)生的文化教育功能正在不斷地嬗變和異化,尤其是5•12汶川地震之后,羌人居住環(huán)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使得日漸式微的族群傳統(tǒng)更加需要尋取一種新的方式來(lái)進(jìn)行維系和傳承。如何在當(dāng)前的生活環(huán)境中,繼續(xù)從世代相襲的古老宗教文化中汲取民族凝聚的力量,這對(duì)于當(dāng)代的羌族族人而言,無(wú)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教育層面而言,如何在現(xiàn)代學(xué)校教育廣泛普及的基礎(chǔ)上,重建新時(shí)代的民族教育價(jià)值內(nèi)核和教育框架,除了外在的物質(zhì)文化保護(hù)和重建之外,可能還更需要以客觀、內(nèi)化的途徑,挖掘和刷新原始宗教的文化資源,還原羌民族的文化本真,統(tǒng)合文化元素的商品化、零星化呈現(xiàn)方式,構(gòu)筑文化尋根的整體思維,從而探索本民族文化教育的現(xiàn)代之路。
一、羌族的自然宗教特征及宗教教育的混融性
羌族是我國(guó)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由于地域環(huán)境和族群生存等諸多因素,羌族宗教文化的形成呈現(xiàn)出較為特殊的多元融合特征,不論是早期陶然士與葛維漢有關(guān)一神教或“多神教”[1]的辯論,還是后來(lái)胡鑒民認(rèn)為“羌族之信仰還在靈氣崇拜與拜物的階段”[2]等開(kāi)創(chuàng)性的觀點(diǎn),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羌人在民族延續(xù)過(guò)程中,自身的原始崇拜和其他宗教信仰交流與雜糅的成型過(guò)程。因此,從宗教文化的角度來(lái)看,羌人的社會(huì)生活植根于其宗教生活,而羌人有語(yǔ)言無(wú)文字的文化傳承方式,又使得本民族的社會(huì)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與宗教教育混融在一起。
(一)作為民族教育原生動(dòng)力的羌族宗教文化
盡管從魏晉至民國(guó)以來(lái),羌族的宗教生活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道教、喇嘛教甚至西方宗教的影響,但真正讓羌族區(qū)別于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征,仍是源自于古羌人自然崇拜而來(lái)的原始宗教內(nèi)容。這種原始宗教的信仰內(nèi)容和信仰方式,在相當(dāng)長(zhǎng)時(shí)間里既是古代羌人民族教育的主要內(nèi)容,又同時(shí)作為一種根本動(dòng)力促使了羌族民族教育的逐漸獨(dú)立。由于族群地處的山林、河谷等地理環(huán)境,古羌人以自己獨(dú)特的方式詮釋了本民族所面對(duì)的自然萬(wàn)物。這種原始宗教的詮釋方式,雖然很大部分是基于對(duì)生存環(huán)境的依賴(lài)、敬畏和恐懼等等,但其中也包含了生存經(jīng)驗(yàn)和生存技能的總結(jié),更代表了民族得以誕生和延續(xù)下去的一些基本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正是讓一代又一代的族群后人能夠堅(jiān)守和繁衍的重要原因。一如佛羅斯特所說(shuō):“由于原始社會(huì)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傾向于靜止?fàn)顟B(tài),因此教育是一種保守的力量,總是致力于維護(hù)現(xiàn)狀和給青年人傳授那些在變化中固有的東西。”[3]10原始宗教所蘊(yùn)生出的民族教育,其外在強(qiáng)調(diào)的是面對(duì)自然生存條件趨利避害的種群繁衍法則,而內(nèi)在強(qiáng)調(diào)的則是在趨向一致的心靈歸屬中,維系族群穩(wěn)固壯大的精神觀念法則。按照一般規(guī)律而言,隨著社會(huì)生產(chǎn)力的進(jìn)步,這種自然宗教和教育共生的現(xiàn)象會(huì)逐步分離,世俗教育的獨(dú)立成為民族教育的主要承擔(dān)者。然而,由于在羌民族漫長(zhǎng)的發(fā)展歷史過(guò)程中,并沒(méi)有形成嚴(yán)格意義上的“一神教”,而其“多神教”的特征也并沒(méi)有像道教或神道教那樣形成完整的宗教教義和嚴(yán)密的教派組織等。因此,羌族保留至今的、源自于原始時(shí)代的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禮儀、民俗等文化,并沒(méi)有隨著自然崇拜的消退而消失,而是在獨(dú)特的口耳相授、演示實(shí)踐的文化傳承過(guò)程當(dāng)中,一直與本民族的社會(huì)教育相生并存。而來(lái)自于原始自然宗教所強(qiáng)調(diào)的“看不見(jiàn)的力量”,也在這一過(guò)程中逐漸演化為民族精神教育和哲學(xué)認(rèn)知的基礎(chǔ)。羌人以“白石崇拜”為基礎(chǔ)的宗教文化,浸透到整個(gè)族群的教育過(guò)程中。由于羌人居住地區(qū)相對(duì)偏僻和閉塞的條件,在大規(guī)模的文化發(fā)掘和學(xué)校教育進(jìn)入羌區(qū)以前,羌族民族教育的所有內(nèi)容,幾乎全部由自然宗教的內(nèi)容演繹而來(lái),在羌寨的祭山會(huì)、釋比唱經(jīng)以及婚喪嫁娶等場(chǎng)合,很明顯可以看到這種“教育本身也滲透了神學(xué)的性質(zhì)”[4]400。以北川地區(qū)而言,如青片鄉(xiāng)、小寨子溝等尚保留較為完整的神樹(shù)信仰、山神信仰、藥王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代際之間教育的主要內(nèi)容。盡管新一代的年輕族人接受了更多的現(xiàn)代觀念和生活方式,但上一代在實(shí)際生活中的一些宗教儀禮行為,同時(shí)也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著耳濡目染的影響。
(二)近代以來(lái)羌族宗教教育與學(xué)校教育的分合
由于受到“夷夏之辨”思想的影響,在傳統(tǒng)中國(guó)社會(huì)中,中原地區(qū)與羌族地區(qū)的文化交流,一直是站在文化輸出和文化同化的角度進(jìn)行的。從清初開(kāi)始對(duì)羌區(qū)實(shí)行的“改土歸流”和里甲制度,更是強(qiáng)行民族同化的顯例。以北川地區(qū)為例,清代“漢民里”的劃分以及近代民國(guó)政府“行政督察區(qū)專(zhuān)員公署”的設(shè)立和保甲制度的實(shí)行,北川羌人“通漢人語(yǔ)者幾半”[5]37。在這種文化影響過(guò)程中,羌族宗教文化固然吸收融入了其他宗教元素,比如觀音、玉皇和孔子供奉等等,但這種漠視民族特性的文化政策和宗教政策,必然導(dǎo)致民族教育自身的反彈。因此,晚清到民國(guó)以來(lái),盡管政府投入了相當(dāng)力量,在羌區(qū)進(jìn)行了現(xiàn)代教育機(jī)構(gòu)的興建,并形成了羌族現(xiàn)代學(xué)校教育的雛形,如清光緒二十九年開(kāi)始將舊九峰、岷山、酉山等書(shū)院相繼改為小學(xué)學(xué)堂,以及1931年“松理懋茂汶共立中學(xué)”的草創(chuàng)成立,各類(lèi)中學(xué)、職業(yè)學(xué)校相繼出現(xiàn)等。但這種學(xué)校教育在實(shí)質(zhì)上并沒(méi)有對(duì)羌族自身的“宗教+民族”的文化教育方式產(chǎn)生根本性的影響,其原因之一固然是由于羌人村寨環(huán)境的偏僻閉塞,物質(zhì)條件貧乏,所謂“教資不良,教法尚未改善,經(jīng)費(fèi)支絀,設(shè)備無(wú)法補(bǔ)充,生活困難學(xué)童易于輟學(xué)”[6]26等,但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恐怕也有基于對(duì)歷來(lái)強(qiáng)制同化的反感,故而由此產(chǎn)生的對(duì)外來(lái)文化為主導(dǎo)的學(xué)校教育的抵觸心理。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羌族原有的民族教育所具有的神秘化、巫術(shù)化等原始宗教特征,而學(xué)校教育又無(wú)法真正有效開(kāi)展,故此在羌區(qū)出現(xiàn)的是“社會(huì)教育比學(xué)校教育還落后”的局面,民族宗教教育和現(xiàn)代學(xué)校教育從一開(kāi)始就沒(méi)能夠找到適當(dāng)?shù)慕Y(jié)合點(diǎn)。但總的看來(lái),近代從清末到民國(guó)這段時(shí)期,誕生于新文化思潮之中的現(xiàn)代學(xué)校教育制度,已然開(kāi)始從教育資源、教育方式以及教育對(duì)象等方面影響羌族本民族傳統(tǒng)的原始宗教文化教育。此時(shí)期西方傳教士和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對(duì)羌族宗教文化的自覺(jué)性研究及總結(jié),也為后一時(shí)期探索傳統(tǒng)民族教育和現(xiàn)代學(xué)校教育之間的關(guān)系奠定了基礎(chǔ)。新中國(guó)成立后,宗教與教育分離原則的實(shí)行,對(duì)剝離宗教神秘主義外衣,進(jìn)行知識(shí)文化的科學(xué)普及和教育功能的合理分配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羌區(qū)學(xué)校教育的規(guī)模和水準(zhǔn)相比近代時(shí)期,有了跨越式的發(fā)展。但另一方面,就西南地區(qū)尤其是居住地域較分散的羌民族而言,由于羌族并沒(méi)有嚴(yán)格意義上的宗教教義和宗教義務(wù)的限定,因此,在羌區(qū)學(xué)校教育廣泛普及、完全融入社會(huì)主流教育體系的同時(shí),如何保存和傳播本民族固有的民族文化,進(jìn)行具有民族特色的社會(huì)教育,又成為羌族教育所面臨的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尤其在經(jīng)歷了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暴力性毀壞之后,羌族傳統(tǒng)宗教生活呈現(xiàn)出衰落態(tài)勢(shì),比如神靈偶像的破壞、廟宇的拆除,以及由于祭山會(huì)遭禁所帶來(lái)的釋比傳承和釋比文化的瀕危等等。汶川地震后,北川原縣城被基本摧毀,有近萬(wàn)羌族人喪生,異地重建之后的分散居住、外出務(wù)工、現(xiàn)代信息和生活方式的沖擊等,無(wú)疑皆進(jìn)一步加劇了本民族文化傳承和民族教育的危機(jī)。如何恢復(fù)族群文化的本來(lái)面目和民族文化傳承的價(jià)值精髓,尤其是羌族傳承至今的原始宗教內(nèi)容,其存留的篤信神秘自然力量的原始思維,與其衍生的豐富多彩的禮儀民俗等文化內(nèi)容,如何在傳授現(xiàn)代知識(shí)文化的學(xué)校教育中進(jìn)行有效的民族文化融入,成為羌族宗教民族教育和羌區(qū)學(xué)校教育的新問(wèn)題。
二、新時(shí)期羌族宗教文化的開(kāi)掘與嬗變
(一)改革開(kāi)放及震后羌族宗教文化功能和宗教教育功能的蛻變
八十年代以來(lái),部分羌寨恢復(fù)了祭山會(huì)的儀式,但由于此前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運(yùn)動(dòng)的影響,羌區(qū)的諸多宗教祭祀儀式和民間信仰儀式在一度中斷之后,開(kāi)始逐漸銷(xiāo)聲匿跡。以個(gè)案調(diào)查為例,“祭山會(huì)、打太平保護(hù)等上壇儀式在雁門(mén)鄉(xiāng)白水村,已經(jīng)基本上失去了生存空間,只有修房子或春節(jié)前后的安神儀式、治療疾病的踩燁頭、放音童等中壇、下壇儀式還有一些生存空間”[7]35。傳統(tǒng)節(jié)日和祭祀活動(dòng)在羌區(qū)的淡化,帶來(lái)的直接影響是羌族原始宗教文化傳承的斷裂和嬗變。羌族的大型祭祀活動(dòng)曾是維系羌族族群團(tuán)結(jié)、凝聚精神力量和傳播文化的重要手段。隨著這些傳統(tǒng)儀式生存空間的縮小,羌族宗教文化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也在進(jìn)行著新的調(diào)適,一是宗教儀式針對(duì)性的現(xiàn)實(shí)化和功利化,比如上述的具有治病作用的放音童、跳紅鍋等儀式。二是宗教內(nèi)容的固定化和形式化,羌族原始宗教文化的保存、整理和研究多數(shù)是由專(zhuān)門(mén)的學(xué)者來(lái)完成,這些文化內(nèi)容已然外化為固定的符號(hào)標(biāo)志,比如白石崇拜、萬(wàn)物有靈、多神信仰等,而羌族原始宗教文化內(nèi)容自身的瀕危卻與這種研究恰恰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這種調(diào)適一方面反映了現(xiàn)代羌人對(duì)自然和社會(huì)認(rèn)識(shí)程度的提高,對(duì)原始神秘力量崇拜的減少,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現(xiàn)代語(yǔ)境下源生于原始宗教的民族文化認(rèn)同心理的弱化。伴隨著物質(zhì)生活條件的提高和現(xiàn)代科技的進(jìn)步,年輕一代羌族對(duì)各種傳統(tǒng)祭祀活動(dòng)以及禮儀民俗日漸陌生,而對(duì)來(lái)自原始宗教中的世界認(rèn)知方式和價(jià)值觀念更是知之甚少。在汶川大地震后,一些熟知傳統(tǒng)的老一輩羌人的離世以及羌寨聚居地的舉家遷徙,讓一些固定的地域文化特征亦逐漸消失,比如北川新縣城的外遷、平壩地帶居住建筑樣式的改變和房屋內(nèi)火塘的取消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民族精神力量核心存在的羌族宗教文化,如何在新環(huán)境中尋找本民族的生存延續(xù)動(dòng)力,既關(guān)涉到民族宗教文化的保存,也關(guān)涉到民族教育的未來(lái)方向。
(二)媒體傳播和文化多元化對(duì)羌族宗教文化的雙重影響
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的迅速發(fā)展和廣電網(wǎng)絡(luò)在羌區(qū)的逐漸普及,使得新的信息和文化交流方式隨之出現(xiàn)。以北川縣為例,震前已經(jīng)實(shí)現(xiàn)廣播電視的“村村通工程”,覆蓋率達(dá)到了100%,災(zāi)后重建的廣播電視發(fā)射塔和數(shù)字設(shè)備等,更進(jìn)一步地讓多數(shù)山區(qū)羌寨迎來(lái)了“數(shù)字電視”時(shí)代。文化信息的雙向交流過(guò)程,既讓羌族宗教文化得以在廣闊的平臺(tái)上更便利、更直接地對(duì)外傳播,同時(shí)也使得本族宗教文化受到了更為多元化的沖擊。在全媒體和影像傳播的時(shí)代,影視符號(hào)對(duì)羌族文化的展現(xiàn)可以更為直觀、鮮明,讓人身臨其境,將一些單純用語(yǔ)言、音聲無(wú)法表達(dá)的東西傳播到世界各個(gè)角落,比如原始宗教信仰里的各類(lèi)祭祀儀式和有關(guān)的音樂(lè)、舞蹈等。在這種民族原生文化形態(tài)的基礎(chǔ)上,重新以影像符號(hào)編制的媒體產(chǎn)品,如紀(jì)錄片、新聞紀(jì)實(shí)報(bào)道以及電影電視作品等,正在取代以往的包括錄音、文字、圖案等傳統(tǒng)媒介方式。互聯(lián)網(wǎng)終端的多元化、及時(shí)性?xún)?yōu)勢(shì),以及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的快速滲透,更是讓羌族宗教文化的保存、傳播和延續(xù)都進(jìn)入到前所未有的全新時(shí)期。以中國(guó)羌族網(wǎng)(cnqiangzu.com)、中國(guó)羌族文化信息網(wǎng)(qiangren.2000y.com)以及中國(guó)羌族文化網(wǎng)微博(t.qq.com/qiangzuren)等網(wǎng)媒為代表,網(wǎng)站對(duì)羌文化的分門(mén)別類(lèi)以及與網(wǎng)絡(luò)受眾互動(dòng)的過(guò)程,反映了當(dāng)前羌人自身對(duì)原始宗教文化的認(rèn)知狀況,也反映了羌族宗教文化的生存現(xiàn)狀。在網(wǎng)站的介紹當(dāng)中,羌族宗教文化所展示給受眾的,是色彩分明的巫師服、猴皮帽以及皺紋滿(mǎn)面的羌族老釋比等。通過(guò)生動(dòng)鮮明的圖像和聲音,外界固然比以往更為直觀地看到、聽(tīng)到了羌族宗教生活,但這種固化的、觀賞式的方式,也正在使羌族宗教文化膚淺化和娛樂(lè)化。也就是說(shuō),在具有隔膜感的媒介生態(tài)中,包括羌族宗教文化在內(nèi)的整個(gè)羌族文化面貌,正處在“被建構(gòu)”[8]的狀態(tài)。這種情況,一方面吸引了更多受眾關(guān)注羌族文化,但另一方面則由于媒體話(huà)語(yǔ)權(quán)的導(dǎo)向,使得羌族文化的原生狀態(tài)和傳承有所異化。近年來(lái)在北川縣城各廣場(chǎng)組織的莎朗舞活動(dòng)和“萬(wàn)人莎朗”吉尼斯記錄的創(chuàng)造,實(shí)際上也透露出一種對(duì)媒體間離化的反撥。因此,開(kāi)展多元媒介的全方位民族志記錄,結(jié)合羌族年輕一代的現(xiàn)代教育背景,以新的影像敘事手段進(jìn)行宗教文化內(nèi)涵的教育轉(zhuǎn)換,應(yīng)當(dāng)是媒體時(shí)代羌族宗教文化和宗教教育延續(xù)的重要問(wèn)題。
三、媒體語(yǔ)境下羌族宗教文化的教育重構(gòu)方向
(一)文化融合背景下的文化本真性還原
在媒體文化和他族文化不斷沖擊的文化融合背景下,羌族宗教文化在面臨內(nèi)在文化資源和教育資源延續(xù)危機(jī)的同時(shí),另一方面卻要不斷應(yīng)對(duì)紛至沓來(lái)的文化發(fā)掘和文化觀光等活動(dòng),在文化生態(tài)的不斷變動(dòng)之中,羌族宗教文化需要從其原始宗教所具有的精神凝聚力入手,還原其文化的內(nèi)在本真狀態(tài),而非外在表象性的客觀記錄,從而建立民族教育與宗教教育結(jié)合的良性結(jié)構(gòu)。本真性(authenticity)一詞,源于希臘語(yǔ)的“authentes”,意為“權(quán)威者”或“親手制作”。此概念最早來(lái)自海德格爾對(duì)自我存在和共同存在的討論[9]144,是西方哲學(xué)中的一個(gè)重要概念。二十世紀(jì)中葉后,本真性進(jìn)入文化領(lǐng)域,為考察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之間的關(guān)系提供了新的視角。尤其是在民俗學(xué)和旅游文化人類(lèi)學(xué)等領(lǐng)域,對(duì)真實(shí)性、原生態(tài)等的討論,成為當(dāng)前民族文化保護(hù)和文化開(kāi)發(fā)的熱點(diǎn)。就國(guó)內(nèi)的文化淵源而言,“真人”“純真”等觀念既是老莊學(xué)說(shuō)的核心,也是中國(guó)原始哲學(xué)“無(wú)極”“太極”等思想的演繹。因此,就具有典型原始宗教特征的羌族文化來(lái)說(shuō),在民族教育中積極開(kāi)展對(duì)本族宗教文化原生精神力量的探尋和重建,應(yīng)當(dāng)是現(xiàn)階段文化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具體而言,針對(duì)當(dāng)前羌族地區(qū)的文化生態(tài)實(shí)情,一是要在旅游文化的興起過(guò)程中突破一些符號(hào)化的文化表象,比如招攬性的民族服飾展示、表演性的歌舞以及禮儀展示等;同時(shí)在民族教育中著重關(guān)注旅游文化經(jīng)濟(jì)效益背后所蘊(yùn)含的文化原生動(dòng)力所在,以及這種文化活動(dòng)的根本目的和民族生存前景等。二是在面對(duì)外來(lái)力量的文化保護(hù)和文化開(kāi)發(fā)活動(dòng)的同時(shí),比如震后出現(xiàn)的政府諸多“客位保護(hù)”[10]現(xiàn)象等,需要通過(guò)民族教育和宗教教育的結(jié)合,強(qiáng)化對(duì)本族宗教文化內(nèi)部保護(hù)和延續(xù)的自覺(jué)意識(shí)。三是需要將民族生活中的宗教內(nèi)容適當(dāng)引入學(xué)校教育,進(jìn)行道德精神的重構(gòu)教育,以民族節(jié)日、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為切入點(diǎn),抽取宗教中的神圣性教育,與個(gè)體對(duì)自然、社會(huì)的敬畏教育相結(jié)合,在科學(xué)認(rèn)知的基礎(chǔ)上,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精神教育內(nèi)容。由此,讓羌民族在自我探尋、真實(shí)自我表達(dá)的過(guò)程中,銘記“存留在集體記憶中的深刻影響”[11]。以北川地區(qū)來(lái)說(shuō),震后十年,在北川地震遺址逐漸成為新的旅游紀(jì)念地的情況下,羌民族原始信仰中推崇的勇于犧牲、自強(qiáng)自立的精神,與這一新的集體記憶符號(hào)之間的映射,正提供了宗教教育與民族教育的兩相融合二次契機(jī)。
(二)地域變遷后的民族文化尋根
教育對(duì)于聚居地域相對(duì)固定的羌人來(lái)說(shuō),以宗教文化為根基的民族文化,其發(fā)源和傳承都與濃厚的地域意識(shí)密切相連。在部族漫長(zhǎng)的歷史長(zhǎng)河中,“建立在地緣意識(shí)基礎(chǔ)上的種種價(jià)值觀念由此應(yīng)運(yùn)而生,如家園之戀、故土之思、鄰里鄉(xiāng)黨、宗廟社稷、籍貫祖墳等等”[12]。從八十年代到今天,羌族的地域情況發(fā)生了較大變化,其標(biāo)志有二:一是現(xiàn)代消費(fèi)觀念和商品大潮的影響下,羌人堅(jiān)守故土觀念的轉(zhuǎn)淡;二是汶川地震之后許多羌族村寨的整體搬遷,對(duì)傳統(tǒng)羌族生活環(huán)境的根本改變。如果說(shuō),現(xiàn)代化生活方式的進(jìn)入,是媒介生態(tài)和技術(shù)理性讓羌族經(jīng)歷的“隱性”的地域變化,而在汶川大地震后的舉家遷移,則以直接可見(jiàn)的方式讓羌人感覺(jué)到了地域陌生化的不適。在從震后的應(yīng)急狀態(tài)中逐漸恢復(fù)和適應(yīng)過(guò)來(lái)的情況之下,如何重建羌民族的文化核心,進(jìn)行新時(shí)期的民族身份認(rèn)同,需要重新借助曾是民族誕生根源的原始宗教文化,進(jìn)行民族文化尋根教育,以獲取其宏大、深沉的精神召喚力。尤其對(duì)于今天的羌人而言,在地域意識(shí)和物質(zhì)環(huán)境都已迥異于過(guò)去的情況下,“每個(gè)人都需要擁有多重的根。每個(gè)人都需要,以他作為自然成員的環(huán)境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靈性生命的幾乎全部?jī)?nèi)容”[13]33。
文化尋根曾是二十世紀(jì)西方波及范圍最廣的一場(chǎng)思想運(yùn)動(dòng),其對(duì)現(xiàn)代性的反思和對(duì)民間文化的復(fù)興至今影響至深。但國(guó)內(nèi)八十年代以來(lái)以“尋根文學(xué)”為代表的思想潮流,在注重鄉(xiāng)土地方特色的同時(shí),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文化尋根所蘊(yùn)含的本質(zhì)意義。如葉舒憲所說(shuō):“文化尋根是牽涉到我們這個(gè)星球和人類(lèi)的互動(dòng)以及人類(lèi)內(nèi)部互動(dòng)關(guān)系的終極關(guān)懷問(wèn)題,而絕不只是懷舊、復(fù)古、保守的傳統(tǒng)主義、迷戀民間鄉(xiāng)土習(xí)俗或者展現(xiàn)地方特色。”[14]所以,就現(xiàn)代語(yǔ)境下的羌族而言,其文化尋根教育面臨著兩個(gè)問(wèn)題:一是重建以原始宗教文化為依歸的民族精神家園,進(jìn)行新的民族身份認(rèn)同;二是在文化開(kāi)發(fā)和文化保護(hù)活動(dòng)中,區(qū)分形式化、零散化的文化懷舊與完整的文化體系修復(fù)之間的異同。對(duì)前者來(lái)說(shuō),由于羌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在外在文化符號(hào)上至今依然存在,如白石、釋比、莎朗、羌笛等,其所內(nèi)涵的文化心理亦潛藏于族群內(nèi)心,因此,需要將這些本屬于宗教儀式附加物的文化符號(hào),融入民族教育資源之中,提升來(lái)自于傳統(tǒng)宗教的心理功能,即在去除了宗教的神秘信仰后,依然具有“強(qiáng)化群體規(guī)范,為個(gè)體行為提供道德約束,并為那些共同體福社仰賴(lài)的共同目標(biāo)和價(jià)值提供基礎(chǔ)”[15]391這樣的精神意義。比如羌族宗教信仰的祖先崇拜和靈物崇拜,在更加注重個(gè)體心理體驗(yàn)的今天,尤其是在經(jīng)歷了大地震之后心理狀態(tài)發(fā)生巨大改變的背景下,可以通過(guò)血緣親情的追溯和生存環(huán)境的對(duì)比教育,重塑民族道德精神的宗旨和感恩文化等。對(duì)后者來(lái)說(shuō),更為迫切的問(wèn)題則是,需要在當(dāng)前的旅游文化開(kāi)發(fā)過(guò)程中,通過(guò)深層次的民族文化素養(yǎng)教育,來(lái)應(yīng)對(duì)文化商品化的泛濫問(wèn)題。盡管關(guān)于文化商品化的討論有著較為對(duì)立的觀點(diǎn),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羌區(qū)的地域狀況和羌人的地域意識(shí)都發(fā)生較大變化的今天,羌族原生文化的消退,各種外來(lái)的“他者敘述”已然無(wú)法掩蓋,比如羌族舞蹈風(fēng)格和功能的轉(zhuǎn)換、羌繡藝術(shù)逐漸的模式化和膚淺化等。故此,必須通過(guò)族群內(nèi)部的文化教育重構(gòu),重新樹(shù)立羌人對(duì)文化的自我認(rèn)同,培養(yǎng)一批具有民族文化自覺(jué)意識(shí)的傳承者,去探索和思考新時(shí)期羌族民族文化的“現(xiàn)代性矛盾”與“文化尋根的內(nèi)部矛盾”。
參考文獻(xiàn):
[1]RALPHCOVELL.羌人的宗教和民族淵源考[J].焦玉琴,譯.宗教與民族(第壹輯),2002(00):232.
[2]胡鑒民.羌民的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型式[J].金陵大學(xué)金陵學(xué)報(bào),1941(10):10-11.
[3]佛羅斯特.西方教育的歷史和哲學(xué)基礎(chǔ)[M].吳元訓(xùn),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趙德.石泉縣志[M].成都:巴蜀書(shū)社,1992.
[6]馮克書(shū).理番縣視察述要[M].杭州:杭州古籍書(shū)店,1964.
作者:張偉平 單位:綿陽(yáng)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與歷史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