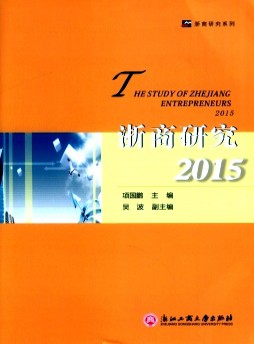桂學(xué)研究的區(qū)域文化理論基礎(chǔ)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桂學(xué)研究的區(qū)域文化理論基礎(chǔ)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新西部雜志》2014年3期
一、“區(qū)域”概念闡釋與區(qū)域文化研究基礎(chǔ)
區(qū)域概念過(guò)去常常被作為地域、地方、地區(qū)概念使用,主要因其與行政區(qū)域概念緊密聯(lián)系有關(guān)。但即便是依行政區(qū)域劃分,歷代都有所變化,呈現(xiàn)跨區(qū)域行政交叉現(xiàn)象。如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guó)后的行政區(qū)域劃分,“秦王朝統(tǒng)一嶺南,置桂林、南海和象郡,現(xiàn)在的廣西含當(dāng)年的桂林郡全部,南海、象及長(zhǎng)沙、黔中等郡部分地區(qū)”,足以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行政區(qū)域劃分與現(xiàn)在區(qū)域劃分也有跨域交叉現(xiàn)象。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及其特定語(yǔ)境下,區(qū)域含義有所擴(kuò)大和延伸,一方面在地理空間范圍含義基礎(chǔ)上,賦予其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經(jīng)濟(jì)地理等空間范圍含義;另一方面在行政劃分所指區(qū)域含義基礎(chǔ)上,超越行政區(qū)域而擴(kuò)大延伸到非行政劃分區(qū)域含義;再一方面擴(kuò)大延伸為跨域、跨界所形成的區(qū)域范圍,帶有跨區(qū)域的特征和色彩。由此可見(jiàn),以自然與文化相互關(guān)系構(gòu)成的非行政化區(qū)域概念從古至今仍在使用。以江河湖海流域作為水域空間范疇的區(qū)域,如黃河流域、長(zhǎng)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構(gòu)成跨省水系區(qū)域;以洞庭湖為紐帶與分界,劃分湖北與湖南省域及其水系溝通形成的楚文化區(qū)域;以黃河為界劃分河北與河南省域及其水系溝通形成的中原文化區(qū)域;廣西西江水域由西向東的紅水河與由北向東的桂江匯合入珠江,又構(gòu)成泛珠江流域及其珠江水系區(qū)域;廣西興安自秦始皇統(tǒng)一嶺南修筑靈渠,溝通北上的湘江水系與南下的漓江水系,形成湘漓分派與水域貫通的湘漓流域,形成跨省湘桂區(qū)域,等等。以山脈為紐帶與屏障,五嶺以南的廣東、廣西在先秦時(shí)期就稱(chēng)為嶺南地區(qū),此后所謂“兩廣”、“粵桂”表明其具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度的區(qū)域范圍;處于嶺南的廣西與嶺北的湖南通過(guò)湘桂古道形成湘桂走廊,構(gòu)成湘桂之間連接的區(qū)域,等等。此外,以語(yǔ)言(方言)、民族、民俗、政治、經(jīng)濟(jì)、交通、歷史淵源與文化形態(tài)為紐帶構(gòu)成的跨地區(qū)的區(qū)域概念使用不勝枚舉。
其二,區(qū)域合作背景下的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格局。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及其文化語(yǔ)境下的區(qū)域概念使用,因全球化與多元化影響下的區(qū)域經(jīng)濟(jì)崛起以及世界經(jīng)濟(jì)共同體需求,越來(lái)越著眼于從經(jīng)濟(jì)發(fā)展視角建構(gòu)與重構(gòu)區(qū)域概念。從國(guó)際區(qū)域關(guān)系看,一方面基于國(guó)際社會(huì)及其世界各國(guó)發(fā)展需求,經(jīng)歷了“二戰(zhàn)”后“冷戰(zhàn)”時(shí)期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jì)結(jié)盟以及意識(shí)形態(tài)陣營(yíng)與三個(gè)世界的劃分,形成國(guó)際社會(huì)(如聯(lián)合國(guó)、世貿(mào)組織)以及一定范圍內(nèi)的區(qū)域性跨國(guó)聯(lián)盟(如歐盟、東盟)等概念含義;另一方面,世紀(jì)之交以來(lái)在全球化視野中著重于經(jīng)濟(jì)的區(qū)域聯(lián)盟或跨區(qū)域聯(lián)盟,構(gòu)建跨國(guó)、跨界、跨境的經(jīng)濟(jì)聯(lián)合體、共同體、同盟體,以及不結(jié)盟的區(qū)域間合作、協(xié)作、協(xié)同關(guān)系,構(gòu)成國(guó)際社會(huì)及其國(guó)際性區(qū)域經(jīng)濟(jì)合作基本格局。從世界性區(qū)域聯(lián)盟產(chǎn)生背景與語(yǔ)境看,除相對(duì)于國(guó)際社會(huì)以及超級(jí)大國(guó)霸權(quán),即區(qū)域相對(duì)于中心而言,帶有一定的對(duì)抗性外,更多地是強(qiáng)調(diào)區(qū)域合作與協(xié)作,構(gòu)成或緊或松的國(guó)際關(guān)系共同體與聯(lián)合體。從國(guó)內(nèi)區(qū)域關(guān)系看,在改革開(kāi)放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背景下建構(gòu)的區(qū)域發(fā)展視野中,除相對(duì)于中央而言的地方所指區(qū)域概念含義外,一般所指省市縣鄉(xiāng)行政區(qū)域;隨著區(qū)域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相繼構(gòu)建非行政化的、依賴于一定的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基礎(chǔ)的、以經(jīng)濟(jì)為紐帶的、跨地區(qū)結(jié)合的經(jīng)濟(jì)開(kāi)發(fā)區(qū)以及經(jīng)濟(jì)合作、協(xié)作區(qū),如沿海經(jīng)濟(jì)開(kāi)發(fā)區(qū)、國(guó)家經(jīng)濟(jì)開(kāi)發(fā)區(qū)、國(guó)家高新技術(shù)開(kāi)發(fā)區(qū),以及跨區(qū)域的“長(zhǎng)三角”“、珠三角”經(jīng)濟(jì)合作區(qū),還有更大范圍的東部、西部、中部、東北等區(qū)域概念的劃分。區(qū)域經(jīng)濟(jì)崛起與跨區(qū)域經(jīng)濟(jì)合作協(xié)作方式興起極大地推動(dòng)區(qū)域發(fā)展步伐,既通過(guò)競(jìng)爭(zhēng)拉開(kāi)區(qū)域間差距,率先成為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地區(qū);又通過(guò)區(qū)域合作協(xié)作,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欠發(fā)達(dá)、后發(fā)展地區(qū)趕超跨越,逐步縮小區(qū)域差距,構(gòu)成協(xié)同發(fā)展、共同富裕的趨向。總之,區(qū)域發(fā)展觀念比任何時(shí)期都深入人心,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大趨勢(shì)。
其三,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背景下區(qū)域文化興起。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在推動(dòng)區(qū)域經(jīng)濟(jì)崛起的同時(shí)也推動(dòng)了區(qū)域文化建設(shè)發(fā)展,區(qū)域文化的區(qū)域概念也隨著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而擴(kuò)大與開(kāi)放。文化的交往性、綿延性與包容性特點(diǎn)不僅促使區(qū)域概念含義理解不僅僅涵蓋地域、地方、地區(qū)含義,而且?guī)в锌绲赜颉⒖绲胤健⒖绲貐^(qū)以及跨境、跨界、跨文化的意義;區(qū)域文化不僅局限于區(qū)域空間,而是超越區(qū)域空間而擴(kuò)展為文化空間。其文化區(qū)域空間范圍立足于而又不僅僅局限于自然地理空間與行政地理空間的地域范圍,而且擴(kuò)大為文化地理空間范圍。其區(qū)域界定以及域界劃分不僅僅為一個(gè)要素決定,而是包括自然、歷史、文化、政治、經(jīng)濟(jì)、交通、族群、語(yǔ)言、民俗、交往等各要素系統(tǒng)關(guān)系的綜合性整體構(gòu)成。盡管為了更為明確清晰界定區(qū)域概念內(nèi)涵與外延及其所指對(duì)象范圍的需要,尤其是為了劃分區(qū)域界限的需要,往往習(xí)慣于按照思維定式,簡(jiǎn)單化地將區(qū)域等同于主要依據(jù)行政化劃分的地域、地方、地區(qū)概念,更便于構(gòu)成條塊分割的行政地區(qū)空間與從上到下的線性垂直行政管理域限,但則不能否認(rèn)和掩蓋依據(jù)非行政化的其它要素及其綜合性要素所構(gòu)成的區(qū)域及其區(qū)域文化客觀存在的事實(shí)。尤其是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及其區(qū)域經(jīng)濟(jì)崛起的現(xiàn)實(shí)需求,更凸顯出非行政化劃分區(qū)域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更為凸顯區(qū)域文化內(nèi)涵外延的開(kāi)放性與跨區(qū)域交往交流與融合的特征。區(qū)域文化含義不僅是因區(qū)域空間形成其內(nèi)涵外延,而且是因文化傳承、傳播與發(fā)展的歷史性與傳統(tǒng)性構(gòu)成其內(nèi)涵外延。通常所說(shuō)的區(qū)域文化,往往指稱(chēng)當(dāng)代社會(huì)區(qū)域空間及其行政區(qū)域的文化形態(tài),諸如作為省域文化稱(chēng)謂的廣西文化,作為市域文化稱(chēng)謂的桂林文化,作為縣域文化稱(chēng)謂的臨桂文化,等等。但歷史上所稱(chēng)區(qū)域文化概念則豐富多彩,不僅從區(qū)域空間而言具有跨區(qū)域的開(kāi)放性,而且從文化形態(tài)的內(nèi)涵外延而言具有多樣性、開(kāi)放性與包容性。諸如中原文化,從區(qū)域文化角度而論,當(dāng)然屬于中原地區(qū)這一特定區(qū)域空間的文化形態(tài),中原所指區(qū)域指河南,古稱(chēng)豫州,即中州,“古豫州地處九州中間,稱(chēng)為中州。漢王充《論衡•對(duì)作》:‘建初孟年,中州頗歉,穎川、汝南民流四散。’今河南為古豫州地,故相沿亦稱(chēng)河南為中州。”
《辭源》釋“中州”有三義,狹義為河南,中義為黃河中下游區(qū)域或黃河流域,廣義泛指中國(guó)。中州即中原,作為中華文明的發(fā)源地或發(fā)祥地并非僅僅局限于河南,后擴(kuò)大到黃河中下游區(qū)域或黃河流域,以及泛指中國(guó)。更為重要的是,中原文化并不簡(jiǎn)單等同于中原,中原只是中原文化的發(fā)源地與傳播源。文化的傳播性、開(kāi)放性與擴(kuò)展性使中原文化跨區(qū)域擴(kuò)大為黃河流域范圍以及整個(gè)中國(guó)范圍,并影響到海外、域外的周邊更大范圍區(qū)域,以致于此后中原文化影響全國(guó),成為中國(guó)文化主流、正宗、中心,甚至常常用來(lái)指代中華文化,反而淡化其區(qū)域文化含義。由此可見(jiàn),歷史上所使用的區(qū)域文化概念,在充分考慮其產(chǎn)生區(qū)域空間含義的基礎(chǔ)上,更為注重其文化含義及其特征,以及文化在歷時(shí)性傳承、傳播和發(fā)展的開(kāi)放性、包容性與擴(kuò)張性。
廣西歷史上也有一些表征區(qū)域文化的概念,諸如嶺南文化,顯然作為區(qū)域文化而言的區(qū)域是指五嶺以南的嶺南地區(qū),亦即廣東廣西的“兩廣”地區(qū),但就其文化形態(tài)特征而論,既不能僅僅涵蓋“兩廣”,其文化外延可以擴(kuò)展到南方各地跨界區(qū)域以及沿邊沿海跨境區(qū)域;又不能僅僅以之涵蓋“兩廣”所有區(qū)域文化形態(tài),況且廣東與廣西各自的區(qū)域文化也有差異性,下屬各地文化形態(tài)更為豐富多樣。更為重要的是,文化并非像地域那樣固定,而是具有運(yùn)動(dòng)性、流動(dòng)性、活態(tài)性的生命表征,嶺南文化也是在與其它文化形態(tài),尤其是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區(qū)域文化。粵西文化亦如此,歷史上所謂粵西地區(qū),指簡(jiǎn)稱(chēng)為“粵”的廣東以西的廣西,地域范圍雖然涵蓋廣西,但粵西文化形態(tài)及其特質(zhì)特征并非涵蓋廣西區(qū)域所有文化形態(tài),粵西地區(qū)概念并非等同于粵西文化概念,粵西文化概念也并非等同于廣西文化。這足以說(shuō)明粵西文化具有超越粵西地區(qū)概念的跨區(qū)域性意義,粵西文化所指對(duì)象范圍的模糊性正印證其開(kāi)放性,其性質(zhì)特征也并非僅僅與“粵”相關(guān)的廣西文化形態(tài),或者說(shuō)兩廣文化的融合,或者說(shuō)廣西文化受到粵文化影響的結(jié)果,而且應(yīng)該作為一個(gè)獨(dú)立文化形態(tài),其獨(dú)立性與特殊性也正說(shuō)明其相對(duì)性,具有跨區(qū)域文化交流、交融特征。由此可見(jiàn),區(qū)域文化立足于區(qū)域而又具有跨區(qū)域特點(diǎn),從而由區(qū)域空間范圍擴(kuò)大為文化空間范圍,使之不僅具有相對(duì)性與多樣性,而且具有開(kāi)放性與包容性。
二、廣西區(qū)域文化發(fā)展及其生成環(huán)境條件
廣西區(qū)域文化作為一個(gè)區(qū)域性概念理解,區(qū)域、區(qū)域文化應(yīng)該成其界定以及內(nèi)涵外延理解的前提,同時(shí)也需要從歷時(shí)性建構(gòu)與共時(shí)性構(gòu)成的內(nèi)在邏輯與時(shí)空關(guān)系角度深化認(rèn)知,辨析其與通常所習(xí)慣使用的廣西文化概念的異同及其在區(qū)域研究視野中凸顯區(qū)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一,廣西區(qū)域文化含義。就廣西作為一個(gè)區(qū)域概念而論,從自然地理空間意義上的區(qū)域劃分與行政管理區(qū)域意義上的廣西區(qū)域界定應(yīng)該十分明晰;同時(shí)相對(duì)于廣西與周邊區(qū)域間關(guān)系而言,以及廣西相對(duì)于中國(guó)所屬關(guān)系的更大區(qū)域范圍內(nèi)的定位而言,以確定廣西區(qū)域概念及其區(qū)位特點(diǎn)也并非難事。而對(duì)廣西區(qū)域文化理解則相對(duì)于廣西區(qū)域界定而言就復(fù)雜得多了,不僅文化具有衍生性、融合性與開(kāi)放性,而且文化具有區(qū)域性與跨區(qū)域性,因此廣西區(qū)域文化并不能簡(jiǎn)單等同于廣西文化,或廣西區(qū)域內(nèi)的地方文化與本土文化,區(qū)域空間大于行政空間,文化空間大于區(qū)域空間。盡管不難理解區(qū)域都必須界定在一定的地域空間范圍內(nèi),因此也會(huì)有廣西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社會(huì)、教育等地方性概念使用及其所指含義及其對(duì)象范圍,習(xí)慣上也是以這種稱(chēng)謂能夠達(dá)到更為明確與簡(jiǎn)單表述的目的。但卻不能將其簡(jiǎn)單化與封閉化,忽略其中內(nèi)涵與外延的復(fù)雜性與開(kāi)放性,以及非行政化區(qū)域界定范圍及其跨區(qū)域文化構(gòu)成的各種因素影響。
廣西區(qū)域文化當(dāng)然應(yīng)該首先立足于廣西來(lái)理解,其區(qū)域所指空間范圍當(dāng)然應(yīng)該是落實(shí)于廣西,將其簡(jiǎn)單理解為廣西地域、地方、地區(qū)文化無(wú)可非議,這對(duì)于理解廣西區(qū)域文化含義及其內(nèi)涵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考慮,對(duì)廣西區(qū)域文化的理解應(yīng)該更為寬泛和開(kāi)放,而且廣西區(qū)域文化在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上有著區(qū)域間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加之將其作為研究對(duì)象范圍需要更為寬闊深遠(yuǎn)的視野與背景。因此,對(duì)廣西區(qū)域文化的外延范圍理解應(yīng)該拓展:一方面應(yīng)該認(rèn)識(shí)到這是中國(guó)及其中華文化構(gòu)成中的廣西區(qū)域文化;另一方面是廣西與周邊區(qū)域關(guān)系中跨域、跨界構(gòu)成中的廣西區(qū)域文化;再一方面是歷史文化傳承、人口遷徙與文化交流構(gòu)成的跨時(shí)空、多樣性與開(kāi)放性的廣西區(qū)域文化。作為一定區(qū)域的廣西文化形態(tài),其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獨(dú)立性與關(guān)系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穩(wěn)定性與流動(dòng)性、自足性與開(kāi)放性、相對(duì)性與絕對(duì)性、多樣性與融合性等對(duì)立統(tǒng)一規(guī)律及其特征凸顯,不僅對(duì)于廣西區(qū)域文化概念含義及其內(nèi)涵外延理解更為深化,而且也有助于對(duì)其性質(zhì)特征作進(jìn)一步理解。其二,廣西區(qū)域文化生成的歷史建構(gòu)。任何一種文化形態(tài)形成與構(gòu)成都應(yīng)該有其背景與語(yǔ)境,區(qū)域文化形態(tài)的形成與構(gòu)成也是依賴于所依托的區(qū)域空間和所屬背景與語(yǔ)境。從歷史文化傳承角度而論,廣西區(qū)域文化形成與構(gòu)成應(yīng)該與歷史上所涉及其內(nèi)容的相關(guān)文化概念使用有關(guān),諸如百越、駱越、西甌、嶺南、嶺西、粵西、八桂等,大致上可以認(rèn)定為主要從文化地理空間界定的歷史性概念,這些歷史概念對(duì)于廣西區(qū)域文化生成與構(gòu)成有著密切聯(lián)系。當(dāng)然,這些歷史概念的含義及其內(nèi)涵外延需要進(jìn)一步厘清,廣西區(qū)域文化在其歷史文化傳統(tǒng)基礎(chǔ)上的傳承關(guān)系也需要進(jìn)一步研究。
值得重視的是,這些歷史文化概念的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具有區(qū)域性特征,所指區(qū)域及其區(qū)域文化都限定在一定區(qū)域范圍內(nèi);二是具有跨區(qū)域特征,所指區(qū)域范圍包括幾個(gè)或多個(gè)相關(guān)區(qū)域范圍;三是具有開(kāi)放性特征,所指區(qū)域界限較為模糊,含義較有張力和彈性,外延范圍有所擴(kuò)展和綿延;四是具有文化交融性特征,包括中原文化與廣西地方文化、漢文化與少數(shù)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化等交流融合;五是具有歷史性特征,這些區(qū)域性概念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時(shí)期或階段形成,包含特指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與內(nèi)容,表明特定的歷史文化形態(tài)所形成的文化傳統(tǒng)。因此,廣西區(qū)域文化生成具有深厚博大的歷史性依據(jù)與歷史積淀厚重的文化傳統(tǒng),廣西區(qū)域文化概念與這些歷史性區(qū)域文化概念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也具有彼此之間聯(lián)系的共同特征,這說(shuō)明廣西區(qū)域文化與歷史上存在的這些區(qū)域性概念及其所表征的歷史文化是一脈相承、薪火相傳的。其三,廣西區(qū)域文化生成的當(dāng)代背景。廣西區(qū)域發(fā)展推動(dòng)其區(qū)域文化生成與發(fā)展及其研究的崛起。廣西在改革開(kāi)放與“全球化”、“現(xiàn)代化”背景下,實(shí)施“富民強(qiáng)桂”新跨越及其“民族文化強(qiáng)區(qū)”戰(zhàn)略,區(qū)位特征與區(qū)域優(yōu)勢(shì)凸顯。廣西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特征、沿邊沿海的地緣政治文化特征、南方唯一的少數(shù)民族自治區(qū)的民族特色得到國(guó)家與地方的高度重視,在國(guó)家戰(zhàn)略發(fā)展及其區(qū)域戰(zhàn)略發(fā)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lái)越重要。廣西發(fā)展戰(zhàn)略不僅關(guān)系到廣西地方自身發(fā)展,而且關(guān)系到國(guó)家戰(zhàn)略發(fā)展及其區(qū)域戰(zhàn)略發(fā)展,也就是說(shuō),必須將廣西放置在國(guó)家與區(qū)域發(fā)展中定位,由此形成當(dāng)代廣西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及其區(qū)域文化發(fā)展的特點(diǎn)與優(yōu)勢(shì),其區(qū)域性與世界性以及國(guó)家戰(zhàn)略性地位凸顯。
一是北部灣大開(kāi)發(fā),既將廣西納入國(guó)家沿海經(jīng)濟(jì)大開(kāi)發(fā)戰(zhàn)略發(fā)展進(jìn)程中,又將區(qū)域經(jīng)濟(jì)戰(zhàn)略提升為國(guó)家戰(zhàn)略,并通過(guò)沿海經(jīng)濟(jì)大開(kāi)發(fā)的整體推進(jìn),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欠發(fā)達(dá)后發(fā)展的廣西趕超跨越發(fā)展步伐,逐步縮小東西部差距,實(shí)現(xiàn)沿海地區(qū)區(qū)域經(jīng)濟(jì)整體同步發(fā)展目標(biāo)。從這一角度看,北部灣大開(kāi)發(fā)在進(jìn)一步推動(dòng)廣西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更強(qiáng)有力地推動(dòng)西部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步伐,將廣西區(qū)域文化放置在北部灣大開(kāi)發(fā)背景下審視,區(qū)域文化才會(huì)具有更為廣闊的區(qū)域與跨區(qū)域視野。二是廣西地處沿邊沿海的中國(guó)南疆,毗鄰越南及其東南亞地區(qū),中國(guó)-東盟自由貿(mào)易區(qū)建設(shè)發(fā)展及其確定廣西首府南寧為其一年一度的博覽會(huì)永久性會(huì)址,使廣西南寧成為中國(guó)-東盟自由貿(mào)易區(qū)的橋頭堡,既成為跨境、跨區(qū)域經(jīng)濟(jì)文化合作、協(xié)作、交流的實(shí)質(zhì)性伙伴,又增強(qiáng)了廣西區(qū)域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動(dòng)力與活力,形成其區(qū)域性與國(guó)際性的區(qū)位特色與優(yōu)勢(shì)。三是國(guó)家西部大開(kāi)發(fā)戰(zhàn)略實(shí)施,使廣西不僅在西部地區(qū)戰(zhàn)略發(fā)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作為西部唯一的沿海地區(qū),北部灣及其海港成為大西南出海通道,發(fā)揮其交通樞紐的地位作用及其拉動(dòng)西南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作用,實(shí)現(xiàn)孫中山先生對(duì)北部灣建成國(guó)家大型出海港口的遺愿,以及國(guó)家海洋戰(zhàn)略及其南海開(kāi)發(fā)戰(zhàn)略實(shí)施。北部灣大開(kāi)發(fā)將北海、欽州、防城港三市經(jīng)濟(jì)開(kāi)發(fā)及其港口建設(shè)連成一片,并擴(kuò)展到南寧、崇左、玉林、來(lái)賓、百色等更大區(qū)域范圍,輻射柳州、桂林、梧州、賀州、河池等廣西區(qū)域范圍,影響云南、貴州、重慶等西南地區(qū),對(duì)于西部大開(kāi)發(fā)及其大西南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使區(qū)域合作、協(xié)作、協(xié)同發(fā)展成為廣西區(qū)域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重要方式。
四是廣西作為南方唯一的少數(shù)民族自治區(qū),不僅具有豐富多彩的民族特色與民族文化建設(shè)發(fā)展優(yōu)勢(shì),而且創(chuàng)構(gòu)了各民族聚居、文化融合、凝聚力與向心力強(qiáng)的民族生態(tài)環(huán)境;廣西不僅享有民族區(qū)域自治以及國(guó)家民族政策的優(yōu)越條件,而且享有民族團(tuán)結(jié)模范的殊榮;廣西世居十一個(gè)少數(shù)民族不僅與毗鄰廣西的云南、貴州、湖南、廣東等省際交界少數(shù)民族關(guān)系緊密,而且與毗鄰中國(guó)的越南以及東南亞各國(guó)民族具有歷史淵源關(guān)系與經(jīng)濟(jì)文化交往關(guān)系。廣西實(shí)施“民族文化強(qiáng)區(qū)”戰(zhàn)略既推動(dòng)區(qū)域民族文化發(fā)展,又跨區(qū)域影響與推動(dòng)南方少數(shù)民族現(xiàn)展步伐,確立其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及其南方少數(shù)民族現(xiàn)展格局中的定位。五是桂林作為山水甲天下的世界旅游名城與國(guó)家歷史文化名城,具有得天獨(dú)厚的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特色與優(yōu)勢(shì)。桂林國(guó)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yàn)區(qū)與國(guó)家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綜合改革試驗(yàn)區(qū)建設(shè),實(shí)質(zhì)上將桂林旅游經(jīng)濟(jì)與服務(wù)業(yè)經(jīng)濟(jì)發(fā)展納入國(guó)家戰(zhàn)略發(fā)展軌道;最近,桂林世界旅游勝地建設(shè)規(guī)劃方案獲得國(guó)務(wù)院批準(zhǔn),將桂林旅游發(fā)展推向一個(gè)新的高度,提升了桂林旅游的國(guó)內(nèi)外影響力與競(jìng)爭(zhēng)力,同時(shí)也將桂林旅游發(fā)展放置在國(guó)家旅游與世界旅游發(fā)展格局中定位,使桂林旅游具有區(qū)域性與國(guó)際性發(fā)展的重大意義。由此可見(jiàn),廣西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交通、民族、教育等各方面發(fā)展既必然融入和匯入各種跨域聯(lián)結(jié)與合作所帶來(lái)的內(nèi)在與外在因素,也必然會(huì)以更為寬廣與開(kāi)放的視野理解廣西區(qū)域概念的含義、內(nèi)涵與外延、對(duì)象范圍。同時(shí),也會(huì)因區(qū)域發(fā)展及其跨區(qū)域共同發(fā)展需要推動(dòng)區(qū)域合作、協(xié)作機(jī)制形成,如中國(guó)-東盟經(jīng)濟(jì)文化合作、中越經(jīng)濟(jì)文化合作、泛珠江流域經(jīng)濟(jì)合作、北部灣區(qū)域經(jīng)濟(jì)合作、西江流域經(jīng)濟(jì)合作、西南區(qū)域經(jīng)濟(jì)合作,以及桂港、桂臺(tái)、兩廣、湘桂、滇桂、黔桂等區(qū)域經(jīng)濟(jì)文化合作,等等。當(dāng)前,廣西又面臨國(guó)家海洋戰(zhàn)略實(shí)施及其海洋經(jīng)濟(jì)文化開(kāi)發(fā)機(jī)遇,以及海洋主權(quán)維護(hù)及其南海島嶼爭(zhēng)端與邊界糾紛等關(guān)系國(guó)家安全的重大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廣西處于沿邊沿海的南疆第一線,更需要將區(qū)域發(fā)展視野擴(kuò)大到國(guó)家發(fā)展與國(guó)際關(guān)系發(fā)展的戰(zhàn)略高度,將廣西發(fā)展戰(zhàn)略上升為區(qū)域發(fā)展戰(zhàn)略,將區(qū)域發(fā)展戰(zhàn)略上升為國(guó)家發(fā)展戰(zhàn)略。廣西發(fā)展不僅僅具有區(qū)域發(fā)展意義,而且具有國(guó)家戰(zhàn)略發(fā)展以及帶動(dòng)輻射周邊區(qū)域發(fā)展意義。總之,廣西在國(guó)家及其區(qū)域中的定位,使之區(qū)域概念范圍既指稱(chēng)廣西區(qū)域,也指稱(chēng)與廣西關(guān)聯(lián)的更為開(kāi)放性區(qū)域,帶有區(qū)域性與跨區(qū)域性的特征與意義。因此,廣西區(qū)域發(fā)展應(yīng)該立足于廣西、走向全國(guó)、放眼世界。
三、桂學(xué)的區(qū)域文化研究?jī)?nèi)容及其跨區(qū)域研究視野
桂學(xué)可謂廣西之學(xué),是對(duì)廣西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歷史、宗教、民族、民俗等現(xiàn)象與事象進(jìn)行分門(mén)別類(lèi)與綜合整體研究的地方性學(xué)科、學(xué)術(shù)、學(xué)問(wèn)、學(xué)派。從區(qū)域研究角度而論,其研究對(duì)象及其內(nèi)容范圍為廣西區(qū)域。從區(qū)域文化研究角度而論,文化并非局限于小文化與中文化的的狹義理解,而是將其包括在內(nèi)而擴(kuò)大延伸為廣義的大文化,文化構(gòu)成涵蓋精神文化、物質(zhì)文化、制度文化;同時(shí),依據(jù)自然地理空間與文化地理空間的相應(yīng)性與差異性,廣西區(qū)域文化研究對(duì)象不僅僅指稱(chēng)廣西文化,而且應(yīng)該包括與廣西區(qū)域文化密切相關(guān)的跨區(qū)域文化及其文化融合現(xiàn)象與事象,既生成廣西區(qū)域文化的開(kāi)放性、綿延性與融合性特質(zhì)特征,又構(gòu)成其研究的更為廣闊的學(xué)術(shù)視野。因此,桂學(xué)從這一角度而論又可稱(chēng)之為廣西區(qū)域研究之學(xué),其學(xué)術(shù)研究視野與研究指向應(yīng)該落實(shí)于廣西區(qū)域文化研究,研究對(duì)象及其內(nèi)容范圍也應(yīng)該為廣西區(qū)域文化。桂學(xué)研究可考慮將廣西區(qū)域文化作為研究對(duì)象及其內(nèi)容范圍,具體可從三個(gè)視角考察。
其一,區(qū)域文化研究的學(xué)科與跨學(xué)科研究視角構(gòu)成。從學(xué)科研究視角而論,桂學(xué)既相對(duì)于湘學(xué)、徽學(xué)、楚學(xué)、粵學(xué)等而言獨(dú)立自足的地方性學(xué)科,又可視為分門(mén)別類(lèi)的區(qū)域社會(huì)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文化學(xué)、人類(lèi)學(xué)、宗教學(xué)等多學(xué)科構(gòu)成的學(xué)科群。桂學(xué)作為廣西地方學(xué)科的總體性稱(chēng)謂,更大程度地表現(xiàn)為跨學(xué)科綜合研究指向,可以針對(duì)一個(gè)具體現(xiàn)象或事象,從多學(xué)科、跨學(xué)科、學(xué)科協(xié)同研究角度進(jìn)行立體綜合性研究。歷代廣西地方歷史文化研究典籍往往都具有文史哲與地方民俗糅雜一體的綜合性研究特點(diǎn),如唐劉恂《嶺表錄異》、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張鳴鳳《桂故》《桂勝》、清李調(diào)元《粵風(fēng)》等廣西歷史文獻(xiàn)均帶有這一特點(diǎn)。桂學(xué)作為廣西地方之學(xué)研究學(xué)科及其學(xué)科群,針對(duì)廣西區(qū)域文化對(duì)象類(lèi)型與性質(zhì)內(nèi)容可分門(mén)別類(lèi)進(jìn)行各學(xué)科研究,體現(xiàn)不同學(xué)科專(zhuān)業(yè)研究特點(diǎn),如區(qū)域經(jīng)濟(jì)學(xué)其實(shí)就是從經(jīng)濟(jì)學(xué)學(xué)科角度對(duì)區(qū)域經(jīng)濟(jì)進(jìn)行研究的學(xué)科,其學(xué)科理論與方法論具有普遍性與特殊性統(tǒng)一的特點(diǎn),同時(shí)也具有將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方法應(yīng)用于區(qū)域經(jīng)濟(jì)研究的特點(diǎn)。因此,桂學(xué)以廣西區(qū)域文化作為研究對(duì)象,學(xué)科研究與跨學(xué)科研究結(jié)合應(yīng)該成為桂學(xué)指向。對(duì)于受一定區(qū)域范圍限定的研究對(duì)象來(lái)說(shuō),學(xué)科研究也會(huì)在區(qū)域性與跨區(qū)域性關(guān)系的結(jié)合與協(xié)調(diào)上明確指向,目的在于拓展與深化研究視野以整體綜合把握研究對(duì)象。
其二,廣西區(qū)域文化的多樣性與融合性構(gòu)成。桂學(xué)以廣西區(qū)域文化作為研究對(duì)象,必須在厘清其含義及其內(nèi)涵外延與性質(zhì)特征基礎(chǔ)上認(rèn)清其文化構(gòu)成。區(qū)域文化形態(tài)的生成與構(gòu)成主要有三條路徑:一是本土文化積淀、積累、傳承與傳播的結(jié)果;二是區(qū)域間和跨區(qū)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與碰撞的結(jié)果;三是在主流文化影響下,文化變革、轉(zhuǎn)型與發(fā)展的結(jié)果。廣西區(qū)域文化生成也通過(guò)這三條路徑形成其構(gòu)成,又因其沿邊沿海與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特點(diǎn)更形成其多樣性、復(fù)雜性、融合性等構(gòu)成特征。具體表現(xiàn)在:一是廣西本土文化的多元化構(gòu)成性。廣西考古發(fā)掘,發(fā)現(xiàn)廣西在新舊石器時(shí)代都有大量的史前人類(lèi)活動(dòng)遺跡及其文化遺物、遺址存在,如桂林寶積山洞人、柳州人、桂林甑皮巖人等廣西先民遺存以及大石鏟文化遺存,這是廣西文化之根、本、源。先秦時(shí)期,在秦始皇統(tǒng)一嶺南前,廣西并未有行政意義上的統(tǒng)一性,盡管有百越、駱越、西甌、嶺南等稱(chēng)謂,但未能明確與具體指稱(chēng)廣西文化形態(tài)。廣西自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guó)建立中央集權(quán)制后,推動(dòng)廣西文化形態(tài)生成發(fā)展,但畢竟因其地處偏遠(yuǎn)與邊緣,本土文化發(fā)展緩慢,各地區(qū)文化存在差異性。當(dāng)然,也形成文化特色與優(yōu)勢(shì)、文化形態(tài)多樣化、文化構(gòu)成多元化、文化類(lèi)型鮮明的本土文化特點(diǎn)。李建平等學(xué)者概括為,廣西擁有民族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文人文化、民間文化等豐富多彩的文化形態(tài)。從文化區(qū)域類(lèi)型構(gòu)成看,以桂林為中心的桂北文化,以梧州為中心的桂東文化,以柳州為中心的桂中文化,以宜州為中心的桂西文化,以南寧為中心的桂南文化,以合浦為中心的北部灣文化;從民族文化類(lèi)型構(gòu)成看,形成廣西十二個(gè)世居民族文化形態(tài),各民族之間既交往交流與文化融合,又存在各民族文化差異性與特殊性,呈現(xiàn)出各民族文化鮮明個(gè)性與特色;從語(yǔ)言及其方言文化構(gòu)成看,廣西至今都是全國(guó)方言富礦區(qū),依托語(yǔ)言構(gòu)建的文化形態(tài)也千差萬(wàn)別,形成彼此不同的方言區(qū)域及其方言文化區(qū)域;從自然地理風(fēng)貌構(gòu)成的文化類(lèi)型看,江河湖海構(gòu)成不同的流域文化,如西江文化、紅水河文化、漓江文化、北部灣文化等,此外還因山地、濕地、平原、丘陵、森林等自然地理特點(diǎn)構(gòu)成不同文化形態(tài)。二是中原文化影響下的區(qū)域文化融合的構(gòu)成性。文化交流與交融是文化形成與發(fā)展的動(dòng)力源之一,即便是本土文化,本土之間的文化交流交融必不可少,對(duì)于外來(lái)文化進(jìn)入本土,廣西受到中原文化影響及其交流融合也是理所當(dāng)然。這也是地方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構(gòu)成部分,具有向心力、凝聚力與包容性特征所在。中原文化對(duì)廣西文化影響從秦始皇實(shí)行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quán)制之后,主要通過(guò)行政建制及其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中央派遣或貶謫地方官吏、外派守護(hù)邊疆駐軍、人口遷徙、商貿(mào)往來(lái)、大型水利建筑工程等因素構(gòu)成。旅桂士人、文人及其人口遷徙的客家人,帶來(lái)中原文化的影響與傳播,并與當(dāng)?shù)匚幕涣髋c融合,形成廣西政治文化、土官文化、藩王文化、科舉文化、書(shū)院文化、戲曲文化、工藝文化、文學(xué)藝術(shù)及其各種社會(huì)生活文化形態(tài)。明清之后,常被中原地區(qū)稱(chēng)之為“南蠻”地區(qū)的廣西,其文化形態(tài)與中原文化并無(wú)二致,完全融入中華文化的主流。至晚清時(shí)期,粵西文化發(fā)展到高峰“,嶺西五大家”步桐城派古文余緒,崛起于文壇;臨桂詞派入主詞壇,名震京師,王鵬運(yùn)、況周頤被稱(chēng)譽(yù)為“清季四大詞人”。至近現(xiàn)代以來(lái),廣西在鴉片戰(zhàn)爭(zhēng)、推翻帝制、民國(guó)建立與國(guó)民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功不可沒(méi),對(duì)中華民族及其中華文化作出重要貢獻(xiàn)。三是跨區(qū)域文化交流的廣西區(qū)域文化的構(gòu)成性。與廣西毗鄰的廣東、湖南、云南、貴州等省域各具有獨(dú)特鮮明的區(qū)域文化特性特征,也都與廣西在跨時(shí)空、跨區(qū)域交往交流中建立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形成區(qū)域文化融合的構(gòu)成性特征。處于廣西與湖南交界節(jié)點(diǎn)的桂林,歷史上也是廣西省府所在地。通過(guò)秦始皇統(tǒng)一嶺南時(shí)期修筑的興安靈渠,溝通湘漓水域以及湘江溝通長(zhǎng)江水系,漓江溝通珠江水系,從而貫通長(zhǎng)江文化與珠江文化。并開(kāi)發(fā)翻越五嶺的湘桂古道,建立湘桂溝通交流的各種渠道。中原文化及其湘楚文化影響廣西,尤其是桂北地區(qū),構(gòu)成具有湘桂文化融合特征的桂北文化形態(tài)。此外,先秦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楚國(guó),其南面邊界綿延至廣西荔浦,楚文化影響廣西不言而喻。處于桂東的廣西與廣東交界的梧州,古為蒼梧地區(qū),粵文化影響范圍擴(kuò)大到廣西賀州、玉林等地;桂南沿海的廣西合浦,構(gòu)成現(xiàn)在北海、欽州、防城港三足鼎立的北部灣地區(qū),與廣東沿海毗鄰,也是粵語(yǔ)區(qū)域,粵文化影響至南寧,廣西桂東南文化交融特點(diǎn)顯而易見(jiàn)。桂西地處廣西與貴州交界的宜州、河池地區(qū),廣西與云南交界的百色地區(qū),桂黔滇區(qū)域交往及其文化交流形成廣西桂西文化特點(diǎn)。特別值得重視的是語(yǔ)言,廣西語(yǔ)言構(gòu)成大體分為四大板塊,一是以桂柳話為中心覆蓋桂北、桂中、桂西地區(qū),為西南官話,屬北方方言語(yǔ)系,包括云南、貴州、重慶、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均屬于這一語(yǔ)系;二是以南寧、梧州、北海為中心的桂東、桂南粵語(yǔ)地區(qū),與廣東粵語(yǔ)同屬這一語(yǔ)系;三是以壯侗語(yǔ)系為中心的廣西各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四是廣西各地方言與土話。顯然,廣西語(yǔ)言及其方言具有區(qū)域性與跨區(qū)域性,通過(guò)語(yǔ)言進(jìn)行文化交往與交流,形成文化交融與融合的文化構(gòu)成性形態(tài)與特征。
其三,廣西沿邊沿海的跨境交流的文化構(gòu)成性。廣西沿邊沿海的桂南區(qū)域的憑祥、龍州等崇左地區(qū)與越南接壤,北部灣海域與越南海域接壤,跨境交往與跨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與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廣西沿邊沿海地區(qū)文化特色明顯,文化形態(tài)豐富多彩,不僅聚合中華文化及其中原文化、南越文化、粵文化以及本土文化、民族文化、洋文化等文化形態(tài)與類(lèi)型,形成跨區(qū)域文化交匯的節(jié)點(diǎn),而且以跨境交往交流形成邊境文化特色,構(gòu)成中越文化及其中國(guó)-東盟文化交接點(diǎn)。廣西沿邊沿海地區(qū)一方面承接與傳播中華文化向越南及其海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形成廣西區(qū)域文化的跨區(qū)域、跨境交流與影響;再一方面也在跨境交往交流中受到域外文化影響,其邊境文化形態(tài)帶有一定的域外特色。更為重要的是,合浦漢墓發(fā)掘及其北部灣地區(qū)考古發(fā)現(xiàn),早在漢代北部灣就開(kāi)辟了“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中國(guó)古代最早的出海海外始發(fā)港之一。由此證明,廣西對(duì)外開(kāi)放與跨文化交往傳統(tǒng)源遠(yuǎn)流長(zhǎng)。由此可見(jiàn),廣西區(qū)域文化不僅具有區(qū)域性與跨區(qū)域性交融的構(gòu)成性特征,而且具有跨境、跨文化交流與影響的構(gòu)成性特征。綜上所述,桂學(xué)需要進(jìn)一步深化與拓展廣西文化研究,就必須構(gòu)建廣西區(qū)域文化研究視野,將其放置在區(qū)域文化研究框架中及其跨區(qū)域文化交流關(guān)系中來(lái)認(rèn)識(shí),充分考慮其區(qū)域性與跨區(qū)域性、對(duì)內(nèi)與對(duì)外、多樣性與構(gòu)成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等特征,從更為深入和廣闊的跨時(shí)空研究視野與跨區(qū)域視角確立廣西區(qū)域文化的定位及其研究對(duì)象與內(nèi)容構(gòu)成。
作者:張利群?jiǎn)挝唬簭V西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